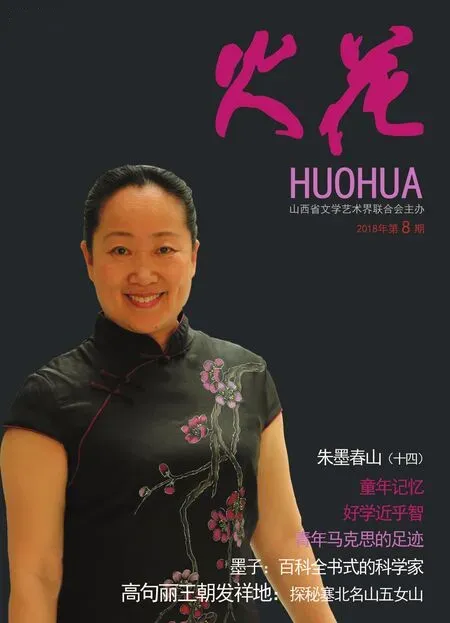那些年,入口穿肠的冰爽(外一篇)
2018-11-21丛棣
丛棣
注定又是一个溽热难耐的夏天。
动弹不得,光是坐在那里就已汗流浃背了。身边有吃雪糕的,喝冷饮的……对此,我是望而生畏的。肠胃不好,不敢吃生冷的东西,而且这种愈来愈造作的甜蜜与清凉于我已无半点诱惑。
过去不是这样,套用一句经典的广告词:小时候,一听到冰棍的叫卖声,我就再也坐不住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还是辽南某小镇上的小屁孩。夏天一到,总能看见若干头顶草帽的人跨着大二八的自行车,后座驮着个白色冰棍箱,于巷口一闪而过。镇子不大,也不必去追,卖冰棍的人会穿街走巷盘桓很久,所以,更多时候那若即若离的吆喝声,拖着长音,很勾魂。本人小时候就含蓄,从不直截了当要这要那,抓耳挠腮老半天才会挪步至母亲跟前,嗫嚅着:“妈,我想吃那个东西了……”
“哪个?”
“就是那个嘛,长方形的……”我勾着头用手比量了一番。
那是冰棍的形状。有时母亲会佯装不知,任我心急火燎地继续描述,也是在逗我,眼看我都快哭了,她才撇撇嘴将早就准备好的零钱塞到我手里,再看着我如获大赦般蹦跳着跑出去。冰棍箱里衬的白棉被一打开,就有冷气氤氲而出,有时翘翘脚探探头就会看到层层叠叠的冰棍和雪糕被蜡纸裹着,码放得整整齐齐,煞是可爱。冰棍箱多是自制的木箱,漆成白色,有的外面还会描两个红字“冰棍”,感觉有点多此一举,想想,除了卖冰棍的,谁还会顶着大日头驮着这样的大箱子四处转悠啊。都是些能吃苦的人,也都是些脑袋活络的人,有的是贴补家用,有的是养家糊口,也有年复一年借此过上了好日子的。
当时冰棍是主流。雪糕有些奢侈,要一毛一根。没记错的话,冰棍只需五分。不管是冰棍还是雪糕,在当时都只有两种口味,即奶油的和小豆的。看上去也泾渭分明,一种奶白,一种深褐。奶白的能吃出浓郁的奶香味儿,深褐的还夹杂着些许红小豆粒,怎么看都是货真价实。偶尔也能吃到三分钱的冰棍,多半是因为快化掉了,当时都没冰箱,反正也不能糟蹋了,各退一步,成交!三分钱的冰棍当中也有“异类”,就是赶上哪一批次的冰棍配料什么的没调开,颜色有异,说不定哪一口下去就会又咸又涩,即便这样也没见哪个孩子会将嘴里的东西吐掉。对了,那时我们吃冰棍不是咬着吃的,而是用舌头舔,用嘴唇啜,一副吃到天荒地老的模样……
镇子东头就有个冰棍厂,我们叫“联合厂”,每次玩耍至此都会止步,还会抻脖子往里面望。其实院子不大,很杂乱。有大人进进出出,都板着脸,看到我们这样的顽童还会瞪瞪眼睛,因此一直也没放进去过。当时街上有一智障少年,就爱一脸傻笑地四处梭巡,一副绿色无害的模样,某天早上就被发现死在了冰棍厂的盐水池里。事后推断,傻子应该是前夜从屋顶的气窗口栽下去的,也不知是摔死的还是呛死的,被发现时手里还攥着一根长长的塑料管。他应该以为下面的都是冰棍水,他以为趴在屋顶借用工具就能吸食得到……
我有个挺要好的小伙伴,我叫他父亲“大叔”,他很喜欢孩子,每次去他家都会逗弄我一番,有好吃的也会拿出来。有次也是天热,大叔好像忽然想起了什么,说,你俩等着啊,我给你俩弄“果子露”喝。“果子露”我们都知道,街边有散卖的,就是一大塑料罐子里面冰着汽水模样的东西,颜色各异,口味不同,反正都是水果味。没有口杯,直接给灌进软软的塑料瓶里,瓶体多呈葫芦形和鱼形,瓶嘴细细的,喝完再鼓足气扔在地上,一脚跺下去,能踩出震天一响。“果子露”的价格和玻璃瓶的汽水相仿,有点小贵,平日里难得一尝。所以,一听说有“果子露”喝,连我那小伙伴都两眼放光,看来他也不是时时都有这种待遇的。那个大叔只是里外屋转了一圈,再回来时手上就多出两个大碗,我俩张大了嘴巴,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分明就是满满两大碗“果子露”啊,颜色对,散出的果香也对,怯怯地尝上一口,酸酸甜甜的,就是这个味儿,跟外面卖的“果子露”简直是一模一样!我俩都有些发懵,心想,这分明就是在变戏法嘛。
没过几天,那个小伙伴神秘兮兮地把我带到他家,家里没大人,他从柜子的某个角落摸索出几个小纸包来,逐一打开,有的是带颜色的粉末,有的是颗粒状的晶体,两碗清水在侧,各取一点放进去再用筷子一搅拌,于是,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我面前呈现出两大碗“果子露”来!过了很多年我才回过味儿来,小纸包里的分明就是些“香料”“色素”“糖精”之类的东西嘛。那个下午,我俩勾兑了一碗又一碗,直喝到不能弯腰不敢低头。只几天的工夫,纸包就变回了纸片,而纸里也是包不住火的,有天我那小伙伴告诉我,我俩的秘密被他爸发现了,发现了就发现了,他爸也没把他怎么样。再去,有点不好意思,那个大叔冲我呵呵一笑,还用手指刮了下我的鼻梁。
上学了,学到了很多东西,以课外知识居多。什么都跟风,只要跟在高年级男生屁股后面,就能学到一身的本领。小学校园里有一口老井,井口不大,也不怎么深,但井水清冽,可以直饮。当时每个班级的墙角都备有小水缸,配一洋铁皮小水桶,我们每天都会打水贮水,洒扫用,也饮用。虽然喝的是生水,可也没见谁闹过肚子,可见当年的水质还是相当达标的。还是高年级的男生有办法,就地取材,人手一个空酒瓶,先放进几粒糖精,再拴上长长的细绳,投入井中后要让水吃满,得一直探到井底才行,这样打上来的井水才会拔凉拔凉的。那个时候,糖精不是什么稀罕物,人人都能搞到一点。酒瓶多是“大曲”“老窖”之类的白酒酒瓶,以方棱形的居多,剥掉商标,里外洗净,灌满冰凉的井水,于阳光下清冽通透。喝上两口,直沁心脾,那才叫一个爽啊。
等到上了初中就有了“冰袋”。软包装的,各种水果味,从小卖店的冰柜里取出,迫不及待地用牙齿撕开一角,几乎是一口气灌下去,脑门上的热汗也会随之转凉。当时地方上的小食品厂夏天都会灌装那种果味饮料,有的叫“雪梅露”,有的叫“大白梨”,反正贴上什么标签就是什么,都是大瓶的,两毛一瓶,也没什么汽儿,喝起来就是以前“果子露”的味儿。我家附近就有这样的小饮料厂,我曾亲眼看见他们直接从大井里抽水灌装,也不避人,大家也心知肚明,照喝,百无禁忌。
第一次喝啤酒,已经是读技校时的事了。小城有自己的啤酒厂,出产的“大北”啤酒很有劲儿,开始的时候喝不惯,总感觉是在咽马尿。也是赶上了盛夏酷暑,某日和两个同学分享一瓶冰镇啤酒,我是最末一个,结果敞开了喉咙,将余下的半瓶一气儿给咕嘟了。用他们的话讲,是喝通了。从此就一发而不可收拾了,正赶上那几年小城啤酒厂主推扎啤,直接供应到街角和路边。夏日傍晚,到处都是大排档,人们袒胸跣足,都在喝这样的生啤。酒是给冷压在一个个小啤酒桶里的,开阀自接,一大杯能抵上一瓶的量,也没太多的泡沫,酒劲不大,就是图个畅快。一元一杯,再要上五元一大盘的辣炒田螺,几个人能折腾到很晚。一个夏天过去后,我就彻底沦为一个纯粹的啤酒主义者了。
后来分配到车间,开始有了各种劳保待遇,入夏先是每人分十斤绵白糖,等入了伏就该发雪糕票了。当时的工厂都下设综合服务部,也都有自己的雪糕厂,满足自家福利供应的同时也能流到市面上创收。我们那是拖拉机制造厂,我姐所在的是机床附件厂,相距有点远,偶尔顶着日头去看她,她会用机床附件厂的雪糕来款待我。相较之下,就属我们厂的雪糕口味最差。吃了一圈,也和大伙儿达成了共识,还属“新生厂”出产的奶油雪糕最够味。“新生厂”是劳改监狱下辖的一家机床厂,雪糕货真价实,似乎还透出一股子严苛的体制味儿。
单位的雪糕票是一人八十根,看似很多,其实吃不上几天,没有一根根取的,都是十根二十根地请客,今天你请,明天他请,都没把这当成是了不得的待遇。当时几乎所有的工厂效益都不太好,也是山雨欲来,大势所趋,改制的洪流即将奔涌而至。车间里也没有太多的活儿,工人们都在细水长流地“磨洋工”,有时吃过午饭连机器都懒得开。夏日炎炎,大伙都躲进阴凉的角落,睡觉的睡觉,甩扑克的甩扑克,偌大的车间难觅人影,只能听到知了在一惊一乍地嘶叫。我们的车间主任人称“老马”,劳模出身,什么机床都能摆弄,喜欢冲在前面带头干活,到后来带头都没用了,就脚踩工具箱做个大弓步,架着胳膊抽烟。我们都说他是在“鼓捣烟”,好像也不往肚子里吸,到后面都不用打火机了,就是一根一根地续,不大一会儿就会整出一地烟蒂来。临了,还会叹口气,像是自言自语地嘟囔一句:“倒是弄出点动静啊!”逮着两个毛头小子就直接给支使出去:“那个,去抬一筐雪糕回来,给大伙儿凉快凉快,吃完了都把机器开开!”车间有个竹筐,好像就是专门用来装雪糕的,我们也由此得知雪糕票没数,只要“老马”想请客,想吃多少有多少!
当然,有时候也会换换样,几个大小伙子一人抱俩西瓜回来,切切分了,见者有份。那还说什么,雪糕也吃了,西瓜也啃了,那就开机器吧。也只是开着,空转嘛,轰轰隆隆的,车间瞬间就有了生气,甚至还透出种热火朝天的气势,有如回光返照……
转过年,我们就步入了万千下岗职工的行列,水深火热的,再也没有免费雪糕可吃了。
时至今日,我的胃肠早已与冰点冷饮绝缘,也只有在回味这些清爽的片段时才会口舌生津,于炎炎夏日里获得习习凉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