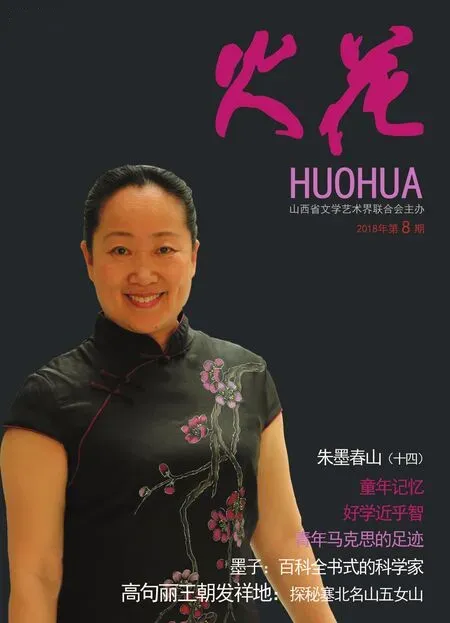文化聊城
2018-11-21北方
北方
聊城,无论如何都算得上是一座历史文化古城。
2013年,当我骑行到东昌府区,站在斜阳照射下熙熙攘攘的大街上,我忽然有种异样的感觉。曾经跑过全国大大小小不下百余个城镇,可这里怎么也不像一座北方的城镇,怎么也不像北方城镇中的一条街道!街道两边浓密的树荫遮盖着一所所古朴的民居,那感觉就像是到了南方某个小城。这感觉来源于哪儿呢?我说不出来,客观地说感觉有时是不准的,尤其是第一印象,可当我转年再次来到这里时,依然还是那种感觉,而且丝毫未变。于是我相信这不是感觉,这里的人文风貌就是南方城镇的一个缩影,就是南方市井的北移,后来我问自己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问了许久,也寻找了许久,直到有一天翻到一篇记述聊城历史人文的文章时,忽然有所领悟——或许和它是一座水城、一座被偌大的东昌湖包裹起来的水城、一座京杭大运河贴身而过的水城有关吧!北方缺水,所以缺乏润泽,而聊城却被人们称为东方的威尼斯,但我感觉它更像北方的杭州,尽管线条粗犷了一些,但它那深厚的历史底蕴决对不输苏杭,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是一座北方的文化古城,那千百年来深厚的文化土壤养育的一代又一代的聊城人,使这座城市真正有了“腹有诗书气自华”的儒雅之气,和南方那“诗书礼乐”信手拈来的人文涵养。
这里有全国十大名楼之一的光岳楼、清代四大私人藏书楼之一的海源阁、宋代的铁塔、山陕会馆、武松打虎的景阳冈、鱼山脚下的曹植墓,以及古阿井、迷魂阵、鳌头矶、临清舍利塔等,此外这里还诞生了伏羲、孙膑、鲁仲连、朱延禧、傅以渐、杨以增、范筑先、武训、张自忠、邓忠岳、李苦蝉等一大批名人。
书
聊城人爱看书,这是走在聊城的大街小巷,我留下的一个深刻的印象!
在东昌府区的一条陋巷里,竟然接连开了有好几家小书店,这在许多省会城市找家书店都比找恐龙还难的年代,着实让我感动了一把。随后在接连几天的游览中,路边的小书摊随处可见,隔不了几个胡同便会有一家古旧书店,里面的规模绝对不输省会城市的大型古旧书店。尤其是光岳楼下的两家古旧书店里,竟然上架了古今中外的许多绝版书籍。后来在和一家旧书店的老板闲聊时,他说:“聊城是华北地区大型的古旧书籍集散地,每次进书我们都是去北京等地成吨地去购买!”
这是聊城给我留下的第一个印象。
在当今社会全民上网的今天,唯独在聊城还能看到那么多的书肆,不能不说是道风景!后来,随着对聊城的深入了解,我才发现,喜欢读书是聊城的一个重要城市基因,远古时代姑且不论,单从隋朝有科举考试以来,在聊城就曾产生过3名状元、99名进士、439名举人,这么庞大的一群精英读书人,对聊城的文化能产生多大的影响,怎么说都不为过!
聊城人除了喜欢读书之外,还喜欢藏书。清末,这里便出了一位赫赫有名的藏书家——杨以增。
杨以增是清道光二年的进士,曾被分发到贵州的荔波县任知县,居官颇有政绩,后来被提升为知府、道员,直至攫升陕西布政使。当时林则徐正担任陕西巡抚,与杨相交甚深。道光二十八年,杨以增被任命为江南河道总督。而“杨氏生平无他嗜,一专于书”,他在江南河道总督任上曾搜购了大量的江南私家藏书,然后用船运回家乡聊城,藏于自己私人的藏书楼——海源阁中。
说到杨以增,一定会提到他修建的海源阁。这座建于道光二十年的私人藏书楼,位于光岳楼南万寿观街路北的杨氏宅院内,为单檐硬山脊南向楼房,面阔三间,上下两层。下面是杨氏的家祠,上面是杨以增收藏宋元珍本的地方。藏书楼上层中间门额上悬挂“海源阁”三字匾额一块,为杨以增亲书,额后有杨以增自题跋语。
海源阁杨氏藏书始于杨以增之父杨兆煜,后经杨以增、杨绍和、杨保彝、杨承训四代人的不懈努力,多方搜集,到杨保彝时已收藏各类珍本有二十余万卷,而且没有载于书目者还有不少,其中宋元珍本逾万卷。这么浩大的藏书,当时已经与江苏常熟瞿绍基的“铁琴铜剑楼”,浙江杭州丁申、丁丙的“八千卷楼”,浙江吴兴陆心源的“百百宋楼”并称为清代四大私人藏书楼了。此外还有人将海源阁与北京的“文渊阁”“皇史”、宁波的“天一阁”并列为中国历史上官私藏书的典范。
天下事,聚久必散,聚散相依,海源阁集四世之力而收藏的一楼珍本,在清末和民国动荡不安的社会、烽火叠加的乱世中,最后还是没能逃过一而再再而三的劫掠与战火,而烟消云灭……
海源阁第一次遭劫是在咸丰十一年,适逢捻军作乱,海源阁藏于山东肥城西“陶城山馆”的部分珍本首遭战火荼毒,据战后统计“收捡烬余,尚存五六,而宋元旧椠,所焚独多,且经部犹甚”。民国十七年,西北军阀马鸿逵部占领聊城,海源阁的藏书再次遭受了一定的损失。这次战乱之后,惊醒了的杨敬夫,先后分两次将十几箱宋元珍本偷偷地运往天津保护起来。民国十八年,土匪王金发攻陷聊城,司令部就设在杨宅内,这一次海源阁珍藏图书遭受了空前的浩劫。据说,当时除匪首大肆劫掠、匪兵大量携出盗卖外,土匪随手毁弃的景象更是随处可见——“炊火以书代薪,夜眠以书做枕,至拭桌、拭烟枪无不发书代之。”匪兵退后,“杨宅已不见一人,院内室外书籍满地,厕所马厩亦无处不有;院内书籍尽为大雨淋烂”。但此次损失之书,均为海源阁旧藏,即海源阁楼上被杨敬夫移存天津后所剩下的宋元珍本藏书,“其后宅三室,均未波及”。民国十九年,土匪王冠军又攻陷聊城。他们到海源阁后,“尽攫善本秘籍、碑帖字画”。王冠军的此次劫掠,对于海源阁来说是最后的一次劫难。在此之后,杨敬夫恐再有这类事情发生,随即将劫余残存的书籍,装五十箱运送济南杨氏新居保存。由此,海源阁的藏书共做了三种处理:一为运津者,一为运济者,其它即为杨氏零售了一部分。运送天津的藏书,后来因杨氏迫于生计被大量变卖;运送济南的藏书中的宋元珍本若干种,杨氏曾以八万银元抵押给天津盐业银行,后来押期到后,却无力偿还。1938年,日寇攻陷聊城,田庄的“弘农丙舍”所藏的书籍连同房屋尽遭焚毁。至于其它毁失的藏书,实难数计。
在海源阁藏书流散之时,我国著名的藏书家周叔瞍和刘少山唯恐典籍流散国外,曾奔走疾呼,极力抢救、收购了不少。抵押给盐业银行的藏书,后来由国民党行政院长宋子文出资二十亿法币赎出后交给北京图书馆保存,其中所藏明、清版本书籍则归入山东图书馆,也有部分书籍流散到全国其它著名图书馆。海源阁遗书,现主要见藏于北京图书馆和台湾中央图书馆。
杨氏一家四代藏书,历时百余年,在我国近代藏书史上有较为深远的影响。而如此浓重的书香重阁坐落于光岳楼侧,那浓浓的书香在一个世纪的时间内对聊城文化起到多大的熏陶作用,是无法用言语表述的!杨以增及后人对聊城的文化基因的构成起到不可磨灭的推动作用!
院
院,说的是书院!
第二次到聊城时,偶然走进了坐落在东昌府区的七贤祠。正殿之中供奉的是聊城地区七位儒家的圣贤:王道、穆孔晖、孟秋、王汝训、逯中立、张后觉、赵维新。在七位先生站立的铜像前,我认真地阅读了他们的生平事迹,内心不禁心潮澎湃。这就是儒家文化的魅力,它没有佛老的消极遁世,更多的是积极入世、直下担当的气魄,所以千百年来它一直作为正统的思想观念与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为社会所接受。
这七位先生多是修身严谨、一身正气,所以官场之中屡遭贬斥。但他们处于人生的低谷时,却能始终保持着积极向上、克己复礼、直面承当的信念与态度,不抱怨、不逃避,真正践行了先儒提出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信条。他们身居陋室,却依然安贫乐道,或著书立说“为天地立心”,或教书育人“为往圣继绝学”,他们怀着“为万世开太平”的伟大的理想信念,共同承继了王阳明的“心学”在北方的传播与发展。
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一书的“北方王门学案”一章中共记述了七位王门学者,说他们“始兴阳明学于齐鲁燕赵间”。这七人中的前三人,就是聊城七贤中的穆孔晖、张后觉、孟秋。后面的几人也与聊城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可见聊城是当时北方“心学”的主要传播基地,而七贤则是主要传播者。他们为紧接而来的东昌文运大兴、文化昌盛,鸿儒巨宦鹊起的时代奠定了文化与教育的基础。
时至今日,不少聊城人心中仍对这七位先贤怀有深深的敬意。因为他们那特立独行的行事、纯一不杂的治学精神、闲淡朴素的处事胸怀,造就了他们迷人的人格魅力。这里不妨仅举七贤之首的王道的生平事迹,来管窥一下先贤们的“非常人”行事——
据史料记载,王道“少颖悟不凡”,十八岁就乡试中举。正德六年考中进士,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当时,山东盗贼猖獗,为了赡养避难江南的祖母和继母,王道几次上书朝廷,恳请回家孝亲。然后,朝廷不但没准,第二年相反又任命他为应天府学的学官。他接旨后再次“启奏”回家赡养老人。可是朝廷依然没有批准,竟又提拔他为吏部主事、员外郎中,负责选任、考核官员。在任中他“选法公平,门无私谒”,后来他又被辅臣推荐,升任左春坊“谕德”之职,执掌对皇太子的教谕。不久,王道称病回家休养,而他在家这一呆便是十年。十年间,他“杜门讲学,足不涉公府”,“性恬淡夷旷,慕邵雍、司马光为人,而笃志力行实允蹈之”。嘉靖年间,他再次被升为南京国子监最高官职——祭酒。不久,他又因病告归,后又被推荐为南京太常卿。之后,历任北京国子监祭酒、礼吏二部侍郎。王道最后是在任上去世的,死后被追赠为礼部尚书。
由于王道曾在南京任职,所以得以直接听取王阳明讲授“心学”,从而接受了王阳明的“新儒学”的观点。据明万历二十二年版《东昌府志》等史料记载,王道“精择强记”,深研程朱义理之学、儒家经典,崇尚平实简易之学。同时,还能够不受“世俗拘挛”,不标立门户。他的《大学亿》《老子亿》《顺渠文录》等著作,独有所到,“持论多前儒所未及”。当年,“心学”作为新兴起的儒学流派在全国传播迅速,而很多高官、学者都称其为正学。当时经济日益繁荣的东昌,一处处书院相继建起,七贤的推动作用不可轻估。而对于当时聊城文化教育昌盛的局面,用聊城知府胡德琳题写在启文书院上的一幅楹联来概括是再恰当不过了。楹联云:“接武巍科三状首,传薪正学七先生。”是啊,书院中的读书人,前赴后继只望能成为三状元式的学子;书院中的教学者,薪火相接都是七先生式的教师。三状元是指茌平的朱之蕃,聊城的傅以渐、邓钟岳;七先生便是我们上面提到的聊城七贤。
元代会通河的修通,促进了东昌经济的繁荣发展。到明朝中期,在经济日益强大的背景下,聊城的文化教育得到迅速发展。这时的东昌府的学院建设发展十分迅猛。位于道署东街的府儒学,和位于城隍庙街的县儒学,经过数次扩充,到清朝中叶时已经发展成为具有一定规模的学院。当时除去隶属当时府、州、县地方官府编制内的儒学外,还有官方“延请精通经书而又品行端正者任山长,由山长聘请学行有素的举人、进士任教习的书院”。仅聊城城区就有建于城东的东林书院,建于龙湾的龙湾书院,建于南门里的光岳书院,建于府学东的阳平书院,建于孙家胡同的启文书院和建于楼西的摄西书院等。据《东昌古今备览》记述,当时聊城共有大小规模的民办书院二十八处,民办经馆、私塾更是遍及城乡。
清末,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加重,西方的先进教育体制也随之传入中国。迫于形势,清政府于光绪二十四年召谕“各省、府、州、县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西学之学堂”。清光绪二十七年,首先将设在聊城的启文书院改建为东昌府立中学堂,民国三年改为山东省立第二中学,这是山东省创立最早的官办中学之一。此时的聊城教育事业尚处于全省前列,后来由于运河堵塞,河运终结,聊城的经济随之衰退,教育长期困于没有经费而发展停滞的状态。加上日寇入侵,学堂先后停办,从此,聊城的教育一蹶不振。
提到聊城的学堂教育发展,就不能不提到一个人——武训。
这位出生于聊城冠县一家贫苦农民家庭的孩子,生前连个姓名都没有,在他二十一岁时因不识字接连受到地主的欺骗与压榨,一怒之下在破庙中昏睡三天后,狂奔数日,口中大喊“我要办义学”!从此他真的以行乞为生,并孜孜以求,“昼行乞、夜绩麻”,三十年如一日,最终靠要饭、卖短工、演杂耍,在山东临清一带兴办起了三座义学,成就了中国教育史乃至世界教育史上一段佳话!清光绪帝特授“义学正”称号,赐名训,赏黄马褂。张学良称他“身兼孔墨”,郭沫若则称他是中国的“裴士托洛齐”!
深入了解了聊城当时的文化发展之后,我们便会说,这位老百姓称犯了“义学病”的“千古义丐”,之所以能诞生在聊城地区,决不是个偶然的事件,这不能不说是当地文运大兴、精英荟萃的深厚文化背景下所造就出来的。读书成为了改变命运的唯一手段,深植于武训的心中。而能够让穷苦百姓读上书,又成为了武训洗刷自己屈辱人生的唯一出路,所以他不惜一生不娶,住破庙、吃糠咽菜来完成自己创办义学的愿望!
族
走进傅斯年纪念馆,这座两进式的四合院,实际上并非是傅斯年当年的故居,而是当年傅家的祠堂。真正的傅氏故居在北门里路东的相府大院里,光绪二十二年,傅斯年就出生在那里。傅家世居聊城,是鲁西名门望族,在这个家族里仅七品以上官员就出过一百多人。时过境迁,斯人已逝,老房子早已易主而居,但这房子一代代真正的主人却永远留在了聊城的历史当中,熠熠放光!
明清时期,大运河穿城东而过,聊城成为连接南北的枢纽,于是一跃成为北方经济发展的龙头。傅斯年的祖上傅祥,当年正是借重聊城优越的地理位置,成为聊城一带有名的富商。在封建时代,“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个人只有通过科举考试才能获得升迁,而也只有当了官,才会拥有真正的社会地位。除此之外所有的行业都如“水上浮萍”,朝不保夕。傅祥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始终不遗余力地督促子孙攻读“举子之业”,有时还会亲自“口授章句”来教授子孙学习八股文,所以傅氏家族逐渐形成了诗书传家的传统,而且代代相继。
傅祥之后,到了五代孙傅以渐这一辈,傅家终于脱胎换骨,由商贾之家成为了官宦之家。傅以渐生于明万历三十七年,七岁入私塾读经书,曾师从当时的名儒孙兴,所以为人深明义理之学。由于明朝末年宦官专权,官场腐败,科场舞弊之风盛行,傅以渐直到三十五岁仍未取得任何功名。然而,时隔不久清廷入主中原,为了巩固统治,清王朝大力鼓励读书人出来为官,并在入关的第二年便恢复了科举考试。
踌躇满志的傅以渐没有因为改朝换代而改变了自己的科举之路,在乡试中举之后,翌年入京参加会试,又得中贡士。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殿试时竟然得了个一甲第一名,就这样傅以渐成为大清王朝的首位状元。随后他又被授予内宏文院修撰之职;再后来,先是升为内秘书院大学士,转年加太子太保衔;之后,傅以渐又被授为武英殿大学士、兵部尚书职衔。这样,他便名副其实地成为了当朝一品宰相。为显示朝廷恩宠,顺治帝又封赠傅以渐的曾祖父傅谕、祖父傅天荣、父亲傅恩敬都为光禄大夫、少保加太子太保、内翰林国史院大学士加一级之勋号。从此以后,聊城傅氏在当地风光无限、权势熏天,成为鲁西地区跺一脚四城乱颤的显贵。在此之后的几百年,傅家势如中天,先后得中举人、进士、庠生、太学生者不下百余人,在朝为官甚至出任封疆大吏者几代不绝。
值得一说的是,到了民国时期,傅家已是家道中落,这时傅家又出了位杰出的教育家——傅斯年。
1901年春,还不满五岁的傅斯年就被送入聊城名师孙达宸的私塾,接受“经学”教育。1905年又被送入东昌府立高等小学堂读书,1908年他离开聊城前往天津府立第一中学求学。傅斯年在聊城求学的这段时间,正是他品格和学业的初步养成期,他深厚的国学功底均得益于这段时间的寒窗苦读。十七岁那年傅斯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大预科乙部,与顾颉刚、沈雁冰、俞平伯、毛子水同窗。由于他学识渊博、为人豪爽,很快便成为“五四”新思潮运动的学生领袖。后来傅斯年先后出任中山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大教授,北大代理校长和台湾大学校长。但他始终坚持“参政而不从政”,保持一个读书人应具有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大大小小的官宦士族,在聊城明清史上是一股影响深远的势力。说它影响深远,是因为号称聊城八大家族的每个家族都是绵延几代的名门望族。他们在依靠权势、财势对本地产生政治与经济影响的同时,又无一例外地继承了诗书传家的古训,使文化影响也介入到当地的整体文化发展的进程之中。
再以聊城的邓氏家族为例。邓家是明初以军功显达于世的大家族,其始祖邓瑜元末曾参加朱元璋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后因军功被封为昭勇将军,任东昌卫指挥使,子孙世袭。自此以后,邓家后人在聊城一直世袭到明朝中期。随着聊城经济的崛起,当地的文化与教育也迅速地发展起来,这样极大地刺激了邓家由世袭武职向文武全面发展的野心。从邓瑜第六代孙邓邦开始,邓家开始走科举之路,邓邦“博学识,补诸生,以贡授莱州府学训导”。从此邓家子孙多因科举获取功名。邓邦的孙子邓秉恒是顺治六年进士,最初被授予昆山县令一职,后因功擢升为户部主事,之后外放任福建巡海道等职。史书评价邓秉恒“少嗜书,敦大节,强力任事,不为诡随,临事变,机权错出,有古大臣风”。从邓秉恒开始,邓氏家族逐渐成为聊城的文化家族,至其曾孙邓钟岳时则进一步发扬光大。
邓钟岳在康熙六十年的殿试中被点为状元,成为聊城明清时期三名状元之一。之后,他曾先后担任江苏学政、浙江学政,雍正年间升至内阁学士兼礼部右侍郎。他一生博览群书,“于书无所不读,尤邃《易》《礼》”。为人忠孝友悌,父亲去世得早,邓钟岳事母至孝,“御侍诸弟甚挚,督课亦不少宽”,三个弟弟在其督导下读书上进,也都有所成就。邓钟岳任地方官时期,非常重视对民众的教化,经常以封建纲常来训导民众,民间曾流传一段他为官时的故事,说来很是有趣:康熙年间,江西蒙南县有两个乡宦是同胞兄弟,兄沈仲仁,官至翰林院学士;弟沈仲义,官至户部给事中。兄弟二人致仕还乡,因家产分配而起纠纷,直至对簿公堂。而县令不敢评断,正恰邓钟岳钦命巡查地方到蒙南县,县令将此事告知了邓钟岳,邓钟岳听了便写了一张批文让转交给沈氏兄弟。沈氏兄弟接到批文后,拿来一阅,竟深为文中内容而感动,进而抱头痛哭,从此两人和好如初。
在明清时期,聊城地区经济、文化与教育的整体大发展,促成了聊城文化族群的兴起。这些家族在科举选仕的追求过程中,深受儒家伦常礼仪的影响,从而使儒家的文化思想渗透市井,成为模范表率,世风越发淳厚,而淳厚的世风又陶冶了一代又一代的“循吏良士”。因此,聊城地区“士多才俊,文风为诸邑冠”。聊城地区的士族对当地的文化贡献是非同一般的,他们实际上也是当时整个聊城地区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