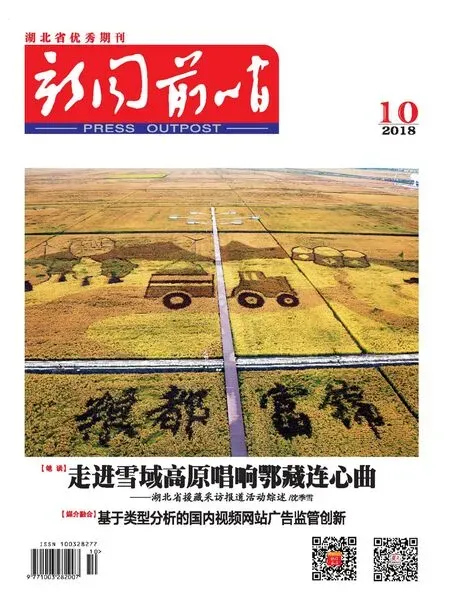传播与建构:乡村居民心中的城市形象
2018-11-20孙明晓
◎孙明晓
城市形象作为国家形象的子系统,是人们对城市的主观看法、观念及由此形成的可视具象或镜像[1]。但现实的城市庞杂无比、千头万绪,限于人类的认知程度,人们很难对它建立起全知全能的完整印象。正如李普曼所言,人们“直接面对的世界实在是太庞大、太复杂、太短暂了……不得不在驾驭它之前使用简单的方法对它进行重构。”[2]
李普曼指出,在社会生活层面,人对环境的调试是通过“虚构”这一媒介进行的,他认为人们所认知的环境,是媒介通过对象征性事件或信息进行选择和加工、重新进行结构化后向人们提示的环境,即拟态环境。[3]也就是说,人们对现实世界的印象,很大程度上是经由媒介对真实世界的提炼与简化,被建构而成。城市形象作为人们对现实城市的简化与重构,同样是被建构的。
那么,作为他者的乡村是如何看待城市的?被建构出的城市形象又怎样影响了乡村?
在长期的城乡二元体制下,我国乡村与城市存在巨大的发展差异,乡村城市化与农民工进城已是当下社会发展的又一重要命题,乡村逐渐成为年轻人想要逃离的场所。这其中,城市形象建构扮演了怎样的角色?笔者认为,站在乡村的角度探讨村民对城市的印象及其建构途径,是必要且有意义的,可惜目前站在这一角度探讨城市形象的文献寥寥无几。
本文运用参与式观察法与深度访谈法,致力于回答三个问题:乡村居民通过何种途径建构心中的城市形象?村民心中的城市形象具体是怎样的?这样的城市形象对乡村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一、城市形象的建构途径
JohnFoot认为,城市形象作为人们对城市的一种主观印象,是通过大众传媒、个人经历、人际传播、记忆以及环境等因素的共同作用而形成的。[4]笔者对位于鲁北的N村展开田野调查,发现其作为比较典型的兼业村落,村民心中城市印象的建构途径同样遵循了这样的路径。
1.媒体
村民接触最频繁的媒体是电视与手机。电视已成为一种媒介环境,是村民了解城市的途径之一。受访者刘女士感觉“电视剧演出什么样,城市里大概就是什么样”。同时,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为村民打开了一扇接触外界的窗口,在互联网海量的信息中,对城市信息的接触,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村民对城市的印象。
2.人际传播
N村及附近村落棉纺印染产业发达,生意人走南闯北,回乡后自会谈起村子与外界的区别,这使村民可以通过人际传播接触到外界的城市。另外,N村也有人通过读大学走出乡村,他们的经历是村民构建脑海中城市形象的重要途径之一。笔者访谈了两位已定居城市的村民,一位在珠海月薪过万,一位在深圳有套七百多万的房子,这些人的讲述形塑了村民对城市人的印象,进而建构起他们心中的城市形象。
3.亲身经历
尽管大部分N村人并无城市生活经历,但他们的城市形象建构也受到亲身经历的影响。N村附近有一县级市昌邑,对它的印象,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村民对外界城市的印象。昌邑或多或少具备外界城市——尤其是村民想象中的“大城市”——的一些特征,这使它在城市形象的建构过程中,充当了村民与外界城市的 “媒介”。村民从在昌邑的所见所闻出发,想象外界城市的生活。
对N村人来讲,城市形象的建构是一个被动的、长期涵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媒体、人际传播与亲身经历,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记忆与环境,共同作为媒介对现实的城市进行简化与重构,建构起N村人心中的城市形象。
二、村民心中的城市形象
那么,N村人心中的城市形象究竟是怎样的呢?形象在差别对比中显现,笔者以“城乡差异”为主题词,询问村民对城市的看法。所有受访村民皆表示,在衣食住行方面,N村与城市已没有差别,N村依托棉纺印染产业,经济发展较好,村民自信在物质方面N村不比其他地方差。
村民口中令人羡慕的城市人,是公务员、医生、律师等有高薪工作与良好生活的“成功人士”,而非拖家带口、辛苦谋生的农民工。常规认为,乡村发展不如城市,村民会涌入城市谋生,但N村人却没有进城的想法。村民认为,年轻人要学习好,才能进城,没有文化贸然进入城市的农民工,过得可能还不如留在乡下的村民。
这样的印象或许可以从城市形象的建构途径中得到解释。新闻媒体对于农民工群体报道的一些词汇,如“文化程度低”、“工资低”、“辛苦”、“需要关爱”等[5]使 N 村人对进城“望而生畏”。
三、城市形象建构带来的影响
理清城市形象的建构途径与村民心中具体的城市形象后,最后一个问题随之而来:上文所述的城市形象对N村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最为直观的影响便是N村人对教育的极度重视。村民羡慕城市人的生活,却不想成为农民工,唯一的出路便是让孩子好好学习,考上大学,成为城市中的“成功人士”。为此,N村人苦心孤诣地在县级市昌邑买学区房。受访者刘女士声称:“(村民看到)哪个学校教得好就在附近买房……父母觉得自己没学好,想让孩子好好学,就买学区房,有些甚至都不在那个房子里住,老人帮他们带孩子送孩子上学放学,他们在乡下上班。”
昌邑规模小、人口有限,无法提供充足的就业岗位,房市并不活跃,但学区房却异军突起,成为热门的“抢手货”,甚至出现“不是学区房就卖不出去”的现象。这并非自然的城市化,而是在良好教育资源的诱导下所产生的城市人口流入。
对教育的重视古已有之,通过教育可以成为精英的观念,也已在我国延续几千年。只是当下社会,学习好的人都进了城,要想变成人才,就不能留在农村。“进城”是往上走,在村民望子成龙的期待里,城市一直都在。
四、结论
笔者通过随机抽样,在人口一百余户的N村选取十余户调查对象进行深度访谈与调查,发现N村电视入户率已达100%,调查对象中只有一位年过七十的受访者没有智能手机。N村已完全处在媒介包围下,受媒介影响至深。N村家庭平均年收入在七至十万左右,90%以上的村民认为在衣食住行方面,N村与城市并无太大区别,但所有受访村民都表示城市在某些方面优于乡村,这些优势集中在教育、社会保障、薪假福利等领域。通过访谈,笔者得知几乎所有受访家庭都已在昌邑买房 (或有买房的打算),而买房的理由则众口一致——为了孩子上学。但访谈中无一人提到孩子大学毕业后定居城市时可能遇到的种种困境。
传媒、人际传播与个人经历共同建构起的城市形象诱导了N村人对城市的向往,使他们希望离开乡村,成为光鲜亮丽的城市人。老一辈中年人希望子女能通过上学跳出农门,一些年轻人确实因此实现了身份的转换,可成绩好的学生毕竟是少数,大部分乡下年轻人仍沿袭着老辈走过的路径,在乡镇企业中找一份工作糊口。但对城市的向往从来没有停止,无法自己走出乡村的年轻人,又将目光放到下一辈身上,再次寄希望于子女,希望他们可以通过教育离开乡村,定居城市。
这个城市,是建构的城市,是拟态的城市,是没有“城市病”的城市。
媒介无法全知全能的反映世界,它传达信息的过程,其实是挑选信息与将其抽象化的过程,而信息被受众接受的过程,则是将信息再度具象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环境失真,拟态环境出现。
媒介——各类媒体、人际传播与中间城市——处于N村与外界城市之间,将现实的、庞杂的城市抽象化,提炼为符号化、片段式的内容,村民通过解读这些内容,又将其具象化为头脑中的城市形象。这样的城市形象诱导了他们对城市的向往,使他们苦心孤诣的购买学区房,将进城的希望投注在子女身上。
人类活动离不开传播,传播的过程就是建构的过程,建构带来失真与想象,想象产生影响与结果。村民进城的背后,始终带着对城市的想象。
注释:
[1]何国平:《城市形象传播:框架与策略》,《现代传播》2010年第8期
[2]沃尔特·李普曼:《公共舆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
[3]沃尔特·李普曼:《舆论学》,华夏出版社,1989 年版
[4]J.MFoot.Fromboomtowntobribesville:theimagesofthecity,Milan,1980-97.UrbanHistory,1999(3).
[5]董小玉、胡杨:《新生代农民工的大众媒介形象建构》,《新闻界》201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