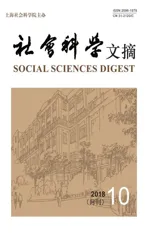宫体诗的“自赎”与七言体的“自振”
——文学史上的《春江花月夜》
2018-11-20
“自赎”还是“救赎”
70多年前,闻一多曾经发表过一篇著名的文章《宫体诗的自赎》,对《春江花月夜》予以极高的礼赞。既然这是一首宫体诗,那么它的成就便属于其内部的“自我革新”,所以闻一多用了“自赎”一词来形容。30多年前,先师程千帆写下《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被理解和被误解》,在肯定闻氏“对此诗理解的进一步深化”的同时,也指出他以及之前的王闿运都将此诗“归入宫体”,“就是一种比较重要的、不能不加以澄清的误解”。如果这不是一首宫体诗,张若虚就是从外部出发对宫体诗作出了改造,那就应该说是“救赎”。因此,这里首先需要处理的,就是如何理解文学史上的宫体诗。
就宫体诗的得名而言,通常引用的文献不外乎《梁书·简文帝纪》《徐摛传》《隋书·经籍志》集部序等。我要强调的是,宫体诗创作典范《玉台新咏》的编纂,就含有扩大宫体诗内涵的动机和作用。《大唐新语》卷三“公直第五”载:“梁简文帝为太子,好作艳诗,境内化之,浸以成俗,谓之宫体。晚年改作,追之不及,乃令徐陵撰《玉台集》,以大其体。”所谓“以大其体”,用现代的表述就是扩大该体的范围。由此可以知道,至晚在陈朝,宫体诗的内涵已经被扩大,并且通过一个权威的选本固定下来,扩散开去。唐代李康成编《玉台后集》,写了一篇序称:“昔(徐)陵在梁世,父子俱事东朝,特见优遇。时承平好文,雅尚宫体,故采西汉以来词人所著乐府艳诗,以备讽览。”李康成的编纂起讫虽然从梁代延续到唐代,其基本原则与《玉台新咏》还是一贯的。有了前后两个选本为凭借,宫体诗概念的扩大也就仿佛成了不言自明、古来如此的“公共知识”,一直延续到晚清民国。
宫体诗既然在当时已经是“境内化之,浸以成俗”,其作者就不限于围绕在简文帝身边的东宫学士。宫体诗既然在陈、隋、唐初仍有遗响,其历史也就不限于萧梁一朝。因此,对宫体诗人以外的创作就无法一概而论,需要作出厘清。但判断一诗是否属于宫体,不能仅仅根据其文辞的“丽靡”与否,也不能仅仅根据其内容是否在谈男女恋情,更不能仅仅根据其音乐来源,需要作具体分析。回到本文,就是如何判断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归属。
《旧唐书·音乐志》二记载了《春江花月夜》等作品,《乐府诗集》几乎全部抄录。根据郭茂倩的分类,这些曲子的基本旋律都属于“清商曲辞”中的“吴声歌曲”,这指的是曲调的来源。但既然经过陈后主、何胥之手制作,《春江花月夜》等三曲就只能被看作宫廷音乐,其作品也只能被看作宫体诗。到了编辑《乐府诗集》的时候,郭茂倩能够看到的只剩下隋炀帝等人的7首作品了。如何判断这7首作品?我以为,用了宫体旧题写诗,无论其辞是艳丽或典雅,都是宫体诗。
大约90年前,胡小石写过《张若虚事迹考略》,认为《春江花月夜》受梁、陈宫体之“重沐”,其诗也本于“陈曲”。更早的《中国文学史讲稿》提及张若虚,也将他归为“齐、梁派”。我同意这个看法,也因此而认为张若虚此作是对宫体诗的“自赎”而非“救赎”。
何谓“《西洲》格调”
王闿运对《春江花月夜》的评论,最为人熟知的就是“孤篇横绝,竟为大家”,但这段评论的重心是在指授后学,唐诗中“歌行律体是其擅长,虽各有本原,当观其变化尔”。具体到这一首诗在诗歌史上的成就,其“变化”旧章的关键,就是“用《西洲》格调”。
什么是“《西洲》格调”?它集中在两方面,即结构和句法。先言结构。《西洲曲》在结构上的最大特征,就是四句一换韵。全诗32句,犹如8首五言四句小诗联缀而成。四句一换韵的结构在古诗和乐府中不常见,清代郎廷槐曾提出“五古亦可换韵否,如可换韵,其法如何”等问题。王士禛答道:“五言古亦可换韵,如古《西洲曲》之类。”张笃庆答道:“五古换韵,《十九首》中已有。然四句一换韵者,当以《西洲曲》为宗。”因为是四句一换韵,所以在形式上,后人觉得好似若干首绝句合成了一首长篇,尤其妙在转接无痕,不见斧凿,义脉连贯,声情摇曳。沈德潜也说:“续续相生,连跗接萼,摇曳无穷,情味愈出。”他又说:“似绝句数首攒簇而成,乐府中又生一体。”古人显然已经注意到此诗在结构上的特征,并且是独有的(所谓“又生一体”)。
再言句法。《西洲曲》在句法上的最大特征是复沓和蝉联。这本是南朝民歌的一般特征,但此诗将这一特征表现得淋漓尽致。以复沓为例:
树下即门前,门中露翠钿。开门郎不至,出门采红莲。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
前四句以“门”为关键词,后四句以“莲”为关键词,第四句“出门采红莲”又绾合了“门”与“莲”,从上一解过渡到下一解。蝉联句法往往在两解同时也是换韵之间,因而造成转接无痕的效果:
……风吹乌臼树。树下即门前……
……出门采红莲。采莲南塘秋……
……仰首望飞鸿。飞鸿满西洲……
……尽日栏杆头。栏杆十二曲……
所以这是用蝉联法转韵,一韵一意。除此以外,还有个别错综句法,比如“忆郎郎不至,仰首望飞鸿。鸿飞满西洲,望郎上青楼”,以“一四”“二三”的照应交错成句。
张若虚《春江花月夜》既“用《西洲》格调”,那么,在结构和句法上也就拥有这些特征。如上所述,清人将《西洲曲》看作四句一换韵的代表,张若虚继承了这一结构方式,并将它从五言转移到七言。《春江花月夜》共36句,四句一转韵,是9首七言小诗的联缀。而在转韵的过程中,也如《西洲曲》一般宛尔成章。《西洲曲》写一年之事,张玉谷指出:“由春而夏而秋,直举一岁相思,尽情倾吐,真是创格。”情之所至,一吐为快,不必实事求是,所以王尧衢说:“皆属虚想,非实境也。”《春江花月夜》写三春之事,从花开到花落,用笔则浓缩于一夜之间,而在空间上更由潇湘到碣石,也同样“非实境也”。最后一解四句,“斜月沉沉藏海雾”写时间,“碣石潇湘无限路”写空间。诗人为一对恋人的南北睽隔而伤感,也暗含了“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的意思。但诗人是富于同情心的,他不忍把人生推到绝处——“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满江树”,试问月下究竟有谁能及时而归,虽然没有把握,但无论如何总不会无人能归吧?“归”象征着在青春时光里爱的圆满,同时在诗人的心目中,月亮即便西斜,也还是会满含同情地给人生以安慰,并将这种同情和安慰洒满江树。
在句法上,《春江花月夜》也多用复沓:
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照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
王尧衢指出:“题目五字,环转交错,各自生趣。春字四见,江字十二见,花字只二见,月字十五见,夜字亦只二见。”诗人又以不严格的蝉联句法安置在两解换韵之间:
……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
……何处相思明月楼。可怜楼上月徘徊……
……江潭落月复西斜。斜月沉沉藏海雾……
因为不十分严格,所以少了些民谣风,因为还是蝉联句法,所以宛转关情,情文相生。所谓“用《西洲》格调”,大抵就是如此。
七言体的“自振”
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张若虚之前的《春江花月夜》,有三人五首,这里不妨人举一首:
暮江平不动,春花满正开。流波将月去,潮水带星来。(隋炀帝)
花帆渡柳浦,结缆隐梅洲。月色含江树,花影覆船楼。(诸葛颖)
林花发岸口,气色动江新。此夜江中月,流光花上春。分明石潭里,宜照浣纱人。(张子容)
这三首诗,并没有直接描写男女之情,更多的是写自然。但按照上文的看法,我仍然认定其为宫体诗。以上三诗有词无情,只是堆垛了一些与题目相关的字词,虽然有些描写还不失生动,但总体来看就像在制题。张若虚若是照着他的前人依样画葫芦,则其诗写到第二解即可完篇: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
第一解出现了“春江月”三字,虽然“连海平”“共潮生”“千万里”“何处无”,写得雄浑壮阔,婉约中有豪迈,豪迈中寓婉约,但也没有能够超出隋炀帝之作多少,“滟滟随波千万里”不就是“流波将月去”吗?如果一定要计较,张若虚还多费了两个字呢。
江流宛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
第二解出现了“花”还有“芳甸”,既然“月照花林”,当然“夜”寓其中。“似霰”之喻虽然贴切,不过是隐括了又一位宫体诗人萧绎的句子:“昆明夜月光如练,上林朝花色如霰”。若是以前的宫体诗人写到这里,“春江花月夜”五字皆有交代,全诗就可以结束。但张若虚这首诗的伟大,恰恰就是从此后开始的。
胡小石在《中国文学史讲稿》中,谈到初唐诗歌的内容时,概括为三个方面:宫闱、边塞、玄谈。几乎所有的中国文学史,绝无以“玄谈”作为初唐诗的内容之一,这可以说是该书的“特见”。胡先生特别举出张若虚《春江花月夜》来说明其“玄谈”。作为时代特征,他还举出了刘希夷、李峤的一些诗句,但最富代表的还是张若虚。我以为此处所谓的“玄谈”“玄理”指的是人生哲理,虽然其说明仅寥寥数语,但他以“玄谈”“玄理”来概括仍是启人深思的。
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写了闺情,也写了自然(这些本来都是宫体诗的传统题材),不同处在于,他把人生哲理融入自然和闺情之中,又从自然和闺情之中提炼出哲理。正因为有了“玄理”的加入,七言诗的品格也因此而得到大幅度提升。请看第三解:
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
前两句是写景,但又不止在写景。《世说新语》曾记载司马道子和谢重的对话:“于时天月明净,都无纤翳。太傅叹以为佳。谢景重在坐,答曰:‘意谓乃不如微云点缀。’太傅因戏谢曰:‘卿居心不净,乃复强欲滓秽太清邪?’”因此,“无纤尘”不止是写外景,也是诗人内心明朗的写照。由此而引出对于时间的追问,这是青春自我觉醒的第一个标志。王尧衢说:“人有死生,世有古今,而月则常常如此,这个根底,有何人穷究得出?”于是第四解来了:
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照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
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一代又一代的人生是无穷的。个人的生命是小生命,人类的生命是大生命,这是一扬。然而永恒的江月却总是那样冷静,不动表情、不露声色,以年年相似的模样看着月光下不断变幻的人生,这是一抑。世界到底是有情还是无情?若说无情,江月何以有“照”?又是一扬;若说有情,江流何以分秒东逝“不复回”,全不顾念“吾生之须臾”?“是江流又一无情之物也”,又是一抑。第五解转向了青春觉醒的第二个标志——爱:
白云一片去悠悠,青枫浦上不胜愁。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
人生有限,时间永恒,能够抵御时间的侵蚀和消磨的,只有人世间永恒的爱意。但爱是有忧伤的,恰如明朗的内心有时也会被微云滓秽。白云一片,悠悠而去,“又是一无情之物”。水边送别,依依难舍,总是一有情之人。《楚辞·河伯》:“子交手兮东行,送美人兮南浦。”江淹《别赋》:“春草碧色,春水渌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诗人用了“谁家”“何处”,并非特指,也因此而显示出一种人生的共相。第八解是作为青春觉醒标志的时间与爱这两大主题的双重奏:
昨夜闲潭梦落花,可怜春半不还家。江水流春去欲尽,江潭落月复西斜。
就时间而言,一方面是一夜将尽,一方面是一春将尽。江水代表了时间的流逝,而流走的是四季中最美好的春季,也是一生中最美好的青春。不仅流走,而且“欲尽”,又一次提出了时间的主题。但人生不仅短暂,而且无奈;不仅是青春时光的流逝,而且相爱的人也未能还家,人生真可能彻底辜负了“春江花月夜”。而这千古之谜,既无人能解,也是永恒的憾恨。
从文学史上来看,七言诗只有到了《春江花月夜》,才“一洗万古凡马空”。就像五言诗到了阮籍,才从哲理的高度思考人生问题。她既开发了我们的理性能力,也培养了我们更细微的感官。到了他们这儿,无论是五言诗还是七言诗,在品格上都彻底摆脱了闾里歌谣的传统。在陈、隋两朝文人的努力下,到了初唐,七言歌行在句法、用韵、规模上已经成熟,但就品格而言,多数诗作还是难免卑下。就题材来说,这些作品集中在宫闱和边塞,我们可以不予比较。但刘希夷和李峤的作品,就很可以拿来一较高低。刘希夷《白头吟》中有“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以及“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等含有“玄理”的句子,但这样的“玄理”却被诗人用更大的篇幅、更浅白的意思“稀释”了。李峤《汾阴行》的结句“山川满目泪沾衣,富贵荣华能几时。不见只今汾水上,唯有年年秋雁飞”,也含有世事感慨,但这些朝代兴亡、人世沧桑的喟叹,却出之以浅露直白的表达方式。《春江花月夜》的“玄理”,不是浅表的人生感叹,不是虚恬的玄学思辨,而是由生命伦理意识为支撑的哲思,是用那种明朗而又蕴藉的方式揭示出的人生神秘、无奈和忧伤,并且这种种的神秘和忧伤又是无法解释、没有终了的。让我们再读一次钟嵘《诗品》对阮籍的评语吧:
《咏怀》之作,可以陶性灵,发幽思。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洋洋乎会于风雅,使人忘其鄙近,自致远大,颇多感慨之词。
如果把“《咏怀》之作”改为“《春江花月夜》”,难道有任何的不合适吗?所以我要说,《春江花月夜》岂止是“宫体诗的自赎”,实在是“七言体的自振”!有了这篇杰作,还有谁敢用“体小而俗”去评价七言诗呢?如果运气足够好的话,张若虚本可以和陈子昂在唐诗历史上的地位相当。令人叹息的是,这样的杰作居然在文学史上被冷落了好几百年。张若虚之后的李白应该是读过《春江花月夜》的,就算“空里流霜不觉飞”未必引发了“疑是地上霜”,但“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等句,能说没受到张若虚的启迪吗?而李白以他惯有的目空一切的眼光横扫建安以来的诗坛,用一句“绮丽不足珍”便轻轻抹去;在谈到当时的几种主要诗体的时候,还秉持着“兴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的老调,仿佛是刘勰、钟嵘、萧子显批评声音的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