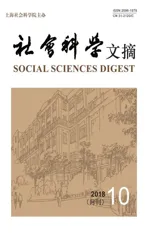重提一桩学术公案:“要康德,还是要黑格尔?”
2018-11-20
对于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发展的回顾与反思,有一个话题似乎绕不过去,那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康德、黑格尔哲学的关系问题。在这些讨论中,一桩关于康德、黑格尔哲学的学术公案,不可避免地会被提起。尽管如此,这种提及却似乎往往被漫画化了,并未得到认真的对待,因而在此便值得我们重新提起,并予以真切的审视。这桩学术公案非他,就是近四十年前李泽厚提出的、被人们掐头去尾加以漫画般传播的“口号”:“宁要康德,不要黑格尔”。
“宁要康德,不要黑格尔”
这个“口号”是李泽厚于1981年9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纪念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出版200周年和黑格尔逝世15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提出来的。据会议报道,“李泽厚认为,今天我们的时代对康德的兴趣胜于黑格尔。在这个意义上他说,‘一般说来,我们既要康德,又要黑格尔。不过,假如一定要我在两者之间选择一个的话,那我的回答就是:要康德,不要黑格尔’。”
李文先是简单地指出了康德哲学之贡献,而后在与黑格尔哲学的对比中强调了康德哲学比之黑格尔哲学的优胜之处:“康德在某些方面比黑格尔高明,他看到了认识论不能等同也不能穷尽哲学。黑格尔把整个哲学等同于认识论或理念的自我意识的历史行程,这实际上是一种泛逻辑主义或唯智主义。这种唯智主义在现代受到了严重的挑战……人为什么活着?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存在的内容、深度和丰富性?生存、死亡、烦闷、孤独、恐惧等等,并不一定是认识论问题,却是深刻的哲学问题。它们具有的现实性比认识论在特定条件下更为深刻,它们更直接地接触了人的现实存在。在这些问题面前更深切地感受到自己的存在及其意义和价值。把一切予以逻辑化、认识论化,像黑格尔那样,个体的存在的深刻的现实性经常被忽视或抹掉了。人成了认识的历史行程或逻辑机器中无足道的被动一环,人的存在及其创造历史的主体性质被掩盖和阉割掉了。”
然而,人们在评论这一提法的时候,却往往只是抓住“宁要康德,不要黑格尔”一句,认为提出者就是无条件地不要黑格尔,只要康德,却不再理会提出者对此一提法的限制:“一般说来,我们既要康德,又要黑格尔。不过,假如一定要我在两者之间选择一个的话,那我的回答就是:要康德,不要黑格尔。”显而易见,这一“宁要,不要”的句子是在有条件限制的前提下的一个假言判断,而非无条件的直言判断。而一旦将提出者的意思转变成一个明显偏颇的断言之后,批评者们也就易于对这种被“偏化”了的言论简单地进行“有力”驳斥了。
尽管这一当时反响颇大的事件已过去多年,国人对于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水平也有了极大幅度的提高,但这种基于“偏化”的驳论方式在时隔30多年之后,似乎仍然是人们所习惯的。
“既要康德,也要黑格尔”
近些年来,学界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德国古典哲学关系问题的关注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但这主要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围内进行的,而在更广泛意义上对于这一问题进行学术性回应的评论,首先当属邓晓芒教授发表于2016年的《重审“要康德,还是要黑格尔”问题》一文。
邓晓芒教授的基本主张是:“一个康德,一个黑格尔,是中国当代学术跨不过去的坎。当然其中还应该包括费希特、谢林等人,但最重要的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康德和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但上世纪80年代提出的那个问题现在又摆在了面前:在两者之间,要康德,还是要黑格尔?不过现在这个问题已不再具有当年那种情绪化的偏向,而是需要进行一番冷静的客观评价,即康德和黑格尔对我们今天的哲学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各自具有哪些优势和软肋?”
邓晓芒教授接着顺次指出了康德与黑格尔哲学各自的优势与不足。
康德哲学有三大优势:
“首先,康德哲学具有前所未有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一般说来,真正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本身就是理性精神,这正是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其次,康德哲学的确又是直指人心的,即他是立足于人的知、意、情三种心灵能力来建构自己的整个哲学体系的。”“第三,康德哲学的保守性使人类的理想主义不因过激的行动而丧失信用,而是超然于现实生活的功利性评价之上,并成为现实生活的一种不断努力的目标和永恒的批判性标准。”
与之相应,黑格尔哲学也有三个方面的优势:
“首先……在西方哲学史上,黑格尔是一个把逻辑和历史看成一体的哲学家”。“黑格尔的第二大优势,即对理性思维的根本性的深化,也就是辩证思维的确立。”“黑格尔哲学的第三大优势在于,他有广阔的文化视野,在这方面几乎无人能与他相比。”
邓晓芒教授同时也通过对比指出了康德哲学和黑格尔哲学各自的缺陷。
康德哲学的缺陷,首先在于“康德虽然已涉及人的主体性的问题(如确立起人的道德上的‘尊严’),但还是在极其抽象空洞的意义上的涉及”。其次,康德哲学的又一个缺陷则在于,与黑格尔建立起了辩证理性的法则从而由此提出“历史理性”相比,他没有把辩证理性当作真正的理性,于是在历史问题上就只能限于“猜测”。再次,与黑格尔具有广阔的文化视野,对后世文学艺术批判产生了广泛影响相比,康德在这方面简直是乏善可称。
黑格尔哲学的缺陷则在于:
首先,与康德哲学的开放性与包容性相对,“由于黑格尔不承认有不可知的自在之物,因此使他的包容性受到了某种限制,他的理性是排斥感性、排斥不可言说的‘意谓’的,他的怀疑(这被看做消极的理性环节)是最终被扬弃了的,在他那里没有什么可以‘存而不论’的东西。因此,如果完全相信黑格尔的话,那么黑格尔以后的人就什么也不用干了,甚至都不用活了,只需按照他已经制定的程序去做就行了。这就是黑格尔体系的封闭性和排他性,哪怕所有的哲学都在他的哲学中,但所有的哲学都只能由他来解释,不能有别的解释”。其次,与康德哲学的直指人心的“人类学”相反,“黑格尔所鼓吹的人性本恶只有依靠世界历史中的上帝之手才能把人类引向自由意志的提升,在这种眼光之下……人类的道德只是上帝实施自己的‘理性狡计’的工具而已”。再次,“在他的历史观中是没有道德的评价标准的,眼光固然老辣而透彻,但对具体的人是冰凉冷漠的,毫无希望的”。此外,“对于现代科学的发展,黑格尔所做的贡献也乏善可陈,他过于热衷于到牛顿物理学中去挖掘内在的神秘主义的精神意味,从‘自然哲学’的眼光来看固然不是没有意义的,但在自然科学本身的进展上却很容易闹出笑话(如色彩理论)”。
邓晓芒教授是当今康德哲学与黑格尔哲学研究大家,他对于两种哲学优缺点的分析,无疑是十分恰切和中肯的。虽然邓晓芒教授力主由于康德和黑格尔哲学各自的优势所反映的都是人类理性的优势,因而两者都是不可偏废的,即“两个都要”,但从他对两者优缺点的分析来看,总的感觉似乎是较之康德哲学的缺陷,如现象与物自身的二分,不承认辩证理性,缺乏广阔的文化视野,黑格尔哲学的缺陷更为严重一些,如体系的封闭性,对个体人的冷漠,将人类道德视为上帝实施“理性的狡计”的工具等,因而,读罢该文,给人的感觉是,顺理成章的结论似乎应该是,即便“两个都要”,但“要康德”似乎至少“要得”更多一些。
“既不要康德,更不要黑格尔”
许苏民教授之“既不要康德,更不要黑格尔”的理由,首先在于“既要康德,就不可能不要黑格尔,从康德必然要发展到黑格尔,没有康德就不可能有黑格尔。黑格尔的很多观点,无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几乎都可以从康德那里找到其最初的表达方式,何况黑格尔被看作是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呢”?
“康德黑格尔哲学中明显是错误的、逻辑上很可笑的东西”有七条:第一,德国唯心论的结构性伪善;第二,从康德的曲解逻辑到黑格尔为了肆意鼓吹犯罪而违反逻辑;第三,德国唯心论把人性看得太坏,其道德律令多不近人情;第四,割裂科学与人文,这体现在康德“理性的双重立法”中;第五,以君主的意志取代多数人的意志;第六,以普鲁士国家为“地上神物”;第七,把精神的最高角色指派给日耳曼人。
许苏民教授的论证方式大致上可分为三类:一部分是引用诗人文学家的一些作品片段,这种文学性的援引方式,此处亦无法讨论,暂且只能交由文学评论家去考察其意思的真伪;另一部分则是引用英美学者对德国古典哲学的评论;还有一部分是引用中国学者的相关评论。我们这里主要看看这两部分论证。
在引用英美学者评论方面,比较重要的是引用诺斯罗普的话:“‘德国皇帝和希特勒德国的文化都是康德或其哲学后继者关于善的观念培养起来的’,即使清除了纳粹统治者和他们的将军,并使战后德国人获得舒适的生活,也难保他们不去信奉康德和费希特开创的不受约束的浪漫主义道德哲学和尼采的狂热信念。”还有引用杜威的话:“杜威说得很公正:康德是‘启蒙运动的儿子’,但却走向了‘与启蒙运动决裂’”;“杜威说康德的‘绝对命令使人想到出操的军士’,实在非常贴切”;“杜威说,虽然康德因受18世纪启蒙思想的掣肘而并未成为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但他的后继者却十分得心应手地用《纯粹理性批判》来强化战争准备的意图,用《实践理性批判》来造就绝对服从、勇敢地向着死亡前进的战士”。
鉴于德国与英美哲学家之间的互相贬低的历史事实,这里以诺斯罗普和杜威对于德国古典哲学的一些言论来作为对之定性的论据,似乎过于薄弱。而且,若是考虑到作者所主张的“要以中国哲学的尊生齐物义为最高宗旨,扬弃德国唯心论与英美经验论两大价值观念体系,克服其弊病而重建现代理性”,现在却以其中一种具有“弊病”的观念体系持有者的论断为依据去评价另一种具有“弊病”的观念体系,似乎有失妥当。
在对中国学者的引用方面,最重要的是引用贺麟关于德国古典哲学的论述。作者指出,“贺麟……在1961年写的《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评述》一文,不仅揭示了黑格尔如何使‘哲学在‘本质上’也得依靠国库’而成为干禄之具,而且还深刻指出:‘黑格尔的《法哲学》已经为德国转变成帝国主义预先铺平理论的道路。’”这里且不说作者引用来作为凭据的贺麟在那个特殊改造思想的年代的话语,是否为贺麟思想的真实表达,而只须对照一下贺麟先生1981年“在纪念康德、黑格尔学术讨论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对康德、黑格尔哲学的高度评价,就足以见出作者选择性引用之不当了。在这个讲话中,贺先生有如下言论:“我们纪念康德,因为他坚持人的尊严。人是生活在目的的王国中。人是自身目的,不是工具。人是自己立法自己遵守的自由人。人也是自然的立法者。在认识过程中,人们探讨自然不是像小学生服从教师那样甘当自然的奴仆,而要像法庭的裁判官那样,拷打自然,向自然提出问题,强迫它答复我们的问题。换言之,康德在认识论上强调主体的能动性。”而“我们纪念黑格尔,因为黑格尔是辩证法大师,马克思‘承认黑格尔是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尽管他正确地指出,要把黑格尔的辩证法颠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显而易见,这些话语与其1961年的评论是截然不同的,因而,如果不能证明贺先生晚年的思想并非其内心观念的真实表达的话,那么,对于贺先生不同时代的有关言论,却只选择其1961年那个特殊年代的论述加以引述,恐怕也是有失妥当的。
多要点康德,少要点黑格尔
让我们再回到这一问题提出的原初情形。如果人们不去“偏化”李泽厚的原话,不掐掉“一般说来,我们既要康德,又要黑格尔”这个前提,而是在这个前提条件下再比较认真地理解“假如一定要我在两者之间选择一个的话,那我的回答就是:要康德,不要黑格尔”这句话,且考虑到在发表的文章中论证的话,那么,人们是不会得出提出者是“只要康德,不要黑格尔”的结论的,而只能得出“多要点康德,少要点黑格尔”的结论。我们上面也指出,从邓晓芒教授的文章中,人们读出的感觉并非半斤八两的“两个都要”,而也是“多要点康德,少要点黑格尔”。或许,这一观念才是从李泽厚提出问题以来中国哲学界一大批学者思想的真实表达。
余论:是否还会有其他可能的排列组合方式?
从“宁要康德,不要黑格尔”,到“既要康德,也要黑格尔”,“既不要康德,更不要黑格尔”,再到“多要点康德,少要点黑格尔”,看上去多少有点像在玩一个排列组合的数学游戏。但若从排列组合的可能方式来看,以上四种还未穷尽可能的选项,尚有两种方式可供选择:一种是“宁要黑格尔,不要康德”,还有一种是“少要点康德,多要点黑格尔”。
考虑到“宁要康德,不要黑格尔”并非是“只要康德,不要黑格尔”,而只是人们为了更易于驳斥而“偏化”的结果,那么,“宁要黑格尔,不要康德”这个选项大概也不会是一种真实的观念表达,而只可能是论战中矮化对手的策略性“恶谥”,因而可以存而不论。这样,要讨论的便只剩下“少要点康德,多要点黑格尔”这一选项了。那么,这种情形会不会出现呢?窃以为,是有可能出现的。笔者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提出,“先要康德,再要黑格尔”,所表达的意思是,“中国的哲学家们必须从正视文化冲突的现实开始,必须重新考量这种中西文化的胶着状态,特别是分析前贤们的哲学文本,发现其中对于中西文化冲撞的反映,客观地把握这种形势,不强求一种不成熟的统一,而宁可坦承这种分离。就此而言,当今中国最迫切需要的是能够直面并把握和揭示出精神文化中深刻对立的康德精神的追随者,而不是动辄构造体系的黑格尔的肤浅的模仿者”。一旦这种文化冲突被充分地表达于哲学理论之中,便需要做进一步的融合化解工作,而在这个时候,黑格尔的通过否定达到更高的肯定的辩证法也就有用武之地了。但前提是必须真正以康德哲学的精神把握住文化冲突之实际。因此,必须是“先要康德,后要黑格尔”。此时,就有可能出现“少要点康德,多要点黑格尔”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