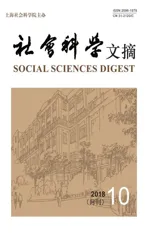现代生命的社会化图景
2018-11-20
社会化的“形式”
百年来,齐美尔的社会思想通常被冠以“形式社会学”之名,意思是说他的研究对象并非社会实体,而是“社会化”(Vergesellschaftung)。既有的大部分社会学研究像处理客观事物那样看待已经提炼成型的社会组织,例如国家、行会或社会分工体系,它们考察这些“社会”实体,追问“社会是什么”。然而在这些“脏器”之外,还有许多尚未固化的、脉搏不息的局部综合,即社会化:每时每刻,绝缘并立的个人不断形成特定形式的互相、互为。因此,齐美尔研究“社会化”其实问的不是“社会是什么”,而是“社会何以可能”。
齐美尔之所以提出“社会何以可能”是呼应康德的“自然何以可能?”齐美尔评论道,康德会这么发问是因为对他来说自然无非表象,是我们的智性借以整合感觉印象以形塑成统一世界图景的方式,于是“自然何以可能”针对构成我们理智的诸形式。类似地,齐美尔这里社会化的统一过程也是零散的感觉要素综合形式,然而他们的问题有着截然不同的含义。对康德来说,“自然何以可能”是个认知问题,主体将给定的要素综合为“认知的统一体”——自然。然而,“社会何以可能”或者说“社会化”不是拿先天范畴构建社会。“社会化”近似于现象学所说的“去存在”,是一种源发构造性的过程,人如何与周遭建立最具体的相互作用。它不可能达到康德那样纯粹的先天范畴,因为“个人心灵”时时刻刻已经浸入无数简单的过程,它在其中感到自己被决定、被抛入与“他人”的某种最具体的互相和互为之中,并且这种具体的相互作用过程对“我”来讲是无条件成立的事实。这些“先天”过程并不是逻辑上先于社会存在的原因,而是所谓社会这种综合的各个局部,换言之,社会化形式的研究虽然带有审视的味道,却是身处“被社会化”的过程之中去知晓、熟悉其形式,而非康德式的认知过程。齐美尔正是由他对社会化形式的研究来诊断现代社会和现代生命。
外在化的现代世界
古今之间,人与周遭打交道并由此构建自我的方式经历巨变。原先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更直接也更短促,想要什么就去拿,受到阻碍可能得打一架,就像物物交换一样,目的近在眼前,手段不会遮蔽目的,随着目的实现,手段也就淡出视野。人们聊天或辩论,是为了生存而利用语言与知识,不是为了知识而活,换言之,知识或语言本身并不支配他们之间的关系。随着群体规模日趋庞大,交换越来越复杂,直接交换难以为继,人们便逐渐分离出各种功能,片面地与更大规模的人群交换。当分离出的功能越来越片面,亦即越来越抽象时,交换关系也变得抽象,甚至逐渐发展出独立的运转逻辑,成了外在于个体意志和行动的东西。比方说,科学发展出它自己的一整套运转逻辑,不再是人们活着并发生关联的临时性手段而已,毋宁说人与人是为了科学才相互接触,他们只不过是科学逻辑下的某种“功能”载体而已。原本充当手段的某种短促过程逐渐成为了外在于人的客观秩序,随着我们越来越严格、越来越符合客观原则地组织生活手段,我们的生活就越发成为一整套外在于我们的客观对象。活着慢慢变为一种自我割裂的技术,每时每刻我们都在将自己分割,交付给不同的客观秩序,在这些客观秩序内将生活内容以一种近似于自然规律的理智方式严格编织起来。
无根的人缺乏与这些客观秩序之间的深刻关联,却紧紧攀附着这套秩序。就像没有“天职感”(Berufensein)的科学家可能对他所研究的学问漠不关心,他一心将知识编织成稍微完整的体系,不断复杂化,然而这般忙碌仍旧无法解除根本的荒谬感:在片段性的生存之中,生命渴望朝向某种统一的终极与绝对。问题在于,现代生命竟然将这股强大的意志投射到客观秩序内部的发展,仿佛这些客观秩序的严整统一就等于自身生命的完满。手段逐渐被当成终极价值,生活的外化与这种情感过程并行,它依赖物质的完美而非人的完善,挣得多、知道得多莫名就成了目的本身。“最终,人们处处陷在密集交织的制度与手段之网里,完全没有明确的终极目的。惟独在这样的文化处境下,才出现对终极目的和生命意义的需求。”
生命直观:在康德与歌德之间
外在化的、分裂的现代世界如何回到统一的生命图景呢?齐美尔基于他对康德与歌德的解读,认为契合当今情形的生命观只能在康德与歌德之间寻找。
康德问道:“自然何以可能?”针对的是客体与主体的统一。自然无非是事物之间可理解的、有规律的相互关联,只是表象,而表象活动的条件就是一切客体的条件,知性将感觉材料领会成经验的对象,不断生成客观世界。在这一经验世界的彼岸还有一些事物不是为我们而存在的,即物自身,康德将绝对性落在这一决然彼岸的领域之中。简言之,按照齐美尔的解读,康德通过将自然归结为主体的表象,将绝对性置于置于经验世界之外来回应主体—客体问题。康德的方案凭借着一个事实,即我们知道,可这一事实相应地划定了限度,世界只能在其可知这一形式内被把握,主体仿佛沦为某种认知功能。齐美尔作为著名的新康德主义者,确实在大体上认同康德有关表象世界的学说,不过一旦涉及到对生命的理解,相较于康德他还是更欣赏歌德的基本倾向,并受歌德的影响提出了不同于康德的生命图景。
齐美尔曾对比康德与歌德迥异的基本倾向或者说基本韵律:康德不断划定边界,歌德则是艺术式的统一。对康德而言,科学通过划定边界所能达到的世界图景本身也有清晰的边界,永远无法彻底达成事物的统一,除非凭信仰之跃,借助宗教、审美或道德等实现。歌德的统一不是像康德那样先明确各种界限,再靠认知活动统一起来。“歌德从客体这边解决主客体同一的难题,康德则从主体这边来解决。”按照齐美尔的理解,歌德在意的始终是直接表达他的世界感,对他来说,像康德那样宣称自然只是主体的表象简直不可饶恕,另一方面,绝对统一只能在不可知的物自身那里达成,同样是不可接受的,歌德的绝对就在世界之中,在现象之内,不在彼岸。
一切事物固然是外在的,但事物的直观性始终被赐予人,按照他对世界的直观感受,自然与精神的绝对性是有可能被经验到的。他在《温和的警句诗》里感叹道:“是了,这就是正确的轨道,人不知道他所思的,思索时,仿佛一切都被赐予。”思虑本身并不能挣得知识,当生命达到某一层次时,自然或上帝自会将相应的感受与理念敞开。在绝对性的问题上,“最好停留在哲学上的自然状态,尽可能地利用人未经分割的存在。”
对歌德而言,人的使命是让他之内的自然实现其全部可能性,人的生命只是自然大全生命的一种形式或者说一次脉搏,二者之间有着预定的和谐又有待后天的合宜。不过,仅从《浮士德》来看,经验常常并不能如愿让人合乎他的自然,因此浮士德才不得不借助梅菲斯特的超自然力量来实现他的合宜性,并且按照契约的隐喻,一旦他停留在任何经验关系之中,便会因未经发展的能力而死。在这个意义上,人越是具有个性、能力越丰富,越要求灵魂不朽,因为未经施展的潜能必须在生命之外,以另一种形式实现。
沿着康德与歌德的脉络,齐美尔在其最后一部著作《生命直观:先验论四章》当中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书里讨论的是康德那样的概念体系所无法涵盖的生命之先验感。类似于叔本华和歌德,齐美尔始终朝向生命的统一,而社会化形式乃至任何形式都是界限,人要能感知到界限存在、指涉它,就意味着人在某种意义上外在于界限。这已经涉及到一对贯穿全书的矛盾:有界限的生命形式—连续无限的生命涌流。
“每一内容都遗留下某些生命的残余,不断扣响它身后关上的门。生命就像这样从它的每一内容里探出,于是,人感到灵魂之永恒,一种无法被必朽穷尽的永恒。”所以说,生命不是对某些内容的机械回应,狭隘的现实总是弥散着伸向其外的“无限”感。在我们与世界的关系上,个体生命内容本身的偶然性、未及展现的天赋等等,都会强化对偶然性的感受。人经历越丰富,慢慢会遭遇到更多偶然,就越发觉得自我是一个连续的统一体,身陷动荡的命运之中。随着生命逐渐推展,自我也逐渐向内收拢,在偶然内容之间不断自我阐释,尝试着发展出一套独立于内容的意义和观念。每一生命的统一体都追求他的存在法则。
所谓存在法则是一个人生命之中各要素总体的关联方式。从生到死,灵魂游走在截然对立的宿命、倾向或生命内容之间。人可能既是野兽又是圣人,智者转瞬疯癫,如果从生命内容强行构建法则,规定生命,就得借助无数种相互割裂的解释,这些原则根本没法拼贴出生命的统一图景。人在一生中可能会无数次感到“不再是自己了”,每一瞬间的感情和行动都很容易背叛“自我”,甚至有时候会感到自己被整个世界抛弃。这样的“自我”像人悬于世界当中,拼命抠住一截柱子,这柱子越结实越好,人也得不断收拢缩紧,时刻不能放松,万一发现柱子是浮动的,一切就全完了。
但齐美尔这里,能将生命统一起来的法则并不是对现实指手画脚的命令,对人来讲,现实与应然都是生命的存在方式,应然式的生命就是说总有一些要求,并且这种被要求的义务感对人客观有效。齐美尔并不打算讨论这些义务究竟是怎么来的,或者提出新的道德学说,那齐美尔所谓的个体存在法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首先,个体性与主观性不能混淆,法则性也不是普遍性。“我们此处不关心独特性,(个体性是指)每一有机生命——尤其是精神生命——真正独特的展开形式恰恰是从自身生命的根基生长出来的。”像浪漫派只在内容层面区分特殊个体与普遍法则,然而特殊与否仍然停留在内容要素的层次上,在这里齐美尔不觉得与众不同就天然好过普普通通;关键在于,在最本质的生命之中,相对于这些内容,人是一整个活生生的统一体。
其实跟康德的普遍道德法则对比,个体法则之“法则性”更强:人不仅要对是否符合某道德法则负责,还要为该法则是否对自己有效负责,有效意味着它由我的生命整体涌出,无法开脱。康德式的道德原则乍看很严格,但对人的要求其实没那么高,具体到个别行动时,义务已经给定了,遵从它即可,即便生命之应然是不连贯的碎片,没能深刻植根于自己的整个存在,也不妨碍人遵从义务。齐美尔的版本就是另一回事了,义务必须首先是他的义务,是他整个生命涌流的进程,仅仅说它是某道德原则的要素是不行的。应然作为一种存在方式不能够止于碎片,必须是能够与其他生命内容统一的。每个道德要求或行为都是此刻的心跳,承载着我们曾经所是、所做、所应该做的一切。如果说尼采假设某行动法则在永恒轮回之中不断重复,康德的判断基于某法则对所有人普遍成立,那么齐美尔问的是某义务能否承载整个生命。“整个个体的应然决定着当下的义务,其实,这只不过是从伦理的维度阐释‘生命在每一瞬都是它的总体’”——生命在每一瞬都存在为它的总体。
抛开了我的存在图景,就不能真诚地谈论道德。不是说义务要听从主观意愿,不能有任何强迫,义务本身内含着对立—服从的结构,生命作为应然本来就始终在服从,跟禁锢或自由无关。所谓禁锢,是刻板固守一个原则来统摄整个应然生命,与其他活生生的关联发生冲突,这本来就算不上道德。人的应然生命遵从生命之中涌出的义务,就像“道德版本的命运”一样客观有效。
齐美尔所谓客观有效是指必须与生命之中其他部分、与周遭世界相关,个体所谓“自我”或“性格”也不是凭空诞生的,不能凭着乐不乐意随便开脱。假设某个和平主义者坚决不服兵役,可能在他看来,即便服兵役有国家权力和公意的支持,只要这种要求与他的道德学说无关,就不算伦理行动。但在齐美尔这里,倘若所有圣俗力量都认定他有义务服兵役,那他就该服兵役,不管他怎么想,正是这些关系编织形塑着他的生命,援引歌德的说法“人不仅是天生的,亦是后致的”。
一个人所处的具体关联和种种看似外在于他的形式,并非单纯的桎梏,事实上,在齐美尔那里,生命的自由指的是与不同形式、不同世界发生关联的能力,是自由地形成各种关系,而非通常所理解的“解放”似的挣脱束缚、切断关系。当我们不局限于桩桩件件的事实,而是将触及到的零星经验关联起来,将“不可知”与可知内容一并把握为统一的庞大视野,即是“世界”。一个人能否存在于哪些世界取决于他如何与生命内容相连。假如一个人只用某种实际生存的原则来把握内容,那现实世界就是唯一绝对的世界。不过,对超脱实际生存的人来说,现实更像断断续续的梦,艺术世界反倒是必然的。
生命与世界的关联不意味着掌握更多技术、看见更多内容,关键是在观看上投注更多生命,更加全身心地让整个生活都跟那些事物发生关联,直到能听见这个世界对他的“召唤”(Ruf),而他被世界“召唤”(berufen)恰恰是他与世界最深刻的统一。
结语
乍看齐美尔的生命学说与康德的“自律”相比并无新意,既然道德法则是人自己赋予的,那肯定是由他的生命出发的,其实不然。正因为康德严格排斥任何他律,便不得不先将个体理性立法的部分与感性严格分开,设定前者才是真正的普遍的个体以满足道德自律。虽然康德作出各种划分,但又无法完全消解被拆分掉的感性部分对应然生命的意义。齐美尔抱怨道,康德的自律设定反倒给人开脱的借口,自律的理性自我总是纯洁无辜的,罪只能归咎于不够纯粹的“他律”引诱人,他律类似于魔鬼的弱化版本。“人类道德上最懦弱之处就是发明魔鬼,它招认了人根本不敢直面自己作的恶。”
理性道德主义预设每个人完全知道他的全部义务,与此同时,他只知道能够通过意志实现的义务。“但是,我们从来不单作为‘理性动物’而活,生命是统一的整体,唯独回顾反思时才依照科学的、实践的或目的论的观点将人分析为理性与感觉等。”康德的道德学说以自然科学及民法为典范,他在逻辑框架上借助自然科学,道德原则是先天普遍有效的,因此我服从它,就好像我事先就明白我应该依照该法则展开生命,在法学上,民法只对人提出部分的、绝对适用的要求,不针对生命总体,齐美尔的个体法则却要求整个生命的存在方式必须是统一的,不能只遵循某项义务不顾其他生命关联就自称是道德的人。比起康德,齐美尔更贴近歌德所谓“日常的要求”,日常不是说每天外部环境对人的琐碎要求,他是指下一刻之后的一切仍然在黑暗之中,直到生命进展到那一刻才舒展开,在每一重周遭世界、每一重关系形成时,道德不能逃避与它们的关联,随着社会化关系的生成与消散,日常的要求也不断流动着,即歌德所说的“永恒的、灵活的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