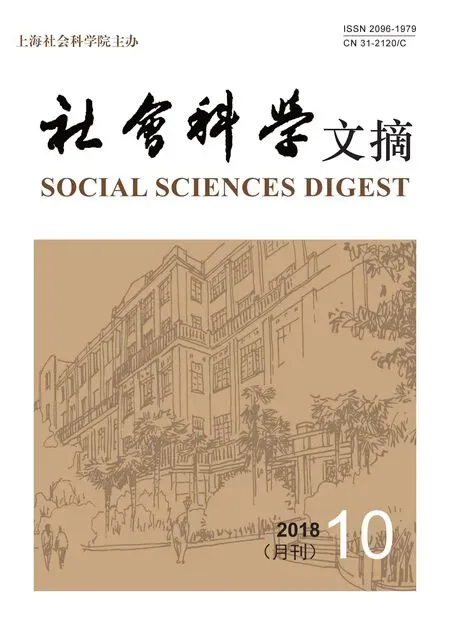约翰·加迪斯对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的借鉴与批判
2018-11-20
任何熟悉美国对外关系史和冷战史的学者对约翰·加迪斯这个名字都不会感到陌生,这位美国历史学家关于冷战起源、终结以及美国遏制战略的诸多著作早已成为当代经典。不过,在国内外众多学者的笔下,他却往往显露出“多重面相”。本文拟在相关学术文献的基础上,分析约翰·加迪斯对与自己学术生涯关系极为密切的国际关系结构现实主义的借鉴与批判,进而揭示借鉴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外交史(冷战史)的价值、意义和局限性。
现实主义理论:从旧到新
威尔士大学于1919年设立了首个国际关系学教席,这标志着国际关系学作为一个学科的地位得以正式确定。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爱德华·卡尔常被视为国际关系现实主义流派早期的重要代表之一,强调“国际政治永远是权力政治”。为躲避纳粹迫害而移居美国的犹太裔学者汉斯·摩根索进一步发展了卡尔的观点,并结合大量世界现代史的具体案例,建构起更为系统也更加强调“权力”的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
美国政治学家肯尼思·华尔兹在1979年出版了《国际政治理论》一书,他所提出的结构现实主义学说改变了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最初十分依赖历史学的局面。在他看来,建构国际关系理论需要严格区分结构和单元。首先,定义国际结构要依据国际体系内部的排列原则。毫无疑问,这便是“国际无政府状态”,它与一国内部的“等级制状态”形成鲜明的对立。其次,定义国际结构要依据互动单元间的能力分布。主权国家,尤其是大国由此成为建立国际政治普遍理论的关键。同时,为了实现理论的简约性,必须抽象掉国家的一切特殊性和具体联系,进而得出一种总体性描述,这实际也就斩断了国际关系理论与具体的经验性历史知识之间的联系。在华尔兹的理论中,所有的国家都成了均质且封闭的“弹子球”。
新的现实主义理论由于对“结构”的突出强调也被称为“结构现实主义”,它对一些重要国际关系现象的解释也与古典现实主义有较大差异。例如,后者强调国家对权力的追求与渴望,而结构现实主义则认为国家在无政府状态下以安全为最高目标,权力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以其理论为基础,华尔兹还有几个著名但“耸人听闻”的推论:第一,国家间的相互依赖未必能带来和平;第二,美苏两极格局较之前的多极状态更加稳定;第三,核武器有利于降低战争爆发的可能性。
共识与借鉴
约翰·加迪斯出版于1972年的《美国与冷战的起源,1941—1947》一书体现了一种“后修正派”的研究视角。在加迪斯看来,二战后美国领导人并不想引发冷战,不过他们更不希望“不安全”。那种认为美国本可以避免与苏联对抗的观点未免显得“事后孔明”。以往谈论冷战起源的历史学家仅仅强调某一方行动进而另一方反应的观点有失偏颇,因为冷战发端于美苏两国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的互动。在纳粹德国战败后中欧地区出现权力真空的情况下,两大国对彼此的错误判断引发了它们在这一地区的对峙。如果一定要强调冷战的责任,我们应该思考谁的责任更大。苏联的政治体制赋予斯大林更大的行动空间,故而应为冷战的爆发承担稍大的责任。
加迪斯在冷战史研究中所采取的视角不仅和华尔兹多有共识之处,亦多借鉴后者的理论框架来分析问题。这首先体现在他为革新美国外交史研究方法所提出的建议之中:学者们应进行跨学科的有益尝试,开展比较史学研究,尤其要克服“体系分析缺失”(systemic innocence)的老毛病。历史学家要记住,美国一直都是“国际体系”(international system)的一部分,而后者自身的特征则能引发某种效应。加迪斯对冷战时期美苏两大国为何能维持“长久和平”的解释最能体现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对他的影响。在他看来,华尔兹理论的一个尤为可贵之处在于“它提供了区分稳定的政治结构与不稳定的政治结构的标准。这有助于解释缘何有的国际体系比别的国际体系更为持久的事实”。这提醒研究者注意“如果缺少结构上的先决条件,单靠行为是不能保证稳定的;而在特定情况下,甚至在行为上的先决条件并不理想之时,结构却能够带来稳定。”
将冷战视为“长久和平”的历史观也渗透到了加迪斯对现实国际关系问题的评论之中。两极格局抑制了欧洲内部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故而冷战对欧洲而言也是‘长和平’”。加迪斯在1990年曾提醒政治家不要忽视北约和华约曾起到的维持秩序的功能,甚至建议在修正二者对抗性功能的基础上继续保留这两大冷战联盟,进而防止欧洲不断复兴的民族主义再度成为脱缰之马。同时,统一后的新德国应在两大联盟中都占有一个席位,这样可以促进后两者的接触与合作。
批判与发展
任何理论都有其“阿喀琉斯之踵”,这构成对其进行反思、批判与发展的逻辑起点。
加迪斯首先反思了支撑结构现实主义的“科学观”。冷战的终结使整个国际关系学界陷入了极端尴尬的境地,华尔兹所预言的已经进入成熟稳定状态的两极格局在12年后就土崩瓦解了。在加迪斯看来,华尔兹预言失败的原因在于他本人几乎完全依据军事力量界定权力,坚持并过于将“体系”和“单元”彻底分隔开来。这使得他忽视了国家的行为与意志(这属于华尔兹所说的单元层次的现象)完全可以影响国际体系的结构,1985年之后苏联放弃与美国继续敌对的举动就说明了这一点。华尔兹所追求的“科学”其实恰恰正是牛顿时代的那种绝对主义的“硬科学”(hard science),相信通过将研究对象与其起源和周遭环境隔离开来便可以确保解释和预测的准确性,将现实中的事物完全抽象化——例如,假设存在绝对光滑的、不受摩擦力作用的物体,羽毛和石块可以同时着地。如果把这些都抽象掉以求建立理论,那我们也恰恰违反了人最基本的观察能力。这样获得的所谓“正确理论”也不过就是确定了的显而易见的东西。随着相对论等学说相继问世,即便是自然科学家们也已经抛弃了这种科学观,他们非常清楚地认识到随机性、偶然性、复杂性与规律性、普遍性、一致性并存于现实世界。坚持那些所谓“科学”方法的国际关系学家的预见力未必强于在他们看来不够科学的历史学家和小说家,乔治·奥威尔在《1984》中对极权主义所表现出的洞见便不可谓不准确和深刻。
“硬科学”同时强调理论范式间的“不可通约性”,即“我们不能通过添加内容来对理论加以完善。一个理论是一个合乎逻辑的、前后一贯的整体”。可是如果我们将自己界定为“理论的消费者”,认识到理论也不是建立在水蒸气的基础上,不同的理论为何不能实现互补呢?华尔兹主张的两极稳定论与一些学者坚持的单极稳定论的互补性就在于发现霸权的多层次性:军事领域的两极状态并不影响经济等领域内的单极格局。
乔治·凯南的观点深得加迪斯之心,人类要对自身的局限性保持警醒,而“历史,也只有历史才能给予这种提示”。当然,加迪斯并没有陷入幼稚的历史学科自恋情结中,也并非是要彻底铲除所谓“科学”的研究方法,而是呼吁在坚持前者的同时,不要遗忘了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叙事、类比、直觉、想象等一系列传统的方法。
需要指出的是,对“硬科学”的反思与批判是20世纪后半叶学术观念变迁的产物。知识社会学和科学发展史研究的进步使人们看到“科学家的旨趣、价值观、语言习惯,甚至其骄傲与贪欲,都是影响科学家研究自然界的因素”,由此曾经的“科学英雄从供奉他们的高台上跌了下来”。同时,这也是加迪斯本人的“社会观”与“政治观”的自然流露。在他看来,19世纪绝大部分的历史始终围绕这样一个观念展开,即人类可以将政治活动、政府行为乃至自身行为转化为某种“科学”,进而预测未来并决定他们自己。这种观念发端于当时的物理学界和生物学界,继而又影响到社会科学。它的确表达了某种追求进步的积极愿望,不过其自身所固有的将具体事物抽象化的倾向也忽视乃至压抑了人的主观能动性。苏联的统治形式恰恰是这种科学观在政治领域的一种表现形式。
第二,加迪斯发掘了“结构”的多样性。华尔兹的视角聚焦于无政府状态和权力分布,他的结构是“根据物质因素来定义的”。加迪斯在冷战后所倡导的“新冷战史研究”中更加注重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等“文化结构”产生的影响。在他看来,马克思列宁主义培养出的“极权浪漫主义”(authoritarian romanticism)决定了苏联的对外行为。例如,斯大林对列宁有关资本主义国家贪婪无度、剥削成性且永远不可能真正实现合作的教条深信不疑,这使得他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在战后的扩张行为促成了美国和西欧逐渐形成同盟关系。
加迪斯对结构现实主义进行反思的第三个方面体现在他对国际体系中能动性与差异性因素的重视。如果说华尔兹的理论真的考虑到什么能动性的话,那也只是“体系的能动性”,具体国家的外交行为以及重要历史人物的作用往往被忽略了。杜勒斯和艾森豪威尔之间的配合在稳定二战后动荡的世界格局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而里根和戈尔巴乔夫对冷战的终结也功不可没。
华尔兹对结构性的过分重视与他对相似性的极端强调密不可分。譬如,他认为在冷战中,美国的行为与苏联逐渐趋同,都保持了高额的军事投入,都进行对外干涉,都以一套强大的意识形态为之辩护。不过这种趋同也并非是单向性的,20世纪80年代末世界舞台上最引人注目的便是“苏联自身也逐渐倾向与极权主义划清界限”。与华尔兹和传统冷战史学主要强调大国的研究视角不同,加迪斯甚至注意到了国家内部的底层民众在国际关系中所起到的作用,例如二战后苏联红军在德国的暴行严重削弱了后来东德政权的合法性。直至20世纪50年代早期,美苏之间的竞争还没有影响到中东和拉美地区;在东欧地区,斯大林甚至也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当地势力的权力。
最后,与华尔兹不同,加迪斯的冷战研究还十分强调伦理评判。华尔兹一般很少进行道德评判,这也是绝大多数现实主义理论家的共同特点。与之相比,加迪斯的道德臧否显得直截了当。在他看来,“如果说这个糟糕的世纪给予过我们什么教训的话,那么便是不管出于什么理由,只要抛弃了道德对人类行为的约束,那将会产生何等骇人的结果”。
如果说《美国与冷战的起源,1941—1947》只是让苏联为冷战的爆发承担较大份额的责任的话,那么“新冷战史研究”则把苏联当成了引发冷战的罪魁祸首。加迪斯认为,斯大林迫切需要一种充斥怀疑和犬儒心态的社会环境才能维系自己的统治,因此“只要他统治苏联,冷战就不可避免”。更为可悲的是,斯大林还是一条死而不僵的百足之虫,他所建立的体制贻害于“去斯大林化”之后的苏联,限制了继任领导人们的头脑,使他们不知“其他的统治方式”。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加迪斯书写的“新冷战史”向我们展现了一幅具有历史渊源,多元主体、多种结构、多种因素和多种情愫在多个领域以多种方式交织互动的动态历史图景,这自然比华尔兹式的,只有少数(甚至只有两个)大国点缀其间,并彼此警惕地注视对方的历史画面生动得多。
加迪斯的某些观点在冷战后的国际关系学界得到了共鸣。与华尔兹同属现实主义理论阵营的威廉·沃尔弗斯认为,“世界政治学界的主流学者对于科学与历史学之间关系的看法,非常类似于布尔什维克对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关系的认识”。这已经严重影响了国际关系理论的进步,打破这种僵局的办法就是承认国际关系学是一门“历史的科学”(historical science),融合理论论证与对具体历史事件的解释,注重结合不同理论所包含的因果推理机制,以问题导向的研究取代具有排外性的范式与方法之争。
很明显,沃尔弗斯已放弃了华尔兹那种咄咄逼人的绝对主义决定论立场。以他为代表的一些学者试图将传统现实主义与华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结合起来,从而研究“结构如何影响行为体的行为选择,行为体又如何对结构的影响做出反应”,因此他们的学说也被称为“新古典现实主义”(neoclassical realism)。
当然,我们不应对华尔兹过分苛责(实际上加迪斯也并没有如此)。对国际社会中“互动”以及带有整体性特征的“环境”的强调恰恰是当今全球史观的着眼点。世界史观、全球史观的发展不也经历过抽象的历史哲学阶段吗?“新冷战史”恰恰是用具体的研究内容为其赋予了具体的时空形态和内容,进而剥落了华尔兹理论形而上学的外壳。
同时,我们也不应忽视加迪斯思想中的缺陷。他强调学术要有现实关怀,要对社会产生正面影响的倡议无可厚非,但也正暴露了他的“阿喀琉斯之踵”。冷战结束后原苏联集团的大量档案文献得以解密,恰恰在最需要尽量摆脱主观预设,充分利用上述新材料拓展冷战史研究的时候,加迪斯却越发偏执地强调美国和苏联间绝对的善恶之分,这绝不是严谨的学术态度,也违反了他“新冷战史研究”主张的一项重要原则:利用多国多方,尤其是美国以外的档案和文献资料。
余论
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解读这一学术案例。首先,在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学术界,传统的外交史研究由于视角狭窄和内容陈旧,已然沦为历史学领域中的“继子”。在这种情况下,新的理论自然成为外交史学界进行自我更新的重要“法宝”。不过,随着冷战的终结,大量档案资料得以解密开放,得到充分发展的外交史再度重视起自身的学科主体性。戈登·克雷格在1982年美国历史学家协会第97届年会上的发言充分表达了这一心态:“尽管与政治学家的合作能给外交史学家带来好处,但这些好处当然不应成为外交史学家的主要关注。外交史学家有太多的工作要做。”加迪斯恰恰成就于这一特殊时期,他对结构现实主义的借鉴与批判恰恰是美国外交史学发展历程的一个缩影。
其次,从学理逻辑而言,历史学一般习惯归纳式的经验研究,而这种方式并非完美无缺。因为“在长时段中‘实际’发挥作用的东西,以及在此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变化,并不能完全从我们所拥有的书面文献中推演出来。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们首先需要理论性框架和术语性根基”。同样,社会科学界推崇的基于理论的演绎研究法也并非完美无缺,因为“一个新的事实一旦被观察到,先前对同一类事实采用的说明方式便不能再用了”。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更为完善的研究必然要求人们“沿着实证科学和利用辩证思维对这些科学成果进行概括的途径去追求可以达到的相对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