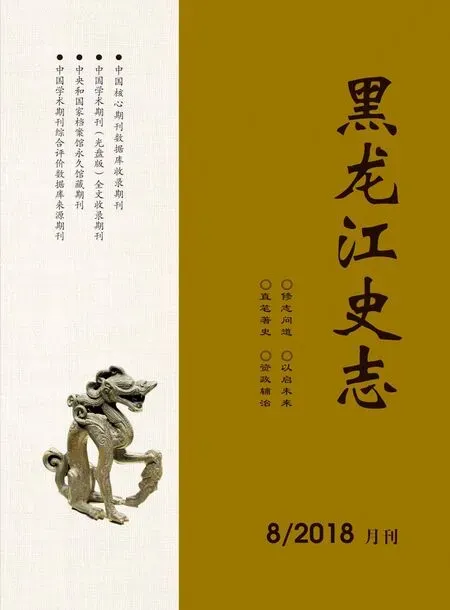北宋密州市舶司兴起原因考略
2018-11-19王可佳
王可佳
(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山东 青岛 266100)
成书于清乾隆年间的《胶州志》卷二记载:“唐高祖武德五年改高密郡为密州。六年省胶西入高密县,以县东鄙置板桥镇”。[1]板桥镇由此兴起,其建制虽晚,但发展迅速,在北宋时期成为北方第一大港,也是同时期与宁波、广州齐名的海上丝绸之路三大港口之一。对于板桥镇的研究,相关学者从港口、对外贸易、历史文化遗产、贡使往来等角度进行了关注,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2]但对于密州板桥镇市舶司的考察则显得较为欠缺,板桥镇市舶司作为同时期与广州、泉州、明州和杭州相媲美的北方唯一一个设立市舶司的港口,相较于广州、泉州、明州等传统对外贸易大港,密州港的存在时间及规模略逊于闽浙等路,但其在短时间内骤然兴起有着众多的原因,对于是否在板桥镇设立市舶司朝野上下也有不同的意见,板桥镇市舶司的设立反映了北宋王朝对于板桥镇的重视,是对其重要海外贸易港口和战略要地的认可,通过对板桥镇市舶司设立原因、过程和影响的分析,可以窥见其兴衰过程,同时也可以反映北宋海外贸易的兴盛。
一、设立市舶司的原因
宋朝海外贸易兴盛的一个重要表现和标志就是贸易港口的发展和繁荣,唐代对外贸易的主要港口有广州、交州、扬州、泉州等四大港。而宋代北自东京路,南至海南岛,港口以数十计,更为明显的是这些港口不再是零星的点状分布,而是受区域经济和贸易状况的影响,形成了广南、福建、两浙三个相对自成体系的区域,各个区域中的港口大小并存,主次分明,相互补充,形成多层次结构。[3]密州港作为北宋北方第一大港,其兴起有着众多的原因,既包括其自身地理区位优势、经济腹地的广阔、经济重心的南移、又包括海外贸易的发展和特殊的国际形势等因素,对于其设立的原因分述如下:
(一)北宋市舶制度逐渐成熟,为设立市舶司提供外部环境
市舶司是中国古代对外贸易管理机关。它始于唐代,在两宋时期得到发展和完善。学术界普遍认为它是现代海关的前身。市舶,是中国历史上中外贸易船舶的通称,始于汉武帝建元时(公元前140-135年)。在唐、宋、元三代,本国商人和外国商人之间用于海上开展贸易的船只,被称为“市舶”。经济文化高度繁荣的唐朝在造船技术和航海能力方面,较前朝而言,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市舶使,又称为押蕃舶使、结好使,是唐高宗时期在广州设立的主要掌握海外贸易及其他涉外事务的职位,主要由兼职的官吏来担任,从“环水而国以百数,则统于押蕃舶使”之说,便可看出该职位之重要性。
宋代的“市舶司”是由唐代的“市舶使”发展而来的,即由市舶官吏发展成了市舶机构,进而又建立了完善的市舶制度。宋神宗时期,王安石发动了旨在改善北宋当时积贫积弱局面的变法运动,《广州市舶条》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管理海外贸易的专门法规被订立,并正式推行。这一举措,意味着市舶制度开始朝着规范化和法典化方向迈进。同时,也说明这一时期海外贸易受到了政府足够的重视。
(二)优越的地理环境和广阔的经济腹地
板桥镇位于胶州湾附近,“胶州湾水域深阔,波平浪静,夏无酷暑,冬无严寒,不冻少淤,具备了天然良港的条件”。[4]密州地理位置优越,“东则二广、福建、淮、浙,西则京东、河北、河东三路”,[5]其所在地可以贯穿山东半岛的大部分,并与大沽河相连,同时濒临胶州湾,本身拥有海运和陆运的便利条件。山东自古物产丰富,经济发达,山东自唐代以来就是著名的丝绸产地,《新唐书·地理志》记载:青州的仙纹绫、密州和登州的赀布、兖州的镜花绫、曹州的绢锦和齐州的丝娟等。这些上乘的丝绸制品在高丽、渤海和日本大受欢迎,通过海路联运,板桥镇能把其腹地丰富的物资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运销海外各国。[6]板桥镇港口水深开阔,可以停靠大型的船舶,凭借自身的优势积极发展和高丽、日本,乃至东南亚各国的海外贸易,同时又是南北海上丝绸之路的中转站,随着南方丝织业的空前发展,“广南、福建、淮浙贾人,泛海贩物,或在板桥镇卸船,或自行“至京东、河北、河东等路贸易,”[7]“控东南海道,风飘信宿可至吴楚,”[8]板桥镇地理位置优越,东西海商络绎不绝。
(三)经济重心南移东倾,对外贸易中心向海上转移
中国古代对外贸易历史悠久且一直存在着两条路线,即学界所说的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这两条道路上的贸易往来在汉武帝时期已经明确被中国典籍所记载。《汉书·西域传》称,汉武帝派张骞凿空西域后,“白玉门关,阳关出西域有两道”,南道经南疆,越葱岭出大食、波斯,北道经北疆大宛、康居。[9]两条丝路上商属交织,相望于道,少者数十人,多者上百人。《汉书·地理志》对于海上丝绸之路也有明确记载,“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黄支之南,有已不程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10]这是以徐闻、合浦为主的南方海上丝绸之路,在同时期的山东半岛也开辟出了沿古琅琊港、胶州湾、鳌山湾、过成山头,到芝罘、过庙岛群岛、到朝鲜和日本的循海岸航行的东方海上丝绸之路,这条丝绸之路自开辟以来就一直被民间商船所沿用,在北宋时期又开辟出一条由胶东半岛横渡黄海直抵朝鲜半岛西海岸的航线,这条航道由“密州板桥镇启程,出胶州湾,东渡黄海,直航道朝鲜半岛的西海岸”。[11]在唐宋以前,相较于西北丝绸之路的繁盛现状,海上丝绸之路则[12]并没有像西北路上两道并进,络绎不绝的盛况。安史之乱后特别是唐宋鼎革之际,北方陆上丝绸之路被少数民族政权所阻断,北宋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逐渐南移东倾,经济重心的南移对海外贸易产生了重要影响,出口商品的供给地转移到离港口更近东南沿海及北方沿海的港口城市区,板桥镇成为沟通南北的重要中转站,将来自波斯、阿拉伯、东南亚的货物转运至高丽,浙江地带的货船也时常转运从海外进口的小商品和香料转运到板桥镇附近贩卖。[13]造船航海技术的进步也促进了海外贸易的繁荣,最迟在北宋时期,水密隔舱及导航技术指南针就已经广泛的应用于航海,如1117年成书的《萍洲可谈》中就明确记载了指南针技术的应用,其作者朱 曾经跟随他的父亲在广州生活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在广州期间记录了很多见闻,其中有一段说到航海使用的指南针:“海舶大者数百人,小者百余人,以巨商为纲首、副纲首、杂事......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或以十丈绳钩取海底泥嗅之,便知所至”。[14]政府十分重视海外贸易的发展,对外贸易的重心完全转移到沿海港口,北方以板桥镇为主,南方则以广州、宁波、泉州为主,西北陆上丝绸之路独占鳌头的局面一去不复返。这一转变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管理对外贸易及进口商品营销的整套机构都是根据海上贸易的需要制定的,特别是市舶司和市舶条例的制定。二是海上贸易的收入已经具有一定的财政意义。三是海路成为中国与海外各国交往的主要通道。两宋时期,与中国交往比较频繁的朝鲜、日本、阿拉伯、印度东南亚各国等,人员往来,对外商贸都是通过走海路的形式入境。四是出口产品的主要产地转向沿海地区。[15]
(四)外部形势下登、莱港的角色转变为板桥镇的兴起提供了十分有利的契机
密州市舶司的设置与当时北宋的外部形势密切相关。宋神宗即位后,面对积贫积弱、屈辱于契丹、西夏之局,任用王安石进行变法,通过变法,内则富国强兵,外则积极打开外交局面,以摆脱辽夏结盟而给宋朝造成的被动局面,制定“结高丽起兵,欲图大辽”,选择联合高丽图谋辽国的政策。在这样的形势下,为了满足北宋政府开展与高丽交往的需要,北宋将密州板桥镇改为与高丽等外国通商的北方商港。
北宋都汴京(今河南开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偏向东南,“天下根本仰给东南”、“天下根本在河北”。[16]前者指东南为经济重心和国家财赋重心,后者河北为军事重心,事关国家安全。北宋立国之初就面临着与北方多个少数民族政权并立的国际形势,登州港地处胶东半岛东北部,与朝鲜半岛隔海相望,自唐代以来就是东北亚中日朝三国往来的重要港口,北宋初期仍是宋与高丽往来的主要港口。“高丽自国初皆自登州来朝”,但随着宋辽关系的紧张,登州港口的性质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成为北方的海防重地。北宋政府为了保证登州的安全和稳定,杜绝辽国奸细的进入,于熙宁七年下令封闭登州港,严禁商人前往贸易,即如《胶澳志》所记载:“辽金方强,登州海口非宋人所得利用,宋都卞州海外往来以胶澳为最捷”,[17]登州港的封闭,使贸易中心南移到密州板桥镇,密州的贸易也因此而兴盛。南宋时,密州为金所占领,南宋政府更严禁商船前往,登州曾是唐及宋初与高丽、日本联系的重要港口,密州也曾是宋初东京、河北等路的出海口,由于政治局势的影响而在短暂的辉煌之后都很快的陨落。
(五)加强对外贸易管理的需要
板桥镇,“由唐至今,商业极盛”。[18]早在元丰朝之前,属于京东路的密州板桥镇就已经成为中外海商汇聚的大口岸。除了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的商船停泊外,还有从大食国、南亚诸国辗转来贸易的蕃舶;另外,江南一些大口岸的海商也多来此处贸易。由于板桥镇没有设立市舶司,来板桥镇贸易的成本相对较低。由于海外贸易获利颇丰,密州和邻近地区的商人、富户以及其他阶层之人纷纷加入高丽、日本及其他海外诸国的贸易。《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四九记载:“元丰七年东十月癸未,密州商人平简为三班差使,以往高丽通国信也。”这位平简多次往来于密州板桥镇与高丽之间,获利颇丰。平简与高丽通商时,还为两国政府间传递信息,联络感情,消除误会。因此,平简被北宋官府破格授予“三班差使”头衔。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假借与高丽通商,却违禁与辽国做买卖的海上王应升。据苏轼《乞紧商旅过外国状》所载:“有商客王应升等,冒请往高丽国公凭,却发船入大辽国买卖,寻捉到王应升等二十人及船中行货。”
(六)地方官员的大力推动
密州板桥镇市舶司的建立离不开地方官员的大力推动,其中知密州范锷的功劳最大。他和当年力主在泉州设置市舶司的泉州知州陈 极其相似。元丰六年(1083)之前在范锷知密州任上就提出:“板桥濒海,东则二广、福建、淮、浙,西则京东、河北、河东三路,商贾所聚,海舶之利颛于富家大姓。宜即本州置市舶司,板桥镇置抽解务。[19]”都转运使吴居厚担心设立密州市舶司会“牵制明、广州己成之法”,又认为影响国防安全“登莱东北密迩辽人,虽立透漏法,势自不可拘栏”等,否决了范锷的建议。
元三年(1088)范锷联合其他官员再度上书,请置密州市舶司。范锷等人认为:其一,板桥镇是商贾齐聚之地,“买卖极为繁盛”,商品经济发达,南北商人往来频繁,北宋政府为了更好地控制当地贸易和税务,以从中获取巨额利润,来扩充财政实力;其二,板桥地区辐射辽阔,腹地广阔,从地理位置上而言,位于板桥地区北部的京东、河北以及京冀地区自古以来就因物产丰富而远近闻名,有充足的“丝绵、缣帛”与“藩商”交换贸易,这就为板桥镇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货源;第三,在板桥镇设置之前,商人在板桥地区从事对外贸易需要承担刑狱风险,贸易往来日趋合法化,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商人来此进行商贸活动的积极性;第四,北宋朝廷从还海外进口奢侈品,供朝廷以及统治阶级享用,“每岁市舶抽买物货及诸藩珍宝应上供者,既无数千里道途辇运之费,又无江淮风水沉溺之虞”[20],这说的是,因板桥镇的地理位置正处于南北、陆海中转的位置,这就为北宋政府进口奢侈品提供了交通保障,经市舶司所在港口运送到京城,可以节约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也有利于节约时间。另外,时任户部尚书的李常,在密州市舶司的设置过程中起了很大作用,“泉、密市舶,皆李常建请”[21]。
二、市舶司的地位和作用
北宋在全国共设有八处市舶司,其中密州板桥镇市舶司是唯一一处设置在北方的,这必然使板桥镇成为北方最大的贸易港口。市舶司的的设立对于北宋王朝的贸易、军事和文化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推动了板桥镇贸易的繁荣发展
板桥镇处在胶州湾西南角,海产和物产均较为丰富,贸易活动频繁,自北宋朝廷在设置市舶司,这里万商云集,海运贸易进入空前繁荣的阶段。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09中写过:“自来广南、福建、淮浙商旅,乘海船贩到香药诸杂税物,乃至京东、河北、河东等路商客船运见钱,丝、锦、续、绢,往来贸易。”另外,当时契丹几乎控制了半个渤海海域,今山东、山西、河北、河南等地的货物外运必须经由板桥镇,南方和海外的货物要向北方的市场,也必须以板桥镇作为中转地。板桥镇设置市舶司之后,主要负责山东半岛的对外贸易,近到高丽、日本,远到中东、近东,胶州湾海面上来自各地的船只骤然增多。许多来自波斯、印度、阿拉伯及周边地区的商人,先到达我国南方的港口然后转运到板桥镇。
(二)限制走私贸易,促进对外贸易更加规范化
板桥镇自古以来就发挥着交通枢纽的作用,一直是国内对外交往、开展贸易活动和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板桥镇作为北方唯一的沿海口岸,与高丽、日本等的海外贸易尤为兴盛,加之唐宋以后“北人尤重南货”等因素使当时的走私贸易泛滥。板桥镇市舶司的功能类似于今天的海关:第一,严格管理外来商人和商船,外雇的商船在达到板桥镇口岸后,必须按照程序向市舶司汇报,并接受例行检查,同时要缴纳关税,才可进入中国内陆地区;第二,凡是本国商船对外贸易的要事先向市舶报告,获得公凭后,才可出海;第三,凡是朝廷明文规定禁止在国内市场流通和买卖的货物,全部由市舶司统一收购和收缴关税后上交朝廷。这样规范化的管理,极大地限制了走私贸易,使北宋与高丽、日本等国的海上贸易活动更加规范化地有序发展。
(三)推动了北宋与高丽两国的关系
苏轼曾有一首诗:“檐楹飞舞垣墙外,桑拓萧条斤斧余。尽赐昆邪作奴婢,不知偿得此人无。”描写的是北宋时期朝廷了为了迎接来自高丽的商人而设置的高丽亭馆。北宋神宗熙宁、元丰年间,朝廷为了抵御来自辽、契丹等国的骚扰,与高丽建立了友好的往来关系。随着两国交往的日益频繁,两国的人员往来也日益增多。两国交往的鼎盛时期,也是密州板桥镇发展的全盛时期。密州板桥镇作为北宋对外交往和交流的重要窗口,再次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据《宋史·高丽传》:“元丰六年,高丽王徽卒。讣闻,神宗诏明州修浮屠供一月,遣杨景略、王舜封祭奠,钱勰、宋环吊慰。”
三、结语
板桥镇港口的出现,逐渐取代了登、莱,成为北宋在北方唯一的港口,是中国古代南北往来和对外贸易的重要窗口,留下了丰富的海洋文化遗产。宋代密州板桥镇市舶的建立是这一时期海运贸易繁荣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这一时期市舶制度发展和山东半岛海上贸易繁荣的必然要求,更是人类海洋文明的产物。宋代在密州设置市舶司,是受到当时国家政治、军事、经济诸多方面的重要影响,是古代山东半岛历史记载最早的海关机构,尽管存在时间较短,但它存在的历史价值和意义确是不可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