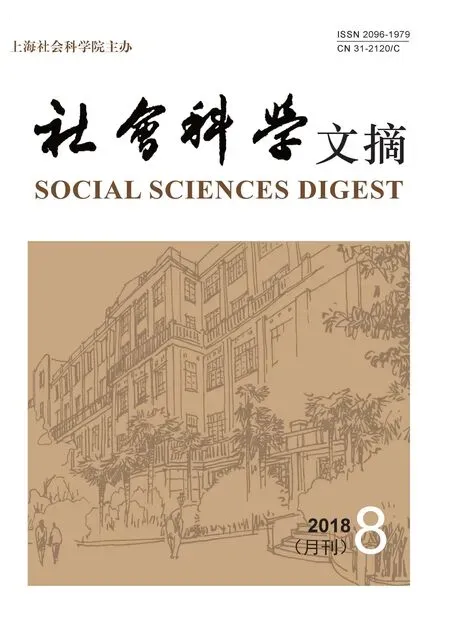“思无邪”作为《诗经》学话语及其意义转换
2018-11-18
孔子曾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此后“思无邪”就成了《诗经》学的重要命题。但当历代学者不断追求这一命题的本旨,并意欲给出一种合理解释时,他们可能在立场和认知上犯了错,即忽视了该命题之内涵在历史发展中的复杂变化。孔子这样说当然有自己的界定,可战国中期以前,孔子后学对“思无邪”之“思”有一个误解,促成了汉代经学家的新解释,奠定了人们对这一命题最基本的认知;宋代以降,质疑汉唐旧说者渐多,以朱熹为代表的学者为了消除旧解与《诗经》学发展的紧张对立状态,再一次完成了对这一《诗经》学话语的意义转换。总之,历史不断地层累,而当下对这一命题的所有诠释,几乎都是不同旧说的余绪。
孔子以“思无邪”概言《诗三百》之本意
《诗三百》各篇若使用重章迭句,处于各章相同功能位置的语汇,其意指常常相同或相近,至少往往可以贯通。《》诗采取重章迭句之表达方式,其第四章之“无邪”,与前数章之“无疆”“无期”“无斁”处于相同的功能位置,其意指与前三者一致,即同样是形容空间之无边际,便也毫不奇怪。于省吾尝考证从吾从牙之古字可通,谓《仪礼·聘礼》“宾进,讶受几于筵前”,郑注谓“今文‘讶’为‘梧’”,《山海经·海内北经》之“驺吾”,《史记·滑稽列传》作“驺牙”,《公羊传》文公二年(前625)“战于彭衙”,《释文》谓“衙,……本或作‘牙’”,等等,均可为证。而“圄”与“圉”古同用。《说文·㚔部》云:“圉,囹圉,所以拘辠人,从㚔从囗。一曰:圉,垂也。”段注云:“他书作‘囹圄’者,同音相叚也。”然则,“无邪”即“无圉”,犹言“无边”,指牧马之繁多。此说甚是。以上解读的合理性,回到《》诗原文,可以看得十分清楚。《》诗自身实可证明“无邪”本指无边际、无穷尽。
孔子引“思无邪”一语概括《诗三百》,当是指三百篇之蕴藏既富且广,无所不包,是就其内容而言的。
我们先看看“思无邪”之“思”。上海博物馆所藏战国楚竹书《诗论》,通常也被称为《孔子诗论》,是现今所知与《论语》孔子论说《诗经》关系最明确的文献。在考辨孔子以“思无邪”论《诗》时,《诗论》提供给我们的信息是多方面的,首先就涉及孔子对“思”字的理解。传世《毛诗·周南·汉广》云:“南有乔木,不可休(息)〔思〕。……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乘泭以求济)思。”《诗论》第四章论曰:“□□□□□,可(得),不(攻)不可能,不亦(智)亘(恒)(乎)?”又曰:“《(汉广)》之(智),则(智)不可(得)也。”这些评论代表了孔子对《汉广》的认知。而由这些评论,可以断定孔子并不把该诗中的“思”字理解为实词,否则无法解释他给出的《汉广》“不可(得),不(攻)不可能”的断语。实际上,传世《中庸》第十六章记子曰:“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诗》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显,诚之不可掩,如此夫。”孔子所引“神之格思”诸语,出自《诗经·大雅·抑》篇,他的相关论说,也表明他并未把作为语助词的“思”理解为实词——比如“思念”“思虑”“思考”之“思”。
其次,更重要的是,《诗论》评析50余首作品或其部分文字,几乎比后世所有旧说都更加契合对象的本旨——即便涉及较为明显的形而上的发挥。鉴于这一事实,认为孔子予取予求、断章取义地拿“思无邪”来概括《诗三百》就不太合理。尤其不可忽视的是,《诗论》的核心内容可以证明,孔子以“思无邪”概言《诗三百》,乃是指三百篇之蕴藏既富且广、无所不包。《诗论》第一章云:“□□□□□□孔子曰:《訔(诗)》,丌(其)猷(犹)塝门与?戋(残)民而(逸)之,丌(其)甬(用)心也(将)可(何)女(如)?曰:《邦风》氏(是)已。民之又(有)(戚患)也,上下之不和者,丌(其)甬(用)心也(将)可(何)女(如)?曰:□□□□□□氏(是)已。又(有)城(成)工(功)者可(何)女(如)?曰:《讼(颂)》氏(是)已。”“塝门”即广大之门。孔子是以城门之广纳人物,类比《诗》之蕴蓄宏富,故他接下来便说《诗三百》各部分篇什因应着政教的种种情态。《诗论》第十章尝论《颂》《大雅》《小雅》以及《邦风》,这里只看其中论《邦风》者,所谓:“《邦风》,丌(其)内(纳)勿(物)也尃(博),(观)人谷(俗)安(焉),大(验)材(在)安(焉)。丌(其)言(文),丌(其)圣(声)善。”这一论说,几乎可作孔子以“思无邪”概言《诗三百》的注脚。此语虽只是就《国风》而言的,即是说《国风》之诗所含之物事至多至广,可由以观民俗,可由以验政教,但移之以论《诗三百》之整体,也完全合理。《诗论》第一章谓,残民而使之逃逸,民之用心由《邦风》可知;民有忧患,上下不和,其用心由《小雅》可知;为政者功成德盛,则颂声起,由《颂》诗可知;同样的道理可以适用于《大雅》,惜乎相关论析缺轶。这些与称《邦风》纳物博、大验在,同样可以贯通。这一切,均可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第一次意义置换之启基:关于“思无邪”之“思”
在孔子弟子至子思时代,“思无邪”的意义发生了一次深刻的转换:“思”字实词化,即被理解为“思想”“思虑”之“思”,对《》诗“思无疆”“思无期”“思无邪”的接受因此发生了通盘的变化。
第一次意义置换之完成:关于“思无邪”
基于“思无邪”之“思”被理解为实词(“神思”之“思”),“思无邪”之“邪”差不多同时被理解成了“邪正”之“邪”。毫无疑问,这牵动了对《诗经》与《诗经》学两方面的认知。
孔子开启了《诗三百》经典化(即转化为儒家经典)的旅程,战国时期,数代儒家学者不断加以诠释或再诠释,《诗》最终被赋予了系统的儒学价值,成了儒家重要经典;而至汉初,这一进程又从民间学术层面跃升至官学层面,《诗经》被立在学官,《诗》的经典化最终完成。由此,对传统《诗》学话语的认知、阐释或者再阐释,都必然地在这一学说体系的基础上进行。
总之,包咸、郑玄以下,绝大多数学者将“思”解释为动词性的思考或者名词性的思想,将“邪”解释为“正邪”之“邪”,将“思无邪”解为诗思之正。其所谓正,自然是基于儒家政教规范而言的。此时,关于《诗三百》的所有诠释都可以落实“思无邪”的取向,这一取向因此就意味着三百篇或者“诗人”全都是向世间提供儒学价值的渊薮(并非本然如此,这只是《诗》经典化的结果)。我们几乎可以依据这一取向及其嬗变,来区隔和定义《诗经》学发展的形态模式——就是说,这一取向凸显了汉唐《诗经》学的特质。
之所以使用“《诗经》学形态模式”这一表述,而不偏倚于历史时段,是因为某一历史时段成熟的形态模式往往不会在后来的历史时段中消失,会反反复复发挥其影响作用,即使新的形态模式正在生成甚或已经成熟。作为一种形态模式的“汉唐《诗经》学”就是如此,它至今依然会在某些历史层面上浮现。比如北宋谢良佐(1050—1103)称:“君子之于《诗》,非徒诵其言,又将以考其情性;非徒以考其情性,又将以考先王之泽。……思其危难以风焉,不过曰‘苟无饥渴’而已(案指《王风·君子于役》)。若夫言天下之事,美盛德之形容,固不待言而可知也。其与忧愁思虑之作,孰能优游不迫也?孔子所以有取焉。作《诗》者如此,读《诗》者其可以邪心读之乎!”略早于朱熹(1130—1200)的学者张戒尝云:“孔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世儒解释终不了。余尝观古今诗人,然后知斯言良有以也。……其正少,其邪多。孔子删诗,取其思无邪者而已。自建安七子、六朝、有唐及近世诸人,思无邪者,惟陶渊明、杜子美耳,余皆不免落邪思也。”吕祖谦(1137—1181)说得更加简洁:“仲尼谓《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诗人以无邪之思作之,学者亦以无邪之思观之,闵惜惩创之意,隐然自见于言外矣。”这些论说虽皆出于宋人,却都呈现着汉唐《诗经》学形态模式的特质。而张戒的说法,再次明确了汉唐《诗》学形态模式的逻辑前提,是孔子删诗或编《诗》。
第二次意义置换以及《诗》学内在冲突之消解
汉唐《诗经》学形态模式遭遇的严峻挑战,来自对文本自身价值的认同。在文本的力量被释放后,汉唐《诗经》学的整个体系便出现了塌陷。所以朱熹提出,变风“多是淫乱之诗”,“今但去读看,便自有那轻薄底意思在了”。《诗序》解《鄘风·桑中》云:“《桑中》,刺奔也。”朱子则说:“此正文中无戒意,只是直述他淫乱事尔。”总之,朱熹认为,就三百篇之本文而言,“思有邪”者正多。他指出:“若以为作诗者‘思无邪’,则《桑中》、《溱洧》之诗,果无邪耶?……如《桑中》、《溱洧》之类,皆是淫奔之人所作,非诗人作此以讽刺其人也。”又说:“若言作诗者‘思无邪’,则其间有邪底多。”朱熹反对《诗大序》“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说法,称:“中间许多不正诗,如何会止乎礼义?”
在汉唐《诗经》学形态模式成熟以后,朱熹《诗经》学说从各个方面看都称得上是与之并列的新的形态模式,它绝对不是宋代《诗经》学的全部,却足可命名为“宋代《诗经》学形态模式”。在这一学说体系面前,汉唐儒者以诗人、诗思之正定义的“思无邪”这一《诗》学命题已经不能成立,它跟这一新体系发生了严重冲突。在传统《诗经》学发展的整个过程中,孔子的论说都受到高度的尊重。既然孔子以“思无邪”概言《诗三百》,那么这一命题就不会被朱熹彻底抛弃,再度进行意义置换于是成了历史的必然。
朱熹认为,孔子以“思无邪”概言《诗三百》,不是说“作诗之人所思皆无邪”,而是说《诗》之“用”归于使人“无邪”,是《诗》之“立教如此”,是读《诗》之“功用”如此。朱熹认定《邶风·静女》《鄘风·桑中》《王风·大车》《郑风·将仲子》等几十首诗歌为“淫诗”,却没有像王柏(1197—1274)那样力主把这些诗歌逐出《诗经》,他认为孔子将这些诗歌编入三百零五篇,目的是使读者“即其辞而玩其理以养心”(《诗集传·关雎》),“淫诗”虽有邪志而无妨,“读三百篇诗,善为可法,恶为可戒,故使人‘思无邪’也”。
这一《诗经》学形态模式凸显了《诗》学立教者的存在——很明显,他就是通常所说删诗、编《诗》的孔子。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回到儒家《诗经》学最原初的立意来重新定义“思无邪”。太史公谓:“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史记·孔子世家》)朱子则说得更加细致:“昔周盛时,上自郊庙朝廷,而下达于乡党闾巷,其言粹然无不出于正者。……是以其(孔子)政虽不足以行于一时,而其教实被于万世。是则诗之所以为教者然也。”(《诗集传序》)在《诗经》学的这一种形态模式中,阅读主体必须发挥其积极性和主导性——由于《诗三百》中存在“淫诗”,由于其中思有邪者正多,坚持“即其辞而玩其理以养心”的朱熹必然会强化阅读主体的自觉批判,缺少这一点,致力于使读者“思无邪”的立教期待就会落空。
朱子《诗》学代表的这种新的《诗经》学形态模式虽然重新给出了一些定义和设计,目的则仍在实现《诗经》所负载的儒学价值(毫无疑问,儒学价值本身也有承继前人和重新解释的问题)。
朱子《诗》学代表的这种新的形态模式可以说是儒学内部“拨乱反正”的结果。不过,这一体系既释放了文本,又释放了阅读主体,最终会导致一切经学附会的崩塌,而走向现代《诗经》学形态模式的建构。这恐怕是朱子本人未尝料及的更伟大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