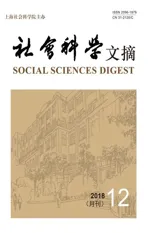从物化到数字化: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异化理论
2018-11-17
当智能技术、大数据、云存储、区块链技术正在日益改变我们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周围的生活节奏变得越来越快,这种超级加速度带来的不仅仅是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和智能进步,也让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活生生的人感到无所适从的眩晕感。当加速度超过了我们忍受力的时候,我们不仅被绑定在一个不知道开往何方的高速的装置之上,也让我们的心灵承受身体上的冲击和震撼。我们现在所面对的异化,是一个全新的异化形式,即数字异化。我们必须回顾一下思想史上关于物化的论述,才能更清晰地看见今天数字化技术带来的新异化形式,对于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一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首先给异化概念给出了一个描述性的判断:“按照国民经济学的规律,工人在他的对象中的异化表现在:工人生产的越多,他能够消费的越少,他创造的价值越多,他自己越没有价值、越低贱,工人的产品越完美,工人自己越畸形,工人创造的对象越文明,工人自己越野蛮,劳动越有力量,工人越武力,劳动越机巧,工人越愚蠢,越成为自然界的奴隶。”
在这段文字之前,马克思曾说过这样一个问题:“工人对自己的劳动的产品的关系就是对一个异己的对象的关系。”怎么理解这句话?简单来说,一个工人,在马克思看来,在其劳动过程中,将自己的一部分生命力转化为一个外在的产品,工人付出的越多,所创造出来的,作为其对象出现的产品就越强大。实际上,马克思在这里使用的词,并不是物化,而是对象化,对象化意味着,一旦这张木桌作为一个产品出现,它就不是一个纯粹的自然物质,而是在人的实践活动中,与人建立了某种关联,人的活动将生命力凝结在这张木桌之中,木桌一旦作为产品出现,它成为与人相对立的凝结着生命力的物质,是工匠生命的对象化和外化。
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节中马克思提到的“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它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活动”的意义。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虽然将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的头尾倒置的状况扭转了过来,但是,费尔巴哈所理解的物,或者他所感性直观到的物,是一种与人的实践活动完全无关的物。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认为,所出现的物或者说被生产出来的产品,是对象性活动的产物,对象性活动产生的不是自然物,而是生命的外化和转移,让居于我们内部的生命可以外化为一个可以被直观的对象,即对象化。
这样,我们可以理解,异化其实并不发生在对象化或外化过程中。因为对象化和外化是自我意识或人类实践活动的升华和辩证发展的必经阶段,没有那个对象化的产物,人实际上无法实现生命运动的回归,也无法达到圆满。纯粹停留在朴素意识阶段上的意识,或者完全不通过实践活动来外化自己生命力的人,只能在低层次上徘徊,无法实现真正的发展,只有通过对象化,即将意识或生命力外化到一个外在的具体对象上,这种循环才能得到实现。那么,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究竟是如何发生的?马克思指向的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在这里必须说明的是,19世纪40年代的马克思还没有深入地阅读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著作,还无法从劳动价值论的高度来具体审视资本主义的运行模式,也尚未提出建立在剩余价值基础上的剥削问题。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实际上明确指出了异化的问题所在:“对工人来说,劳动的外在性表现在:这种劳动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别人,劳动不属于他,他在劳动中也不属于他自己,而是属于别人的。”这个形而上学逻辑的关键在于,原本应该通过对象化产品回归自身的循环运动,在雇佣劳动体制下发生了中断,由于工人生产出来的产品并不属于他自己,而是属于资本家,这样,原本应该回归工人的生命力,却流向了资本家,工人的外化的生命力丧失了,原本应该回归的对象化的生命,在雇佣劳动体制下,反而变成了异己的力量,反过来凌驾在工人的活动之上。原本应该受到工人实践活动支配的对象化力量,现在反过来变成了资本家的力量,成为主宰和奴役工人的力量,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工人的劳动变成了异化劳动,而其生产出来的产品也凌驾在他之上,成为异化的产品。这样,工人无法完成生命的辩证循环,工人也离圆满的健全的人的类本质越来越远,工人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上的蝼蚁,而产品中所凝结的工人的生命力被资本家所占有,于是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异化,一部分人成为另一部分人的统治者和压迫者。
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仍然是十分清楚的,即人的生产实践活动本身不是异化的根源,相反,生产实践是人的类本质实现的必要条件。问题真正的症结在于市民社会,这种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具有不平等关系的社会结构造成了外在化的对象与生命活动的主体的分离,让人类的生命循环的活动无法完成,也无法最终实现人类的类本质,而最终要打破这种异化的状况,只有革命化的实践,即摧毁市民社会的体制,才具有可能性。
二
卢卡奇在他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中,也谈到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异化。不过,他所使用的异化并不是马克思使用的异化劳动,而是物化。与之相对立,正如卢卡奇自己所强调的那样,他是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得出了物化的逻辑。卢卡奇指出:“商品结构的本质已经被多次强调指出过。它的基础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获得物的性质,并从而获得了一种‘幽灵般的对象性’,这种对象性以其严格的、仿佛十全十美的合理的自律性掩盖着它的基本本质,即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所有痕迹。”
这是卢卡奇第一次对“物化”问题的描述。卢卡奇关注的问题与早期马克思关注的问题有一点区别,马克思关注的是作为对象化劳动产品的丧失,由于产品被资本家所占有,由于不平等的社会关系,让对象化劳动无法完成生命的循环,从而沦为异化劳动,一种与自己相疏离,无法完成生命的辩证运动的劳动。所以,马克思批判的对象是这种“疏离的”对象化产品,一种永远不能回归自身生命的产品。显然,卢卡奇的物化批判的锋芒指向的不是马克思的由于市民社会的雇佣劳动关系导致的产品的疏离,而是对象化,即被黑格尔和马克思同时视为自我意识和生命运动不可或缺环节的对象化过程。在卢卡奇看来,人与人的关系一旦表征为物的关系,用一个物的形式来中介人与人关系,已经意味着人的生命的丧失,当生命被凝结在外在于我们自身的物之中的时候,我们已经被物化为一种僵死的“幽灵般的对象性”之中了。
不过,我们还需要注意卢卡奇物化思想的另一个侧面,即卢卡奇批判的是一种关系,即掩盖人与人之间的“合理的自律性”关系。“合理的”即理性的,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现代世界的一切活动,都需要放在“合理性”这个尺度之下来衡量。而“自律性”在德文中的本意是事物自身固有的规律性,所有的对象在“自律性”之下表现出一种类似于自然规律的过程,也就是说,这种合乎理性规律的“自律性”,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自然规律,而是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下产生的,类似于自然规律的东西。而在卢卡奇看来,这种类似自然规律的“第二自然”成为统治,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抽象成为统治的秘密,而这个秘密的核心,就是抽象为关系的物(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背景下,这个物具体表现为商品与货币)成为了凌驾在一切社会关系之上的统治。在这个意义上,原先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直接关系被物的关系中介了,物成为一切关系的准绳,成为可计算化的程序的尺度。
这样,卢卡奇的物化,并不是人被具体的物所统治,而是被类似于商品和货币之类的带有衡量尺度的抽象物的统治着,而这种抽象物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显然,这种抽象物绝不是自然物,而是一个可度量的物,正是这个可度量的物让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交换成为可能。不过,卢卡奇的问题在于,他并没有像《资本论》中的马克思一样,停留在纯粹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之上。他的将物化的原则推衍到整个社会范围之中。也就是说,在早期马克思那里,仅仅只有工人阶级才具有的异化劳动,被卢卡奇无情地推向了整个社会,所有人,包括资本家和统治者在内,都处在这个巨大的物化关系之中。这意味着,卢卡奇在根本上关心的不是资本家对工人阶级的剥削,而是物化关系将所有人都转化为同一种主体——即物化主体,这种物化主体的本质,就是根据冷冰冰的算计来思考问题。
三
在进入到对数字化时代的异化理论讨论之前,我们可以先做出几个结论:
1.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是基于生命的疏离,即对象化活动与生命本身的疏离。这种疏离关系,是由于资本主义不平等的私有财产关系造成的,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生命的褫夺,造成了无产阶级的赤贫,让他们无法实现生命的辩证运动。由于早期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批判基于的是市民社会中不平等的关系,以及资产阶级对工人的对象化产品的剥夺,我们可以将这种异化批判称之为生产关系批判。
2.卢卡奇的物化批判的核心并不是具体的物,而是成为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中介的抽象物,在商品社会环境下,这种抽象物最典型的代表就是货币,而商品拜物教和货币拜物教的根基都是这种抽象物成为凌驾在一切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之上的统治性的力量。这样,对于卢卡奇等人来说,主要的问题不是阶级斗争,推翻某个阶级的霸权和统治,而是反抗这样一个看不见的抽象的建构和机制,让整个巨大的物的机器停止运转,唯有在这个巨大机制不再起作用,失效那一刻,人类才能返回到那个已经被忘却的曾经的故土。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将这种批判路径称之为生产力批判。
这是两条不同的异化批判路径,前者的革命性需要是改变现有的资本主义生产前提下的社会关系,将不平等的关系改造为平等而具有共同体精神的社会形式——即共产主义社会。而后者将挞伐的对象指向了现代性本身,认为造成当代精神悲剧、灵韵丧失的根源在于现代性机制,这个机制在冷冰冰的计算理性的前提下,将所有人和物都放在一个共同的平台上来衡量,以往具有独特性的生命和物质丧失了,每一个生命、每一个物体都成为被抽象的物(货币、景观、符号、装置等)中介而丧失了灵魂的存在。
这样,对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异化批判,实际上也存在着生产关系批判和生产力批判两条不同的路径,我们也可以称之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存在论批判。我们可以分别从这两种不同的批判路径来审视一下,我们在数字化时代的生存方式。
我们首先来看看后一种批判,即存在论意义上的异化批判。如果我们将卢卡奇的物化批判逻辑向前推进,我们实际上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今天成为我们社会关系,以及我们与自然之间关系的中介,不再是那个抽象化的物——商品或货币,而是更为基础的东西,即“一般数据”。简言之,今天的数字资本主义,已经创造了一个完全由一般数据组成的界面,在这个界面中实现的交换和交流,完全是由数字算法得到的一个对象包来实现的。那么,今天的在地铁上,当我忘记了带我自己的智能手机出门,也没有任何可以联网的智能设备的时候,我会发现自己处于一个很尴尬的境地。地铁上到处都是人,但是每一个个体的目光都盯着自己手机的屏幕,在那一刻,尽管我周围全是人,但是我感到十分孤独,因为我不能与这些正在享受手机屏幕上的乐趣的个体构成任何有效的社会关系,他们的身体虽然处在地铁之内,但是他们的存在却是在智能手机背后的那个巨大的赛博空间里。
与之相反,在大数据时代,更能产生实际效果的交流,是由数据上的虚体对虚体的交流,这些交流的结果本身也成为了一个庞大的数据。所以,一般数据构成了一个庞大的机制,这个庞大的机制已经将每一个参与到智能界面上活动的个体都换算成了一串字符,并在云计算中对其进行分类和存储。按照这个逻辑,今天的数字化时代,比卢卡奇时代面临着更深刻的异化,在卢卡奇时代,货币和商品的逻辑还不具有最强大的建构力量,它只能充当一种中介或尺度。而在今天,卢卡奇意义上的物化的异化,毫无疑问已经变成为了数字化的异化,因为数字化的异化不仅意味着我们所有的个体和个体的交往,已经完全被一般数据所穿透,是一种被数据中介化的存在,这意味着,除非我们被数据化,否则我们将丧失存在的意义,就如同在地铁上忘了带智能手机的乘客一样。
在这样的数字化时代下,我们肯定会感觉到我们被异化了。然而,面对这种海量级的一般数据的统治和支配,人们能采用的策略是远离和撤退。具体到今天的现实,我们是否拥有《头号玩家》中的解药?显然没有,我们不可能对人们说,我要放弃我的微信号,借此来逃脱数字异化的控制。退出微信,不再使用智能手机,真的是数字化时代超越异化的道路吗?显然不是。所以,在马克思看来,真正的问题不是在于技术,即便在今天,一般数据和数字化的中介,并不一定成为异化的根源,而最基本的根源,仍然需要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即生产关系批判)中来寻找。也就是说,一般数据的来源,比如我们在百度上的搜索记录,在淘宝上的购买记录,实际上都是我们这些最普通的用户生产出来的,这些平常在我们看来似乎无用的东西,实际上在经过上千万次数据采集之后,会变成非常有用的东西,那么这些数据实际上是我们普通用户数字劳动的结果,但是,这些数据却被某些机构垄断了,成为了他们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牟利的工具。由于这种数据垄断,以致于这些数据与他们的生产者之间产生了疏离关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回到了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数据与具体的生产者割裂了,形成了异化。
在这个意义上,其产生的进展和产品需要返回到构成数据共同体的集体本身,才能完成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提到的生命的辩证循环运动,这些数据本身就属于全人类的财富,任何团体和个人对这些数据的占有,势必都是对这种生命循环的破坏,会造成异化。这样,我们似乎看到了一条真正克服异化的道路——一般数据的共享,让数据成为构筑未来人类共同体的根基,而不是拒绝数据,拒绝数字化。因此,对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结论是,我们需要进行的是政治经济学批判,改造不平等的生产关系,而不是进行存在论批判,将数字技术和数据拒之门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