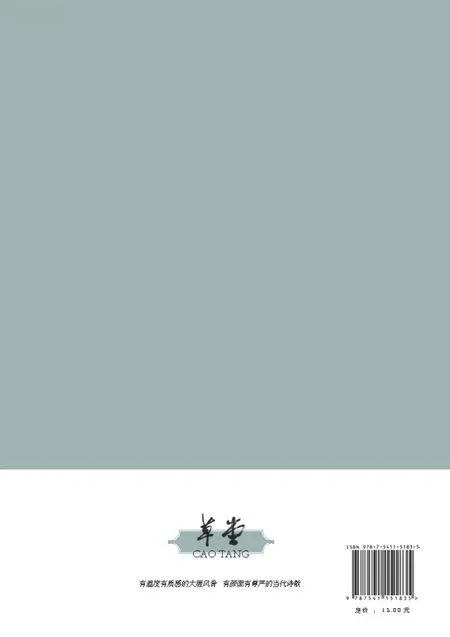食指:在无欲无望中潜心写作
2018-11-16食指vs单于桑眉
食指 vs 单于 桑眉
用作品来宣泄自己的感情,这是我没有彻底垮掉的原因
单、桑:
您从小就开始接触诗歌,与家庭环境有关吧?早期都写了些什么作品?食指:
在《我的生活创作大事记》中小时听母亲读古诗的记录有误。据健在的六叔回忆,新中国成立前后父母及六叔、六婶都在平原省的省会新乡工作。1952年11月平原省撤销,1953年父母调回天津,1954年调回北京。母亲给我读古诗是在新乡,那时六婶上速成中学,她也教我认字。听母亲诵读古诗应该是三、四岁,那时小就觉得好听,并不知道意思,到大了才慢慢懂得。到现在都清楚地记得有两首:一首是《凭栏人·寄征衣》(元·姚燧),就那么几个寄与不寄的字,把心中纠结缠绵的感觉说了个清清楚楚,我觉得十分新奇。还有一首《春怨》(唐·金昌绪)。这两首诗特别耐读,读来语音缭绕,意味隽永,所以直到现在都记得。上小学开始喜欢诗歌,买了好多儿童诗集看。对我影响大的是柯岩的儿童诗,如 《两个将军》《帽子的秘密》等,让我印象很深。受其影响,大概在四年级时写了:鸟儿飞过树梢/三八节就要来到/在老师阿姨的节日里/问一声老师阿姨好。初中又读到了贺敬之、郭小川的诗 (他们写的是新诗),都找到了小时听母亲诵读古诗的感觉。印象比较深的有贺敬之的《桂林山水歌》《三门峡梳妆台》,郭小川的《乡村大道》等。贺敬之的《桂林山水歌》,就那么几个句子稍加改动,读着绕来绕去余音绵绵不尽,和小时妈妈读的“欲寄君衣君不还”如出一脉。还有冰心的《繁星集》,里面的每一首诗都很短,就像元曲的小令一样,都有那种味道。这样的诗作对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朦胧中我感悟到诗歌的魅力——诗应该是这样的。这些可能是引导我走向诗歌道路的起点,我开始对诗歌着迷。
初中时,语文课开始接触诗词,到书店买了本王力的《诗词格律》看,知道了诗词的常识,但没下功夫。初二下学期的清明节前后,由于家庭的教育,写了首纪念二大爷郭耕夫、三大爷郭宗斌烈士的诗,他们在对敌斗争中牺牲得很英勇,很惨烈,让我深受震撼。记得其中的几句:无数的花圈和挽联/萦绕在烈士墓边/花圈上那迎风抖动的鲜花/像是一簇簇跳跃的火焰。高中时,常和同学写诗唱和。写的诗有《书简》《海洋三部曲》的第一部《波浪与海洋》。
单、桑 :
从1964年读函授学校时,您开始(被)成为“问题学生”,问题是 :看外国文艺作品、写诗,都看些什么作品?食指:
函授主要是在家自己温习,由于功课底子较好,就有了许多自己支配的时间,便比较系统地按照外国文学史认真读了些外国文学经典,并进行了分析。还阅读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诗词、散文),以及自白话文运动以来的优秀作品。此时认识了同在西城函授学校的学生牟敦白,牟敦白和郭世英、张郎郎有来往,牟敦白接触外国现代文学艺术较早、较多。我和他交往,开始接触西方的现代作品和现代派艺术。但学校里在搞“反修防修”的反“自来红”教育,老师让我做典型发言,批自己爱看外国小说。我对此事反感,不干,得罪老师(班主任),老师便联合团委书记整我。挨整很厉害,激烈的冲突竟使我有了退团的行动(上高一时父母找西城区团委讲明情况,才恢复了团籍)。1964年底或1965年初,曾在一天夜里走到复兴桥上,想投护城河自杀,前思后想,最终获解脱。我在桥上徘徊至黎明时,农村进城拉粪的马车经过,马铃声将我从黑暗中唤回。之后的一天早上迎着阳光骑车出行,心情和阳光一样灿烂,想了四句:喜逢朝阳送,清风款款从。飘然辞嚣市,田园育乡童。
单、桑:
1967年串联返京前,您曾在山西上花庄短暂停留,让您收益很大。您是从何时喜欢地方戏的?食指:
在上花庄,大队安排一个中年单身饲养员(时间久记不清名字了)和我同住。我白天和社员一起劳动,晚上汇集整理群众上报的材料。和我同住的饲养员话不多,我每天晚上回来他和我打个招呼,给我搁几支烟就自己休息去了。烟是大队买的,我就是在那时学会了吸烟。吃饭是大队派,在老乡家吃一天饭自己交四毛或三毛钱(时间太久记不太清了),一斤粮票,钱和粮票都是从家带的。在上花庄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让我收益很大。特别是返回北京之前,已临近春节,村里的社员排练山西梆子古戏,让我开了眼界。我亲眼看到村里平时并不起眼的年轻人,排戏时的一个亮相,一个眼神,一招一式,却是那么专业,演得可比专业演员有味道。戏虽是古戏,可排练演出之好,令我大为赞叹。山西梆子的唱腔都唱到人的心里,这也是我后来喜欢地方戏的原因之一,也深感到群众对寓教于乐的需要和艺术的重大意义。时至今日,更感觉到自古以来的历史和忠良的悲剧就这样“口口相传”,使人们明白了善和恶、忠和孝,这对于民众的教育和影响是巨大的。单、桑:
回京后与朋友们相聚是您人生中最丰富多彩的时光吧?除写诗之外,您还编曲、写歌、参加“老兵话剧团”“老兵合唱团”……食指:
首先说明没有编曲,因为放不下写诗也没再参加“老兵合唱团”。回京后和朋友们相聚,了解情况。和曲磊磊、郭忱来往较多。郭忱,北京第一一〇中学学生,喜欢音响、录音等。来往甚密,写诗词互相交流。曲磊磊是北京男三中学生,住我们家楼上,喜欢诗歌、绘画和摄影。我俩经常在一起读诗唱和,记得1968年夏天一次我俩骑车去玉渊潭游泳的路上,用苏联歌曲《小路》的曲调随口现编着唱:荒凉埋没了这条小路多凄凉
多少情人的眼泪洒路上
我怎忍心踏碎这晶莹的夜露
抛下爱人独自去远方
没有星星也没有月亮
后面一句是第二段里的一句,是磊磊随口唱的,可惜第二段我只记住了这一句。这歌后来传了出去,我当兵复员回来听说有人接着编了好几段,很是风行了一阵。我曾把写的一首词交曲磊磊拿给他父亲看,磊磊回来告诉我,他父亲看到“雨帘卷作霓虹”时,说这是大家手笔。词已经记不起,这一句因受到曲波伯伯的赞扬所以记得特别清楚。

食指、翟寒乐夫妇在三星堆遗址博物馆
1967年4月由李平分挑头组建“老兵话剧团”,我和邢鸿远执笔,写出话剧《历史的一页》。平分先找到我,谈组织剧团的计划,让我写剧本。意见一致后,他联络人组团。在这里特提及杨晓阳,对“老兵话剧团”和另一个团体“老兵合唱团”,杨晓阳都是积极的组织者之一和大力支持者。剧团的主要组成人员还有:邢鸿远、章予、何京颉、何辛卯、叶子、叶丽娜和主演姜昆、王晓敏、江希莲、刘昌平、苏晓农,以及负责道具的赵强和后勤组赵笑然、梁明明。剧务及演出人员由以前北京市少年宫的话剧组、舞蹈组部分学生为主,还有家在百万庄的中学生,一一〇中学、西四中学、育鹏小学等学校的学生参与演出。老兵话剧团组团后参加者自带被褥住在育鹏小学,交钱、粮票给后勤,大家过集体生活,直到1967年10月解散。在我们演出《历史的一页》的同时,城里的学生金波红、徐雅雅他们演出了《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在长安剧院演出,观众购票入场,演出持续时间较长,影响较大。
1967年的秋冬,在李平分的倡议下,杨晓阳和李平分又组织了老兵合唱团。合唱团成员以西城区中学生为主,兼各大院,包括百万庄大院的中学生。乐队由和平里大院里的中学生组成,乐器齐全,阵容强大,演出专业(可能是因为中央乐团在和平里,所以当地的孩子乐器演奏水平较高)。教唱歌的周晓华也很专业,对参加的成员先测试,再按嗓音分声部,然后分声部排练,最后合练。指挥是沈自由,领唱是臧晶晶。演唱歌曲以毛泽东诗词为主,兼阿尔巴尼亚和苏联革命歌曲,演唱水平较高。杨晓阳让我写朗诵词,写好后怕影响太大(自己又是学校的问题学生),未敢拿出,只给何其芳和何京颉看了。杨晓阳转请李丹刚(京工附中学生)给写的朗诵词。剧团和合唱团演出好几场,合唱团还去天津演出一次,我都没参加,在家写诗。
单、桑:
您的诗在知青中广为传抄,甚至谱成歌曲,您当时有没有觉得自己成了他们的偶像?有没有疯狂的粉丝来找您见面、交流?食指:
这个问题免谈。单、桑:
1970-1972年在部队期间,您的兴趣爱好似乎有所改变?写的诗不多,打篮球、阅读的书籍也不属于文学类……但也有不少收获吧?食指:
我参军的年龄是入伍要求的最后一年,我为了写军旅诗才参军的。部队有部队的要求,我只能在紧张的部队施工、训练、政治学习中体验军旅生活,不可能接触到文学书籍,更没有多余的时间写诗。这不是我的兴趣爱好变了,而是我既然当兵了,就要在各方面严格要求和锻炼自己,努力成为一名合格的战士,这样才能写出军旅诗。从济宁应征入伍,去浙江舟山定海的舟嵊要塞司令部直属通讯营三连(永备架设连)当战士这两年,是我人生很重要的两年。紧张的施工、严格的训练、刻苦的读书,两年的部队生活使我对生活、劳动、读书的思考等都有了和以往不同的体验,思想和身体都得到很大的锻炼。有了坚强的意志和结实的身体,扛住了以后的磨难,更重要的是写出了和任何时期都不同的军旅诗。刚入伍在新兵连写出《新兵》一诗,分到连队后在班里挤时间写出了《刺刀篇》《架设兵之歌》。徐庆东来信说,在舟山有个诗人陈山诗写得很好,军宣传处干事叶文艺与陈山认识。恰巧我又认识叶文艺,我从他那借到陈山的诗集《擂鼓集》,读着很吃惊,真好!还抄了很多。受其诗作《擂鼓赋》《扬旗赋》的影响,写出《刺刀篇》。他的诗对我影响很大,改变了我的诗风,铿锵有力的长短句很适合军旅生活。我后来写出的 《壮志篇》《红旗渠组歌》《海礁赋》等,均受到陈山的影响。遗憾的是部队施工训练紧张,纪律严明,未能去看望在擂鼓镇蚂蚁岛工作的陈山。
当战士期间,我挤时间读完了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别人施工回来都忙着洗涮,我一回来就到我们班的学习室看书。训练中我很认真,能吃苦,曾背着备复线从山坡上直接往下跳,把班长吓坏了,告诉我若跳到老乡砍的竹子茬上能把脚扎穿,让我买很厚的帆布鞋垫垫在鞋里。部队的生活紧张又充实,每周只有半天的自由时间处理个人杂事(洗衣服、写信、请假上街买东西等),写的诗不多。
1971年底我被任命为连里的文书,工作比在班里更加繁忙。文书室在北边的一栋房子,是一个单独的房间,保管的有档案、手榴弹、子弹、连排长的手枪。前任文书交班时提醒我:吸烟注意点,离弹药箱远一些。除了分管的工作(每周要制定出各班排每天的施工、训练任务以及学习的具体时间表,协助指导员讲国内外形势,准备各种材料,按时出时事和思想板报、每周定期擦拭保养一次手枪)以外,还有上级安排的临时任务,几乎没有个人读书、思考的时间。因配合给战士讲国际形势写出《澜沧江湄公河》。
义务兵陆军是两年的服役期,以我的年龄不可能再超期服役。1972年底决定复员。复员前听说军里组织人写军史,我专门请假去军招待所看。见到叶文艺,他说:“连队那么紧张,怎么写诗?你还是复员去文化馆写诗吧。”
单、桑:
您是什么时候被确诊为精神分裂症?是否了解自己的病情?如何对待与调整?食指:
诗集里可以看到,我的不平、愤怒、痛苦和郁闷。我是用作品来宣泄自己的感情,这也是我没有彻底垮掉的原因。1973年回北京,被安排在北京市第二光学仪器厂(通县)的技校任辅导员,后因去河南林县红旗渠写诗离职。红旗渠是中国农民用人工创造的奇迹,令世界震撼。1973年3月初,我决定亲自去红旗渠看看,看看农民创造的奇迹,希望能写出歌颂农民的诗。记得很清楚,我是穿着棉袄、绒衣、绒裤,背了一(军用)挎包馒头,带着部队发的搪瓷茶缸出发的。先坐火车到安阳,再打听着去红旗渠,沿着红旗渠走到拦河大坝,看到了漳河。一路饥了啃干馒头,渴了舀红旗渠的水喝,晚上住两毛钱一夜的大车店,在大车店才能喝到热开水。后来钱花完了,把身上的绒衣脱下卖了五元钱,买了张到邢台的火车票。我的一位本家大爷在邢台,去了他家,让他给我买了张回北京的火车票。
1973年的夏天很热,时常休息不好。在我刚过了二十五周岁生日三天后的11月25日,被送到北医三院精神科。在有理想和梦的年龄,被当成疯子,只有忍着委屈,听命运的摆布,这样反而使我更豁达地面对人生了。沉静是内在生活的力量,我提笔面对命运,诗就这么一路写了下来。1974年9月30日出院,被照顾安排在北京光电技术研究所工作,之后写出《灵魂之二》,完成《红旗渠组歌》。再之后,我结婚离婚、再次入院……
1978年12月下旬,北岛、芒克、江河、黄锐等带着刚刚油印出来的第一期《今天》来家里找我,约我投稿。此后一段,和他们来往甚密。1979年以食指为笔名在《今天》发表诗;1983年有机会去《词刊》工作,我怕上班组稿、看稿影响自己写诗,就没去(我的不少朋友做杂志编辑和当剧团创作员,他们的工作情况我十分了解)。那几年,我写了《热爱生命》《海礁赋》《我的心》《遐想》《献给你》《人生》之一、之二,和《我的小房间》《诗人的桂冠》《枯叶》《大地与落叶的对话》等诗。
1974-1984年我基本是上半(天)班和进进出出精神病院。1974年刚出院不久,有天我站在临街的院里吸烟思考问题,下班的母亲把我叫进屋里。过了会母亲才心情沉重地和我说,以后你别站在那吸烟了,回屋里吸,刚才有路过的人指着你对另一个人说:那人是个疯子。母亲说了后我不敢再去前院,就去后院站着吸烟,思考修改以前写的诗,然后回家整理、修改诗稿。虽然心情不好,诗写得很苦,但到1980年代后还是注意了锻炼身体,坚持洗冷水澡,能连续做三十多个俯卧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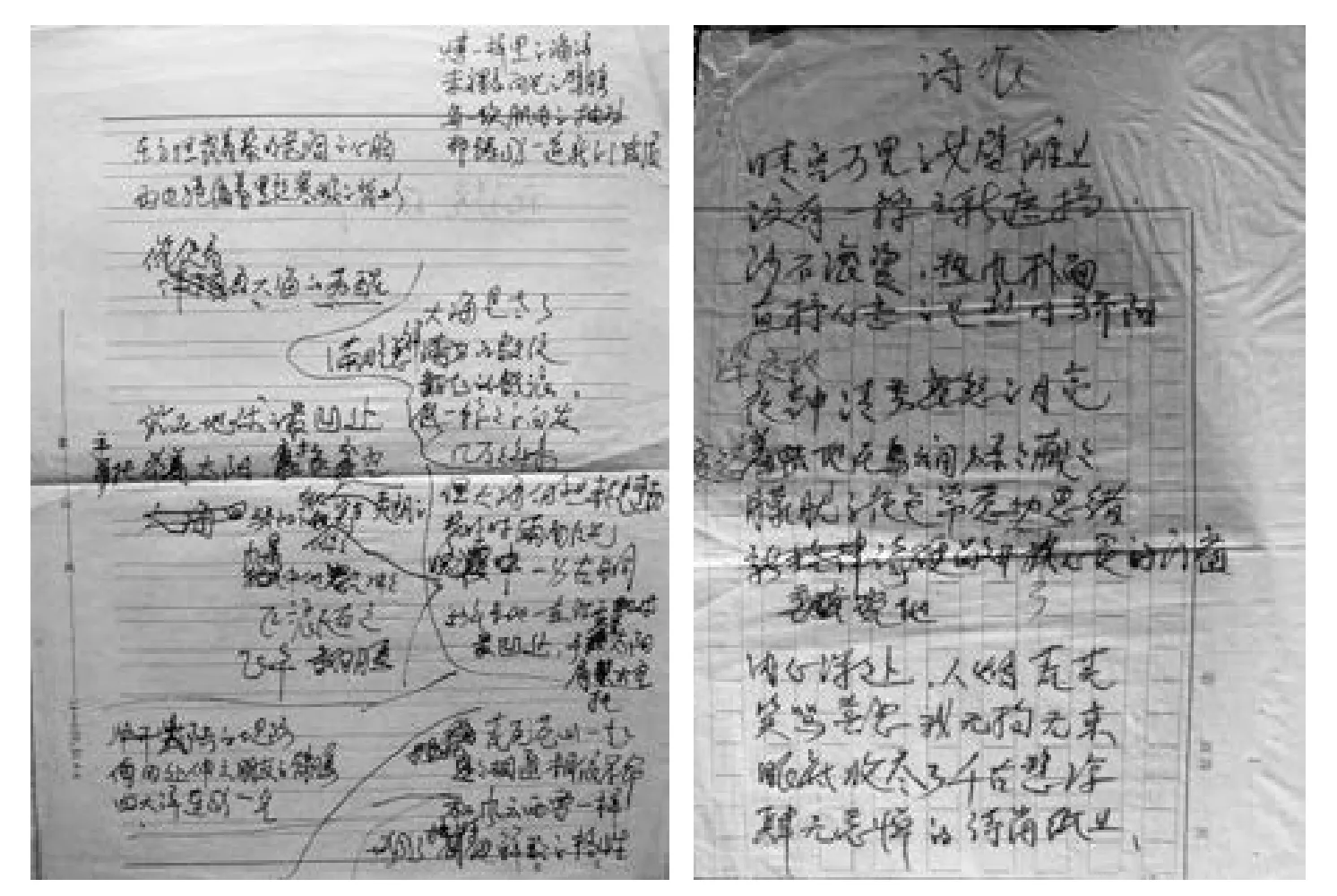
食指手稿
单、桑:
在北京第三福利院,您保持最低的生活费,抽低价的烟,没有受到外界的影响。您是怎样将写诗之外的生活缩减到最低程度?食指:
这个问题不便回答。单、桑:
离开福利院后,您写下了《冬日的阳光》等温馨诗篇。能否谈谈您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和近段时期的生活状况?食指:
2002年3月21日,寒乐接我走出福利院,这一天恰巧是世界诗歌日。2005年5月1日迁居海淀区上庄,开始了真正的晚年生活。2006年2月9日我和寒乐办理了结婚手续。我们的生活很简单,甚至简朴。两年前国庆那天寒乐写过一段文字:“佳佳说3号晚7:30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有维也纳童声合唱团的演出,我俩若想看他给买票叫车。真是想看,路生说好多年没听音乐会了。再问票价500-880元一张,和路生商量还是不去了。对我们来说消费最上限的500元票价在此为最低价,是坐在边角的票,还有来回的车费,加上天也凉,再有老鸡和小狗得操心。佳佳说他出钱,我还是觉得算了,我们不是这个消费层次的人。
想来我这辈子最奢侈的消费是2001年五一在丽江,有天晚上到牧民家做客的活动我没去,花50元钱听了一场纳西族音乐会。联想到也是这一次的旅游在昆明的一次游玩活动:在一个游玩景点导游带领大家去摸龙头祈福。我和同事李力看到有聂耳墓的指示牌,就没随大家走,我俩顺着路标,走上离人群越来越远的山路,国歌的作曲者聂耳的墓园建在一块不大的缓坡上,干净、简单:五线谱、小提琴、郭沫若的文字。清冷的墓园,寂寞的展室,木讷的工作人员……和山下景区的拥挤热闹是截然不同的世界……我俩各拿着一本《聂耳传》下山,在祈福回来还沉浸在兴奋的人群中仿佛还一下回不到现实的热闹中,随着大流木然的赶往下一个景点。”
我们的生活粗茶淡饭,却从容放松。自由地读书、看报,心中感动了写首诗,可以从容地沏上杯茶,可以随意地点上支烟,关注自己有兴趣的问题,在“平平淡淡才是真”的生活中品咂生活滋味。
单、桑:
去年秋天您第一次入川,感受如何?据说您曾笑言,一想到四川,就想能在某个茶馆打个悠长的盹该多幸福呵!食指:
去年(2017年)去四川参加成都金堂5月20日举办的“世界华语爱情诗会暨四川金堂蜀葵文化节”,印象深的有三件事。首先是都江堰和江上的廊桥夜景。都江堰真是神斧天工,及他造福的成都平原使四川成为富庶的天府之国,真令人惊叹!记得晚上去看廊桥和江水,灯光照耀下甚是壮观,给我们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其次是广汉的三星堆文化,因原来较熟悉中原文化,中原文化较多的是政权和世俗,当然也有祭天的仪式,祖先还有敬天的原因,发展下来逐渐和天子的皇权结合得越来越紧密。而这次看到的三星堆文化才知道他的文化是和天神相通的,令人大吃一惊。这样的文化,对于脑力的开启及带来的创造力比中原文化大多了,怪不得四川人杰地灵。最后是金堂蜀葵文化节的节目。整台节目诗朗诵、音乐和舞蹈安排的起伏有致,自然流畅,特别精彩。尽管天公不作美,下的雨很大,但观众在雨中一直聆听观看,可见节目的水平不一般。更令我们惊奇的是这台节目的编导是一伙年轻人,领头的小邵还是学电子专业的,可见四川人才济济。因为我们是第一次去四川,回来时特在成都停留一下。《草堂》诗刊的孙婉豫、宋世超细致周到的安排,杜甫草堂与讲解人员的清谈,以及“碧潭飘雪”的茶香……都让我们现在还常提起,很难忘。遗憾的是由于桑眉去学习,没有见到(编者注:没能引荐)诗歌界更多的朋友并举行座谈,是一大憾事!特别要提及的是《草堂》诗刊(原《星星》诗刊)主编梁平,刚从外地出差回来就到我们的住地看望,并共进晚餐,令人感动。四川之行接触学习了好多新鲜东西,真可谓不虚此行。
《相信未来》及其有“中国气派”的诗歌形式
单、桑:
与何其芳的交往对您一生的诗歌创作影响极大,让您受惠的有哪些方面?言传身教是否比阅读作品更为重要?食指:
言传身教和阅读作品都很重要。在学校阅览室读到过何其芳主编的《文学评论》,那些作为批判“靶子”的外国诗歌,虽多是零散片段,但美国的象征主义诗篇和苏联年轻女诗人阿赫玛杜林娜的诗令我惊叹,让我大开眼界。认识何其芳之后读他的诗集《预言》。发现读何其芳的诗有一种空灵感,如《月下》中的诗句, “但眉眉,你那里也有这银色的月波吗?/即有,怕也结成玲珑的冰了。/梦纵如一只顺风的船,/能驶到冻结的夜里去吗?” 以及《预言》等诗篇都是能把人心中的神性召唤出来的作品。我先是在老兵话剧团认识了何其芳的孩子何京颉、何辛卯,于同年(1967年)初夏认识了何其芳。自此之后,才对诗的韵味和诗的形式及语言的知识有了更深入更系统的了解,并开始了有意识的自觉追求,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诗歌写作。
和何其芳的交往是我在诗歌写作道路上的最大幸事,对我一生的诗歌创作影响极大,使我终生受惠。尤其是何其芳关于新格律体及诗与歌关系的教导,使我懂得了中外诗体由古典到现代的发展过程。没考上高中那年我在家还学谱曲(给烈士诗抄谱曲),所以音乐感比较好。那时按心情谱,还不了解诗和音乐的关系,听何其芳讲了才知道的。
何其芳专门给我讲授“新格律体”诗歌,讲得非常细,非常耐心。记得何其芳老师先给我讲新诗的“形式”,他说:新诗是应该有形式的。诗体的变化从来是从没有形式到有形式,之后再打破旧形式,形成新的形式,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这跟社会和语言的变化有关,跟时代有关。在新诗的形式上,他主张“新格律诗体”,基本上和闻一多提倡的差不多。但在为什么要提倡写新格律诗上,何其芳老师更多地强调新诗应该有音乐感和韵味,有了音乐感和韵味才受老百姓欢迎。
那时我们特别喜欢唱歌,经常一起在何其芳老师家唱苏联歌和其他外国歌。何其芳老师曾对我说:你们喜欢唱歌,歌词配上曲子,好听好记,而且各种感情的歌唱起来,永远都忘不了。为什么呢?因为一首歌的谱子是由几个乐句组成的,而乐句又是由若干小节组成的,小节又是由音节组成的。他说:你要知道歌谱里的乐句就像一行一行的诗一样,一首歌里乐句里的小节数量是一样的,同样每个小节里面音节的长度也是一样的,像2/4拍、3/4拍……这样唱起来非常和谐,感觉余音绵绵不断。新格律诗体,像歌的曲子一样,一首诗几段组成,每段中的诗句和曲子里的乐句一样,句数基本相同,每句中的顿数也叫音步也应和乐句中的音节一样,大致相同,再按照中国人的习惯(一、二、四或二、四)押尾韵,就会产生和歌一样的效果。我问过何其芳老师:民歌也非常有音乐感,配上小调也很有韵味,民歌体是否也应该提倡?记得老师说:在反映现代这个博大深沉的社会时,新格律诗体比民歌体要好一些。
我听得认真,牢记在心。这等于是说,照这样,写新格律诗体的诗人就和音乐家作曲和谱曲一样,有节拍、有句式、有章法了。再加上押尾韵和略微注意点平仄,诗就有了乐感。一首好诗会和受欢迎的歌和乐曲一样好听、好记,会产生余音绕梁的韵味,令人拍手叫绝。如果你了解新格律诗体和懂得音乐简谱,就知道何其芳的联想多么神奇,把歌、曲的体式与新诗形式的形成联系在一起,必然产生妙不可言的效果。何其芳的思考与实践是对新诗形式的形成和发展所做的重要贡献。
我把当时写的诗稿拿给何其芳,何伯伯不但看得认真,还写上自己的意见,再耐心地和我谈,一点没有名家大诗人的口气和做派。谈完了,还嘱咐我“要记得”。还有一点要提及:从小我一直觉得诗的抑扬顿挫特别好听,像声音的回廊,有回响,觉得新诗里也应该强调一下。1967或1968年我问过何其芳老师新诗中平仄的问题。何其芳老师说,他也考虑过这个问题,也问过语言所一位好像是姓陈的所长,陈老是这么说的:现代口语亲和力强,仄声字多,新诗中这个平仄的问题很难解决。所以我写诗时,一句诗中仄声字多的时候,就适当地换几个意思是一样的平声字的词,使诗句朗朗上口。参看我的文章《纪念诗人何其芳诞辰一百周年》(2012年第2期《上海文学》)。
单、桑:
您的早期诗作在意识形态空前严酷的特殊时期,为什么没有被扼杀,而能够在民间获得较广泛的传播?食指 :
在那个时期,我的诗作虽然有倾向性,但主要是感情的宣泄。在特殊时期的中期以后,很多人成了“逍遥派”,不关心政治斗争,而是谈恋爱打毛衣(所谓毛衣针上的路线斗争),看外国小说,这些人还不占少数,大有人在。我的读者群主要在这些人中,我写的也是他们的生活。由于我们这些人其实是远离政治的,所以我的诗作能在这些人中流传。当然之后有人上报,所以后来种种就不足为怪了。可惜这些事和我的“病根”现在无人提起,人们却在下面疯传着我是因为感情纠葛受的刺激。
单、桑:
1978年之后,您开始了一个创作的新阶段,为什么要改用笔名“食指”而弃用本名?(您讲到过,“食指”的来历与母亲有关。)食指:
“食指”的意思是“时之子”,时是母亲的姓,又和老师的“师”谐音,别无他意。单、桑:《
相信未来》里写到人们对“我们”会有公正的评定。有评论认为说它依然在为红卫兵辩驳、为他们的悲剧申说,而不是在传达“尊严、权利、自由和对未来文明事物的瞩望”,这是否是这首诗的局限?食指:
各有各的解读,我不便说。用现在人们的思想观点来解读50年前20岁的我的创作,要求有点高。今天我看来,其实相信未来就是相信历史,50年前的未来就是今天,而今天必定又是50年后的历史,还是让历史来解读。单、桑:
1980年1月,您的诗作《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历经12年后在《诗刊》正式发表,谈谈《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和其他诗作的创作历程,可以吗?食指:
《相信未来》和《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是在《诗刊》工作的柯岩向我多次约稿,在母亲的催促下才寄去,不久就发表了。1968年12月18日乘下午四点零八分的知青专列赴山西汾阳杏花村插队。在车上秦晓鹰说“给你找个空点的车厢写诗去吧”,随后找到一节人较少且有暖气的车厢。是夜写出了《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第一稿,19日抵达杏花村,20日完成定稿。初稿的第六段是:“……然后对她粗声粗气地叫喊:听见吗?记着我,妈妈北京!”当时车站特别乱,只能这样大声喊着说话,三个小短句也符合节拍。原稿的第三段“人们都用手捂住了眼睛/放下你们的手吧/让我再看看你们/那两颗闪烁着温情的明星”在定稿时删去。
小时候,衣服扣子掉了,母亲给我缀扣子时,我穿着衣服站在母亲面前,母亲把扣子缀好了,就把头俯在我的胸前,把线咬断,这是印在我脑子里非常深的印象。临走的那天,母亲又给我钉了扣子,是将扣子加固。母亲没有去车站,只有妹妹丽娜一人去送我们。以后才知道,那天父亲也去了火车站,只站在远处望着。我们走的那天,全家没吃晚饭,连灯也没开。
这之前写过送别人下乡的《送北大荒战友》。送别人下乡和自己真要离开北京感受太不一样了,尤其火车开之前“咣!”的那一声,一下让心里一震。“一声尖厉的汽笛长鸣”改成过“一声雄伟的汽笛长鸣”,“雄伟”和周围的环境符合,但内心仍感觉是尖厉的声音,后又改了回来。这首诗曾在多个场合朗诵,有时会随心情脱口朗诵成“一声心碎的汽笛长鸣”。
写于1968年的《还是干脆忘掉她吧》原创第三段的后两句:“一手扶着摇曳的垂柳,一手召回南去的雁群”,正式发表改为“迅速地消失在我的蓝天里,只留下鸽铃那袅袅的余音”。有朋友觉得“一手扶着摇曳的垂柳,一手召回南去的雁群”是神来之笔,删了可惜,可我特别喜欢鸽群飞时的铃声,听着心里舒服。在听到我们百万庄两个大学生的感情故事后,写了《难道爱神是》这首诗,随后将写好的诗抄给了当事人。《你们相爱》一诗是根据另外两人的故事而写。
单、桑:
您曾说过“人们评价我的诗歌时,总说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那些……七八十年代写的那些诗更有价值。”能否举例谈谈?食指:
《相信未来》诗集的编后记中有这样一段:细心的读者会注意到,1973-1983年间,作者同期写出的诗中情绪反差较大,这和作者的痛苦经历、飞速发展的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冲突有关。具体到诗作,如《疯狗》《热爱生命》《我的心》《诗人的桂冠》《心胸》《挑起重担》《人生的启示》,这一时期这些作品中剧烈的感情冲突是作者的经历和理想之间的反差造成的。这是那个时代我们这代人感情经历的一个缩影,这是现代和历史的碰撞点,仔细品读会读出其中的心酸与无奈,是很有味道的。读者不妨自己去读读(这些)诗去。
单、桑: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对当时的您而言,如同荒凉的人生绝境!在那期间您写下了哪些诗篇?食指
:1997-2000年期间写下:《当你老了》《我这样写歌》《中国这地方……》《生涯的午后》《在精神病福利院的八年》《我从冰天雪地中走来》《暴风雪》《世纪末的中国诗人》《青春逝去不复返》《相聚》……《相信未来》的编后记中写道:在精神病福利院里(1990-2002)1997年到2000年期间作者的作品和其他住院时期的作品,格调显然不同,这也与作者的“特殊”经历有关。这里我要说明一下,所谓“特殊”经历是我在1996年秋被福利院领导安排管理职工之家,这是院职工休息娱乐的地方,住在那打扫卫生,管理乒乓球台和棋牌,相当自由,而且还有台电视机,也由我们掌握,只回病区吃饭。抽烟(我自己有打火机)喝茶方便了,自己的安静时间充裕,这具备了写诗的基本条件。但更为重要的,按福利院大家的观点看来,安排在这的是永远出不了福利院但病情又较轻的病人,也就是我的最后的归宿。这时我的心境一片荒凉,也就是说到了人生的绝境。
2000年春节后,由于不便说明的原因,我被“惩罚”回福利院病区,没有在职工之家自在了,这时候我写了《青春逝去不复返》,这首短诗的写作前后持续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是在不允许我写诗的情况下完成的。我只能在吵闹的环境中一点一点地思考,把写的字句一开始写在手背上(我们不允许带笔的,只有向护士借笔)。由于我主动要求洗碗(怕病友生病),早午晚三顿饭前我会把洗好的碗筷再用清水洗一遍,这样就会把写在手背上的字冲模糊,之后我便把在吵闹环境中想好的诗句写在小臂上,以便在中午允许回自己房间的时候整理在笔记本上。由于诗句里的词汇要形象准确需不断推敲、改动,所以一个多月才完成了这首小诗。记得当时的心情是非常痛苦复杂委屈的,但结果诗写得非常流畅,像一气呵成,便心中充满喜悦,溢于言表。写了一辈子诗,这首诗在这种情况下写成,是唯一的一例,所以记忆清晰。
之后听到“绝境”是后现代哲学探讨的问题。所以我把这一时期的写作引申为“绝境写作”,也就是在无欲无望中的潜心写作。我想这和史铁生患病晚期写作的心情是一样的,这一点是值得人们注意的。
单、桑:
您曾提到“中国气派”,要创造出一种新的诗歌体,在您的诗歌创作中有过相关的尝试吗?食指:
谈中国气派的问题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和我的朋友刘会远一次关于文艺状况的谈话后想到的,当时正是伤痕文学流行的时候,我对会远说:古人说“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之后我考虑到要有中国气派,当时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当全会一提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我就想到中国特色的内容和具有中国特色的形式合在一起就是中国气派。当然还要加上新中国成立十七年来许多作品反映出的革命英雄主义的大气凛然。我当时就试着写出了《海礁赋》,但这当然不能否定何其芳老师教我的新格律体和民歌体。要知道何其芳老师教我的新格律体,虽然有些“洋气”,但是是深得中外诗歌精髓和要义的。民歌体则是深得民间乡俗村风的,再加上在古典诗歌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古体诗、赋、曲,都是非常受老百姓欢迎的诗歌形式,是各有特长具有中国气派的诗歌形式。
单、桑:
新诗的形式多种多样,汉语诗歌应该怎样处理传统和现代的关系?食指:
这个问题我在思考之中。何其芳老师给我讲的新格律诗的长处和贺敬之的观点以及陈山的诗作都给我以巨大的震动,我的作品中也有一定的尝试。任何艺术都有个形式,电影有荧幕,戏剧有舞台,绘画有画框,小说和散文也有各自的规矩,怎么诗歌就没有自己的形式呢?当然有时突破一下也可以,古诗中也有这种情况。正像季羡林先生说的:新诗连个形式都没有,何必叫诗?至于新诗的形式有几种,现在看来肯定不会是一种。我的老师的理论和实践是这样告诉我的,我在作品中的尝试也是这样的。白话文新诗的形式取决于诗人对于白话文韵律的感觉和研究,看来这一点我们现在忽视了。要知道我们的诗人要是读不出白话文句子中的韵律就不可能写出白话文新诗的诗句,就更别谈新诗形式的形成了。
单、桑:
早在1935年,朱自清就提出诗坛分为三派:自由诗派、格律诗派、象征诗派。您认为格律诗是现代汉语诗歌的唯一出路吗?食指:
上面问题的回答基本谈清这个问题了。借此机会郑重申明:这次访谈所谈及的所有问题,纯属我的一家之言,执不同意见者大可一笑置之,希望不要引起各位方家的争论。
单、桑:
您有一句话“诗歌是化苦难的生活为艺术的神奇”,回过头看,苦难也是一种馈赠!您认为诗歌就应该是直面现实与命运的吗?食指:
这只是我的体会,每个写诗的人都会有自己的体会。前人说愤怒出诗人,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能没有感情起伏,也就是说有痛苦、有迷惑、有抑郁、有探索、有欢乐,但痛苦和迷惑是生活中本来就存在的,是基本的。所以诗人尤其是年轻诗人应该勇敢地面对命运面对现实。那种假大空歌颂的或应景捧场的根本就不是诗,但是面对现实写命运的诗人特别少,只有俄国的莱蒙托夫,可他只活了27岁。在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中国有位这样的杰出诗人叫于庚虞,在黑暗的年代面对血淋淋的现实,直面惨淡的人生,他的诗和郭沫若、戴望舒、徐志摩完全不同,可惜他现在被埋没了。前些年,河南大学整理出版了他的诗集,由于我认识他的外孙,有幸得到一套,看后唏嘘不已。
单、桑:
您不同阶段的诗歌都体现了诗人和所处时代的关系,现在很多诗人都倾向于个人化的叙事,您如何看待他们的创作?食指:
这个问题提得很好。前些年北岛到我家,我和他谈到,我们那会写诗是有追求的,是有理想有抱负的,现在诗坛成这个样子和理想和追求有关,北岛表示完全同意我的意见。不知道这点补充的回答能否把你提问中的问题说得更清楚?以我看来,你问题提到的是那些年轻诗人的诗作,那些写个人琐碎的小情调的作品,是“浅”写作,缺乏深度的开掘和凝练。这种情况在现在相当普遍,当然我也不能主观地否定别人的情趣、喜好,诗歌创作在内容方面是多方面的,不是一概的否定别人的创作,只是个人的喜好而已。中国诗坛出现目前这种情况,我觉得从根源上讲这是一个引导的问题。因为朦胧诗开创了个人写作,脱开了以前的“大我”,强调“小我”,由于当时没有明确和很好的处理及引导这个问题,由其自由发展,再加上诗歌形式的问题(这是一代代老诗人一直要解决的问题)被完全搁置不提,要知道没有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群众是不买账的,只能诗人小圈子里互相吹捧,这就成了诗坛现在这个样子,这个问题是应该提出来的。
单、桑:
在那个没有诗歌的年代,您写出了影响一代诗人的诗歌作品,如何看待“新诗潮诗歌第一人”的评价?食指 :
“第一人”的评价不合适,前有郭世英、张郎郎等一批被埋没的诗人,我只是一个传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