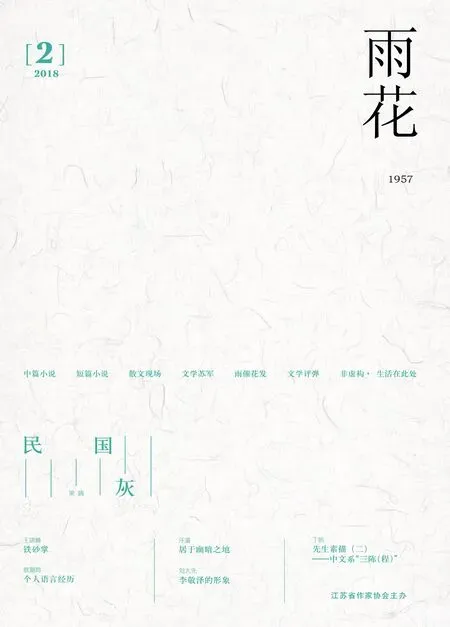居于幽暗之地
2018-11-15汗漫
汗 漫
居于幽暗之地
“像树木似的成熟,不勉强挤它的汁液,满怀信心地立在春日的暴风雨中,也不担心后边没有夏天的到来。”这是里尔克《给青年诗人的信》中的一句话,引导年轻人爱自己的寂寞,“无忧无虑地寂静而且广大”。
春日的寂寞值得热爱,因为夏天总会到来,充满汁液的枝条终将开花结果。青春期的寂寞亦如此,不必担心没有盛年的到来。但对于老人、一棵果实落地的树来说,盛年夏日不再,尘埃落定,他或者它,将成为寂寞本身——记忆像年轮、像唱片,在身体内寂静旋转,回放出春日暴风雨声。
“关注内心,关注渺小”,是里尔克给某个青年诗人所写的一系列信札的主旨。在对内心与渺小的关注中,去拥抱寂寞、去爱。市侩、暴徒、投机者在交易和狂欢,反衬出这寂寞和爱的高贵。
在里尔克的《马尔特手记》这部自传体长篇小说中,出现了大段大段《给青年诗人的信》中的句子。我明白,里尔克其实是在给自己写信,解决个人危机,厘清现实疑难。
“主呵,是时候了。夏天盛极一时 / 把你的阴影置于日晷上,/让风吹过牧场。/让枝头最后的果实饱满;/再给两天南方的好天气,/催它们成熟,/把最后的甘甜压进浓酒。/谁此时没有房子,就不必建造,/ 谁此时孤独,就永远孤独,/就醒来,读书,写长长的信,/在林荫路上 /不停地徘徊,落叶纷飞。”
《秋日》这首短诗,从主、果实再到孤独,三段,奠定了里尔克的大师级位置。当代,房地产开发商们,拒绝承认世界上存在这样一个鼓励读书、写信、徘徊而不主张建造房屋的孤独者。
里尔克写作此诗时只有二十来岁。伟大的诗人一张嘴就是秋声。
里尔克的照片,从少年到中年,两只大眼睛都是泪汪汪的。只有充满了无限爱意和寂寞的人,才会拥有这样一双让人心痛、心动的眼睛。
在《马尔特手记》中,马尔特或者说里尔克,走过巴黎塞纳河边的一系列店铺。橱窗里满满当当,主人坐在店铺里埋头看书。他假设自己也能买下这样一个店铺,与一只狗坐上二十年,而不是在落叶纷飞的巴黎街头徘徊,会是怎样一种生活?一年四季,他总是习惯于打开出租屋的窗子,即便是寒冷的夜晚,也可以随时抬头与巴黎的星星自由交流。
“他们要开花,开花是灿烂的,可是我们要成熟,这叫做居于幽暗而自己努力。”里尔克在饱满的果实里看到自己的肖像,于幽暗中努力生成酒意和诗篇,把最后的甘甜压进自身。最终,为花朵所伤,得了败血症,长眠瑞士——五十一岁,依属盛夏。
“我像一面旗帜被空旷包围,/ 我感到阵阵来风,我必须承受;/下面的一切还没有动静: / 门轻关,烟囱无声; / 窗不动,尘土还很重。/ 我认出风暴而激动如大海,/ 我舒展开又卷缩回去,/ 我挣脱自身,独自 / 置身于伟大的风暴中。”里尔克在一面旗帜上也看见自己——承受风暴,挣脱自身,因“认出风暴而激动如大海”。
现在,我也人到中年,白发飘拂如旗帜。但我回避风暴和大海,只想凡俗地生活于微风里、溪水边。我知道自己缺乏在风暴中“承受与挣脱”的力量。
收到里尔克信件的那位青年诗人,说:“一个伟大的人、旷百世而一遇的人说话的地方,小人物必须沉默。”
我必须沉默。
人的未来就是爱
1930年,四十岁的帕斯捷尔纳克写出回忆录《安全保护证》,题献给四年前去世的诗人里尔克,也是向里尔克1910年写出的自传体小说《马尔特手记》致敬、对标。
四十岁就开始回忆。四十岁就足以回忆。四十岁就必须回忆了——为中年、晚年的逐步降温,积蓄火种和燃料。
全书分三章,我尝试概括如下:(一)十岁时随父亲在一个火车站遇见里尔克及其情人莎乐美,初习音乐学;(二)在德国马尔堡大学,研究哲学与初恋;(三)中年开始,认领诗人身份并面对马雅可夫斯基之死。
这一结构富有意味:从认识一个诗人开始,到对另一个诗人的辨析与纠正结束。四十岁以后,一个伟大的俄语诗人成长起来,并以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带来盛誉——那其实也是一部伟大的叙事诗。
《安全保护证》一书中最难忘的比喻如下:“少年时代是漫长无边的。不管以后我们还能活几十年,都无法填满少年时代这座飞机库。我们会分散地或成堆地、不分白昼或黑夜地飞进去寻找回忆,就像教练机飞回机库去添加燃料一样。”
书中最动人的情节,是帕斯捷尔纳克对弗家姐姐的感情:始于十四岁时为她补课,表白于马尔堡大学的重逢——“这三天不像平日的生活,过节一样”,被拒绝。在火车站,“我完全丧失了送行的本领。……我在火车启动时跳了上去,为的只是向姐姐说一声再见。……我们在向柏林飞驰。那个差点中断的节日又延续下去了。”但是,“我与柏林是毫不相干的。”再一次与弗家姐姐分别,其实就是永别了,“我的脸在一阵阵抽搐,眼泪时刻不停地想要夺眶而出”。夜晚,在柏林车站前的一个下等客栈里,他埋头在一张桌子上,哭了。
书中最好的一句话是:“人的未来就是爱。”
写这本书之前,1926年,帕斯捷尔纳克、茨维塔耶娃与里尔克相互通信一年。语言中的爱,热烈、抽象得近于虚无,但也使病中的里尔克的生命坚持到了年底。后来辑成《三诗人书简》一书,最后一封信,是茨维塔耶娃写给已经到达天国的里尔克:“亲爱的,既然你死了,那就意味着,不再有任何的死。亲爱的,爱我吧,比所有人更强烈地爱我吧,比所有人更不同地爱我吧。”
之前,茨维塔耶娃对帕斯捷尔纳克有过不明确的爱。里尔克的出现与消失,使她彻底忽视了帕斯捷尔纳克的感受。
最终,茨维塔耶娃只能对一张书桌来抒情:
“三十年在一起——/ 比爱情更清澈。/ 我熟悉你的每一道纹理,/ 你了解我的诗行。/ 难道不是你把他们写在我的脸上?/ 你吃下纸页,你教我:/ 没有什么明天。你教我:/ 只有今天,今天。/ 钱,账单,情书,账单,/ 你挺立在橡树的漩涡中。/ 一直在说:每一个你要的词都是/ 今天,今天。/ 上帝,你一直不停地在说,/ 绝不接受账单和残羹剩饭。/ 哼,明天就让他们把我抬出去,我这傻瓜/ 完全奉献于你的桌面。”让我想起米沃什“在大海光线颤动的小酒馆中”遇到的那一张厚木桌子。
这一充满漩涡的书桌,像拥有三十年历史的情人和导师,教导她“绝不接受账单和残羹剩饭”,只要情书,只要一个词“今天”——这稀缺的、温暖的事物,迟迟不来,像一列晚点的火车迟迟不来。
年长于茨维塔耶娃的阿赫玛托娃,也在同一时期低语:“既然我没得到爱情和宁静,/ 就请赐予我痛苦的荣誉”。在俄罗斯,在这世界上,怀抱诗篇的女子,都像是怀抱着痛苦之神所颁发的获奖证书。白银时代的这批诗人,都爱得那么极端、恳切、激烈、广阔——在爱中丧失,才会在诗歌中丰收。
曼德尔施塔姆的妻子娜杰日达,谅解曼德尔施塔姆婚前与茨维塔耶娃之间长度为四个月的一段恋情,认为茨维塔耶娃影响了曼德尔施塔姆的语言。在丈夫死于流放地后,将其诗稿暗藏于一个平底锅的夹层中随身携带。她甚至背诵下全部诗稿,以防平底锅被盗、被掠夺。她写下回忆录,关于丈夫、诗歌、一个时代,文风酷似曼德尔施塔姆。研究者认为,这是她长时期每天背诵丈夫诗歌的结果。
“娜杰日达”在俄文中的意义是“希望”——人的希望就是爱。
帕斯捷尔纳克作品中经常出现哭泣的女性形象,都美好,也似乎是在对他未来葬礼场景的一种预言——在一片黑纱和鲜花中,人们记住了他情人伊文斯卡娅哭泣的形象。黑白遗像里的帕斯捷尔纳克,像大雾中突然涌现出的马头。临终前反复念叨说“周围有太多的庸俗”,而他也说过:“我很幸运,能够道出全部。”这样一种俄罗斯思想者的高傲和坦诚,当代汉语写作者们有吗?
帕斯捷尔纳克反复写到的火车,代表着希望、爱、漂泊,在俄罗斯无穷的雪野、飞溅的泥泞、凌厉的春风里,呼喊、奔跑——那完全就是披头散发的、恋爱中的女人形象,茨维塔耶娃、阿赫马托娃、娜杰日达们的形象,拉拉的形象——五十六岁那一年,帕斯捷尔纳克开始动笔写作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医生的情人是拉拉。
火车的未来就是爱——铁轨伸出去像灼热的双臂。没有爱的火车,是野草与蝉鸣中的一堆废铁。曼德尔施塔姆在与茨维塔耶娃恋爱期间,反复乘坐火车去莫斯科看望她,以至于被误认为是一个铁路工人。
在散文《第五元素》中,帕斯捷尔纳克写到:“一本书就是一份立方形的、感情强烈的、热气腾腾的良心——仅此而已。不善于发现和说出真理,这是任何一种说假话的本领都无法掩盖的缺陷。”英语中的“发现”一词,就是“除去遮蔽”,而谎言制造者们则是在建立遮蔽,让被欺骗者生活在幻象之中——走在虚构的街道、机场、天空下,走在虚构的爱与自由里。
“诗歌和散文是不能分离的两极。凭借与生俱来的听觉,诗歌在词汇的喧嚣中寻觅大自然的旋律。散文则凭借其崇高精神,透过嗅觉,在语言范畴中探索并发现人。”帕斯捷尔纳克如是说。他的诗、散文、小说,都是不可分割的两极——南极和北极,构成一个写作者完整的世界和内心。他的听觉和嗅觉都应该很好,在纸上重现出悲怆的俄罗斯风琴声、草地上女子们的复杂香气……
“宛如在沉重的荒年,几十架风磨在裸露的原野边缘不详地转动。”他长短参差的诗行像风磨,依靠风力而转动的磨盘,在荒年里能磨碎什么样的词,作为饥寒者的粮食?他就是一架风磨。他就是不安。在写作中缓解不安——死,是一部最后的作品,用棺木作为木质的封面,了结不安。
中国的作家、诗人也可能幻想在自己葬礼上出现一个美的女子。但笔下的汉语,配得上那美的哭泣吗?
我醒来又降新雪
1985年,我刚刚开始写作不久,就读到了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一套“世界百年经典诗歌丛书”——《从两个世界爱一个女人:勃莱诗选》《秋天奏鸣曲:格奥尔格·特拉克尔诗集》《时间与水:战后冰岛诗选》《玫瑰祭坛:埃迪特·索德格朗诗歌全选》《纸上幻境:迈克尔·布洛克诗选》。从此,喜欢上了勃莱的诗。
后来,渐渐明白,这喜欢是有理由的:勃莱像一个中国古典诗人在写作,像一个乡村里的隐居者在写作,风格清新、宁静、广阔——玉米地窜过的野雉,树林里闪烁的晚雪,湖面上传来的鸟鸣……
我有过一段童年乡村经验,跟随外公、外婆在旷野里生息,背着书包去庄稼地环抱的小学读书,钟声回荡。风声似乎说出了阴历控制的一切:炊烟、鸟群、池塘上的反光、庄稼起伏如同虎皮蠕动、出嫁与出殡的行列色彩不同……这样一段生活,决定了我的性情和走向:敏感,寡言,多思,用勃莱笔下的蚂蚁的方式,在纸上寻找一条生路与归途:“冬天的蚂蚁颤抖的翅膀/ 等待瘦弱的冬天结束。/ 我用缓慢的、笨拙的方式爱你,/ 几乎不说话,仅有只言片语。”
勃莱喜欢中国诗,尤其喜欢陶渊明。“在古代中国,各个层次的知觉能够静悄悄地混合起来。它们不像冬天的湖水那样分成一层又一层,而是都流在一起了。我以为古代中国诗仍是人类曾写过的最伟大的诗。”于是,他和朋友们一起创造了“深度意象派”,向中国古典诗歌的“圆融之境”致敬。
《在多雨的九月》:“在我们之前,男男女女都能做到这一点:/ 我会去见你,你也能来看我,一年一次;/我们将是两粒脱壳的谷子,不是为了播种;/ 我们蛰伏在房间里,门关闭,灯熄灭了;/ 我陪你一同抽泣,没有羞耻,顾不得尊严。”一对情人拥抱着哭泣,使九月多雨。脱去的衣服像稻壳,等着他们灼热的身体重新穿上,就像在田野里重新生长一次。
情人离去,冬天来临:“四点左右,几片雪花。/ 我把残茶泼到雪地上,/感到清新的寒冷中的一丝愉快。/ 入夜时分,风刮起来,/ 南窗上的窗纱缓缓飘动。/ ……/我醒来又降新雪。/我是一个人,但另有一个人/ 和我一起喝咖啡,一起眺望雪夜。”《冬日独居》的首尾两节。
我猜测,勃莱写《冬日独居》时,大概想到了白居易的《邯郸冬至夜思家》:“邯郸驿里逢冬至,抱膝灯前影伴身。想得家中夜深坐,还应说着远行人。”以及王维的《冬晚对雪忆胡居士家》:“寒更传晓箭,清镜对衰颜。隔牖风惊竹,开门雪满山。”
当然,勃莱在喝咖啡不喝茶。没尝过中国的米酒与黄酒吧?但中美两国的雪夜保持一致,又黑又白。当然,他不思忆自己居舍以外的功名、离乱和途人。他或许读过《世说新语》?东晋名士殷浩,因一句话而名动古今:“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勃莱与勃莱周旋久,宁作勃莱——“放弃所有的野心是多么美妙!/ 突然,我清楚地看见/ 一朵刚刚飘落在马鬃上的雪花!”
在明尼苏达州的一个农场里读书、写作、打猎、骑马、观察马鬃上的雪花……这完全就是陶渊明式的生活。他的诗就是一个美国人的《桃花源记》。
我曾经在一个深夜,开车去上海浦东机场送母亲回故乡南阳,途中想起勃莱的《开车送父母回家》:“开车送父母回家,穿行在风雪中/ 在山崖边他们衰弱的身躯有些犹豫。/ 我朝着山谷高喊/ 只有雪在回应。/ 他们低声说话/ 说到提水,说到吃橘子/ 说到孙子的照片昨晚忘记带了。/ 他们打开自己的屋门,然后消失。/ 橡树在林子里倒下,/ 隔着数英里的寂静,谁听见了?/ 他们坐得那么近,好像被雪挤压在一起。”
我不可能开车送父母一同回家了。父亲在多年前去世。我周围,是南方中国的暖意和灯火,没有森林和风雪。母亲比我提前二十三年老了,坐在汽车后座上,什么也没有说。她不知道勃莱。她慢慢推着行李车消失在候机厅深处。机场上腾空而起的某架飞机里,她与陌生人一起进入云端。在云端,她或许能与父亲的亡灵更近一些,甚至在进入故乡上空时与父亲的另一种形态擦肩而过?
读勃莱这首诗的时候,只有感动,似乎没有发现什么技巧。清代张船山说:“天籁自鸣天趣足,好诗无非近人情。”诗人就是天光下的有情人。诗歌的责任就是抒情。抒情就是爱,对万物人间的爱,从两个世界、无数世界去爱。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诗坛,我成为意象写作的代表性诗人之一。但没有勃莱写得那样好,原因大约在于爱的深度不够,天空下的生活的广阔度不够。
2016年11月,纽约去华盛顿的高速公路上空,云朵绚烂,像各种肤色的游荡者。时而下一场阵雨。就读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儿子在开车。我和他母亲像勃莱的父母一样坐在后座上。这个十五岁就一个人拖着行李箱来到美国小镇读高中的孩子,长大成人,开始掌握大局和方向。我微微有些失落。又想到勃莱的《开车送父母回家》这一首诗。沿途是旷野,小镇、木屋时隐时现。霜降中闪烁着光辉的河流、树林,大约散发出小动物们喜欢的气味。勃莱定居于明尼苏达州的一个农场,房子周围应该也是这样的景象。
勃莱目前依然活在这个世界上,八十一岁了,让我感到幸福。
这个美国老头认为,所有诗歌都是旅行,“最好的诗歌是长途旅行。我喜欢那些想着另一个世界旅行的诗,那个世界可能会是一处有如蜜蜂翅膀一样被忽略的地方”。当然,他诗歌中屡屡写到旅行,火车、汽车、马屡屡出现。“正是微雪的时候。/ 黑暗的铁轨自黑暗里涌出。/ 我注目蒙着轻尘的车窗。/ 在蒙大拿的米苏拉,我愉快醒来。”他总是能够在雪意中醒来。他大约知道中国的一个出自《庄子》的成语:澡雪精神。
按照勃莱的观点,这次美国之行是我的一首长诗?是我最好的诗?有些欣慰,也有些感伤。
“在林中最后一次散步直到黎明 /我必须回到那没有陷阱的田野 / 回到那顺从的大地。”跟随勃莱,在没有陷阱的田野和顺从的大地上散步,就能获得安定的内心和晚年。如果沿途遇到一面湖泊,我和他会停下来,在这最清澈的镜子里,辨认出各自衰老的容颜。
让马粪进入诗歌
美国诗人詹姆斯·赖特《在明尼苏达州的松树岛,躺在威廉·达菲农场的吊床上》:
“头顶之上,我看见那只青铜色蝴蝶,/ 休憩在黑色的树干,/ 似绿荫中的叶子拂动。/ 沿着空屋后狭深的山谷,/ 牛铃一声一声走进下午的深处。/ 我的右边,/ 两棵松树间的一片阳光下,/ 去年落下的马粪/ 燃烧成金色的石块。/ 我斜躺着,暮色渐暗着降临。/ 一只老鹰飞过上空,寻找归巢。/ 我虚掷了我的一生。”
标题很长,赖特在模仿中国古代诗人的做法?
白居易有一首诗,题为《自河南经乱,关内阻饥,兄弟离散,各在一处。因望月有感,聊书所怀,寄上浮梁大兄、於潜七兄、乌江十五兄,兼示符离及下邽弟妹》。古人诗题漫长,有其不得已之处:诗律、结构无法承载过多的背景交代、人物关系描述,只能求助于标题。20世纪之初新诗的出现,就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让诗能够承载驳杂的日常生活,那些驳杂的词。
赖特神往于中国古典诗人的生存状态和表达方式,尝试以有力的意象和明澈的口语传达诗意,像王维们那样。1980年去世,五十三岁,他虚掷一生了吗?那只老鹰,可能就是赖特躺在吊床上抬手掷进天空的一句诗——
一个诗人消失了,其句子与美国农场的景色一同活下来,就没有虚掷一生。
与中国田园诗不同的是,马粪可以进入现代诗,而且,闪闪发光——“让敞亮发生,使存在物发光和鸣响。”海德格尔在《诗·语言·思》一书中这样写到。不能对马粪的存在视若无睹。风吹动一团旧马粪发出的声音,也应该记录下来,否则,一个农场就丧失了完整和真实。
闻一多《口供》一诗,被传诵的名句是“鸦背驮着夕阳,黄昏里织满了蝙蝠的翅膀”,古典、唯美、抒情;但结尾的一句,暴露他现代诗人的身份:“可是还有一个我,你怕不怕?——苍蝇似的思想,垃圾桶里爬。”
让马粪、苍蝇进入诗歌,让诗歌获得现代性——对当下生活、自身处境进行辨认和发言。
当下写作者的使命,就是要让笔介入被遮蔽、被掩饰的一切,让汉语敞亮、发光、鸣响。
“在我看来,诗人的任务是阐明而不是遮掩。当然,有时必须将灯熄灭,以便能看清灯泡。” 德国诗人、小说家君特·格拉斯如是说。开、关、开……他大概搞坏了不少灯泡。在开灯、关灯的技艺掌握熟练以后,他开始写长篇小说《铁皮鼓》《狗年月》,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写长篇小说的人,需要在书桌上建立一个大探照灯?
格拉斯的书房窗外,或许也散落着去年的几块马粪,暗藏了一匹马的轮廓、体力和光……
一朵重要的云
布莱希特,因剧作《四川好人》《高加索灰阑记》而著名。前者以中国南方为背景,后者源于元杂剧的启示。愤怒而尖锐的革命气质,使他在1955年获得了苏联的“列宁和平奖”。
最近读了他的一首小诗《回忆玛丽·安》,我才觉得这个德国人背叛了其著名的“间离原则”,把隐藏一生的温柔,暴露在字里行间了:
“她的脸是什么样子我已经记不清楚。/ 我只知道:那天我吻了她。/那个吻,我早已忘记。/ 但我依然记得那朵在空中漂浮的云。/ 我永不会忘记,它很白,/ 在高空中移动。/ 那些李树可能还在开花,/ 那女人可能生了七个孩子。/ 而那朵云只出现了几分钟,/ 当我抬头,它已不知去向。”
那朵云多么重要,让一个人念念不忘,让诗产生,让多年以后的读者眼前也能升起几分钟的云朵与李树。
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中说:“爱情的问题都是在床上解决的。” 中国乡村俗语:“天上下雨地里流,两口子打架不记仇,白天吃的是一锅饭,晚上睡的是一个枕头。”与马尔克斯的话异曲同工。解决男女之间的问题,床、枕头、夜晚具有重要功能。
但被解决了问题的爱情,反而无法产生一首诗。诗,只能在种种的不可能、种种的丧失里产生,在一个个问题所形成的重重阻力中产生——像远离了床榻和枕头的那一个吻、那一朵云。
“上天同云。雨雪雰雰,益之以霡霂。既优既渥,既沾既足。生我百谷。”这是《诗经》中的云,一朵很重要的云,代表丰收。
“霭霭停云,濛濛时雨。八表同昏,平路伊阻。静寄东轩,春醪独抚。良朋悠邈,搔首延伫。”陶渊明的云朵停在空中,像友人驻足,但无法落实到门前。昏暗的时光里,即便有春醪可以独饮独醉,也孤单啊——幸而有停云霭霭。
“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李白也需要借助于浮云来指代游子。
“天很热,我给你写信,现在墨水都被蒸发了,房间里飘着一朵朵云。”喜欢写信且对如何写信有很多见解的英国作家刘易斯·卡罗尔,在给某小朋友信中写了这一句话,也像诗,也是一朵重要的云。卡罗尔是1865年出版的童话《爱丽丝漫游奇境》一书的作者。童话本质上就是诗,充满了想象力,打破时空、万物之间的壁垒,让植物、人物、动物相互转化、对话和倾慕。
《爱丽丝漫游奇境》的汉语首译者赵元任,是现代汉语言学家,也是《教我如何不想她》的作曲者。两人都善于抒情,在汉语和英语中都保持天真、爱意和孩子气。“天上飘着些微云,地上吹着些微风。啊!微风吹动了我头发,教我如何不想她?”《教我如何不想她》的歌词,刘半农作。他是江阴人,借助于长江上的一朵微云传情达意。
古今中外的云朵都那么重要,久久仰望它,就会充满诗人气质和美感。写诗就是写信,给一个匿名、隐形的读者写信。只是收不到回信而已。特别是玛丽·安那样女子的回信,特别是孩子们的回信,特别是被一个时代勒令失踪者的回信。
“我现在甚至不抬头看天了。如果我看见一朵云,我该把它指给谁看呢?”曼德尔施塔姆夫人娜杰日达最后一封情书中的天空和云朵,没有抵达收信人。从此,云朵也注意悄悄绕开一个俄罗斯著名遗孀的头顶,避免让她伤心。
悲哀的人,爱与被爱的人,诗人,身体内飘着一朵朵重要的云。
在群峰下安放身心
歌德《浪游人夜歌》有多个译本——
“群峰一片/ 沉寂,/ 树梢微风 /敛迹。/林中栖鸟 / 缄默,/ 稍待你也/ 安息。” (钱春绮)
“一切峰顶的上空 / 静寂,/ 一切的树梢中/ 你几乎觉察不到 /一些声气;/鸟儿们静默在林里,/且等候,你也快要/ 去休息。”(冯至)
“微风收木末/ 群动息山头/ 鸟眠静不噪 / 我亦欲归休” (钱钟书)
钱钟书用字最少,甚至把群峰之上那个即将休憩的人“你”改成“我”——无论你我,都是群峰之上转瞬即逝的孤独者。后来,钱钟书干脆把歌德的这首诗浓缩为八个字:“诸峰之巅,群动皆息。”完全是即将入睡者的低语,懒得再说太多的话。
似乎正是歌德的这首诗,影响了美国桂冠诗人W·S·默温,导致了《又一个梦》的生成:“我踏上山中落叶缤纷的小路/ 我渐渐看不清了,然后我完全消失/ 群峰之上正是夏天”。
两位诗人表达的都是晚境。写这些诗时,一概年少。伟大的诗人一出生就是老人,一出生就站在“一切的峰顶”“群峰之上”。之后,在山中消失、安息,像夏末落叶一般自然而然。
我喜欢默温晚年的一幅照片:满头白发,衣服整洁,安静地坐在植物中间微笑——愿意坐在植物而非动物园门口照相的男人,都有着女性们身上普遍存在的柔情。
后来读了关于默温的一部传记,才知道他的生活,的确与植物有关。这个纽约的英俊小孩,庞德的学生,多年习练诗歌后,在20世纪70年代获得普利策奖一举成名——站在群峰之上。但他知道夏天之后必然落叶缤纷,就摆脱大堆女性崇拜者的纠缠,与妻子隐居于夏威夷海边一座休眠的火山顶上,劳作不息,修复废弃的种植园,收养了几十种濒危植物,像收养了几十个断臂的孩子——
“我的词语是我永远不会成为的那件衣服 / 就像一个独臂的孩子卷起的衣袖”。
在上海,每次看见独臂孩子卷起的衣袖,我就想起这个美国诗人。他从那“卷起的衣袖”上,看见词语的存在和意义——无用而又必须,沉默而又温存——默温。
喜欢这个在野外、在群峰下安放身心的诗人——其诗中屡屡出现鼹鼠、大雁、苍鹭、夜晚、月亮、山谷、河流、天狼星、风、岁月……对这些自然物象、旧词的热衷,证明他是一个念旧的人,念诵旧物旧人——中国的苏东坡、白居易也进入了他的诗。他似乎没有写过纽约。
在旧词中注入个人经验,就像是捏着一柄锈了的铁锹,蹲在水边用沙石打磨整个下午,直到它能映出一个农夫的脸、一弯新月的轮廓。再起身,去挖掘土豆或者莲藕。
默温在名诗《挖掘者》中,假设一个、两个、八个、十一个扛着铁锹的人,次第来到路上,“而我要藏起来 / 想看这里的一切 / 这只手正好挡在 / 我的眼前 / 而我愿试着把它放下来 / 在他们透过它发现我之前”——
在默温假设而成的野外这样一个广阔舞台上,十一个扛铁锹的人,像十一个演员不断出现、登台,进入一个隐身者、一个观众的视野。他们不断扩张规模,造成对“我”的压力。必须放下、摆脱一只手的遮蔽,“我”才能主动出现在他们当中,登上舞台,加入挖掘者的行列——
对这首诗解读众多。我愿意认为,这个挖掘者群体,是由默温所敬爱的那些写作者构成的,如苏东坡、白居易、庞德、歌德,以及写出《挖掘》一诗的爱尔兰沼泽地里的希尼——
这些从群峰之上走下来的人,阵容浩大,无穷无尽。
必须把它放在一个地方
墨西哥小说家胡安·鲁尔福也是摄影家。
与笔尖相比,镜头更容易暴露内心——眼睛关注到的一切,无不源于观察者的情感:走廊上睡午觉的女孩,巨大灌木丛中的骑手,眺望远山的一个戴破草帽的男人背影,夕阳下骑驴而去的两个依旧戴草帽的人,旷野里起舞的女子,像孤儿一样被遗弃的街道,独行的长袍牧师……
“任何事情,我都必须把它放在一个地方,以便赋予它生命,让我跟随它。这样我就被领上了一条我不知道的路。与我写的东西有关的景物是我童年的大地。那是我记得的景物。一心想回忆那些岁月,这就逼使我写作……对我来说,城市并不说明什么,尽管我在一个城市里生活了四十年。跟那些知识分子在一起,纯粹是一种徒劳的、无益的、不深入的争论。”鲁尔福手捏相机离开了知识分子们,在大地上游荡、低语。
他的话,让我想起美国小说家、油漆厂厂主舍伍德·安德森,对初学写作的福克纳有这样的教导:“你必须有一个地方作为起点。是什么地方关系不大,只要你能记住它并且不为这个地方害羞就行了。你是一个乡下小伙子,你所知道的一切,就是开始你事业的密西西比州的那一小块地方。不过这也可以了。它也是美国。”于是,福克纳渐渐用《喧哗与骚动》《我弥留之际》等等小说,建立起了属于自己的那一小块地方——约克纳帕塔法县。
安德森的另一个学生是海明威,与福克纳关系不和。他说:“我不想拿大海与他的那个县交换。我觉得一个县挤得慌。”反之,福克纳会觉得大海挤得慌吗?找到属于自己的大海、县,赋予它生命,跟随它,就能成为一个伟大的书写者。
非常尊敬鲁尔福的加西亚·马尔克斯说:“面对压迫、掠夺和歧视,我们的回答是生活下去。任何洪水、猛兽、瘟疫、饥馑、动乱,甚至数百年的战争,都不能削弱生命战胜死亡的优势。” 他和鲁尔福代表拉丁美洲,在20世纪80年代给中国带来了文学上的魔幻现实主义。明清时代,拉丁美洲给中国带来了土豆、红薯、玉米——魔幻现实主义风格的土豆、红薯、玉米……源源不断涌出泥土,给我们带来“生命战胜死亡的优势”。
鲁尔福需要“一个地方”,像福克纳需要约克纳帕塔法县、海明威需要大海、马尔克斯需要小镇马孔多、沈从文需要湘西、莫言需要山东高密。鲁尔福后来写出以自己故乡为背景的小说《佩德罗·巴拉莫》,一部开魔幻现实主义之先河的小说,时间循环,空间交叠,死者和生者一同呼吸、生活。
鲁尔福的故乡苦难深重而又骄阳似火,适于魔幻现实主义的产生。这个地方,为作家的灵魂提供了一个容器、一种形式,像东方的佛龛和石窟所具备的功能一样。
对我而言,移居上海二十年,当下生活依旧以故乡中原为参照物、为尺度,继而反观自我、纠正内心。我写上海、写世界,本质上依旧是在写中原、写童年。与那些在弄堂里生长、苏州河里游泳、红房子里喝罗宋汤、复兴公园里谈恋爱的上海本土作家相比,有着根本的不同——皮鞋深处的泥土不同,生发出的脚、腿、身躯、心脏、呼吸、面容……必然不同。
“恪守诗的训诫,包括研究艺术,经历坎坷及保持蛙皮的湿润。” 这是诗人罗伯特·勃莱在《寻找美国的诗神》一文中的话。所谓“蛙皮的湿润”,即诗人应具备的对于周遭处境的敏感性与反应力,像蛙皮之于沼泽、池塘、雨季。我的皮肤目前还能保持湿润,但“研究艺术”“经历坎坷”这两个方面比较欠缺。就这样吧。
鲁尔福关于童年大地的话,让我对自己的写作稍稍心安理得。生活是什么状态,文字就是什么面貌。生活凡俗、内心平淡,适合写碎片般的平常文字,或许也能散发出碎玻璃一样的光辉——在夜晚,不能像金子照亮女人的耳垂,但有能力照亮一只蟋蟀的前途,也好。
就这样吧。只能这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