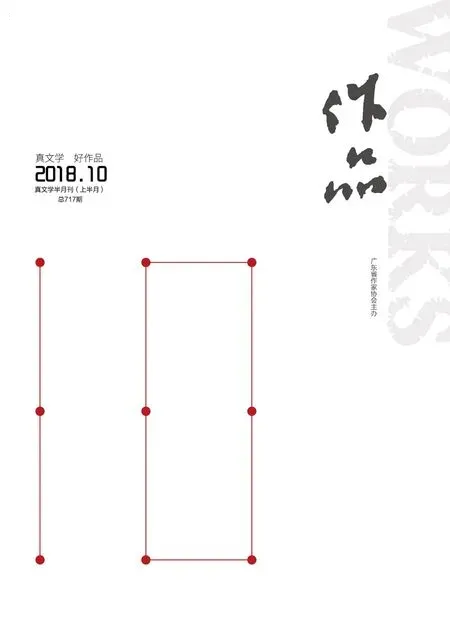内心的恐龙
2018-11-15文/陈芳
文 /陈 芳
1.恐人
恐人的内心有一只恐龙,但是她无法表达。以前她穿高跟鞋,留长头发,像个美女的样子,可是她知道自己并不漂亮,内心的恐龙是表达不了的,她总是郁闷。后来她不再穿高跟鞋,留着干净利落的短发,她想做内心真实的自己,可是她还是表达不了她内心的恐龙。时间一年一年过去了,困扰她的事情很多,她感觉越来越远地离开内心的表达,比如见人就先谈天气之类,一种平庸的昭示,后来她下决心再也不与人谈论天气,但是又会谈论房子、孩子,就是不能和人谈她内心的恐龙。时间又这样一天天过去,她有时觉得就要失去那种表达的欲望了,那才是痛彻心扉的失去,痛得她浑身冰冷了。后来,在她和丈夫的一次吵架中,她发现婚姻里处处是破绽,似乎她终于找到了表达的借口,这些破绽像冬天地里的红薯一样容易挖掘。以前她见过的一对夫妇平时很安静,吵起架来却非常有力,他们的劲头从哪里来的呢,像中了邪,她现在才闹明白。于是恐人就经常钻进这样的茬子里吵架,又终于发觉鸡毛蒜皮的小事正在改变自己,让自己变得更不是自己,这种错误的表达差点毁了她。这样不是,那样不是,如何矫正,如何前行,生活没有什么特别昭示,又有个声音总是说,这样过下去不是也挺好的吗?她最讨厌这个小声音,恐人认为一定是恐龙的敌人在鬼鬼祟祟安慰她。
秋天的天空,蓝天上忽然飘过大团大簇的白云,飘去得也快,也漂亮,它们平时在哪里酝酿呀?好像有一个看不见的大作坊。团团簇簇的白云飘过蓝天,像忽然飘过来的人生!恐人内心的恐龙告诉她,人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
可是表达内心的恐龙的欲望,把她的青春消耗得差不多了。
搬到母亲和姐姐住处后,种菜,养花,有一段平静的生活。有一天,她下班回家,茶几上的很精致很厚实的玻璃水果盘在原处碎为几瓣,凭空碎裂,检查门窗无恙,屋里的空气一下子紧张起来。对碌碌无为要警惕了!接下去茶几上的玻璃器皿总无缘无故炸裂,有一天,她还没有去上班,桌子上的一个杯子就裂开了。恐人抓紧自己的头发,差点大声喊,不要逼得这么紧吧!可是她怕吓着母亲和姐姐。姐姐说,“奇怪,昨天晚上我屋子里,桌子上的打火机自己爆炸了,挺响的,吓一跳。”恐人痛苦地扭过头去,内心的恐龙向上蹿了一下。可是,躯体像铜墙铁壁,难以动摇。她最近吃得不少,又发胖了,自己摸摸肚皮,联想起蛋糕房里的松软的东西。母亲说,“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天上雷劈树我都见过!把玻璃器皿都换成竹制的,又便宜,又安全。”恐人说,不,它们没有玻璃器皿敏感。母亲怪怪地看了她一眼。恐人仍然买回玻璃器皿,有时,姐姐和母亲会一起吃惊地看见,恐人身上发出玻璃的那种光线,她的物质在变化。恐人持续地买玻璃器皿,母亲和姐姐认为她成了这方面的狂人。姐姐说,“这几年,恐人只要做什么,都会成为做什么的狂人。”
恐人要出去买器皿,破天荒地要向北面走。以前也和姐姐向北走过,但是不可长久走下去,因为那里随着建筑物的逐渐矮小,最后落到植物上、草尖上,只剩下一片天光,就好像出现了世界尽头,看到这种景色心里会恐慌。可是,这一次恐人发现,从那里驶出一辆小轿车,恐人心里热火朝天起来,从看起来是世界尽头的地方驶出来朝气蓬勃的小轿车,难道一切还会有希望?会有绝处逢生?她像早晨晨跑的人那样跑起步子。没跑多远,感觉腿沉得像灌了铅,完全不由她使唤。恐人坐在石子路边,呼哧呼哧看着天上的白云。这时有穿制服的人手里好像拿着暴力武器,来驱赶她,吼她:“滚,到有人群的地方去,来这儿干吗?”恐人忙抬起沉重的脚步往回跑,在心里咒骂着刚才的人,为自己还不能做出恐龙的表达恨得直咬牙。恐人认为,那有一片天光的地方,世界尽头,是生发地,原始之地也许能让她表达出内心的恐龙。
母亲对她总是到处野跑感到担心,就说,再别往那边走,那边不静,会被荒野的鬼魂缠上。
“我们家里是有恶魔的,”姐姐看看母亲没在场,偷偷和恐人说,“小到玻璃水果盘碎裂,大到母亲的车祸、舅舅的死,肯定是有恶魔的,”恐人疑惑地点点头,“你信不,你不信我可以把你带到我梦里,看看恶魔是多么的真实。”姐姐总在提炼出生活里的恶魔。母亲说,不要把恶魔具体化,恶魔存在于万事万物之中。对于梦见恶魔,姐姐是有快感的,半夜里醒来恐人会看见姐姐脸上放着恐惧的兴奋的光,是恐人看到的姐姐最好的青春迹象。有一天夜里,恐人听见姐姐和母亲在吵架,还有撕扯的动静,姐姐声嘶力竭地喊,“别拦着我,快跟我一起跑,母亲你太危险了,你不要脱了衣服进卧室,恶魔在屋里,刚才我听见咳嗽,那并不是我父亲的声音!”等一会没有了动静,恐人去看姐姐,姐姐已经从梦中醒来,疲惫又兴奋地说,“我逃得特别快,我去叫上村里有力量的男人,一起俘获了恶魔,它被押到我们的会台上,他的原形真的很可怕。”她捂起脸,恐人引导姐姐说,恶魔什么样子啊!姐姐说,“浑身发光,难以描述!”母亲安慰她们,伸出瘦弱的手给姐姐盖被子,一边唠叨,“明天就要大风降温了!”恶魔,恐龙,这些令人兴奋的词,都要变成我们的梦吗?
夜里刮起大风,风撞击着门,好像一扇门最终要被撞开。恐人感到很兴奋,她在温暖的被窝里辗转,有多少这种错觉啊,其实门永远不会开的!就像她喜欢火车,在火车上总感觉是要去往梦想的地方,然而火车从来没有到达过梦想之地。这种错觉一直在消耗她的激情。房顶上呼呼响,像在过军队。后来,风停了,空气冰凉,好像垂直地掉进冰窖里。院子里的一只羊,房檐里的鸟雀都变了形,母亲说,“外面结冰了!”姐姐说,“温度表也指向零度了。”恐人说,“我们这里纬度高,是温暖之地,我们这里产的植物没有零度的,我们这里的动物也没有零度的,可是,忽然我们这里就零度了,零度是飞来的!”姐姐说,“这里总会生发希望。”
恐人和姐姐经常交换梦,把彼此带到自己的梦里。母亲越来越瘦,还日夜为她们操着心,为她们支撑着平静。
表达内心的恐龙于是呈现出平凡生活的状态:种菜,养花,放羊,不惜花费大量时间发呆。
母亲在半夜里忽然惊醒,叫醒恐人,去看看蔬菜棚,我听见大棚的塑料膜被风掀起来了。恐人忙穿好衣服,又叫起姐姐,一起去看大棚。黑灯瞎火的,两个人深一脚浅一脚往前走。每当夜晚两人在一起,就都戴上了面具,彼此看不清,她们就只靠感觉交流,即使戴着面具,恐人也能想象出她那丰富的表情。恐人说,我最不喜欢半夜塑料的声音。姐姐说,在我们的村子里,一刮大风,就有塑料声响起,大概有大大小小一万块塑料布,窸窸窣窣,它们传出非自然的声响,像是什么东西在进攻,步步紧逼。夜里遇到的人都是戴着面具的,因为大风,起来压塑料膜的有好几家的人,恐人发现他们都戴着不同的面具,他们都能用直觉知道谁是谁,在做什么。这些平常人,他们有不平凡的内心,他们平时珍藏着自己的面具。恐人听见一个戴着面具的人大声喊,快把西边角上压好了,有一阵龙卷风要过来了。然后,恐人感到一阵天旋地转,姐姐大声呼喊她,跌跌撞撞向她靠过来。可是风太大了,她被推拉着向前走,姐姐怎么也靠不拢她,她伸出手上下左右摇晃着。十几分钟的煎熬,风总算过去了,恐人和姐姐离得更近了。那些邻家人,他们的面具更加诡异了,有两个人的面具变了形,大概是被大风拧的,显得很狰狞,恐人不敢多看,尤其在这夜里。但是恐人看到有一个面具背后的人脸,已经筋疲力尽,他刚才和风魔搏斗耗尽了精力,他一下萎在地上,恐人吓了一跳,害怕这个人有心脏病,其他戴面具的人都很漠然,不去理会。果然一会那个萎在地上的人直起腰身,站了起来。恐人松了一口气。恐人从此不会再觉得这里的人是些混天黑过日子的,他们都有惊人的一面。
恐人和姐姐与这些戴面具的邻家人分别回家。恐人又显出空前的兴奋,对姐姐说,“你看,我以前萎靡,现在半夜里都这么精神抖擞,我内心的恐龙起了作用,我们现在的生活多么好啊!这里可真是好地方!”
姐姐说,内心的恐龙,恶魔,理想,不会轻易被表达,它们是难以显现的高潮。我们是普通人,这种夜晚是很难得的,我们的母亲还躺在床上,我们快回去吧!
2.发芽
风一次一次扑打窗户玻璃,是春风,它包含的万物信息惊醒了我。风特别空洞,好像根本没有什么万物。我走出屋子,各类草木都在发芽。在这个庄园,每一颗萌芽的种子都有它的引领者,很小很小的引领者,在春天如果我留心,认真体会,就会把它放大,引领者领着它的种子长出叶片、叶芽,再针对下面的泥土扎下去,直到光明的到来。每一粒发芽的草籽都是独特的,谨慎的,它的引领者是唯一的,是排他的。说春光一片大好,这一片并不是混淆不分的,我是混不进去的,它们是每个引领者的宝贝儿。它们的独特和唯一构成的一片使我感觉到孤立,这种孤立感又好像就是大好春光的角落充斥的阴暗。
一到春天我就特别有劲儿,庄园里春闲,有萌发的力量在身体里回旋,没有方向突破,力量感觉到了黑暗和阻碍,就和它们较起劲来。春风在空气里爆裂,许多微小的信息四处传播。姐姐已经在田地里挖野菜了,她的工作好像就是一年四季挖野菜,晾晒,储存,有一段时间仓库储存野菜过剩,就去送给亲戚朋友。好像挖野菜就是她毕生的事业。她小时候那么聪明,有才华,我一直以为她挖野菜是潜龙勿用韬光养晦,以后会做出什么来一鸣惊人。可是现在看来,她快老了,还是不见动静。难怪有人说,聪明的人成不了事。不知道她耽于什么,她都经历了什么。我们虽然处于彼此的眼皮下,可是在我们庄园,是有其他维度的空间存在的,只要能穿过一面墙,进入一扇门,甚至进入一片浓雾,都可以进入另一个天地,但是需要勇气和智慧,不然就会撞得鼻青脸肿而不得法门。她无心在我们的维度空间里做出点什么,我们庄园只是一个表面上的秩序,有一些小孩子,经常来破坏她的劳动,为此我还帮她追撵过几个小孩子,但是实在感觉不到什么意义。我倒感觉那些小孩是来解救她的天使,还有一些外来的动物,看起来鬼鬼祟祟的,吃菜籽的小鸟也随时降落,它们像是来自外面又好像是内部。我路过时想不跟她打招呼,可是她感觉灵敏地发现了我,她送给我一把奇怪的青菜,我从来没见过的,它新鲜的气息扑面而来,我疑心她是从另一个空间带过来的,另一个空间的她会是什么样子呢?我的姑姑半辈子都在一个矮屋子里面做衣服,总是准备出门的衣服,可是我知道她一次也没有出去过,她害怕外面不安全,久而久之,她就不再出庄园半步。她有时会送我一件衣服。也很奇怪,她不出去,衣服却一件一件追逐潮流,我问她灵感从哪儿来,她说她的信息来自宇宙的变化。相比她们,我就很愚钝,也不专注。不过我总有一些想法,我想一边生活一边记录,可是在这里我憋得团团转都找不到纸,没有白纸可以写,只有一面一面的白墙,于是我就忍不住要在墙上写。可是,庄主这时就会出现,因为他不止一次发现了我,开始以为是我顽皮,后来发现我真的要出手写,就严厉地斥责我,不管我怎么解释,他都说我狡辩,让我保证不再乱写乱画。我看见了白色的墙壁,就感觉它是为我准备的,园长就在附近,我只好克制再克制,让水倒流一样地回旋。园长神通广大,谁知道这园子里哪只蝴蝶蜜蜂是他变的,哪一只又不是他变的呢。每一个小的声音传到园长那里,他都认为声音很大,每一件发生的事在他那里都雷霆万钧,因为他害怕那些事是命中注定的,他大概一直在念阿弥陀佛。他说,我整天提心吊胆的,害怕每一个消息,就算有什么事你们也不要在半夜里打电话给我,那样我的心脏会咚咚咚跳得我受不了。我们都很照顾他,有事尽量不麻烦他。年复一年,我终于知道,现存的生活就是这样在我们的克制中稳定着,事物之间,人物之间,也靠这种克制实现了万有引力。有时我和园子里的人面对面说话,他们会突然噤声,让我担心,一个球体停止了转动,它会怎么办,它掉落向哪里。我姐姐我姑姑就会转移大法,我也见过她们在白墙面前徘徊,忍不住白墙的召唤,但是她们很精明,她们很快就知道该怎么做了,这个园子里不缺的就是方式,有很多项自由。夜里拆迁队就在不远处行动,我听见叮叮当当的砖瓦声,暗自惊喜一下,又惶恐不安,毕竟庄园存在已久,是我们的根据地。在一次无奈的思考之后,我去修剪果木。我走进果园,果园就变成一个大森林,迂回曲折,我想回返很难。我明白它是这样让我远离我的理想,无论往哪个方向走,我走上的哪一条路都是南辕北辙的,也只好一直走,一棵树复制另一棵树,一行树分裂为两行树,越走树就越多,我只是经历它们的自我实现,我和它们的个体一样,没有思想。这些无穷的树木在我的失神里,闪现一只魔掌,一个手心,我惊异地捂住了眼睛……这里什么都具备很大的规模,走进酿酒坊,会有一排排的坛子,走进工具房,有一排排工具,我以为误入其中,却又是真实的,它们形成规模就是为了让我放弃希望,专心经营,死心塌地。我走得头发几乎白了,我拿出了剪子,我要修剪树木了。风很大,果木树上什么也没有。还要再把树枝剪掉一些,我好像在虚空里做虚无的工作,也许成果终会到来,但是此刻我失去了信念。无论我做什么,每一个举手投足,都增加了我与理想的距离。春风扑打树木,空洞地,我总听见它一下一下扑空了的声音,它开始绝望了。我忽然想起很多年前的一件事,有人约过我,想起这件事时我在树杈上打了个寒战,差点摔下来。那时他约我我还没有准备好,现在,我觉得我准备好了,我准备好了,忽然间我浑身充满力量,血液四处奔突。在一个晚上,刚下过一场雨,湿漉漉的,又一些草木萌发,我借了它们的气场,混在它们之间,给外界发出一条信息:我准备好了!我还签下我的名字,在签我的名字时,我的名字震动了我,因为在这里我的名字不被呼唤已经很久,我几乎要忘记它了。信息首先被庄主截获,他把证物放在我眼前,气得捶足顿胸。我非常同情他,又很惭愧,他应该是我们的智慧老人。他问我准备好什么了,我说我也不知道我准备好什么了。他让我必须有所交代,承认错误并忏悔。可是我觉得我没有错,你去问别人,她们都会认为我是一个胆小怕羞的人,从来不想违背什么,他说你王顾左右,将要错上加错,作为惩罚,断我一个月的水果供应。园长最后又语重心长地说,要与园内实物相印证,不要追求虚空里的东西,春天也是有凶险的。你修剪果木要专注,不要形散神也散了,散了神,路就曲折了。我不断地点头,我也害怕曲折的道路,那是让我无比焦虑的梦。果园边是水塘,水塘管理员对我说,你的信息发送时分了叉,如果用量子信息,会瞬间发送成功,可是量子信息是外面才有的,我们连接不上。他说前两天水塘里的水突然失去浮力,两个游泳的人差点淹死,我就心里惊悚,是不是我惹的祸,破坏了园内的和谐。我低头看那些热带鱼,它们拖曳尾巴优哉游哉,忽而转身警惕对我,好像设防我。不断有人问我,你准备好什么了?我说我也不知道,地球从来不把内核打开给人类看。我感到我的尊严像路边的小草一样被人践踏着。信息的另一个分叉,是我朋友收到的是一条我下了很大决心才发出的同一条,它在空气里呼呼地响着,喘着粗气,进入电线就成为电,进入光缆就成为信息,进入声音成为声波,进入水成为涟漪,但是他感觉不到它的力量,于是这条信息就像强弩之末,委顿了。我朋友还是回复了我,只是一个疑问的表情符号。时隔多年,早已心无灵犀。他又问,发错了吧?我回答,大概是发错了。可是,这并不妨碍我,我浑身仍充满力量,仍是我准备好了的状态。
我准备好了是我和我的身体的一次密谋。我把这条信息发送到了云端,为我储存。
这个春天终于所有的草木都发芽了,我体内也有一个引领者,也是独特的,排他的。
3. 鹤
黄昏,一只不是本地所产的大鸟从天而降,落到院子里。过路的鸟,大概是与归家与迷路有关。第二天早晨忐忑不安的鸟儿会不见踪影。第二天刚刚有些天光,阿梅起来喂牛,院子里有鸡鸭,阿梅还要绕过猫狗。阿梅看见一只鹤,细颈扭向后背,细脚伶仃的长腿稳稳地站在院子一隅。发现它是一只鹤,阿梅擦了擦眼睛,走近它,它也扭过头来,看着陌生的阿梅。阿梅说,咦,你怎么到我们家来的?它的细颈非常优雅,弯度也非常有力,它的喙很长,有一个瓶子那么长,它的腿脚简约,适合在仙境摆放。阿梅惶恐地不知道要发出哪种疑问,她去后院,想找东西招待这位贵客,或者说留住它。等阿梅从后院拔些菜来,鹤已经不见了。她懊悔地几乎坐在地上。
早晨的节奏快而凌乱,这是一个大家庭,大家都有事干,阿梅想把看到鹤的事宣布给大家,和大家分享一下,她激动地认为这件事会在平静的生活里激起浪花。可是她发觉自己很久没有在这个家里说过话了,那平时的喧哗里都是谁在说话呢?大家在吵架时都委屈地说自己不敢说话,都尽量闭嘴,少说多听。母亲背着篮子去地里了,姐姐蹬着梯子上房顶了,不知她上房顶做什么,这项活是不是姐姐每天要做的,和生活到底有什么关系。弟弟的身影在周围穿梭,好像脚底穿了溜冰鞋,只是阿梅不知道他在做什么。其他人也没人面对她,无暇顾及她。很久没有发过言的阿梅,忽然感觉公开在大家面前说话是件羞愧而突兀的事,有点难以启齿。她觉得说这事真不合时宜,就想等机会再说。而且一早上大家都像没看见她,好像她不存在。她亲眼所见的鹤退回到昨晚的梦里,梦境与现实的界线模糊了,鹤对她也失望了。她好像在这个早上游来游去,当她想做一件事,或者仅仅想说一句话时,她必须触摸到现实的硬地,而她感觉到的那就是现实的硬地很快又被淤泥淹没了。对真切的场景描述的第一时间就这样错过了。此时阿梅听见知了叫,特别奇异的,保证以前谁也没有听过,那种由内向外扩散,酷似超声波,可是大家谁也没有听见。阿梅也想使用超声波和大家交流一下。
正因为她没有用嘴描述,鹤影就一直停留在她脑海里,经常一闪一闪的。在喝水时,她想象那只鹤细长的颈,仿佛被她使用,水通过细颈落到肚子里,有一段流程是舒缓的,然后是那种美妙的坠落的感觉,仿佛她已经体验到。阿梅和阿娟每天在劳动之余都要写写画画。阿梅拿起笔时,又好像是手握着那只鹤的喙,不管她的身躯多么笨拙,思想和精神汇集到尖尖的喙,挥喙写下的字,让她感到自己产生了独特的见地。鹤在改变她。
如果不告诉任何人,这事她将如何承受,她的心理没有那么强大。可是外面的人们还是知道了这件事。我们的信息总会被邻人窃取,从墙洞被窥见,或者风把话语带出去把声音放大,这次也不例外。鹤飞走三天之后,外面沸沸扬扬,可是家里还是那么安静,都装作不知道,或者等待反应扑面而来。外面的人们从她家的门缝里推进来一个人,带着事件的反作用力。他有些羞涩,阿梅看见他总是扭脸,好像急需一个面具,不愿让人看清楚他的面貌。他说他知道阿梅和一只鹤有一面之缘的事。家里人热情款待了他,庆贺阿梅见到鹤的事件的成立,毕竟这也不是一件坏事。他们一起喝茶到很晚,大家热情高涨,都表示不愿过庸碌无为的日子,而平日大家的忍耐都是无可奈何。原来每个人都在心底有自己的向往,甚至因为一个不切实际的发言而发生了争论。
阿梅到了城里的咖啡店,她喜欢这种脱离了基本生存的环境,或者离生产劳动越远越好。而她每次去城里,都有路边的人幸灾乐祸地在她后面盯视一会,好像他们知道阿梅的前路一个坑连着一个坑,凭他们的经验,阿梅已经在他们掌握之中。
阿梅以为在这里可以躲开关于人们对她见到鹤的这件事的议论,可是她从小酒馆老板和顾客的眼里好像看出,他们知道这个人是见过一只鹤的那个人,见过一只鹤的人和没有见过鹤的人是不一样的。一会她听到人们的那种目光变成低语,窃窃私语,像一群蜜蜂在嗡嗡,像一群小鸟在啾啾,声音越来越嘈杂,好像在追逐什么,逼迫什么,好像有什么要诞生。阿梅感觉自己的身形逐渐优雅起来,虽仍然保持坐姿,却像一只鹤那样与众不同。她低头喝饮品,忽然那液体从杯底被吸上来,她在使用它的喙。四周的声音就不再那么集中那么紧张,而是散开去,松弛了。阿梅像一只鹤那样站起来,踱步出了小酒馆。
阿梅虽然内心起了变化,却仍然在养牛。牛特别能吃,好像胃口又大了,阿梅一个人筛草根本供不上它吃,它伸出舌头疯狂卷草。她透过它的舌头看见里面有一个魔鬼,一个隐藏的会动的小魔鬼。阿梅扔了筛子,恐惧使她半天缓不过劲来。卖掉这头牛吧,阿梅乞求家人。母亲说,可是没人买这头牛,因为谁都喂不起这头牛。阿梅问那怎么办,阿娟说先这样吧,我们先自己留着。家里的许多东西本来不需要的,留着留着就成了自己的,赖在自己家里了。姐姐阿娟又说,我们的两只猫虽然吃得极少,可是太闹了,总是拿我的身体当树爬,一天爬好多次,露出的利爪抓得我生疼。阿梅说,那就送人吧。阿娟说,你现在说什么都轻省得很,我们不是指望猫捉老鼠吓走老鼠,要不我们的鸡鸭就被老鼠黄鼠狼拉走了。阿梅说,哦,这么麻烦啊。阿娟生气白了她一眼,因为听阿梅的话,好像她已经跳出了这些琐碎的麻烦的事,她想狠狠地敲击她,我们现在的生活难道不值得珍惜吗?阿娟也能看出阿梅真实的变化,可是她知道这是徒然的,没有人来救她,这只是一种状况而已。她把牛缰绳恶狠狠交到阿梅手里,阿梅只好接过缰绳又去放牛了。在草地上她看着牛的肚子慢慢鼓起来,在某一个侧面上像升旗一样。阿梅在这面旗帜下,在草地上躺着睡了一觉。快醒的时候,看见有几只小松鼠样的小东西在她身边跳来跳去,她问,“你们是谁呀?”
它们回答,“我们一直在你的内心工作啊,这一段时间我们为你工作好累啊,就出来玩一玩。”阿梅吃惊地问,“我内心的工作者?”“是啊,比如你吃下一个高蛋白的鸡蛋,我们就努力工作,把它消化吸收成你的营养。当然这只是一个比喻,我们不是物质工作者,我们是精神和思想上的。”阿梅醒来,看见牛的肚子更大了,显得很蠢。她站起来,刚醒来也没忘记像一只鹤那样,在身体的物理支撑上透出细脚伶仃的美,在行动上先行。阿梅看见邻居家的女主人走过,她有钱喜欢装扮,可是总有点让人感觉不对劲,上身宽大腿脚细长走路姿势像是一只鸵鸟,而且她的上衣下摆都是花的。而她的女儿走过来则吭登吭登像骆驼。她们都透出生活的实力,嘴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阿梅一到她们跟前就不会说话了,或者说话变得很艰难。那母女二人路过阿梅身边,突然爆发出一阵刺耳的大笑,阿梅这次没有低头看自己的鞋子,她想反正自己得变得不像自己。
鹤的事渐行渐远,阿梅从懵懂中醒来,好像变了一个人,看什么都无所谓了,把自己最心爱的裙子扔给姐姐阿娟,“你不是要穿我这件衣服吗?拿去穿吧。”她的一个首饰,也不再放在首饰盒里,而是随便放在哪个地方。有一天她午觉醒来,感觉脑子昏沉,情绪很灰。她拿起一瓶香水,拧下瓶盖,发现里面是空的,打开一本书,字里行间找不到她珍藏的字义,她还以为等老了可以慢慢读呢。阿娟让她往院子里接水管浇菜,她看了一眼水管里面,惊讶地发现那里面有一个不小的悬崖。
牛仍然不能卖掉,看来只能老死家中,荒谬啊,大概是家里根本不想卖掉。好在那魔鬼一直隐藏在牛舌头后面,只在阿梅喂牛时吓唬她。预感到魔爪张开着,阿梅很谨慎。偶尔想起鹤,阿梅产生了疑问,到底鹤是什么?现在她能从日常生活中随意找到鹤的形象。比如他们使用的鹤嘴锄,它们的脖子真是碰巧了。有一天阿梅又看到了鹤,等她走近鹤时,发现那是一把钢铁打制的鹤形镰刀,它们如此神似。鹤并没有远离,它就在生活中。有一次在田园,她老远看见一只形似的鹤,大小也差不多,姿态优美,令她无限遐想,慢慢走近,那是一株玉米,未舒展开的蜷缩的尖部像极了鹤的颈部,阿梅眼睛有些湿了。
4.薄
在梦中薄丢了女儿,着急,痛哭,寻找,蓦然醒来,很快释然,这个梦根本不能成立,因为薄没有女儿,也就不会丢。梦被推翻,但是梦中情形真实逼人,梦应该是人生的补充,或是潜在的命运。潜在的命运总在提醒不要忘记它的存在,就经常让人做梦。薄总感到自己的盲目,自己的寻找,确实有另一个我或多元的我虚拟地存在。一棵树,它出现分支,一个分支,然后又有分支,形成很密的格局。树枝上叶子对仗工整,人的分支和一步一步对仗的叶子,在虚幻中,它紧贴人的现实,只是人看不见。而虚幻也离不开实体,不能凭空创造。当薄有一天是一个乞丐的感觉时,梦见自己成了国王,那种乐融融的体验,像找到了自己的另一半,独立完整,可以休矣。薄也幻想情爱的另一半,他也时常来紧贴自己,但是薄嫌他妨碍了自己,就驱逐了他。薄呆在家里,因为她的另一个未实现的我经常来提醒她,让她感到自己很扁,很灰,而那另一个我却很丰满,如果她是一个奴隶,另一个我就是一个女王,她和女王的差距就是她的心气的高。她就那么认识自己,呆在那样的落差里,理想那么高远,几乎没有实现的可能。
为了增加自己的厚度,有一天她去一个大城市。当薄走到人群中时,她就感觉自己可以有多元的人生,惶惑中像撒开了一把绳子,不同的她在不同的人群中,有不一样的人生。诚然书店是传说中的,这里是一个分店,门面很小,却称为配送中心。薄走进去,发现很小的门面里面空荡荡,然后发现向下的楼梯,顺着楼梯走下去,下面是一个豁然开朗的天地。工作人员正在认真工作,收银台的电脑打印机发出打印的声响。好像她从地面掉下去了,又进入了一个魔幻现实的领域。她想起了那些存在于地下的知了。工作人员看见薄,觉得她很陌生,她自己也有点畏缩。她的雨伞拿在手里,工作人员怕她把书弄湿,就说,你放在门口的桌子上。她找了半天找不到桌子,不得不继续拿在手里。工作人员有点不耐烦,就顺手拿下她湿漉漉的雨伞,挂在一张小桌子角上,小桌子才终于出现了。薄紧张地出了汗。她不停地矫正自己的认知,乍看上去那是一本书,那其实不是书,那个角落出现的门,其实不是门,是一幅画。她拿了一些文具盒书,企图还价,“诚然书店所有书都是按定价出售的!”工作人员不无客气,语气坚定。按照收银员的引导她报出自己的店名,收银员在电脑上找到了她的账户,她很吃惊,自己怎么会在这样一个地方有账户呢?可能因为这个配送中心太大了,信息也一手遮天了吧,也许是很久以前和这里打过交道,这个中心也是有它的前身。她在这里转来转去,差点迷了路,然后听到广播说要关门了,薄才想起自己来的时候天色已经不早。她就向外走,又顺着台阶向上走,然后,她像结冰时被析出的一片冰,来到了水面。再次回想,虚幻之中有一个你的账户存在吗?火星上是否有一个火星的你呢?弄错这种秩序,会出乱子的。她觉得应该是她在这个店里取了货之后,这个店才存下她的账户,不应该是开始就有她的账户。她是在见到他之后,觉得很久以前认识他,他是她以前在一个城市里暗恋的人,或者上辈子,其实不是,她和他应该先认识,后来她才和他恋爱。
有时薄感觉自己是水面上析出的一片冰,薄,没有高度和厚度,二维,极端。可是她回头,看见了以前的自己,三维世界出现了,她不会再进入爱情的黑暗之中了,她终于进步了。在诚然书店有一个她的账户,这让她在情感方面开悟,他爱那个男人与那个男人对于她,和她在诚然书店有一个账户是不是一致的呢?他为她开设了一个账户而已。
在诚然书店有她的账户,她觉得那为她虚拟了一种人生状态,一种空间,在这个空间,她可以增加自己的深度。可是她后来没有再去过那里。也许那里的会计在查账时会略过她的账单。她认识的那个人也许会想起她,在大海里拉动一下思想之网,她感觉到那网收紧一下而已,然后仍然是海的自由。我到底在网中好呢,还是在网外好呢?她也怀疑过自己的自由。
那紧贴着现实的,或者远远地注视她的现实的,在火星上有一个薄,或者在一个更广大的城市也有一个薄。那个薄是画画的。她的作品抽象,有生命力。这个次元的薄,感觉画画能更好地表达自己,但是她又感觉写文字是她的另一种形式,文字更原始,不容易被利益利用,像水一样普通,像沙子一样平易,可是它们变幻起来可是刹那令人不能应付,也是没有穷尽的。有一天,她遇到一个神经兮兮的行为艺术家,不知为何薄被他吸引,感觉一股新鲜的气息扑面而来,一棵小苗又开始了它的生长,那一瞬间,她又处于薄的状态,二元,看不见自己的过去和未来。在一次讨论会上,薄发现他的思想是浅显的,可是他自以为深刻。众多的头衔,使得很多人粉饰他,薄开始鄙视他,一个人没有有力的思想,很难说再让他吸引薄。再次交谈时,薄看到自己虚幻的那一部分,像阴影然后又像光环罩住了那个人,薄看见他没有虚幻的那一部分,薄感到很失望。即便是很短,爱情得像一棵植物,慢慢经历它的过程,一意孤行地经历它的自身生长。它是黑暗的,是狭隘的,因为它不能看到全局,只能看到一部分。
薄的门前有一棵树,这是一棵有魔法的树,薄只要看到它,来到树下,就丢失了很多想法。仿佛是它的完整,它的分支,它的格局,完善了她的人生。树上有很多知了,每年的数量在增加。知了的叫声很难听,很多年了,薄认为知了的叫声应该改良一些。有一天,她在屋里听到一只知了发出特殊的声音,类似水面的涟漪,一圈一圈向外扩散。啊,这只知了是怎么觉悟的呢?她想。树上的知了知道它们的音乐不悦耳,却无法通知在黑暗的地下成长的幼虫,因为它们在无知的状态下就已经进入与世隔绝的黑暗中了。就像人,像恋爱,她看着进入恋爱的女友很傻,却无法劝说,而让她落得凄凉的结局。就连她自己,不是也一次再次进入恋爱的黑暗之中了吗?认识了地下的黑暗和枝头的光明,有一天,终于有一只知了成了一个会发出超声波的知了,她开始运用超声波同这个世界交流。这之间经历了多少艰难的觉悟,不苟同于他人,被冷落,孤独,穿行于过去未来的壁垒,但是很值。
对于另一种虚幻的人生,或者多次元人生,包括过去的自己,薄想告诉她们,她们很可怜,无知,盲目,薄不能引导她们,因为她们处于不同的时空,不同的维度,即使相见,也会感到陌生,互相轻视至可爱,甚至还会仇视,无法沟通交流。
即使薄如一片云,也会在天空慢慢衍生,有了厚度。经历了这些碎片化,不管是薄冰,还是树上的知了,还是树,书店,艺术家,这些碎片塑造了她的五官,不太漂亮,容易变形,塑造了她的身体,仿佛也可以折叠,可以薄,可以厚。有时她活动一下,听见各处的骨节咔吧咔吧响,容得下变形金刚来施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