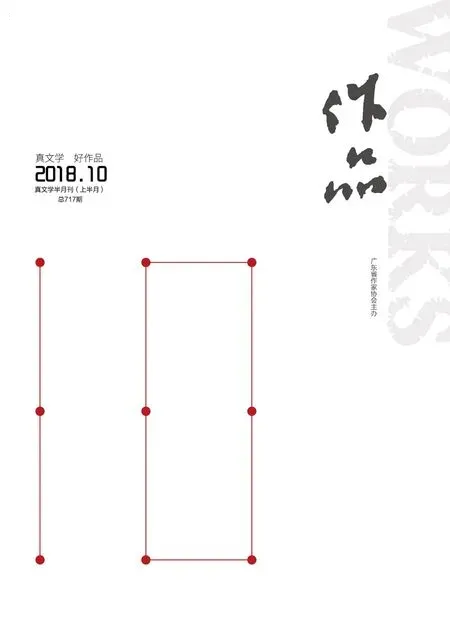评刊团线下评刊精彩评论辑录
2018-11-15作品评刊团
文/《作品》评刊团
编者按:
2018年7月28日,《作品》杂志召开了评刊团的线下研讨会(第一季),来自全国各地的评刊员近40人,聚集在省作协大楼一楼岭南文学空间,参加了这一盛会。会上针对广东省五位青年作家作品进行了研讨,这五位作家是:李衔夏、叶清河、马晓康、王哲珠、周齐林。王哲珠带来了新出版的中篇小说集《琴声落地》。叶清河的《农耕记忆馆》和马晓康的《墨尔本往事》的小说评述,本刊已经发过,这次不再编发;本期撷取了对李衔夏小说《子弹做的刀》(本刊今年7月号)、周齐林散文《底色》(本刊今年1月号)、王哲珠小说集《琴声落地》以及发表在本刊今年4月号的中篇小说《姐姐的流年》的评述,巧的是,中篇小说《琴声落地》首发本刊2015年6月号。茨平是本刊的评刊员,他的散文《开厂记》 (本刊今年7月号),引起了评刊团的热议,本期也节选了部分评论。
王哲珠中篇小说评述
1. 《延续》 广西桂林 熊焕颖
小说的高明之处在于,一开始便把两性之间的对抗悄无声息地植入具体的家庭困境中,从而使小说获得关注社会现实、思考女性问题的品质。
小说的叙事重点是王若雅的爱情如何从陈实转移到李七丁那里。签协议后,王若雅与李七丁结婚,住在李家。习惯城里生活的王若雅开始并不适应农村生活,感到陌生孤独、迷惘焦虑;但随着李家兄弟,尤其是李七丁对她无微不至的照顾,以及恬静美好的乡村生活对她心灵的涤荡,她意识到自己只是骗局里的“棋子”。这是小说第一次出现“棋子”,暗示了王若雅女性意识的觉醒。她明白了在陈家“妻子”只不过是个传宗接代的“棋子”。在城市的陈实忙于公务,对王若雅敷衍、漠然,无异于使两人之间的爱情雪上加霜。小说虽然是以单线开展,但至此文本意义已变得繁复丰赡。作者巧妙地将女性/男性、农村/城市、传统/现代、自然/文明等一系列二元对立的关系融入小说的人物和情节设置之中。在某种程度上,李家兄弟代表了农村、传统和自然,而陈实及其家人则代表了城市、现代和文明。这两组人物在“延续香火”的传统问题上产生了交集,本质上却是上述二元对立的价值观念在王若雅的身体上发生了冲突与碰撞。她的身体就是战场。
当王若雅生下男孩后,陈家希望尽快结束协议。但是王若雅不肯走,陈实觉得她不可理喻。她眼里噙着泪说“我是一颗棋子吧,你想挪哪便挪哪”。这是小说第二次提到“棋子”。这次则暗含了她的反抗与抉择。李七丁对王若雅、对小孩也渐渐产生了情感,不愿离婚。最后陈家出大价钱要强行结束协议。王若雅质问陈实:“我是一件东西?任你这样安排来安排去。”在登记处,王若雅最终选择不离婚,与李七丁在一起。小说结尾温暖且寓意深刻,王若雅夺回了自己身体的自主权,既是女性对男性抗争的胜利,也是对现代都市虚伪婚姻和文明的一种滑稽讽刺,同时还昭示了女性重获人格尊严和实现两性平等的可能性。
在《延续》这部小说中,我们不仅看到了王哲珠的文学旨趣和抱负,也能感受到她对当下社会女性问题的关注与思考。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她的写作带着人性的光芒和温暖,犹如上帝悲悯之手抚摸着那些弱小和受伤的灵魂。
2.《琴声落地》 广东汕尾 蔡赞生
作者在进行虚构叙述的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始终还是现实世界的可能组合,以及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某种现实生存状态。“物”与“人”之间是对抗的,人的内心极度困苦时,物就会愈加闪亮。这里的“物”,是通过老独手中操持的扬琴来体现,“掂起琴竹,老独整个人变了,褪皮般褪去层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琴架前的他成了月下的烟,渺远、神秘,目光蒸腾,表情游离……”只有对着扬琴时,老独的生命才是有光亮的。
人与人之间的靠近实际上是远离,远离则是另一种靠近,这构成了小说中的一种常见表现形式。人追求一种对生命的肯定,或者说是一种理解的生存。小说中重在表现乡村的孤独和生存的慰藉,这种慰藉主要体现在“花旦映婵”对“王扬琴”的青眼有加,二胡老建对扬琴老独的惺惺相惜,女儿阿芝对父亲的理解支持。
“走,一起走,你弹琴,我唱曲……”这一句当是天底下最美的话语,无关爱情,而是孤独的生命中最美的相遇。毕竟故事是故事,日子是日子,即便有瞬息的情爱,也仅是沉醉于故事之中的错觉。“花旦映婵”对“王扬琴”的感情以及他们之间的默契和琴歌对和,本身就是一种高山流水,知音相遇泛起的涟漪。老独心底很清楚,“我就是弹扬琴……”但终究在不被理解中成为呓语。
老独的扬琴与老建兄的二胡,同样也是知音。但因为性别,所以他们之间的情感能够自然地存在。老建的灵前,老独孤独地敲响扬琴,琴声“轻、缓,从白帐布后出来,人莫名地感觉琴音带着灰色的凉意”,老独用琴竹说,“老建,都走了,你走了,她也走了。”在这里,老独对“她”和“他”的情感又有何区别?
生存意义上,知音的交会总在相互错过中绽放刹那光亮,但又转瞬进入了不可再来的永恒等待。花旦的远嫁和二胡的逝世都是一种自然的离场,在贫瘠的生命渴望被理解的孤独中转化成了绝对的遥远和凄凉。
3. 《参与者》 山东聊城 崔会军
说实在的,我挺羡慕刘细平和刘腾的感情。这才是铁哥们,比亲兄弟还亲,他们之间如胶似漆,形影相随。看一眼,就知道对方心里想什么。
作者从烦琐的日常里,提炼兄弟真情,饱含深情地讲述了两个没有血缘关系胜似有血缘关系的人,老哥俩情同手足。从小一起长大,性格迥异的两个人,一辈子“粘”在一起,比夫妻在一起的时间还长,这种兄弟情难能可贵。尽管刘细平事业成功,物质丰厚,但刘腾是一个“热爱”雕刻艺术的人,他能稳住自己的阵脚,有自己认可的自我价值观,这不妨碍他们做兄弟。浮躁社会,这种真情写作是一种向善的指引。
爱和信任,让兄弟俩相互坚持。他们的兄弟感情是纯真的,种下善的因,结出爱的果。人生,得一如此知己,足矣。
4.《少年少年》 四川雅安 李洪彬
读《少年少年》是在与自己的过去擦肩而过,伴随作者手中之笔,伴着作者因“偷钱”买冰淇淋吃带负罪的心狂奔,穿过小镇十字街,走向乱坟地,又因惧怕坟地飘出会飞的“魂”,饿得实在不行,也不敢伸手去抠番薯。怕番薯叶盯着拿过钱的小手,整篇小说切入点映证小说之小的特性,又不失小说之大的特点。以“我”经常调皮吃竹片为契机带出小时候只有贫困农村小孩们共有的经历。
好作品就是一面镜子,折射出另一个自己,把遗忘于人生的过往不经意间拎起,串出无数影集。也叩击心灵,仿佛作者就是量身为自己设计好每一个动作,每一句心里想说的话,每一个心里想表达的思想跃然纸上。《少年少年》不失为忆童年之作,我想凡阅读过此作品的人,只要在农村生活过或者本身是农民的人一定引起身心共鸣。
5.《姐姐的流年》 广东珠海 刘少勇
《姐姐的流年》以细腻质朴的语触,灵动描绘出一位不甘于庸常,积极向上,改变命运的乡村女孩形象。潺潺流畅的行文,如田园诗般清新,似一曲舒缓婉约的民歌。姐姐热爱生活,心地善良,有主见,勤劳,富有爱心,虽生如草芥,却不屈就现实,在隐忍中努力地突破,绽放自己。当家庭的担当和自己的追求冲突时,灵活地调整,不断地改变自己。“我”在找姐姐,其实是发掘人性中闪耀的真善美。无论面对贫穷,流言蜚语,生命凋谢,人事变迁等各种挫折,“姐姐”都能温柔地化解,逆袭而上,在苦难里孕育出智慧之光。
作者布局谋篇巧妙,用四季勾勒姐姐精彩的流年。一名独立坚强个性的女子,塑造得灵动鲜活。从灰暗苦难的背景色调,凸显出她的淳朴和靓丽光彩,将气质和焕发朝气的精神面貌,渲染在这幅代表中国村姑的画卷上。
6.《失控》 广东佛山 侯志锋
王哲珠设置的层层氛围,好像一个地球修理工在大地上深挖,刚开始不知道给我们挖的是什么,挖下去看到水的时候,才知道是在打井。
《失控》这篇小说,也是一篇心理小说。“一日被蛇咬,十年怕草绳”,心理问题上,作者设置得很好。欧阳成认为是尹大发造成的,又认为是为了彩礼钱不嫁给他的姑娘造成的,最后认为是自己造成的。他去找尹大发,我认为是画龙点睛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