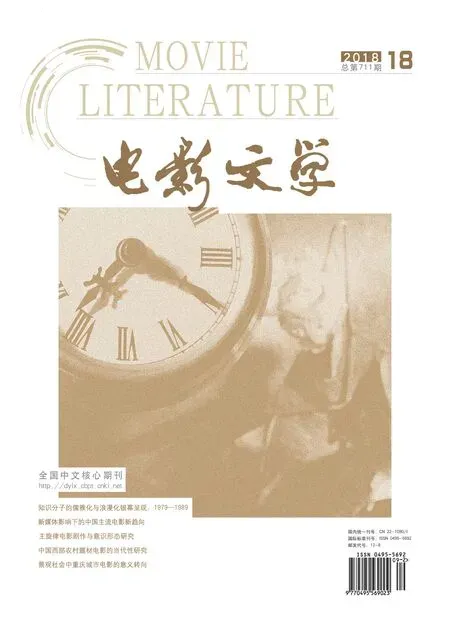西北边疆题材电视剧中的英雄与边疆书写
2018-11-14王月陈涛
王 月 陈 涛
(伊犁师范学院,新疆 伊宁 835000)
英雄是神秘而又崇高的,是每个时代的精神标志和人化丰碑,引领人们不断挑战新的精神制高点,是人类经久不衰的母题。英雄叙事,不仅是政治需要,也是社会需要,根据马克斯·韦伯的观点, 被书写和接受的英雄是所谓的“卡里斯玛”(chrisma),“象征着秩序、信仰和价值的中心”。从微观来讲,作为集体无意识的英雄情结潜藏在个人的深层心理结构中,既包含个人内心的自我价值最高呈现,如修齐治平的英雄理想,也包含源于原始经验的英雄崇拜和期待,还包含历代文本所培养出的英雄审美。
边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遥远而又未知的。虽然借由交通技术的发展,地理意义上的边疆离我们越来越近,但想象中的边疆并未因此变得足够清晰。“边疆”这一概念,从出现之始就承载了太多的想象,又在各种时代语境下由各种不同的动因被建构和重塑,不管是文字媒介还是后来的影像媒介,其所呈现的边疆媒介图景兼具传奇、异常与苦难,又直接勾连自由纯净的世外桃源或荒蛮战乱之地等意象。“作为一个疆域辽阔且边缘区与核心区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的国家,中国的国家治理和国家发展中自然形成了一个‘边缘—核心’结构。”而传统的文本中,从“核心”看“边缘”的固有视角,使边疆长久以来都是一个有异于主流文化的异质区。
当“英雄”和“边疆”这两个元素结合在一起,共同出现在新世纪的影视作品中时,会出现什么样的联系、故事、阐释意义和文化价值?当代的英雄叙事会不会赋予边疆新的型塑和意义?当给予多个英雄同一个地域限定时,将会出现什么样的意味?这些便是本文饶有兴趣的地方。
从2004年到2018年的15年间,央视播出了约15部与西北边疆直接相关的电视剧作品,平均每年一部,而其中有12部,即八成的作品,表现革命、军旅及社会主义建设。如《苍茫天山》(2004)、《西圣地》(2006)、《戈壁母亲》(2007)、《在那遥远的地方》(2009)、《化剑》(2010)、《雪浴昆仑》(2012)、《阿娜尔罕》(2013)、《丝绸之路传奇》(2015)、《马兰谣》(2016)、《沙海老兵》(2018)、《大牧歌》(2018)等,这些剧作着重表现边疆的革命、剿匪、工农业建设、国防、军垦等领域,以英雄传奇折射出国家神话,以个人的生命历程反映出民族的大历史,以正剧正典的风格类型呈现出明显的主流剧特征。剧作塑造了一大批有血有肉、可歌可泣的英雄形象,如在极端严峻形势下机智应对国民党兵变和境外分裂势力并最终英勇捐躯的解放军营长、舍弃优越生活条件到最艰苦的高山哨卡服务边防的女性英雄、一生和时间赛跑为新中国核事业鞠躬尽瘁的核试验专家、留守沙漠边缘建设边疆的军人……以及无数无名英雄。他们是“为民族利益、集体利益和历史进步做出超凡贡献的人”。这些英雄超越了曾经的“图解政治”模式,脱离“神坛”,体现出丰满的人性人情(多数作品也包含了以人性善反拨极左年代的动人情节),兼顾了意识形态功能、艺术审美和一定的大众市场需求。
剧作在建构英雄形象的同时,也建构出一个不同于中华传统书写(如边塞诗)的西北边疆形象,塑造了边疆——这一盛产英雄豪情的精神高地。英雄缔造着边疆,边疆也缔造着英雄。二者以国家意志为叙事动力和逻辑出发点,共生共荣,相互成就,拓展了“英雄”和“边疆”的书写和阐释,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以英雄为中介将边疆有机地融入国家主流话语表述框架之中,以英雄与自然的对抗与象征同构的复杂关系体现对边疆现代性的思索,以英雄主义的怀旧记忆拉近边疆与特定大众的情感纽带,以“他乡—家园”的边疆意象的重构体现国家对边疆和对建疆者的双重召唤,以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的边疆情怀实现主流话语对消费主义的对抗和反消解。
一、以英雄群像铸就边疆书写的主流底色
英雄叙事承载主流意识形态规训方向。英雄角色中一半以上为军旅英雄,代表严密的组织性、高度的纪律性,也深刻透露出隐藏于背后的国家意志,符合主流书写中的“典型”,如进疆先遣连连长、英雄团团长、“铁团”团长、战斗英雄……叙事原点无疑来自主流意识形态中心,叙事风格则有明显的集体化特征。
这些英雄作为价值主体在一定程度上代言了国家主体,其身体背负的政治象征也极其丰富,可以说其首先是政治的身体,然后才是个人的身体,他们是国家福祉的传递者、国家权力的行使者、国家意志的体现者和国家所倡导的主流价值观的承载者。英雄个人一定以集体主义的组织作为行动背景和行动指南而绝不偏离,个人的行动目标和生命理想,与区域目标、国家目标具有通约性。
边疆英雄拥有纯化的人格,超出凡人的意志品格和博大深沉的气魄,荡气回肠的人生经历,是常人难以企及的精神高峰,是主流话语寄予重要意义的人群和典范。即使是以非颂歌式的客观叙事描写有缺点的不完美英雄,也比普通人更接近崇高,具有深层的教化意义,寄托主流意识形态宣教方向,富含主流编码或曰红色编码。
同时,英雄的生命历程多放置于由“旧”到“新”的转折期和二元话语之中,将英雄叙写为使边疆从黑暗到光明、落后到先进、苦难到幸福的改造者、领导者、奉献者。革命历史经典化,“建构共同的历史进程记忆,进一步完成民族国家的合法性论证”。当英雄和边疆这两大主题在新世纪“边疆红色剧”中汇流之时,由文本间相互重叠的印记形成互文性,交叉混合构成了电视剧中“英豪报国之地”“书写青春之地”“建功立业之地”的边疆想象,此种想象融入中华民族整体的“国族神话”谱系与现代民族国家话语框架之中,为边疆形象铺就了深厚的主流文化底色和主色,“中华民族”从而作为一个共同体被有效地建构和强化,注入各民族的国家意识、历史回忆与情感。
英雄叙事的影像文本形成一个整体,具有一个文本重叠另一个文本的印记,即互文性。交叉融合,构成了电视剧中“英豪报国之地”“书写青春之地”“建功立业之地”的边疆想象,有效融入中华民族整体的“国族神话”谱系,形成了革命历史和改革题材的边疆子类型,形成了初具规模的新世纪“边疆英雄剧”或曰“边疆红色题材”,为边疆形象铺就了深厚的主流文化底色和主色,并将其统合到现代民族国家话语框架之中。
二、英雄与自然的对抗与同构显现现代性矛盾
英雄起初是从生物学意义上凸显出来的,人在艰难原始的生存环境中要活下来,需要过人的体能、勇气和机敏。自然的神秘、奇崛、伟力往往会产生让人生畏甚至渺小之感,也正是如此,英雄与自然的对抗往往会有力激发崇高、悲壮的心理体验。剧作中反复出现的自然符号,不仅构成了叙事的环境、行动的动因,更重要的是经常充当英雄非凡品格的重要隐喻和象征。英雄与自然的对抗关系和象征关系显现出当代人对边疆认知的一对现代性矛盾。
先来看对抗关系。在以往的军旅题材电视剧中,英雄对抗的多为革命的对象,即侵略者、反动派或其他人类敌手。而边疆题材电视剧用了很大篇幅,来表现人与自然阻碍的战斗。自然在这时是冷酷无情的,反复无常的风沙、被喻意为死亡的沙漠、夺去无数生命的雪崩、外来者无法忍耐的酷寒、高温、缺水……比如,《戈壁母亲》等多部剧中都出现了雪崩吞噬生命的情节。缺水,是边疆英雄必须面对的普遍的棘手问题,比如《西圣地》里,每人每天只配给一搪瓷缸的水;《在那遥远的地方》中高寒缺氧的高山哨卡上,战士大部分时间喝的是苦水,只有来客人才会去很远的地方拉冰化成所谓的甜水;《马兰谣》核试验基地里只有一喝就会拉肚子,但又别无选择的碱水。还有对人烟稀少、路途艰辛、水土不服、野兽出没等的描写都加剧了英雄与自然的对抗性。这些元素在一定意义上延续了过去对边疆“畏途”“绝境”的书写传统,强化了异质性。但与以往不同的是,在这些新世纪书写中,自然带来的困境并不会真正阻挡英雄的宏伟目标(同时也是国家意志)的最终实现,而且更衬托出英雄的非凡和国家解放和建设事业的不可阻挡。由雪崩、沙暴、饥寒等带来的死亡恐惧突出了自然的未知、陌生、无常、遥远、奇崛,加剧了戏剧冲突与情感张力,同时也激发了对崇高、雄伟、悲壮的心理感受以及英雄在这种非凡环境中取得成功、胜利后或者英勇牺牲后观者对英雄、对英雄背后的政治力量、精神力量的强烈认同感。
再来看象征关系。马克思认为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中国传统美学也有无数托物咏志之作。剧作具有强烈的区域性自然特色和审美风格,西北边疆所特有的高山、雪峰、草原、湖水有着令人折服的刚健、强悍、辽阔与包容,而这种对自然奇观的推崇与赞美实际上是对英雄超凡品格的隐喻和象征。比如《戈壁母亲》和《在那遥远的地方》都让高耸纯洁的雪山矗立在边防哨兵的身后。大西北特有的胡杨树、马兰花等植物也发挥出象征作用,《马兰谣》的片名、反复的暗示以及在片尾主人公去世前的回闪都贯穿了马兰花的精神象征。可以说用自然与英雄的同构将人非凡化、脱俗化,自然也成为英雄们的能量来源和精神给养。
对抗关系和象征同构关系,一个是对自然的祛魅,一个是复魅。这一矛盾的背后是现代人征服自然的理性科学主义和追求复归向往自然的审美人文思考的现代性困局,边疆剧作为一个特定类型将它反映了出来。
三、英雄主义的怀旧记忆成为边疆与特定观者的情感纽带
“虽然‘前过度政治化文化体系’已经解体,英雄的政治神话已成为过去,但英雄的‘神话’内核依然延续,感动着曾被红色激情点燃的中老年观众。”英雄拉近了这些剧作与中老年观众的距离,再具体点说,英雄的边疆岁月更会调动起有边疆经历的人的有关“我的边疆”的回忆。
这些剧作往往兼具宏大叙事和生活化叙事,明线是英雄的生命历程,暗线是边疆的大历史进程(既包含解放、平乱、剿匪的战争烟云,也包含如火如荼、百废振兴的建设洪流)。这些复杂宏阔的历史信息都落实在一个个具体的生命上、一件件大事小情上,展现行为,也展现行为背后的内心世界和具体情感:战天斗地的青春与奋斗激情、“革命+爱情”的革命乐观主义与理想主义的飞扬,至死不渝的爱国信仰,出生入死的豪情,散发出神性光芒;同时,也包括苦难、彷徨、屈辱和牺牲。包含了一切胜利,也包含了胜利背后具体生命所付出的惨痛代价。这些美好和不美好的心理感受,都是能切实勾起怀旧情结的重要因素。
更不用说那些生动可感的具体生活细节,它们更是怀旧的“引子”。军装、地窝子、搪瓷缸子、藤编暖壶;开荒、挖大渠、大会战;文艺女兵、新疆舞……这些怀旧元素频繁地出现(部分也业已出现在当代的怀旧消费中)。笔者注意到一个多次出现的特别元素——墓碑,在《苍茫天山》《在那遥远的地方》《雪浴昆仑》等作品中都出现了肃穆的墓群,承担着重要的叙事和抒情功能,有的直接出现在剧作的开篇或结尾。墓碑和上面镌刻的每一个名字都有着极重的历史分量,它勾起观者对英雄、英雄岁月和英雄情怀的缅怀和深沉思考,它是对牺牲者的尊重,也是对后世人的期待。
这些元素的影像化呈现营造了一场生活史的怀旧仪式,宏大叙事与日常生活叙事共同发力,以主流的题材、标志性的时代记忆、生活细节性的内容迎合了特定大众的文化消费和审美期待心理。如果说电影是一场“抵达”或“经历”,剧作则带领观众重返(或是初探)自己和英雄们战斗和生活的边疆。怀旧也同时成为一种“使用与满足”的大众消费品,将私人话语、国家权力话语和商业话语进行超时空对接。
四、以“他乡—家园”的边疆意象的重构体现国家对边疆和建疆者的双重召唤
西域诗中,可以非常轻易地找到大量以中原文化为参照和怀念中土故乡的诗词文本,在这些作品中,西北边疆是荒凉、战乱、远离中心、远离故乡的他者空间,唐朝诗人李白:由来征战地,不见有人还。——《关山月》;王维: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送元二使安西》……以及历朝历代因各种原因由中原来到西北边疆的士大夫阶层,其文本中大多将西北边疆塑造为凄凉而遥远的他乡、异域,而非故地与归宿。即使是在西域活动三十年的东汉班超,在终老之年也要上奏入塞,离开西域,回归中土。其中很难有人赋予边疆以精神及生命归宿的意义,而多将其当作离乡“失根”之心理空间。其背后都隐含着对边疆的拒斥与逃避。
而本文所论的电视剧作品群则赋予了边疆以新的现代意义。新时代英雄们以各种缘由来到边疆,有的为解放,有的为报仇,有的是为了国家各行各业的建设,总之国家需要的地方就是英雄出现的舞台,不仅是让英雄出现于此,战斗于此,更重要的是扎根于此,这具有重要的政治考虑。《化剑》中刘铁带着队伍一边改造国民党起义军,一边化剑为犁进行军垦建设;《西圣地》中以杨大水为主的英雄的战士们奉献于石油事业;《马兰谣》中的核事业开拓者们,《大牧歌》中的畜牧科技人才……这些英雄的共同点是最终扎根于边疆,事业、爱情、家庭甚至后代都在边疆这个空间里实现了从“他乡”到“故乡”的颠覆,而且无法割舍、依依眷恋,已经具备了“家园”和归宿的意味。而且作品还展现了英雄人物们的“世居”决心而非“旅居”的生存心态,呈现了代代相传、代代相守的风貌。
由他乡变故乡,由异域变家园,从“非家”到“家”的转变,让“边缘”具有更多向“核心”靠拢的气质,让观众多一些心理和情感接近甚至向往。让边疆既是一种号召,也是一种诱惑。在剧情进行中,在英雄人物内心世界的改变进程中,曾经的“关内”对“关外”想象模式也逐渐被改造,通过主人公的驻守—热爱—依恋的具体可感的情感进程,让观众也进一步弱化了传统中“中心—边缘”的区别和隔阂,逐渐建构出一个更具吸引力和精神价值的边疆象征意象,从而实现对在疆者的稳定和对外部人才的召唤,进一步显示出民族国家想象共同体的向心力量。
五、以英雄主义的边疆情怀实现主流话语的反消解
在朝着消费主义后现代社会的门槛里迈进的过程中,已出现“英雄已死”和“英雄未死”的长期争论,一方认为大众的娱乐消费引导着文化生产,英雄已经堕化成了被消解、被戏谑、被当作游戏人物去操纵的角色;另一方认为英雄并未死去,而是作为永恒的母题一直存在。人们反的不是英雄,而是伪英雄、假英雄、陈旧僵化的英雄叙事话语和扁平非人性的过时英雄。
本文所论的主流西北边疆电视剧中的边疆英雄,经过了思想解放后多元文化的祛魅和反思过程,但也绝未堕落为手撕鬼子、绣花针神功的“雷人”英雄。剧作将英雄置身于边疆,集人和自然之力,集历史与现代之思考,叙写了中华民族的民族大义,其舍小家为大家,舍安逸战困境,甚至“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的隐姓埋名,不仅对抗着图人眼球的雷人英雄,更作为一股清流,对抗着消费主义随波逐流消解一切的虚无,痛斥着只为私利忘却家国责任的任何借口。从民族发展和个人精神成长的双重角度来看,这是一个更需要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豪情的时代,有理想才不会退缩,有英雄主义才能对抗庸常和恶俗的吞噬,才能抵御“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思想泛滥,有理想和英雄的民族才能真正实现复兴。
“英雄”与“边疆”,以双重的教化元素、教化主题和教化功能服务于主流意识形态——实现对符合国家话语的公民特征的询唤和确认。在某种角度来说,这些影像可以被称为国家影像,影像书写的背后是国家书写。国家书写中的边疆英雄和英雄的边疆,不仅塑造崇高与光荣,也提醒着中华民族前进中的艰辛和危险,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时代都需要这种唤醒。尤其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阔宏流中,文艺不可缺少这种理性与冷静。
去中心化、去英雄化、后现代主义及多元思潮,尤其在当前文艺创作领域及网络空间里的世俗化、发泄化的倾向,具有解构的作用,但很难建构什么。只标榜大众不接受什么,反对什么,而否定了反对了打破了之后呢?接受价值的土崩瓦解和虚无的来临吗?却没有为大众该做什么、该往哪里去提供答案。而这些边疆英雄的建构,人与境的共同升华,开辟了精神世界里的一片热土,就是为“建构”什么而做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