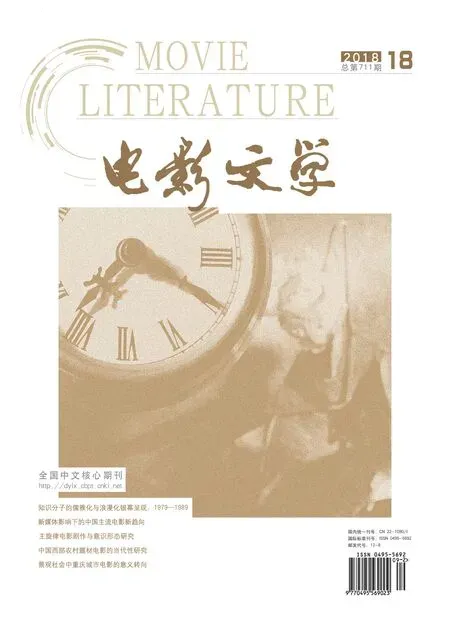中国西部农村题材电影的当代性研究
2018-11-14马珂
马 珂
(西安文理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5)
中国西部农村题材电影进入21世纪后已然没有20世纪后期那样的荣耀和光环,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迅猛发展的当下,农村也在经历着巨变,从某种意义上讲农村和县城的转变是中国当下转型的写照,所以即使在很难获得票房回报的情况下,很多导演依然将镜头对准了这一题材,并且时有精品力作出现,像《惊蛰》《高兴》《一个勺子》《丢羊》《图雅的婚事》《郎在对门唱山歌》《九号女神》《心迷宫》《天狗》《碧罗雪山》和《塬上》等。
中国西部农村题材电影发展到今天,形态到路向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也正是西部农村题材电影当代性的体现,“当代性”是“现代性”在时间上的延伸,但又突破了时间语境,呈现出空间表征。现代性在农村的铺展表现为城镇化,现代与传统、城市与农村的关系既是历时性的也是空间性的,期间还包含着意识形态的角逐和权利的纠缠。张颐武曾说:“所谓当代性其实就是指向一种当下的电影所呈现出的形态,一种在历史和空间之中所展现的新的此时此刻的电影的多重的运作和展开。”从当代性入手其实就是把握当下西部农村电影现实的一种策略。
把握中国西部农村题材电影的当代性需要我们把它放在当下新的语境中来观照,来透视这类题材作品如何想象和构建西部农村,随着农耕文明逐渐消散,尤其是随着新农村发展,西部农村的发展出现了很多新特征,电影往往是现实的投射,西部农村在电影中的呈现势必也要发生变化。
一、西部农村想象:文化符号到文化空间
笔者不止一次听到西部(农村)就是未开化的、落后的和愚昧的这样声音,说这话的人基本都是通过影视或文学作品获得对中国西部的认知。的确,20世纪80年的电影作品把西部农村符号化了,当观众看到《黄土地》中翠巧她爹那张木讷的脸的时候,立马就会意识到这张脸指向贫穷与麻木,此外影片中贫瘠的黄土,蜿蜒环绕的黄河,千沟万壑的地貌等都成为阻隔文明的符号;到了《秋菊打官司》《一个都不能少》镜头开始凝视那些中性“女人”, 性别缺失的西部女性也成为西部农村电影的一个重要符号,类似的还有滑稽的村干部等,无论人物还是文化都被符号化。
除了上述贫穷、丑陋和滑稽的符号还有一种乌托邦式的文化符号,像《那山那人那狗》《我的父亲母亲》和《康定情歌》把西部农村塑造成环境秀美、人民纯朴热情、生活简单安逸的世外桃源景象。
20世纪的电影通过“农村想象”一系列政治、道德和文化的符号构建起西部农村的镜像,在其中一直存在着缺席但在场的“城市形象”,这些镜像的构建是站在以城市主体的位置来审视和想象作为客体的西部农村的。这些作品的西部农村经验是他者化的。随着农村改革进程的加快,城乡二元的对立结构逐渐被打破,西部农村叙事的主体发生转化,城乡距离的拉近然大量的创作者有机会参与到农村的变革中去切身体会,还有一些出走又回到农村的导演和编剧,构成了当下西部农村题材电影的创作主体。
当创作者将西部农村视为他这的时候,他所用来表达“西部”的符号其实成为自己想象和思想的能指,西部成为落后、丑陋和愚昧的的象征与隐喻,要么成为出走或落魄灵魂寻找慰藉的家园符号,这种符号性的叙事使自己离观众越来越远。西部不仅是一个文化符号和一个乌托邦的世外桃源的梦境,应是一个具体的实在,在这个空间里有房屋、农田,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鲜活的人,这里有当下人们面临的问题,如出走带来的农民工群体迁移和离散,环境污染以及权钱至上的问题,以及小镇青年群体的崛起推动着农村消费文化的兴盛,随之带来的对物质和精神享受的高度需求等。不排除还有非常闭塞和原生态的西部空间,也有极其富裕的示范村,但这两个极端都不具有当代西部农村在现代化进程中西部农村发展转型表征的普泛性,一些乡镇和小县城反而成了艺术作品表现城乡、贫富和现代与传统碰撞交织的典型空间,所以像章明和乔梁这样的导演以及贾平凹、钟平这样的与电影结缘的文人纷纷将视角放在了陕西白鹿原、紫阳县城、西安城中村等地理空间,这些地方的自然环境、人、社会关系、意识形态、权利与政治等交织成一个当代农村的新图景,成为西部农村题材电影当代性所关注的超文化空间。
《郎在对门唱山歌》将电影叙事空间放在了紫阳,一个由旧城和新城组成的小县城,新城、旧城、桥、生活在这里的人都是这个地方的组成,没有孰高孰低,章明把西安和北京“在场”的两个空间排除在画面之外,用大量跟拍镜头“深入”紫阳县城人们的生活中,呈现年轻人在新时代的理想和价值观、空间权力关系的构成和变化。《九号女神》更是将乡村和城市两个空间勾连在一起,少了对抗和冲突,多了一些交流和沟通。
西部农村题材电影中的城中村和乡镇的形态就是西部农村现代化进程的缩影,西部农村的现代化比东部和南部要晚,西部农村是一个 “上升空间”,从底层到上层、从农村到城市既包含身份转移,主体性的觉醒和确立,也表达出人们的价值观,人们对权力和利益的追求。
二、沟通性叙事与语言构建
在中国电影历史上,农村长期缺乏自我言说的能力,一直被城市的艺术家和文人当作客体来叙事和表现,当下随着城乡边界逐渐消弭,很多从农村走出去的人才又重新回到养育自己的农村,这些人对农村更熟悉,对农村的喜怒哀乐有真切的感受,他们更自觉的将更真实的展现农村和推动农村发展作为自己的责任,在他们的作品中农村、农民从背景和符号中处出来站在了镜头的前景,西部农村叙事从被“代言”开始转向,反思西部农村叙事和影像构建,形成具有主体特性的叙事,也在探索更深层次的西部农村表达语言。
(一)西部农村当代性主题:出走主题的变奏
现代文明似乎告诉了人们什么是自由:人人平等,人人都可以靠自己的双手去创造自己想要的生活,都有这样的权利,任何束缚人自由的规则都是落伍的。于是,许多人放弃了脚下的土地,放弃了自给自足的生活,出走,投奔到所谓的“更好的生活”中去。实际上,他们只是放弃了没有选择的安全,投入了有选择的不确定之中。越来越多农民甚至毫不眷恋地放弃了家乡赖以生存的土地,跟随社会潮流,到城市谋生。这种“社会无意识”的影响,让人认为“出走”是一种积极向上的选择。
随着城乡差距的缩小,城市的面貌也不再像过去那么“美丽”,而农村的景色也不再是贫困、落后、封闭的代替物,改革开放的历史洪流已经彻底改变了中国农村的现实面貌。在电影产业化的历史进程中,观众对于电影艺术的心理需求开始发生转变,一个单一的“出走”故事,已经不能够满足当代电影观众渴望的人生梦想。在“出走”的主题渐渐淡出中国电影主流的同时,出现了一系列以“进城”为主题的电影、电视作品,艺术家开始续写“出走”之后的城市故事了。
《高兴》讲述了来西安收破烂的一个群体,以往出走和进程都是为了改变底层身份,在这部作品中耐人寻味的是从“农村底层”出走到“城市低层”,在城市的发展受阻,并没有实现,他们原本期待生活会有重大改变, 会得到更多的安全感和确定感, 在此,他们却是被“抽离”的,在此所暴露出来的, 是他们与社会维持的关系是一种十分脆弱并缺少信任感和安全感的关系。从这里可以看出, 吉登斯所谈到的现代社会, 个体所应获得的具有承诺意义的确定感是缺位的, 至少可以说是极度含混不清的。
出走主题的另一个延伸就是出走后的回归。一是有可能面临着城市生活的困境和身份的焦虑重新选择回归到“乡土”,另外一种是当下更值得思考的一种回归主题:自己积极主动选择回到农村,把回归和自我价值实现结合起来看成自我内在需要,但回到的农村发现这个给了自己理想的地方,也是面临着自己无法解决的一些现实问题,继而又陷入困惑、迷茫和痛苦。《郎在对门唱山歌》中的刘小漾在高考前就选择了毕业要回到紫阳这个小县城,她坚信的爱情和视野统统受到挫折,影片里的紫阳从物理层面上,几乎毫无变化。河也好,桥也罢,旧城古镇,统统都没变,只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了:原来承诺的,不再相信;原来相信的,不再真实;原来真实的,不再存在;原来存在的,灰飞烟灭,影片展现的不再是那个千年不变的封闭空间,形成了新的西部农村叙事。
(二)当代性叙事策略:沟通性叙事
现代化的进程逐渐在去中心化,打破简单的城乡二元对立关系,关系复杂到不是对抗能够表述清楚,也不是对抗能就解决的,沟通性叙事就成为一中叙事策略。沟通有交流、沟通的意思,也有妥协的意味,如《九号女神》回避了尖锐的矛盾,只是把一些基本矛盾呈现出来,男主人公选择了“一见钟情”而不是“青梅竹马”,不再是一直在农村守望的人才是自己的精神家园,加上美好的结局和励志精神让这部影片表现出一种妥协,也是一种沟通。
沟通性叙事也体现在底层叙事的主流化,21世纪以来,农村经济的飞速发展使农民的生活状态发生了很大的转变,电影创作者也更加注重对各式人物形象的刻画。为了更全面地展示农村电影人物形象的变化,电影创作者扩大了人物角色选择的范围,不再聚焦于西部农民的落后和愚昧,《高兴》中的农民刘高兴迫于生计,跟好兄弟五富一起来到西安打工,工作是收废品,虽然工作不那么光鲜,但是高兴却乐在其中,还一直保持着设计飞行器的爱好,这种积极的心态感染了五富和邻居夫妇。另外,碰到小流氓石热闹寻衅滋事,也是高兴挺身而出惩恶扬善,一次偶然的机会,高兴结识了按摩小姐孟夷纯,两个人在接触中擦出了爱情的火花。虽然有很多困难,但他们一直保持着乐观的态度,看到的不是对这个群体的粉饰,而是底层叙事也可表现出生活的美好和良好道德。镜头下的这群底层人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即使生活艰苦,自己用破烂搞个时装秀逗个乐,贫贱且可爱这才更像是人,愚昧且麻木多是镜头逼视下的脸谱。《图雅的婚事》这个“嫁夫养夫”的故事从伦理上讲注定是个悲剧,但作为一个不能独立养活瘫痪丈夫的女子而言 “嫁夫养夫”本身是一个妥协的产物,图雅在生存和道德之间寻找一条折中的道路,既不抛弃残疾的丈夫又有可能获得个人的幸福,她想达到一种平衡是不可能的,导演把结局的可能性的想象抛给了观众。这是一个比较聪明的结尾,王全安既表现了底层边缘人的自尊和善良,将一个社会难题的叙事采取了一种既政治正确又不夸张、不草率的结局方式。
在《塬上》这部作品中,导演没有让这部作品简单地成为一部乡村发展的赞歌,影片没有在朱鹮那一刻结束,康文知道了真相后,与水泥厂长摊牌,但最终选择面对面解决问题,这是理性和感性的碰撞,也是问题的终极解决之道。在这里不是某一个人的错,各种因素纠缠在一起,除暴的对抗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所谓黑白的二元对立需要中和。奔跑中的一场彩色戏份,和残疾儿子拍摄朱鹮的彩色定格,给通篇的冷色调增添了温和意味,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对撞在厂长和康文回望儿时的场景时得以缓和,喻含着当下中国解决实现问题的方法,面对现实问题,任何的一方激进都是不妥的,谁又能说服谁呢?康文的“撒谎”是他真正了解了家乡,塬上的问题村民自会解决好。有意思的是全景中常出现一座桥,很有象征意味,是沟通性叙事在影像上的表现。
罗贝尔·布列松认为“当代影像艺术创作实践,它们大都没有明确的含义但又充满征兆,它们提供令人印象深刻、非实用性的物体或者环境,同时还能够展现大众传播媒介不能提供的更为丰富的艺术观念”。当代中国西部农村电影的影像书写与之前的农村电影叙事有很多不同,从镜头长度、节奏和色彩等方便都流露出当代性的美学诉求。电影的发展一直有技术的参与,技术改变这电影的边界和轮廓,当下西部农村题材电影媒介特性逐渐凸显。
镜头的减法让空间中的人更凸显,西部农村题材电影大都是中小成本作品,导演用减法去表达既是一种节约成本的做法,无论是固定机位还是运动镜头,始终会让人处在前景。《塬上》一片采用固定机位、大量长镜头,加上剪辑凸显出主要人物的矛盾,一场聚餐的全景展现就很有玩味。《郎在对门唱山歌》也同样大量采用了长镜头,开篇对冯冈的跟拍以及中秋聚餐的场面呈现,展现了一张利益、权力网,表达着空间里的人的变化和关系。
同样,色彩在当代西部农村题材电影中也是很“吝啬”的,少了第五代那种大色块的张扬,也遮蔽了第六代对边缘空间的零碎、迷离色彩的渲染。章明、乔梁、王全安他们更多选择了生活的中间色调,不张扬,足够节制,《塬上》更是除了小孩照相机镜头里的朱鹮是彩色之外通篇黑白色调,现实和梦想在西部土地上交织碰撞,面对的问题既不需要传奇性解决,也不会想当然的消散,生活还要继续,在困惑中继续寻找自我。至于贫瘠落后,镜头里尽是充斥,无需再过多表现,该片还是抱着积极的态度,相对温和地去展现一个生存资源相对不那么匮乏的地域境况,且结尾给予了一点生存的希望。
三、西部农村题材电影的当代性价值与策略性遮蔽
哈贝马斯曾阐述艺术的现代性:现代性即客观化的科学、道德与法的普世主义基础和自主的艺术发展,艺术和科学不仅会推动对自然力的控制,还能够进一步促进对自我和世界的理解、道德的进步、社会体制的公正甚至人类的幸福。借用哈贝马斯的论说来考量中国西部农村题材电影的价值,看其是否具有当代性就是看这一题材作品是否能真实地表达西部和西部农村,是否表达了观众对当代西部农村的认知和体验,是否参与和推动西部农村的发展。
当下消费文化深刻影响着中国电影,中国西部农村题材电影也面临着生存问题,现代化进程将其推向了商业市场,西部农村题材电影大多为中小成本电影,获得高票房的可能性很小,所以很多电影采取了妥协和曲线救国的策略,一是依靠政府投资,二是通过国外获奖换取进入院线的门票,这就让电影创作者多了一个或多个枷锁,既要获得观众尤其是农村观众的认可,电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媚俗”和“谄媚”,他是科林内斯库所说的现代性五个面孔之一,在当代语境这似乎是必然的和不可回避的,这为我们的艺术创作者们增加了很多难度,其实是带着枷锁舞蹈,由于《郎在对门唱山歌》是政府命题的作品,主创需要既要在电影中宣传紫阳,还要获得观众的认可,影片艺术化地表现了紫阳的山水风光、紫阳富硒茶等有当地特色的意象,并采用了爱情叙事使年轻人为观赏主体的观众所接受。影片似乎是完成了宣传任务,走向主流,但影片中断裂的两段式结构,让我们又隐约发现影片蕴含着一种自反模式,前一段所构建起来的都在后一段消解,导演通过影像的断裂在现代性媚俗和当代艺术探索之间悄悄搭了一座桥,避免了自身沦陷为旅游宣传片。对现实问题的挖掘和呈现是中国西部农村题材电影的当代性重要体现。《塬上》其中一个主题是环保问题,但这个问题大家都知道目前是根本无解的,影片精确地展现了矛盾。《图样的婚事》中图雅面临的牺牲与道义在一个父权社会中是无法两全的,两部影片最后要么抛给观众,要门以妥协结尾,没能指明一条出路。乔梁曾解释到:艺术负责提出问题,不负责解决问题。面对着光怪陆离、支离破碎的当下,很多问题是目前无法解决的,这也是对现代社会所面临问题在电影作品中的当代性投射。
西部农村题材电影的当代性底层叙事和第六代的作者化边缘叙事是有差别的。作者化的作品往往让影片中的角色代表创作者本人来发声或张扬个性,强调独立性。而像《图雅的婚事》《塬上》这样的作品是是将话语权交给了影片中的农民或者小镇青年,用农民个体代表农村底层大群体进行自我表述,不再强调导演是作品的唯一作者,从当下大部分农村电影是根据本土作家作品改编而来的就可以窥探出这一点,本土文学作品的改编很大程度上消解了导演的非本土性。当代性底层叙事抛弃了小众化的叙事,而是代表了亿万农民,也在转换文化精英代言的范式。
从总体上看西部农村题材电影的创作仍呈现出较为严肃的艺术探索精神和试图把握现实的努力,这在当下复杂语境下显得难能可贵。在中国电影历史上表现农民情感生活、生存问题曾是中国电影的时代主潮。如今我们看到了这一主题的回归,并且具有当代性特征,但离哈贝马斯所设想的艺术理想而言,中国西部农村题材电影的当代性任重道远。
注释:
① 这一段摘选自网络上对哈贝马斯在1980年9月被法兰克福市授予阿多诺奖金时所作的演讲原文,《现代性:一个未完成的方案》的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