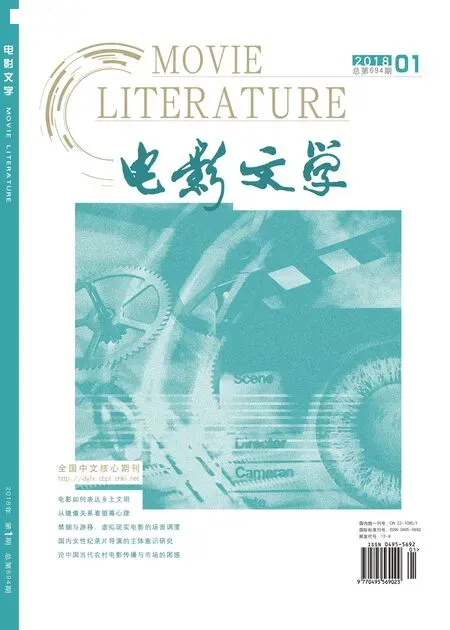美国电影的“反文化”言说
2018-11-14刘雅萍
刘雅萍
(包头职业技术学院,内蒙古 包头 014035)
一、美国“反文化”浪潮的缘起与影响
“反文化”现象最早出现在风靡20世纪中叶西方社会的青年运动之中,而将“反文化”作为一个社会学术语进行阐释则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弥尔顿发表的《反文化与亚文化》一文中。在这篇文章中,弥尔顿指出,“反文化”是某个群体与社会中主导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之间的冲突思想及行为,属于“亚文化”的新的衍生体。如果说弥尔顿从内涵层面定义了“反文化”,那么其后续研究者则对“亚文化”的轮廓进行了“写生”描述。在美国较为主流的观点认为“反文化”的外延广泛,指向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的各类反主流文化的“新左派”运动,包括黑人运动、妇女运动、反战运动、校园运动、同性恋运动等,这些带有文化反叛和文化革命意味的运动虽然与“反文化”浪潮不尽重合,却在诉求、群体等方面高度统一,其中的生力军大多为对社会现实不满、赋有反叛激情的青年群体。在“反文化”浪潮中,不被社会主流文化所容的生活方式成为反叛的主要表现形式,具体来说,性解放、摇滚乐,甚至暴力、吸毒等均成为反叛的手段,正因如此,身处“亚文化”群体的边缘青年运动才备受瞩目,成为美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被铭记的社会浪潮。
“反文化”浪潮的宗旨及表现形式是复杂的,“反文化”所提供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使建立在反叛主流文化和传统价值基础上的,当反叛者们以反叛的姿态融入既定的秩序中时,巨大的现实阻力和文化诱导使“反文化”内部也出现了裂变和扭曲,在怀疑理所当然的现实的同时也怀疑着怀疑本身,在反叛着主流的同时也反叛着反叛行为本身。与此相应的“反文化”的研究也呈现出多元的表现形态:一方面,一些研究者认为“反文化”具有一定的社会历史价值,是在呈现社会阴暗面的过程中对主流的反思;另一方面,更多的研究者对“反文化”秉持着批判的姿态,认为“反文化”只是一群不务正业的孩子们发动的“十字军远征”,是在模糊现实与幻想界限的过程中实现自己无处发泄的生命冲动。对于“反文化”的不同认知体现在大众传媒之中,而作为大众艺术的电影来说,轰轰烈烈的“反文化”浪潮自然成为其表现的对象。自“反文化”浪潮席卷美国以来,美国电影就未停止对“反文化”的言说,这不仅仅是对美国社会历史的简单再现,更是对“反文化”多元解读的重要表征,同时也证明了“反文化”所带来的深远影响力和现实批判价值。本文将从“反文化”浪潮的缘起与影响入手,以《飞车党》《在路上》《邦妮和克莱德》《发条橙》《逍遥骑士》《摇滚校园》为研究对象,以“垮掉”“暴力”“摇滚”这三个“反文化”浪潮中的“[关键词]”为线索解读美国电影的“反文化”言说。
二、“反文化”中的垮掉一代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战争阴霾下成长起来的美国青年们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了“迷惘”和“垮掉”的状态,而“反文化”浪潮则是这种“亚健康”状态的反映和延续,“垮掉”的生存状态在电影中得到了更加集中的体现。上映于20世纪50年代的影片《飞车党》被认为是美国机车公路片的开山之作,影片中的“公路机车”事实上是一群驰骋在公路上的非法机车团伙。影片男主人公带领着非法机车一行青年终日骑着机车在小城中招惹是非,有悖常规的行为方式和桀骜不驯的举止做派成为影片叙事的重点,机车、电吉他、爆炸头等元素在影片中均被赋予了反叛的意义。也正是从《飞车党》开始,美国的公路片出现了新的分支,银幕上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秉持着自己的价值观在“反叛之路”上行驶的机车青年。影片《我心狂野》改编自巴里·吉福德的小说,由著名导演大卫·林奇执导,尼古拉斯·凯奇等好莱坞演员担任主演,讲述了一个关于逃亡的故事,看似众叛亲离的逃亡背后是男女主人公对真爱的追寻和对权威的反叛,这部具有“反文化”色彩的影片拿下了戛纳电影节的金棕榈大奖。在《我心狂野》中,男主人公塞勒两次入狱,一次是被追杀的过程中为自保杀人;另一次则是在朋友的圈套中实施抢劫被捕,而这并没有影响女主人公萝拉与塞勒在一起的决心。事实上,萝拉的母亲玛丽埃是塞勒被捕入狱的幕后黑手,在设计追杀塞勒的同时,玛丽埃千方百计地阻止女儿追求爱情,但最终萝拉还是生下了塞勒的儿子,并在塞勒出狱后共同远离阴谋和桎梏,走向幸福。在这部影片中,男主人公两次入狱的“垮掉”生活并未成为批判的焦点,反而是代表着正义和权威的母亲成为被揭露的对象,塞勒与萝拉坚定的爱情也指向了所谓“权威”的伪善和反抗权威的胜利。
被奉为“垮掉的一代的圣经”的小说《在路上》不仅影响着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青年,其影响力也一直延续到了当代。在这部作品中,主人公们打破了传统的生活方式,反叛着社会主流价值观念,用在路上的姿态以及在路上过程中的酗酒、乱性等放浪行为表现着生存的迷惘和困惑,追寻着模糊的自由与理想。这部经典作品在多年后被导演沃尔特·塞勒斯搬上银幕。在影片《在路上》中,男主人公同朋友们共同踏上了去西部的旅行,怀着各自的伤痛和理想,男主人公一行在路上过着极端自由的生活,他们的“垮掉”不仅在于不被世俗所接纳的生活方式,还体现在他们之间矛盾的关系。惺惺相惜又瞬间消失的情感体现出后现代社会的疏离感。对于影片《在路上》中的主人公们是否真正在精神废墟中重新站立,是否走出极端自由寻找到了自我,不同的观众会有不同的看法,但其中“在路上”的姿态却成为“反文化”群体的重要表征和追寻目标。
三、“反文化”中的暴力青年
“暴力”始终是美国电影中的重要元素,在美国电影的“反文化”言说中,不可缺席的“暴力”不仅仅是博得眼球的看点,更是反叛的重要载体。在根据真实历史事件改编的影片《邦妮和克莱德》中,雌雄大盗的故事讲述里始终伴随着暴力,影片男主人公克莱德在偷车时遇到了车主的女儿邦妮,对邦妮一见倾心的克莱德为了向所爱之人炫耀自己,抢劫了一家超市,由此开启了二人合伙打劫的生活。机枪扫射、警匪火并、炸弹爆炸、血肉横飞、尸体遍地的场景几乎充斥整部影片始末。正因如此,《邦妮和克莱德》也被认为是一部敢于突破底线的影片:一方面,该片对暴力的呈现打破了美国电影CPA审查章程;另一方面对施暴者的正面塑造打破了观众的价值底线。在《邦妮和克莱德》中,雌雄大盗邦妮和克莱德被塑造为敢于对抗国家权力机关、挑战政府管理秩序的“英雄”;而警察、官员、群众则被塑造为奸诈、无能的代表。无论是影片讲述故事的背景年代,还是影片出品的时代,美国社会均处在动荡发展时期,经济萎靡所带来的失业和失序使许多人的生存成为难以解决的问题,民众开始质疑国家机器在社会中的作用,抗议活动和反叛运动不断高涨,这也成为《邦妮和克莱德》从正面呈现极端反叛的重要原因。尽管影片以邦妮和克莱德伏法为结局,但二人的死却源自警察龌龊的阴谋和对朋友父亲的错误信任,而这同样构成了对社会主流和主流价值的反叛与反思。
在由斯坦利·库布里克执导的影片《发条橙》中,犯罪青年的“治疗”方式令人不寒而栗,而这种近乎荒诞、缺乏人性、不顾人权的“厌恶疗法”真实存在于美国历史中。在《发条橙》中,男主人公阿历克斯是一个无恶不作的青年,打架、强奸、过失杀人使阿历克斯被判处了14年的监禁。为了能够获得减刑,阿历克斯自愿接受了美国当局正在实验中的新型犯罪治疗方法,即“厌恶疗法”。在“治疗”过程中,阿历克斯身心受到了残酷的折磨,而在“治疗”后,阿历克斯竟然神奇地痊愈了,但“治愈”的代价却是丧失了反抗的能力。正如前文所述,影片中的“厌恶疗法”实际存在于美国历史中,这种“治疗”就是强制犯人连续不断地观看暴力、色情的影像,以期借助生理和心理上的条件反射戒除他们身上的施暴欲望。被“治愈”的阿历克斯在出狱后“脱胎换骨”,不仅彻底远离了犯罪,还成为一个失去任何反抗能力的人,即便是在遭遇不平等待遇,甚至是被无端打骂时,阿历克斯也毫无反抗的意识和能力。影片中的阿历克斯正是许多“厌恶疗法”的“治愈者”的缩影,在实验失败后,美国当局也彻底废止了这种教化措施。从无恶不作的施暴者到时时处处的受虐者,阿历克斯的被动转变所体现的是主流文化对亚文化的绝对打击,“反文化”的意味不言自明。
四、“反文化”中的摇滚伤花
20世纪50年代末,一位来自美国南方的歌手艾尔维斯发行了首张个人音乐专辑,这张摇滚乐专辑颠覆了音乐传统,嘶吼的歌声、狂放的表演对传统的音乐制作和严谨的舞台表演形成了强有力的冲击。这股反叛浪潮迅速席卷音乐界乃至全美国的青年生活,而这个名为艾尔维斯的歌手就是著名的“猫王”。由“猫王”开始,摇滚这朵伤花怒放开来。随着摇滚乐的发展,狂野的音乐风格已不再是摇滚乐追求的唯一目标,配合音乐风格的反叛性歌词吸引了更多青年人投身到摇滚乐的热潮中。对战争的反叛、对制度的反叛、对文化的反叛使摇滚乐不仅在社会生活中成为“反文化”的先锋,也成为电影中体现“反文化”的重要元素,许多美国电影都在讲述投身摇滚的嬉皮士们的反叛故事。嬉皮士产生之初,主要是传统音乐家对青年音乐家的称呼,但随着摇滚乐的发展和“反文化”浪潮的推进,嬉皮士的指代对象扩展到了运动中的激进分子、崇尚乌托邦的青年以及亚文化中的边缘群体,他们强调尊严、追寻自由、反叛主流文化,影片《逍遥骑士》就是讲述嬉皮士生活的优秀代表作品。在《逍遥骑士》中,两个嬉皮士驾驶摩托行走在公路上,不愿融入也无法融入常人生活的他们经常风餐露宿。他们在摇滚乐中逃离现实,在抗争无力中离群索居,在有悖主流道德的行为中释放自我,表达着对主流文化的不懈与反叛,在摇滚乐中寻找乌托邦世界成为《逍遥骑士》描绘的“美好”画面。
纵观美国影坛,摇滚乐元素的运用十分丰富。近年来,体现摇滚乐元素的美国电影在承袭“反文化”传统的同时,注入了更加积极的励志情愫。在由好莱坞著名喜剧演员杰克·布莱克主演的影片《摇滚校园》中,男主人公杜威·费恩是一个摇滚乐队的吉他手,始终未能实现争霸摇滚乐坛的他已经陷入了经济的窘境中,无奈之下杜威决定冒名顶替去担任小学教师。原本准备回归“正轨”的他却意外发现了学生们的音乐天赋,于是杜威开始帮助孩子们组成摇滚乐队并筹备摇滚大赛。在筹备比赛的过程中,杜威遭到了校方的反对和家长们的抵制,然而带领学生们坚持音乐梦想的杜威最终帮助学生乐队赢得了比赛,自己也成为一位知名的摇滚乐手。在《摇滚校园》中,如果说学校和家长代表着正统的主流文化,那么杜威就是“反文化”的代表。在这次交锋中,没有迷惘与垮掉,也没有暴力与极端,更多的是对梦想的执着,相对温和的反抗最终获得了胜利,使整部影片呈现出一种怒放般的励志色彩。
“反文化”浪潮缘起于美国二战后“垮掉的一代”的反叛,与活跃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新左派”运动合流,大规模的青年反叛运动已偃旗息鼓,但“反文化”浪潮的影响却延续至今,成为美国电影中的重要言说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