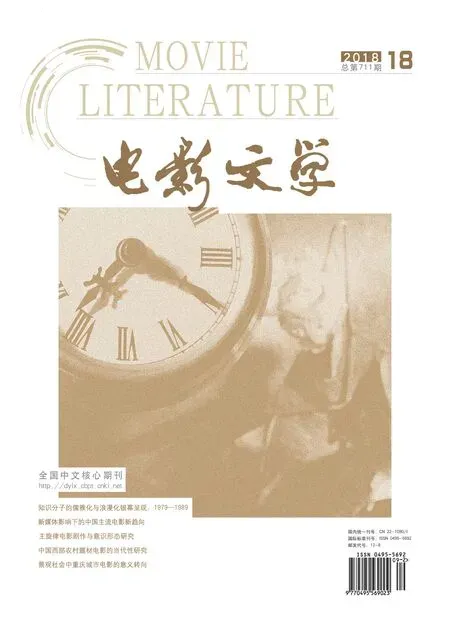《敦刻尔克》的碎片化叙事探析
2018-11-14赵宇
赵 宇
(鞍山师范学院,辽宁 鞍山 114016)
英国独立电影人克里斯托弗·诺兰曾表示,自己与前辈希区柯克一样,是一位拥有精彩纷呈奇思妙想的电影人。在诺兰的电影创作实践中,人们不难发现,传统的电影叙事模式往往为诺兰所抛弃,并且在不同类型和主题的电影中,诺兰会采用独到的,让故事更具张力的剧情处理方式。观众既能感受到诺兰的艺术个性,又一次次地收获新的观影享受。在其战争电影《敦刻尔克》(Dunkirk
,2017)中,诺兰再次展示了自己富有魅力的叙事手法——充满了浓郁后现代气息的碎片化叙事。一、后现代语境下的碎片化
后现代是诺兰等电影人采用碎片化叙事的一个重要外部语境。20世纪是一个支离破碎的,各方面走向枯萎没落的时期,而人性也陷入危机。同时,艺术和消费之间又不断进行渗透,在这样的情况下,以狂欢、混杂、不确定、反讽和无深度等为特点的后现代艺术兴起,而传统的完整而统一的艺术更像是某种美的幻象,已经不能满足身处废墟之中的人们的需要,此时,一种新的,更接近人们直观体验的艺术形式,即以碎片化(fragmentation)的方式来处理外部世界,应运而生。
在后现代主义思潮之中,除了文学领域中的“新小说派”等以外,本身就具有商品性和可复制性的电影也成了一个最早背离权威话语,建立新的表意方式的典型。电影人主动地用电影来反映现实世界让人无所适从,无可奈何的破碎、混乱和无序,反叛与颠覆旧有的艺术表达方式,对个人的情绪和诉求进行宣泄和表达。自然主义,内在意识的表达等在电影中大行其道。正如大卫·波德维尔所指出的那样:“当一大批似乎要将经典规范粉碎的新电影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时,也就到了另外一个实验性的故事讲述的时期。这些影片自夸拥有吊诡的时间结构、假定的未来、离题的游移的行动线索、倒叙且呈环状的故事以及塞满众多主人公的情节。电影制作者们看起来好像正在一场砸烂陈规旧矩的狂欢中竞相超越。”一批几无顾忌,让观众眼花缭乱的电影相继问世,促进着电影叙事学的进步。如除了众所周知的昆汀·塔伦迪诺的《低俗小说》(1994)之外,又有如米尔科·曼彻夫斯基的《暴雨将至》(1994),章明的《巫山云雨》(1996)等。这些电影人来自不同国家,但全都可以作为波德维尔所说的“狂欢”的参与者。观众接触到了一种挑战传统逻辑链和因果链的叙事方式,情节是断裂、跳转的,意识是流淌的,不明确的,意义的获取变得异常艰难。
二、作为诺兰个性化组成部分的碎片化
而《敦刻尔克》采用碎片化叙事,并不仅仅出于后现代环境这一外因,也与诺兰本人的艺术个性这一内因密切相关。尽管姿态并不够先锋,但诺兰本身也是追随后现代审美风格乃至文化立场的。纵观诺兰电影,不难发现,观众几乎永远无法轻易理顺其故事是如何在空间和时间上展开的,从其处女作《追随》(1998)开始,诺兰就开始了一发而不可收拾的,令人匪夷所思的叙事技巧探索。其电影中时间难以被还原,空间是非连续,非延展的,而人物活动也不一定具有可见的关联性。
而值得一提的是,诺兰的几乎每一部电影,都可以让人感觉到其对某个问题(法制、科技、道德、人性等)有着严肃而认真的思考,这是诺兰在当代商业电影和艺术电影中都独树一帜的原因之一,也是诺兰和前述后现代主义艺术的重大区别之一。就像杰姆逊评价后现代主义艺术时提到的,艺术家们普遍不再提出问题甚至是正视问题,放弃了赋予世界意义的意图,而将自己变为一个对客体无能为力的“孤岛”。而诺兰则不然,他的电影尽管也高度关注心理与意识,但始终有着某种向外的思考。这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诺兰的“蝙蝠侠三部曲”。三部电影在掀起全球“蝙蝠侠”狂潮的同时,又让DC备感无奈。诺兰的蝙蝠侠故事可以说完全脱离了DC在漫画中设定好的情节架构,成为诺兰对于黑暗人性和社会法制建设思考的载体。以至于三部曲个人风格极强而与DC的其他蝙蝠侠电影格格不入,是“DC宇宙”中经典却又突兀的存在。其他如《记忆碎片》(2000),《致命魔术》(2006)等亦是如此。可以说,诺兰一直在做一个提出问题,赋予电影强烈社会批判性的电影人。在《敦刻尔克》中,诺兰则抛给观众这样的问题,即在炼狱式的战场中,生命是如何卑微不堪,历史上的非凡行动中,个体将承受怎样的压迫感,将具有怎样的感官体验及思考,会对他人做出怎样的反馈。
这也就使得,诺兰必须采用小人物视点开展叙事,让观众得以近距离接触到战争的惨痛和残酷,把敦刻尔克大撤退从一种集体记忆化为一种个人体验。同时诺兰又设置了多个视点,即电影中的“海陆空”三条叙事线,以给观众一种更为宏观的敦刻尔克图景。只是在这三条线中的每一个主人公,他们对于世界,对于战争的感觉都是主观的,碎片式的。电影的冲突主要不在于敌我,而是在于个体与一个通向希望和“家”但又危机重重的外部环境。在《记忆碎片》采用了“颠倒”叙事,《致命魔术》采用了以日记为线索道具的“超链接”叙事,《盗梦空间》(2010)和《星际穿越》(2014),用套层梦境和虫洞实现时空扭曲,人物错层对话的叙事,诺兰选择了在没有科幻元素且受史实束缚的《敦刻尔克》中,不仅让三条叙事学分别属于空间上的“海陆空”,也使其分别在时间上属于“一周,一天,一小时”。交叉推进的线索间人物对话被降到最低,时空与人物状态呈现出颠倒、反复、预知、互补等效果,最终借此逐渐拼起了完整多角度的“大撤退”,这也就使得,三条线上的叙事全是被割断的,形成一种碎片式的效果,但也就是在这一个个碎片中,人类或伟大或渺小,或恐惧或勇敢,或狭隘或宽容的瞬间,冲击着观众的眼球。一言以蔽之,后现代的创新潮流与蒙太奇大师诺兰本人的多线叙事习惯和对电影深度的要求,共同造就了《敦刻尔克》的碎片化叙事。
三、《敦刻尔克》的碎片化叙事表征
首先是组合段叙事。在组合段叙事中,电影的叙事以人物、事件或事物为标志被分段,几个组合段最终完成整个故事的讲述。对于不同的电影而言,组合段与组合段之间的连接结构是各不相同的。但共同点在于,它们之间有着或明或暗的联系。如王颖与保罗·奥斯特的《烟》(1995)中,组合段是以“滚雪球”的方式实现连接的,不同的人物因为香烟而彼此纠缠。
而《敦刻尔克》则不然,英国空军飞行员法里尔段落中的一小时,属于驾驶自家游艇前去海峡对岸救人的道森先生段落中一天的最后一小时,而道森先生经历的这一天,则是英国陆军士兵汤米苦苦煎熬等待救援的一周的最后一天。三条线的交错不是简单的插叙或倒叙,而是如同三条不同长度的弹簧,以不同的速度回缩,并最终相遇于大撤退成功这一个点。但在意识到这一点之前,观众看到的是,往往当陆军的情节即将进入高潮时,电影却切换到了空军,在频繁而密集的剪切中,观众的情绪被强行打断,加之由于时间的不同步,法里尔段落的叙事势必要被拉长,而汤米的故事则要被压缩,观众往往在看到汤米等人在夜里遭遇袭击,落入海水时,又看到空军驾驶着飞机在白日阳光下追逐,在观众还没有整理出“一周,一天,一小时”之间的关系时,便会陷入疑惑之中,但悬念也由此产生。在这样的组合段叙事中,观众看到了汤米、道森先生和法里尔三个拥有不同命运,不同经历,互不认识,但因为战争而被置于敦刻尔克的人物,人物的背景、身份和战斗经验等显然被故意拉开距离,由此引向战争的不同层面,如经历过泰坦尼克号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道森先生,先救起了罹患PTSD的陆军士兵,理解他因恐惧而不敢进船舱的行为,后来道森先生又救起了迫降于海面的飞行员柯林斯,浑身湿透的柯林斯却在见到道森先生后不失绅士风度地,镇定地说“下午好”,老兵与新兵的区别明显而自然。诺兰对多元复杂的战争情形的概括力也被体现出来。
其次是去情节化。在传统电影中,叙事普遍以戏剧化情节为中心,人物之间的矛盾被典型化,观众能够非常明晰地感受到电影叙事中的“起承转合”,并由此理解、记忆电影。而在后现代电影中,主创则往往把审美焦点置于人物的情感意续,或生活中琐碎的,毫无曲折或意义可言的细微小事上。诺兰在《敦刻尔克》中则介于二者之间,电影中依然有冲突与高潮,如在汤米的叙事线上,英军士兵拒绝让本应是他们盟友的法军士兵上船,当汤米和法国士兵吉布森以及其他几名英国士兵被困在黑暗的小渔船船舱时,德军就在附近,英国士兵们逼迫吉布森出去送死;又如17岁的少年乔治被他们救下来的士兵推倒,头部着地而死等。但从整体上来说,三条线的叙事都嫌简单,这也是诺兰的一次“做减法”的尝试。汤米两番登船,道森先生的“月光石号”满载士兵返航,法里尔在与敌机激战一小时直到燃油耗尽。这种明显有别于《拯救大兵瑞恩》(1998)等的跌宕起伏情节的去情节化叙事,正是为了突出在战争环境中,个人经验是压抑单调,度日如年的,每个人无法以全知视角来复述战争,但即使他们在敦刻尔克大撤退中只完成了一件事,亦是堪称伟大的,他们的内心体验也是丰富的。
第三则是半开放式的结局。通常情况下,电影会以闭合式结局满足观众的情感,回答观众的疑问,如《辛德勒的名单》(1993)等,而开放式的结局则缺乏明确的结尾,给予观众自行添加结局的自由。诺兰同样折中地采用了半开放式的结局,电影结束于在被换为暖金色调的大海中作为画外音的丘吉尔的“我们绝不投降”的演讲,伴随着“我们将在海上和大洋中作战……我们将在海滩上作战……我们将在敌人登陆地点作战……”的陈述,镜头转向海滩、登陆点、岛屿等意味着牺牲与生还的地点,但是电影中的一个个渺小的,但是其命运自始至终牵动观众的个体的结局,如法里尔投降后的结局,汤米是否重返战场等,诺兰却没有交代。诺兰从群体中拈出这几个个体,最终又让其归于群体中。这种有意的对人物命运主宰的缺失,本身符合不介入客体(历史),不强制给予观众意识或立场的后现代美学立场,同时也提示着观众,一度为观众所关注的个体,在战争中必然处于被“淹没”的状态。而在大众的记忆中,也最终将属于被无视甚至被遗忘的对象,人们最终记得的,只会是丘吉尔、希特勒这样的人物。而那些个体的恐惧与无助,高贵与勇敢,以及有意义或无谓的牺牲(如乔治的死),正是不应该被遗忘的。诺兰的这种不交代人物何去何从的戛然而止,可谓意味深长。
随着电影艺术的不断发展,观众势必要不断接受到新的电影观念与形态。而诺兰正是当代电影叙事实验中的佼佼者。尽管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就已经有电影人不断进行碎片化叙事的实践,诺兰作为当前最成功的“电影作者”之一,他的《敦刻尔克》让观众得以实现两个方面的耳目一新:观众不仅能够重新审视几乎家喻户晓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著名事件——敦刻尔克大撤退,其对诺兰电影叙事风格的认识也得到了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