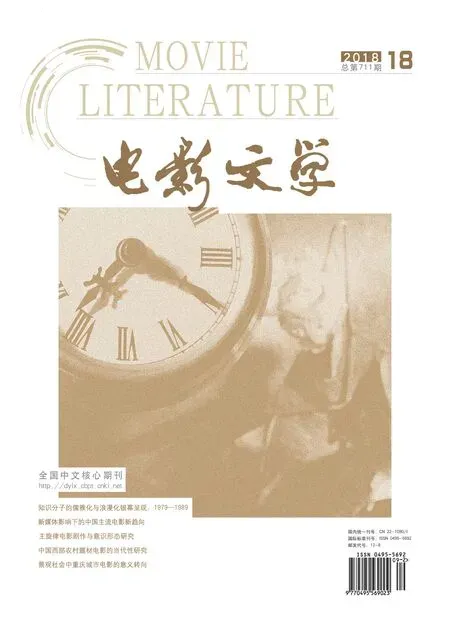解读《寂静之地》中的性别话语
2018-11-14张宋涛
张宋涛
(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加拿大 温尼伯 MB R3T 2N2)
继在北美收获成功的票房与口碑之后,《寂静之地》于2018年5月18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虽然该影片在中国的票房并不如在北美那么理想,但自上映以来连续四天蝉联票房前三的纪录已经足以反映这部影片的名声与口碑。可以说该影片兼具恐怖片吓人的元素与艺术片的审美价值,然而这部影片所建构的性别话语却是那样的保守与刻板。基于此,笔者通过性别研究与女性主义的解读方法对该影片进行多角度的文本细读以试图剖析影片呈现出的性别表述。本文认为该影片呈现出极为鲜明的二元对立式的家庭性别结构,在其间父亲与儿子,母亲与女儿分别被赋予了截然相反的所指。
一、恐惧与温情之外
影片的恐怖来源于两个元素:一个是凶残而一招致命的神秘生物;另一个则是令该生物极度兴奋的“声音”。影片里的未知生物对声音异常敏感,它们以一切发声生物为攻击对象,因而人类首当其冲。面对死亡甚至灭种的威胁,影片所聚焦的一家人因此不得不在噤声中寻求逃离与抗争之法。因而他们的“声音”作为灾难的诱饵成为整个故事情节的核心动力。故事正是在一次次地“制造声音”和“躲避怪物”的捉迷藏式的剧情结构的展开中拉扯着观影者的神经。影片寂静如死般的基调为观众营造了一种强烈的压抑感,而发声必死的环境法则则又给这些与主人公一同深处寂静的观众一种不自觉的畏惧声音的代入感与参与感。影片正是借助观影主体与电影之间的这种心理学上的联系,成功地放大了观影主体的恐惧。这也正是该影片作为恐怖片类型所表现出的独到之处。
此外,影片还力图表达爱与亲情。在经历家中最小的一员被未知生物猎杀之后,全家都笼罩在哀伤、矛盾与无助之中。可以说这一开场的遭遇所带来的悲伤感贯穿着整部影片。而当全家人开始正面遭遇怪物时,躲避怪物袭击时的每一次重聚都携带着无限的感动,但每一次短暂的温馨却又随即面临着被迫分离。父亲为解救子女而牺牲生命的那一刻则将故事的情感的表达推向了高潮。这个家庭在威胁面前所展现的强烈的感情上的凝聚力不断地冲击着观众的内心,而伴随着哀悼式的背景音乐,深刻而持续的感动与挥之不去的紧张相互交织,反复纠缠。
或许也正因此,影片在叙事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更深层次的社会话语则被悄然地掩埋至了一场紧凑而紧张的神经盛宴以及情感的发泄与满足之间。而笔者则试图从影片所编织的这些重重表象之间,揭开它所聚焦的这一美国典型核心家庭典型的矛盾式的性别话语。恐惧与温情之外,呈现的是另一种表述。
二、秩序与反秩序
影片以一段线性叙事组合开场:六组环境镜头过后,一家人在超市里准备必需品。母亲为生病的大儿子寻找药物。小儿子伸手拿玩具火箭,火箭不慎掉落,姐姐接住火箭。父亲出场,站在门口。将走时父母发现小儿子手里拿着玩具火箭,于是父亲谨慎地从小儿子手中拿过玩具卸下电池并把玩具搁置一旁。尔后姐姐把火箭给了弟弟,但在大家都走后小男孩却拿走了电池。回家的路上火箭发出响声,父亲跑去营救但为时已晚,小男孩被怪物猎杀。
在这段线性叙事组合当中,水平与纵深调度几乎参半的交叉剪辑一方面交代了人物所遭遇的由环境所施加的某种压迫式的生存境遇;另一方面又强调了人在适应和改造环境上所做的努力。当小男孩走过废弃的汽车时,当摄影机以上帝视角观望在沙地上光脚徒步行走的一家人时,摄影机采用的是水平调度,呈现出了某种扁平的、颓废的、被压制的生存状态;而其间所穿插的纵深调度则又将这家人所开辟的生存之道嵌入绝望的历史与环境之中,暗示着人在这种生存境遇之中所力图争取的些许的可能与希望,一种建立在父亲所领导和维系的以“别出声”为秩序法则之上的生存希望。
影片中父亲的出场被安排到所有人之后,且正是玩具火箭险些掉落的时刻,同时也正是光源的所在地。这一安排显然赋予故事中的父亲以“父神”般的形象。可以说,影片中的父亲这一角色本身就代表着秩序。当发现小儿子手里拿着玩具火箭时,他如遇怪物般小心翼翼地出面阻止;当大儿子模拟开汽车时,他的到来让儿子垂头放弃……他们住所周围的各个角落都安装有监控,父亲在工作室内通过这些监控观望,监视着周围一切可能发生的危险,当然也必然监视着他的家人。同时他永远都是以一种高大、稳重、深沉而孤独的形象出场,譬如他坐在瞭望塔顶悼念逝去的小儿子时的一段场景。这段镜头中摄影机采用仰拍的角度,上移,首先呈现出他的背影形象,接着仰拍,呈现出侧面形象,居画框左上角。类似的人物调度还如他在地下工作室工作时的场景。影片中对父亲所做的人物调度是最为丰富且最为正面积极的,从而进一步指涉,强化了父亲的律法式的角色。从情节逻辑上讲,秩序是为了躲避怪物的袭击,父亲则在影片中自然而然地承担起了践行和维系这一安全铁律的责任。影片正是在这些叙事情节的呈现中,在娴熟精到的调度上,在影片逻辑的展开上将父亲秩序般的存在表露无遗。
如果说父亲所代表的“秩序”意味着和平、安全和稳定,那么故事的推进、灾难的降临也必然需要“反秩序”的存在。当然这是一种基于影片逻辑发展而言的表述。而另一种表述,一种类似克里斯蒂娃式的表述则是:正是那种从秩序中分离出来的另一种存在确保了崇高的、超越性的父系秩序法则的维系。笔者之所以将两种表述都呈现于此,是因为影片在将父亲设定为秩序般存在的同时却将母亲和女儿安排成了“反秩序”的存在。父亲高大伟岸的“父神”形象正是通过“母女”直接或间接制造的“另一种兴奋”而得以确立。因而这个在灾难面前如此凝聚、如此深情、如此虐心的家庭确乎是将这种凝聚、这种深情、这种虐心建立在一个传统的二元对立式的两性性别结构之上。
影片开场弟弟的死是由姐姐间接造成的,因为她把玩具给了弟弟。而姐姐又是出于对弟弟的同情与宠爱才把玩具给了他。这是一种基于情感而导致的对秩序的破坏。如出一辙的是,母亲也是受到情感的驱使而走进小儿子的房间独自垂泪,但此时的她已经接近临盆,行动极为不便。临走时分娩发生,急忙下楼的她手里还拿着小儿子的照片,结果下楼时脚踩中铁钉,相框掉落打碎发出声音因而招致怪物。从这里不难发现,无论是上楼悼念儿子,还是临走时拿走相框,这些因情感而牵扯的行动都是灾难发生的直接原因。此外,在当姐弟俩站在谷堆塔顶上面给父亲发求救信号时,正是姐姐感情用事与弟弟发生争执才导致弟弟不慎掉落谷堆而招致怪物。这三处致命性的失误皆是或直接或间接地由故事中的两个“感性着的”女性所导致的。同时当问题发生时,父亲永远是缺失的,以致他永远都是以营救者的英雄形象出场。而当他在场时,尽管问题也会出现,譬如儿子不慎打翻灯盏,他却能及时解救。父亲的在场因此意味着安全;相反,他的不在场则预示着危险。
除了女性的情感作为秩序的破坏者之外,母性的身体也在影片中表现出某种“反秩序”的意指。铁钉因何而来?是接近临盆而行动不便的母亲提着衣服上楼时把装衣服的袋子挂住了打弯的钉子头而把它牵拉起来的。母亲的身体在制造和遭受铁钉的两组动作中都被赋予明显的身体上的“反秩序”的指涉。正如西方女性主义思想家Margrit Shildrick所指出的那样,母性的身体在某些西方文化语境下被视为“非秩序”(disordered)的甚或是“妖魔化”的存在(monstrosity)。
三、父与子:男孩成长的秘密
如若母亲和女儿是需要被规训,被保护,被秩序化的与秩序相对立的主体,那么儿子作为父系权利的沿袭者与替代者必然要经历从母系空间出走而进入父系经验的过程,这便是影片所昭示的关于男孩成长的秘密。
有趣的是影片中的儿子本是羸弱的、胆小的,他不愿跟随父亲去探索外面的世界。也就是说,他从最初,从最伊始的阶段是和母亲紧密连接的,他属于那个襁褓式的阴性母系空间。当父亲要求他和他一起外出学习求生技能时,他竭力抗拒。而母亲是这样劝说他的:“你学会了这些技能会很有用的,它能帮助你照顾自己,当我老了,牙齿掉了,头发白了,你也能照顾我。”所以他必须走出这个原初的空间场域而完成与父亲的连接,完成男性气质的建构,因为母亲需要他来照顾,未来的秩序需要他来维持,这是他成长的必经之路。与儿子抗拒外出所截然相反的是女儿极力央求能与父亲外出,可是父亲拒绝了女儿的要求。如同他拒绝让女儿进入地下工作室一样,他再一次以爱与保护的理由拒绝让她进入他的领域,他的历史。父子俩整装待发与母亲临别时的这段场景在布光、构图以及视点上的处理做得别有用心。它采用的是自然光,在光源的左右两边分别站立着儿子与父亲二人,父亲则更靠近光源。此时的女儿与父亲发生争执,成了某种介入般的他者化的存在。在遭遇拒绝之后,她气愤地走出两父子所在的位置背着光朝着相对昏暗的另一条岔路走去。此时的母亲站在正对着儿子且稍有些许距离的对面凝视着这一切,她对儿子投以鼓励,对女儿表达无助。这套精细完美的镜头语言可以说非常成功地呈现了这个典型的美国核心家庭成员之间的角色划分与成员关系,也极其成功地对这对父与子临近的行动赋予了某种正面的积极的价值指涉,同时当然也成功地强化了影片在性别结构上的设定。正是在这次外出探索的过程中,这个原本胆小懦弱的男孩成长了起来,这使得他成功地燃放了焰火,完成了对母亲的最后一分钟救援;也使他坚信父亲总会找到他们,前来解救他们;同时在父亲大声叫喊,牺牲自己的那一刻他也不掺杂任何犹豫地、果敢地发动了汽车带着姐姐逃离了怪物。在影片故事中父亲除了作为引导者之外,他对男孩而言还意味着欲望与本能的成全者。父亲把儿子带到河边,带到瀑布下面以此成全了儿子“言说”的本能。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本能的释放是经由父亲所验证过的一种绝对无害的释放,是一种经由科学和理智所指导和支配的本能的变奏。可以说,父与子的“外出”这一情节线索浓缩了男孩们成长的逻辑,一种建立在父系标准之上的经由承继他的权利,进入他的历史,追随他的脚步而从男孩走向男人的路径。
四、结尾的隐喻
影片结尾母女俩并肩抗击怪物的行动与“木兰从军”的中国传说有着极为相似的性别隐喻,即戴锦华所揭示的“花木兰式的隐喻”——女人以英雄的身份出演于历史的唯一可能,仍是父权、男权衰亡、崩塌之际。同样的结论还出自于加拿大社会学家Murray Knuttila。Knuttila对二战期间加拿大的性别结构做过这样的分析:“加拿大的经济之所以在二战期间得以繁荣,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持续增长的女性劳动力对二战时期加拿大经济建设的参与。”换句话说,也正是投入边疆的男子们在经济建设上的让位才给了女性们投入社会历史建设的机会。在影片的结尾,也正是父亲的牺牲才使得保卫家园的权利得以让渡给了母亲和女儿。而这对母女之所以能够击败凶残的怪物,也在于女儿终于得以进入父亲的场域,得以获取了父亲的经验知识并找到了怪物的致命弱点。
从以上的论证不难发现,《寂静之地》在北美的成功绝非偶然,因为它不仅在电影叙事上表现出独树一帜的风格,更重要的是,它显然昭示着美国传统家庭价值观,传统家庭性别角色与性别结构的复现,抑或是关于这种家庭结构的美丽而崇高的想象。
注释:
① 克里斯蒂娃的原话是:“若没有性别鸿沟,没有这种多形态的局部化也即另一种极度兴奋的身体,另一种性别的笑和需要,那就不可能在象征性领域里分离出一种法则——这个唯一崇高的,超越性的法则,确保了共同体的理念和旨趣。”参见朱丽娅·克里斯蒂娃:《中国妇女》,赵靓译,同济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