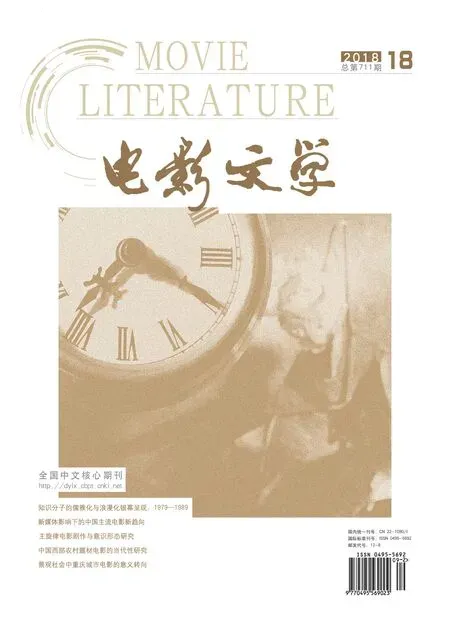谈戏剧改编电影《赵氏孤儿》的符号叙事
2018-11-14王天昊
王天昊 孙 宇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 人文学院,黑龙江 大庆 163319)
由著名导演陈凯歌执导的影片《赵氏孤儿》于2010年岁末一经公映就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该片引起大家热议的原因,不外乎以下两点:其一,其改编自元代著名剧作家纪君祥的同名悲剧作品,故事本源最早可追溯至《春秋》,后见于《公羊传》《谷梁传》,至《左传》故事情节始得以丰富,后在《吕氏春秋》和《史记》中也均有记载,历经唐、宋时期的延续,至元代由纪君祥在前人基础上创作出杂剧《赵氏孤儿大报仇》(后称《赵氏孤儿》),之后由在华传教士于18世纪翻译成法语,再后依次出现英、德、意、俄等各语种版本,可谓声名远播。2003年,《赵氏孤儿》被改编成话剧登上国内舞台。王国维曾评价说:“明以后传奇,无非喜剧,而元则有悲剧在其中。……其最有悲剧之性质者,则如关汉卿之《窦娥冤》,纪君祥之《赵氏孤儿》,剧中虽有恶人交构其间,而其蹈汤赴火者,仍出于其主人翁之意志,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由于原剧作跨时空、地域的超常影响力,使得由原剧改编而来的影片备受瞩目,实属情理之中。其二,改编后的影片与原戏剧在内容上有较大差异,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偏离了原剧“舍生取义”的崇高主题,令部分观众对此持否定态度。就改编艺术来说,观众产生这样的反应是比较常见并可以理解的。
在学术领域,电影《赵氏孤儿》也同样激发了众多学者的研究热情,迄今为止,已发表的相关论文多达数百篇。任何文艺潮流的涌现及文学现象的产生均有其特定的语境条件。近年来,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及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使人们对文化艺术生活的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艺术、文化及传媒等领域百花齐放、异彩纷呈。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改编电影的大量涌现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广大观众的精神需求。但业界普遍认为,“一流小说改编成二流电影,二流作品改编成一流电影”。这种看法有一定道理,但不完全绝对。一般而言,一流作品无论在主题、结构、叙事、逻辑等各方面均已达到最高水准,难以有所突破。而在如此优秀的原作基础上的改编作品,有任何改动,都可能是对原有完美艺术的一种“破坏”,只有保证这种创新式的“破坏”仍然符合新的审美标准,并同样达到技术层面的顶峰,才可避免越改越糟的严重后果,最终得到广大观众情感上的接受。因此这种改编的确需要经受严峻考验,面临巨大风险。而对于二流作品而言,是因为在某些方面尚存在众所周知的不足之处。对这样的作品进行改编的过程,实际也是对原作品的不足进行完善修复的过程,由此使改编后的电影在艺术质量上得以超越原作。当然,艺术改编不应总以超越原作为目的,也可以从不同视角对相关主题进行新的诠释。观众群体当以客观、理性的态度尽力发现改编作品的创新之处,积极、宽容地对待存在的问题,以此保持对艺术审美能力的持续更新,有效促进艺术改编活动的蓬勃发展。从这点来看,电影《赵氏孤儿》的改编应属于前者,即电影改编前的原剧作《赵氏孤儿》在原有历史语境内,排除时空与文化变迁所导致的差异因素,应属于一流作品。
戏剧和电影作为独特的艺术形式,均以符号化的叙事方式来实现艺术家与观众间的交际愿望。从舞台演出符号到镜头语言符号的转换,需要语境符号及情感符号的参与其中,以确保新的主题含义的阐释及情感信息的传达与理解,从而使电影语言交际行为顺利进行。综合考虑,电影《赵氏孤儿》基于原剧作的改编,虽在某些细节之处尚存有大家公认的一些技术问题,但在语境重构与情感叙事方面还是令人耳目一新,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一、电影《赵氏孤儿》中的语境符号重构
在任何言语交际行为中,意义的理解与传达必须结合具体的语境才可得以实现。从戏剧文本的文字语言到剧场舞台的表演语言,至银幕上得以精彩呈现的现代化镜头语言,都是艺术家与广大读者、观众之间开展特殊言语交际活动的不同语言使用形式。艺术家将自身对具体现象的洞察与理解以作品的形式展现给世人,以求揭示、验证、分享或进行有教益的传播,同时带给其本人精神上的审美成就及情感愉悦。无论是戏剧还是电影,其交际行为均围绕中心人物的性格塑造、典型事件的细节描摹、矛盾冲突的合理设计、思想情感的细腻表达及主题意义的揭示升华等,而所有上述内容的呈现均须结合一定的语境才能以被观众所理解的方式得以实现。艺术改编活动是基于同一主题框架由一种艺术表达形式到另一种艺术表达形式的转换。任何交际内容的改编都需要在新的语境下开展。因此,艺术改编的过程就如同新的言语交际行为中对具体语词的重新选择,其意义的传达与理解必然需要重新构建语境。
有别于元杂剧《赵氏孤儿》对“舍生取义”主题的揭示,改编后的影片以原故事框架为基础,重在对基本“人性”的挖掘。无论是在人物的塑造、事件的安排还是冲突的设计,均有较大改变,使得不少观众在情感上很难接纳,但如不考虑原剧作的情节,而只在逻辑上进行检验,那么绝大部分内容的改编还是有一定道理的,语境建构的意义即在于此。
第一,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为了使之更符合“人性”假定,需要对原剧作中二分式的非忠即奸的典型人物塑造进行颠覆,即减少对赵氏一族正面形象的塑造情节,而让屠岸贾除了在弑君灭赵上表现得阴险残酷外,尽量让其展现正常人性的一面。影片中没有提及元杂剧中“锄麑触树自尽”及“赐饭饿夫灵辄”等关于文臣赵盾忠良形象塑造的情节,而是在赵盾与晋灵公及屠岸贾有限的对白交锋中增加了其姿态较高、言语凌厉且咄咄逼人的描写。而屠岸贾则以隐忍、低调的形象示人,在明知被赵氏父子误会时,平静地将弹子吞下以传达歉意的方式示弱;和下属谋臣言谈中表示从不杀女人;在搜寻赵氏孤儿过程中,能理性并耐心对待出现的两个婴儿,在确定哪个是真正的赵氏遗孤前并没有简单粗暴但也是最有效地一并杀害。之所以有部分观众对此表示质疑,是因为他们在观看影片时,对屠岸贾这一人物性格的假定仍停留在元杂剧所描绘的奸臣身份上。而改编后的影片并未将赵氏父子与屠岸贾的矛盾冲突定性为忠奸之战,而是同朝官员间基于政治利益的权力斗争。影片中,屠岸贾除在弑君灭赵及后续的搜孤杀孤行为上表现得阴险残忍之外,并无其他言语及行为细节能够突出其奸诈卑劣之处。而元杂剧中则分别通过锄麑中止刺杀赵盾的行动并触树自尽、韩厥与公孙杵臼等人的话语及内心独白,间接明确了屠岸贾是个残害忠良的奸恶之徒,其行为早已人尽皆知并激起公愤。也正是基于这样的人物形象设计,才使得屠岸贾虽然在电影中最终死去,却只能被赵氏孤儿(程勃)以个人身份在复仇打斗中杀死,而程勃无法像元杂剧中那样以忠臣后代的身份高调地复仇并还赵氏一族的清白。事实上,当晋灵公在影片中被改编成死于毒蚊暗算并成为屠岸贾设局诬陷赵氏父子的一枚棋子时,赵氏父子的冤屈就已在世人眼中成为不解谜团并永远失去昭雪的机会。在影片中,赵氏孤儿的成长过程被作为重点来进行叙述。关于程婴、屠岸贾与程勃三人间的生活细节的设计,是影片改编过程中的难点,同时也在塑造人物形象、诠释影片主题的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第二,在事件的安排上,影片开头依时间顺序先后安排了赵朔出征前送行、凯旋后迎接及殿前宴会等三个场景,简洁明快地展现了晋灵公、赵氏父子及屠岸贾等人之间的相互矛盾关系,为接下来的冲突事件的设计安排做好了语境准备。在影片后部分则通过程勃上学堂、野外玩耍及随养父出征等事件的安排设计,就程婴、屠岸贾与程勃三人间复杂的情感变化进行了描述,为程勃的性格塑造及屠岸贾人物形象的丰富完善奠定了重要基础,也为彼此间的情感冲突做好了语境铺垫。
第三,在冲突的设计上,影片的前段有弑君灭赵,在中段有托孤救孤,在后段有养孤复仇三个关键性冲突。弑君灭赵环节节奏紧凑,场面惊心动魄,突出了有别于戏剧的电影镜头语言的叙事优势,为观众带来极大的视觉冲击。托孤救孤环节的紧张气氛营造,程婴与妻子间的会话及矛盾痛苦心理的表现为观众带来强烈的心理冲击,庄姬、程妻母子及公孙杵臼的先后死去在为影片掀起全剧高潮的同时,也将悲凉压抑的气氛渲染到极致。养孤复仇环节的人物心理刻画则是影片关于人性主题诠释的关键,程婴与屠岸贾二人各自心理矛盾的揭示伴随着赵氏孤儿从婴儿至少年的成长全过程。这个过程也是人性的复苏过程。而屠岸贾的人物形象从阴暗到人性回归的重要过渡必须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从程勃身份最终揭晓的那一刻起,如何设计、安排并处理这样一个复仇活动,理应得到观众的心理关切。相较外在的冲突而言,对屠岸贾内心世界基于人性的挣扎所产生的情感冲突的描述则显得尤为重要。
二、电影《赵氏孤儿》中的情感符号叙事
苏珊·朗格认为:“艺术就是将人类情感呈现出来供人观赏,把人类情感转变为可见或可听的形式的一种符号。”元杂剧《赵氏孤儿》被列为我国四大古典悲剧之一,剧中韩厥、公孙杵臼等人为保全赵氏孤儿先后慷慨就义,使故事充满悲壮的情感。改编后的影片在情感符号的广度上获得了极大的丰富,在悲剧深度上得到进一步深化。
电影开头,赵朔即将奉命率军出征御敌,晋灵公携屠岸贾等人为赵朔送行。通过晋灵公和屠岸贾、屠岸贾和手下谋臣、晋灵公和赵氏父子等会话分别形象地表现了晋灵公对赵盾父子军功显赫的忌惮猜疑并对屠岸贾与赵盾父子之间极尽挑拨之能事,屠岸贾对赵氏父子的嫉妒与敌视及赵氏父子对晋灵公与屠岸贾的不屑与不满。上述消极心理的细腻描摹为后续影片中惨剧的发生做好了情感准备。宴会剧变一幕中,赵盾父子的遭伏遇险、两名随从将官的舍命护卫使影片气氛由消极阴沉瞬间转入悲壮凄凉。斗杀场面惊心动魄,情感的降格扣人心弦。当程婴将婴儿藏好即将离府却被赶来的韩厥迎面拦住时,紧张的气氛又开始升腾起来。冲突的出现总是以对立双方的情感冲突为表现,这一场景中的矛盾最终以庄姬的挥刀自尽将悲情渲染到极致,以此引发韩厥内心深处人性的唤醒,实现由绝望到希望的情感转换,顺利将事件的冲突移转至下一阶段。在程婴家中,其与程妻的对话又将矛盾揭示出来,事关两个无辜婴儿的生死命运,险象环生的残酷现实又将二人推到了人命关天的风口浪尖,整个救孤的过程在极其紧张压抑的氛围中以程妻母子及公孙杵臼的牺牲走向尾声。
但关于影片悲剧情感的表达,则是以赵氏孤儿(以下用程勃指代)成长过程中屠岸贾内心父爱的被唤醒、其人性的复苏为起点。在影片前段,当赵朔接到妻子生产的假信息并将回府探视时,面对屠岸贾的虚伪祝贺回应道:“如果大人的儿子还活着的话,也该有孩子了吧?”这句回答可以看作赵朔对屠岸贾的嘲讽,为揭示二人间的矛盾做铺垫,但同时也客观地为屠岸贾对程勃所表现的慈爱关心提供了重要的现实依据。在弑君灭赵之后,屠岸贾顺利扶持幼帝登基临朝,全面掌控时局,其注意力由原来的争权夺利逐渐向日常生活转移,养子程勃的存在对其丧子之痛起到了一定程度的弥补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程勃逐渐长大,屠岸贾与养子间的日常交流使屠岸贾以往一直为权力争斗所占据的人性世界逐渐开始复苏。他从无法忍受程婴对养子的严厉看护开始,到主动带着程勃出城郊游的态度转变,原本深沉阴鸷的面容开始出现慈爱的光辉。当屠岸贾从披甲佩剑的少年勇士的飒爽英姿隐隐觉察到赵朔的身影并意识到程勃的真实身份时,其长久累积的对养子的父爱与原本隐藏的对赵氏一族的仇恨在其内心开始激烈挣扎。在程勃临阵御敌不利、深陷险境后高声向养父求救时,屠岸贾稍作犹豫,便毅然决然地冲入敌军,力挽狂澜,将养子顺利救出。此时,屠岸贾的内心异常复杂矛盾,其情感的剧烈波动变化被影片演绎得淋漓尽致。而屠岸贾被韩厥的毒箭射中,危在旦夕时,程勃不顾程婴反对夺来解药给屠岸贾服下。用屠岸贾自己的话说,他已经彻底想通了关于程勃的事情。他的情感痛苦已得到缓解。但对于程勃而言,其情感悲剧才刚刚开始。当韩厥说过的话从屠岸贾口中被说出时,程勃真的开始怀疑自己的身世了。至此,经过一系列事件的发生,当程勃身世之谜被完全揭开后,三人之间的情感矛盾彻底被激化。昔日双双蒙在鼓里的父子如今因真相大白却转瞬兵戎相见,无疑使影片的悲剧色彩达到了顶峰。在屠岸贾刺中程婴的同时,自己也被程勃一剑刺中要害。屠岸贾临死前看向程勃的似笑非笑的表情,将其内心情感暴露无遗——如果说他终于获得了精神上的救赎与解脱,那么他之前该有多矛盾与痛苦呢?程婴也倒下了,临死前似乎又回到了梦幻般的家中,推开房门,一切恍如隔世。当程婴步履艰难地走在闹市街头,过往行人视如不见,却望见自己的妻子正抱着孩子在前方向他回眸一笑,转身扭头离去……影片关于赵氏孤儿复仇情节的改编使人物的人性得到了深刻的阐释,人物形象由扁平变得立体化,同时使故事的悲剧程度得到深化,较元杂剧中的复仇情节,更加令人深思。
真正的悲剧,并不总是以剧中人物的死伤数量及惨烈程度为评价标准,而要看剧中的矛盾冲突是否因关键人物的死难而得到解决。矛盾基于一定悲剧结果的被解决程度影响着悲剧主题阐释的深刻程度。元杂剧中韩厥、公孙杵臼为救赵氏孤儿而舍生取义,是在为实现内心某种现实目的前提下的一种主动选择。他们在献出自己宝贵生命的同时,成就了道义,并实现了挽救赵氏孤儿生命的愿望。在影片中,对于屠岸贾、程婴和程勃三人而言,其悲剧的深刻与超越就在于即便程勃顺利杀死屠岸贾,程勃自己也会因生活在无法解决的痛苦中持续遭受巨大情感折磨。他杀死的既是自己的仇人,也是真心养育自己15年的恩人。此时的屠岸贾早已非彼时的屠岸贾了,而是与程婴共同养育程勃多年的屠岸贾。影片后部分并无任何关于屠岸贾的负面形象描述,且他对程勃的身世并不知情,因此其对程勃的养育并非出于利用,而是发自内心的真实情感。如果影片并没有像原剧作那样浓墨重彩地将屠岸贾描述成一个扰乱朝纲、残害忠良、祸国殃民的奸臣形象,那么程勃杀死屠岸贾的行为则不会上升到为民除害的高度。屠岸贾的负面形象越被弱化,其对程勃付出的情感越多,程勃通过杀死屠岸贾所产生的那种为家族复仇的成就感就越低,而其相应的因杀死养父而必然产生的负罪感就越强烈,所造成的悲剧感就越深刻。矛盾冲突实际并未被有效解决,而是由一种矛盾过渡为另一种矛盾。
从这一视角出发,影片《赵氏孤儿》通过语境符号与情感符号的综合运用来实现从戏剧到电影的叙事艺术改编,用较多篇幅描述赵氏孤儿的成长过程,来完成新主题阐释的语境建构,使悲剧情感顺利得到表达并在悲剧的深刻程度上有所突破,成功带给观众新的审美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