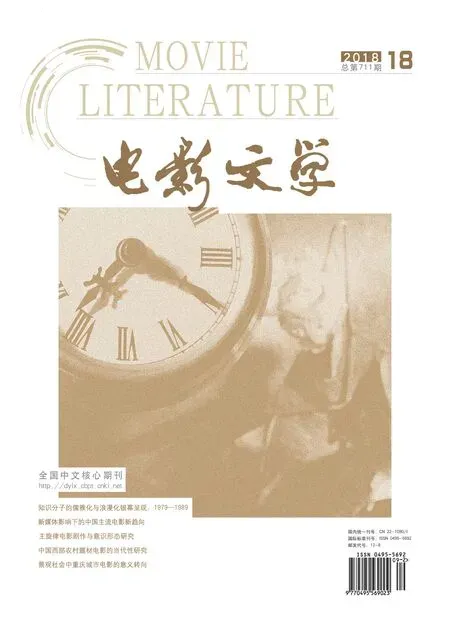《我不是药神》:纯态事实的美学呈现
2018-11-14王立君
王立君 康 超
(长春工业大学,吉林 长春 130000)
2018年7月5日,文牧野执导的《我不是药神》上映,影片成功地实现了“叫好又叫座”的目标,在获取市场的价值认同的同时,又满足了业界批评的期待。人们已经普遍肯定,《我不是药神》是一部现实主义佳作。而事实上,电影不仅秉承了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而且此基础上向着更纵深的方向发展,这也是影片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一、底层生活的客观实录
真实感是现实主义电影的主要体现,也是现实主义电影的主要特色。贾樟柯曾经说过:“世界上只有一个主义就是现实主义,无论哪种类型的影片都是基于现实。作为一个导演,需要努力去捕捉和呈现它,应该诚实和庄重地面对它。”《我不是药神》就秉承了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客观的反映出以慢粒白血病患者为核心的底层人的生活。
观众对《我不是药神》的接受,实际上也是对慢粒白血病患者及其生活圈子的一次接触。如在电影中,思慧因为有一个罹患白血病的女儿而不得不在酒吧跳钢管舞赚钱。在程勇等人的“团建”中,程勇程勇拿钱戏弄酒吧经理,让他去跳脱衣舞,思慧在一旁看得尽兴,大声的喊着脱衣服。这一幕是凡俗甚至恶俗的,但这又是真实的。思慧的发泄中释放的她被迫从事这一有屈辱性质的工作多年积攒的痛苦与怨恨;而另一方面,电影又没有单纯地将病人及其家属们的生活以“痛苦”,“艰难”或“坚强”等标签化。如电影中三个人斗地主一幕,便拥有着十足的生活气息,程勇:“你炸他啊,你炸我干毛啊?”黄毛天真地说:“不炸你跑了啊。”“你会不会玩啊,你他妈把把认错地主,你脑血管全被黄毛堵住了啊。”尽管当时主人公们已经凭借卖药赚了一点钱,但依然没有改变自己的底层身份,他们日常的娱乐,生活的场所,感受到的酸甜苦辣等,依然是底层化的。程勇情急之下的粗话,更是让观众如在目前,这是电影对一个小人物生活状貌的忠实表现。
同时,影片中对人的生物本能的如实展示,也进一步增强了影片的真实感。在《我不是药神》中,人的生存本能就是最大的戏剧冲突。吕受益、黄毛等人因为患病而必须持续吃“格列宁”以缓解病情,一旦停药,就有可能病情恶化,在痛苦中离开人世。然而通过正规渠道购买到的“格列宁”又价格昂贵,非一般病人承受得起,于是为了延续自己的生命,吕受益鼓动贩卖“印度神油”的程勇从印度走私仿制药,黄毛更是不惜犯下抢劫罪,在自己连廉价的仿制药也买不起的情况下,从吕受益的手中强抢仿制药,愤怒的病人们在医药公司门前聚众抗议,甚至向医药代表泼秽物,表示自己左右是个死,已经不再害怕犯法等,这些脱离了正常人生活轨道的,甚至有着动物性的行为,其实都是在求生欲驱使下发生的。而电影中给观众留下印象最深刻的台词,也无不与生存本能相关。如黄毛死后,程勇对曹斌的质问:“他才二十岁,他就是想活命,他有什么罪!”又如老奶奶对警察平静地说:“4万块1瓶,我病了3年,吃了3年,为了买药,房子没了,家人也拖垮了,谁家还没个病人,你能保证一辈子不生病吗?我不想死,我想活着。”生存本能存在于所有人的意识之中,人们都有着对生老病死等问题的恐惧,正是这些台词戳中了社会心理最敏感的部位,引发了观众情感上的共鸣。
二、主体倾向性的隐形化
在现实主义电影中,创作者始终带有一定的立场,而这种立场则通过电影传达给观众。现实主义电影导演往往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这种责任感在影片中体现过于明显,就会呈现出某种说教意味。《我不是药神》则做到了恰当的拿捏分寸,避免在情节的设计,人物的塑造等方面投射过多倾向性,力求将叙述态度保持在客观程度上。
《我不是药神》从头至尾都把握着电影的平衡感,尽管主创有着深切的对白血病人的同情等个人感情,但电影尽可能地以一种旁观、超然的姿态讲述了整个围绕着“格列宁”展开的风波。在悲与喜,正与邪,情与法等矛盾中取得了微妙的平衡。
从悲喜剧的平衡而言,影片悲喜交织,笑中带泪。我们很难把这部现实主义电影具体定义为悲剧或是喜剧,吕受益“满嘴口罩”出场,干瘦的身形,浮夸的神态;黄毛“杀马特”形象的出场是那么的“活力无限”,而真正到他们死亡的那一刻,看着他们苍白的脸和满身的血,又不免有些心痛与不舍;一整条街的人出于尊重自觉地摘下口罩为程勇送行,那时的程勇是他们心中的“药神”;三年后,当格列宁被纳入医保,程勇不再是“药神”,来接他的只有曹斌一个。观众都说:“看着看着就哭了”。当然“看笑看哭”并不是衡量一部好电影的绝对指标,但当一部作品能在曲终人散时予人以“治愈”,其珍贵不言而喻。
从人物的塑造而言,电影中没有彻头彻尾的大反派,也没有自始至终的老好人。在影片的前半部分,程勇绝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完美先生”,穷困潦倒、懒散堕落、打老婆欠房租……这绝对不是一个正面人物的形象;那个心狠手辣的张长林,用报警的方式威胁程勇,夺取他的仿制药代理权,然后漫天要价把众多病人推进深渊……可在影片的最后关头,人性在漆黑的天际中闪现出一丝光亮,这个“小人”居然咬紧牙关保护了程勇。影片没有让我们直面现实中的凶残丑恶,而是向我们讲述了“乌托邦”式的温暖童话。
从情与法的冲突而言,电影中情与法的抉择,相辅相依。踏实肯干的警察曹斌在法律与人命之间最终选择放弃调查;本该因贩卖假药被处以六年有期徒刑的程勇,三年之后就被释放;事实上,电影自始至终,都没让情大于法,同样也没让法湮没情,它很克制的找到了二者之间的平衡感。
正是在这种平衡与中和之中,电影主创最大限度地使自己的倾向性隐形了,主创提供“生活切片”,却并不为观众彻底解答切片暴露的病灶和问题,而将思考的空间留给了观众。这也是电影上映之后,观众热议纷纷,对“《我不是药神》中究竟谁有罪”的问题莫衷一是的重要原因。
可以说,在处理社会现实题材时,相比起以激进的批判工具解释外在世界,《我不是药神》则更接近于给观众展现了某种“纯态事实”,观众跟随程勇一起介入到白血病患者的凡俗人生中,目睹了种种或野蛮冷酷,或温情感人的生存景象。在形式与内容上,《我不是药神》都以客观的立场引领观众而非强迫观众接受创作者的价值观,这无疑为当代中国电影提供了一种宝贵的审美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