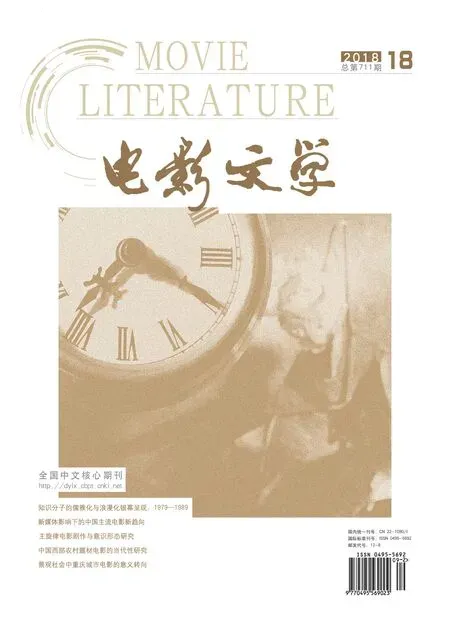《长江图》《路边野餐》之诗情与哲思
2018-11-14朱慧
朱 慧
(中央民族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北京 100081)
戏剧电影与诗电影代表两种不同美学方向的电影形态,导源于对电影是戏剧本性还是抒情诗本性的不同理解,其概念阐释涉及对电影本体论的辨证。回顾中国电影百余年发展历程,不难看出,戏剧性叙事一直占据着影片结构中心地位,成为中国主流电影叙事传统,其主要功绩在于缔造了一系列带有时代历史特色的家国神话、道德神话与票房神话等影像传奇,无论是早期背负的改良社会、教化民众等社会功用主张,还是当下以大众娱乐为导向的商业片滥觞,戏剧性电影更多指向与迎合的是一种集体话语与狂欢。相较而言,诗意电影在历史发展长河中只能屈居一隅,然其虽脉感微弱却也具备着绵亘影史的持久生命力,它以一种突出个体生命意识流动、淡化外部情节冲突的私人话语风格,呈现出相较戏剧性这一主流叙事传统下的潜行泛泭之姿。2016年上映的两部当代佳作《长江图》与《路边野餐》,不仅让我们看到了诗意电影在其坚守的电影美学方向上的突进,更流露出对人历史生存情境的西方现代性哲思情感体悟。基于此,本文试以此两片为互文性参照,探寻中国当代诗电影在诗意叙事结构中呈现出的共同美学表征,及其映现出的独特艺术形态气质。
一、祛幻与入幻:虚实相生的反线性叙事结构
戏剧性叙事偏向表达外部现实,诗意叙事则注重描画心理现实,由于对待现实关系的角度不同,导致影片最后整体叙事风格面貌呈现的迥异之态。诗电影主张电影应像抒情诗那样达到“联想的最大自由”“使想象得以随心所欲地自由驰骋”“应当摆脱与情节的任何联系”,这种淡化外部戏剧冲突的电影美学观,主张通过镜头画面与蒙太奇的重组来结构影片的人物心理时空逻辑表达,从而提供超越外部情节理性发展的诗情画意。简而言之,戏剧性叙事倡导故事外部情节流动的线形时空叙事,注重故事发展背后的逻辑推理与理性经验,传承着现实主义与写实风格,影片基调是祛幻的;而诗意叙事则弱化情节与理性,呼唤着知觉经验的回归,肯定人物心理时空的非线性表达,人物主体是唯心的感性存在,故事演绎与情感表达则呈现出一种入幻的审美诉求。
尽管外部现实不是诗意电影言说的重点,但作为引领观众进入人物内部情感世界的入口却也必不可少,只是笔墨分量较少,因而在内部情感的浓厚隐喻与外部情节弱化简述的结合下,诗意电影营造出虚实相生的间离张力与复式叙事审美效果。如影片《长江图》通过“溯洄从之”这种时空结构的逆推倒转,构建出由实入虚、虚实相生的双向发展时间轴。在故事构架的现实情境中,男主人公高淳与商人罗定协议将10吨鱼苗运送到宜宾,然而随着故事发展的推进,这一现实情境早已被另一重情爱诗意时空冲淡虚化为远景。影像利用大量远景构图,建筑了一个不断流动、不断变幻、不断生成的世界,随着溯江之行中高淳视角中展现的女主人公越发年轻的容颜,我们知道这里时间不是前迈而是后退的。
《路边野餐》则在影像开头借用《金刚经》中一段引语统摄全片的时空观,其中“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成为全片时空叙事中表现虚无主义情韵的“诗眼”。影片前半段以“祛幻”的叙事情节为主,男主人公陈升年轻时因斗殴伤人而入狱九年,用他呢喃在嘴边的现代诗可表达为“没有了心脏却活了九年”,这期间妻子与母亲相继离世,对妻与母的负罪意识衍化为对侄子的责任意识,由此陈升踏上了去镇远接小侄子卫卫回家的旅程。随着旅途的深入,影片正式进入“入幻”的诗意时空情境,在荡麦,已逝的妻子在理发厅为他剪发,长大后的青年卫卫骑着摩托载他到河边,这里记忆、现实、未来同构交错为当下同一时空情境,“过去心”“现在心”“未来心”得其“不可得”之显。“在时间中,每个瞬间只有在消灭前一个瞬间——自己的父亲,从而使自己同样快地被消灭的情况下才存在。过去和未来都像任何一个梦一样微不足道,而现在只是两者之间没有维度和绵亘的界限”,诗意叙事手法实现了影像时空表达的自由化,这里时空可以倒转逆行,可以停滞不前,亦可与未来和历史发生多重折叠碰撞,过去、当下与未来之间的严格界限得以融通,它们相互消解而又相互构筑。记忆与现实的虚实真假无须考辨,因为诗意叙事最终实现的不是戏剧性情节发展的真实,而是在入幻与祛幻的复式叙事结构中抵达情感的真实。
二、癔症式吟游:负罪意识询唤下的抒情呓语
诗意电影中,深层记忆的绵亘永恒性与现实表象的破碎易逝性构成对比,当下生存情境如此乏味,未来又如此虚无,唯有珍贵的情感记忆聊可慰藉,成为主人公们逃离当下的生命出口。换言之,唯有历史记忆可以重整修葺现实这座已然崩塌的生存废墟,抵制、对抗时间对生命情感意识的无情冲刷汰换。主人公们对历史与记忆一再表露出的这种深切归返欲望,毋宁说是受到寻乡返根意识的潜在召唤与驱动。《长江图》中高淳逆水溯源,最终抵达长江源头楚玛尔河,回望记忆中的江水在历史岁月中翻腾时不觉热泪盈眶,《路边野餐》中陈升由物理空间层面上的家乡踏入精神情感上的记忆之乡,事虽有殊,其理则一也,他们在入幻与祛幻间上演的茫然迷醉之态,显露出人与故土分离的情感创伤。由于长久失去了与故土的经验性关联,个体生命意识中沉淀的怀乡意识、历史意识、归返故土的原始欲望被一再反复点燃激发,这种归乡渴求造成人当下生命激情与生命欲望的龟缩、退却,自我意识与当下身体所处时空再也无法结合、呼应、交流。
诗意电影中的主人公便表现出这样一种人与自我分离的“癔症”式病态人格特质,他们意识朦胧,躯体感官功能缺失,与当下生存情境处于“感官剥夺”的隔离状态,对自我当下身份无法认可,行为轨迹犹如漫游症患者。那么,为什么主人公们与当下时空发生了交流障碍?为何会生发出一种所思在远方的归属感?为何当下如此不堪、面目可憎?以上种种杂疑也许可从主人公们身掮的负罪意识揣得端倪。《路边野餐》中这种负罪意识在情节叙述实线上指向母与妻,在诗意叙事虚线上则指向宗教上的“人生而有罪”与因果轮回观。《长江图》中这种负罪意识更是指向多元对象,首先,就故事现实层面而言它指向亡父;其次,这种负罪意识由“家”的人伦情怀指向“国”的社会发展批判意识,不难看出影像涉及三峡大坝修建带来的生态环境、移民拆迁等沉重社会历史问题;最后,通过安陆与塔中佛僧的辩难,也可看出作者对人群兼具“负罪”与“赋罪”的双重情感,安陆质问佛僧“什么是罪”,她觉着“活着就是罪,因为只要你活着,就要跟别人争夺生存的空间和资源”,这里罪与无辜二元违戾,罪是生存宿命,注定清缴无辜。
在负罪意识的体认与压抑下,主人公们对当下的逃遁欲望、对回忆的归返渴望也就不难理解了,“一定有人离开了会回来/腾空的竹篮装满爱……”“我从未体验过由衷的快乐/心满意足如在母亲怀中……”(《长江图》),“我”对当下的鄙憎毋宁说其实就是对自我的鄙憎,“我”想逃离当下其实就是想逃离自我,这种对当下自我身份的否定与厌恶产生了自我分离、自我撕裂。依据拉康的镜像理论,自我与他者的差异感知是确定主体身份的前提,这里负罪之我成为自我的他者,确认这种异质性才能获得主体身份,然而,“我”是厌恶排斥这种异质性他者对自我的填充的,“我”排斥成人世界必须承担的各种缺陷与不完满,意味着“我”对获得主体身份认知的弃权,因而就某种意义而言,“我”是拒绝成长的。回忆中的无罪状态犹如母体般温存,恰如婴儿诞生之初的自我完满圆融之态,这种无罪之“我”,没有任何缺憾、缺失与缺陷,是“我”所渴望回归的自我同一状态。然而,这种回归欲望必定要陷入失落,因为成人之我既已感知负罪之我的异质性,便丢失了自我与他者的融合统一状态,又如何再逆反成长为孩童,重获原初那种未分化的存在?这种悲剧性也便催发了主人公们自我见放的癔症式吟游,唯有脱离对当下在场的感官知觉,才能摆脱自我撕裂带来的情感苦痛,呓语此刻是生命意识深渊的回望呼喊,是被压抑、被禁锢、被封存的心理能量的无意识释放。对自我同一性回归落空产生的焦灼感、丧失感、受挫感,唯有在这种漫游呓语中,才能得以短暂地宣泄、缓释、抚慰。
三、激情的疏离:虚无主义晕染下的存在之伤
归返欲望的落空使得精神主体陷入一种“无家可归”的流亡状态,“我”既无法再次获得生命元初的自我统一圆融感,也无法抵达碰触生命存在的终极意义,“通过生成是得不到什么的,在一切生成中并没有一种伟大的统一性可供个体完全藏身”,在这个异己的世界中,“我”对自我异化与分离的一次次抵抗在负罪与必死面前最终不过都是徒劳。对反抗价值的贬黜消解了人的存在意义与价值目的,而目的论的丧失引发出虚无主义人生观。具体到电影文本中便体现在人物行为动机的生成与消解上,《长江图》中无论是世俗动机上的贩运协议还是诗意精神空间中对女主人公的寻觅,都在男主人公高淳突然被刺身亡,或言在他抵达长江源头楚玛尔河,见证到那块象征生命源头与死亡、起点与终点的墓碑前清零了。《路边野餐》中陈升由凯里到镇远的旅程肩负多重使命,他要接侄子卫卫回家,替女医生跟老情人慰问告别,转交一件衣服与一盒磁带,然而这多重目的最后一件也没有达成,人物对生命的虚无体悟便在这种对目标的弃寻与抵达失败中实现了同构。
就此,虚无主义成为诗意电影呈现出的主要美学范式与原则,在虚无主义哲思情感的晕染下,主人公们呈现出欲望野性退化的、与生命激情相疏离的病态生命面貌。需要注意的是,生命激情的抽空不仅影响了主体人物形象的构建,它最终扭转的是影像文本整体的抒情基调,实现了由“抒情”到“疏情”的情感转向。换言之,影像在不断构筑颓废、伤感、失落的诗情诗意时,也在不断反噬、消解、稀释它,以此走向平静、淡漠、一切皆空的虚无主义情韵。这种抒情消解策略不仅体现在前文提到的人物行为动机的最终归零上,还体现在影片对充斥其中的现代诗的处理上,两部影片皆以主人公沉浸过往的回忆之态呈现诗歌,相对于追忆状态中所指涉的抒情对象,语言符号堆砌而成的诗歌永远只是对情感记忆的一种迟到表述,而影像画面符号既在描绘“此情可待成追忆”的此时此地此情,亦在呈现“只是当时已惘然”的彼时彼地彼情,就此,伤逝成为诗电影表现的主要叙事情境与抒情症候。这也契合了华兹华斯的经典诗论,他认为诗“起源于在平静中回忆起来的情感”,正是这种“在平静中回忆起来的情感”使得诗电影主人公在入幻与祛幻的往返游离间,上演出“平静→抒情→回归平静”的作诗状态与情感波动回路,影像情感基调最终由隐喻构建的浓厚“抒情”滑向“疏情”的平淡、悠远、虚无之境。
四、结 语
“从模仿外部世界的艺术,走向了本体论的诗(艺术),诗不再是去意指实在的绝对本体,而是生存本体自身的诗化,是感性存在自身的诗意显现。”以此观照,相较电影诞生之初对外部物质世界的记录、再现、模仿,诗意电影实现了由“外”向“内”的场面调度,聚焦于对人内心感性世界的诗化呈现。在戏剧性故事片、商业片宰制电影市场的今天,《长江图》与《路边野餐》以独特的艺术形态气质彰显了诗意电影的反抗、独行之姿,在对现代人生存情境的诗化表达与现代性哲思观照下,沉静而自信地开拓着电影美学意蕴表现手法的新疆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