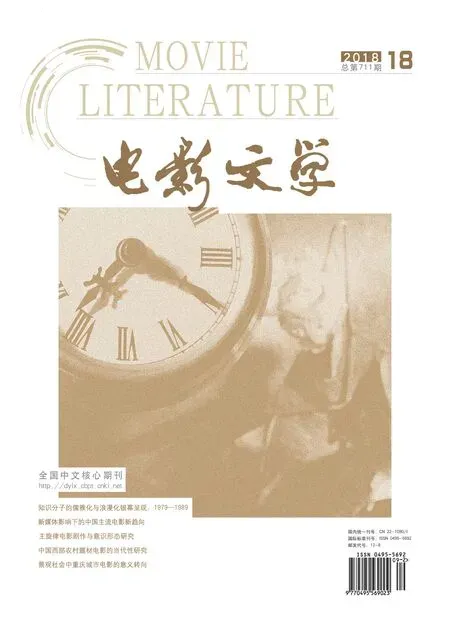王童电影:历史的乖谬与小人物的挣扎
2018-11-14孙英莉
孙英莉
(黄冈师范学院 新闻与传播学院,湖北 黄冈 438000)
王童是一位具有强烈的社会历史批判意识和人道主义精神的台湾导演,他导演的电影擅长以政治修辞来反思历史,以哲理思维来关怀人类,传达出历史的乖谬和小人物的挣扎。他把人物置于大历史背景下,以残酷而又荒诞的笔触为台湾历史立传,以戏谑和嘲讽的叙事格调表达了对统治阶层的批判与控诉。在展现人物命运时,较多地着墨于人性的细微层面,对处在台湾社会底层的百姓和边缘群体给予极大的同情,从哲学意义的高度探讨了台湾以及台湾人的身份认同危机。
一、历史反思
通过小人物命运来揭露、控诉与反思历史是王童电影的一个重要文化主题。王童导演的第一部影片《假如我是真的》就给观众呈现出一种揭露批判的姿态,其后的《苦恋》《无言的山丘》更是对中国“文革”和日本殖民侵略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与控诉。即使在武侠片《策马入林》也仍能看到导演对当局统治者的批判。为了强化批判的力量,导演为这四部影片的主人公设置了悲剧性命运,影片都以他们死亡作为结局。
影片《假如我是真的》和《苦恋》分别改编自内地作家沙叶新和白桦的“伤痕文学”作品,描写了“文革”历史时期在极权政治下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尽管两部影片都体现出导演强烈的批判锋芒,但由于原剧本在真实反映社会现实层面上存在问题,特别是国民党为了达到其政治目的,要求在影片中竭尽所能地渲染和夸大“文革”给内地人民带来的灾难,丑化共产党形象,污蔑社会主义社会生活,企图让台湾民众对大陆产生逆反情绪,因此影片创作有先入为主的倾向,它们不可避免地烙上了国民党反共思想的痕迹。
与前面两部影片不同的是,影片《策马入林》对唐朝末年统治者的批判要含蓄得多,也高明得多,因为导演不是以介入者的姿态讲述故事,而是以旁观者的身份让故事自然呈现。影片中的官兵代表着统治阶级,村民代表着在官兵统治下的普通百姓,而土匪则代表着特殊生存状态下的边缘群体。村民是最悲惨的群体,因为他们既遭受政府的重赋,又遭受土匪的抢夺。但土匪们的生活似乎并不比村民要好一些,正如一土匪所言,“如果日子好过的话,咱们大伙也不必大老远跑来干这个”。当土匪来到村庄抢劫,村民向官兵求救时,不可思议的是官兵不是为了维护村民利益而是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出来迎战。村民的生存状态尽管惨淡,但毕竟有自己的家,而土匪们只能颠沛流离,不但被官兵追捕,还随时可能会因没抢到食物而饿死。因此,影片对统治当局的批判也就不言自明了。
在王童的作品中,《无言的山丘》的批判和控诉是最有力度的,也是迄今为止最能代表王童导演艺术水准的作品。影片描绘了台湾底层庶民群像,如以断指的代价逃脱地主盘剥来到日本人强占的九份金矿打工,不仅没实现发家梦,反而断送了性命的阿助,在反抗日本矿警的搜身中被活活打死的成仔,被新来的、道貌岸然的日本矿长压榨的“万里香”的妓女们,以及自认为是日本人但也无法摆脱身处底层的悲惨命运事实的红目和富美子等。影片在揭示造成群体悲剧命运的原因时,其锋芒明确指向日本侵略者。影片取名“无言的山丘”,山丘作为故事和历史的见证人,它当然“无法言语”,但却形象地反映出历史的失语状态,表达了导演对日本侵略无言的控诉,“将台湾历史的伤痕与台湾庶民的无奈推展到悲情史诗的境地”。
二、政治修辞
王童对社会历史政治的控诉,往往在电影中采用讽喻和嘲讽的修辞手法,表现为以戏谑写悲情的特点。王童继承了中国战后讽刺喜剧诙谐、谐谑、讽刺相结合的优良传统,把政治讽刺类型片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影片《稻草人》和《香蕉天堂》《红柿子》分别对日本殖民统治下和国民党统治下的荒诞历史进行了讽刺和嘲讽。
在《稻草人》种种戏谑与滑稽现象中,我们看到小人物处境的悲情与可怜。影片叙事视角独特,以稻草人的口吻讲述了发生在陈发、陈阔嘴兄弟身边的荒诞故事。稻草人作为历史的见证人,以它为叙事者凸显出影片历史反思的鲜明意旨。为了躲避去南洋打仗的厄运,主人公阿发、阔嘴两兄弟在母亲的“偏方”帮助下变成了“沙眼、散光还带色盲”,想当兵还没人要。这种以伤害自己来躲避更大的伤害的方法,无疑告诉观众其处境的荒谬与悲凉。尽管他们兄弟俩每天都在田地里辛勤劳作,但一家人仍生活拮据、食不果腹。当儿子告诉阿发“老师问要不要改日本名字”时,阿发暴跳如雷,破口大骂:“改你的头!等你阿爸死了,进棺材以后,要改你再改!”可当儿子说改名以后配给的黑糖可以变白糖时,阿发态度又有所转变,并对儿子说:“你去问问老师,看阿爸能不能改一改?”显然,在日本殖民统治下,在经济侵略和压迫下,对于生活在底层的农民来说,这是无奈的生存策略。这样,当美国飞机在阿发兄弟的田里扔下一颗定时炸弹时,为了能够领取日本人的奖赏,兄弟俩自然也就能不顾生命危险,将炸弹抬到镇上的日本军部了。虽然最后企图落空了,但也不是完全没有收获,他们因扔入大海的炮弹的爆炸而捡回了一大筐鱼。末了的荒谬更令人笑中有悲,陈发兄弟一家人都沉醉在某种幸福感中,碗里满满的鱼肉,使他们不禁期望常有炮弹落下。画外音中小孩大声地希望天天有炮弹来,老祖母却以农民乐天安命的语气说:“两三天一次就够好了!”影片的戏谑和荒诞的处理丝毫没有掩盖指涉和批判的力量,因此,影片继承了中国战后讽刺喜剧电影的戏谑传统,成为尖锐的政治讽喻。
《香蕉天堂》揭露了外省人来到台湾后的荒谬处境,导演运用荒诞化艺术手法的才能在这部影片中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身份错乱”成为该影片的叙事框架和主题意旨,在多重身份的交错引出的黑色荒诞和讽刺意味中,深刻地体现出历史与政治的悲剧性。《红柿子》虽然是带有自传色彩的反映王童成长经历的作品,但仍在故事中充满了对政治的嘲讽。为了实现政治嘲讽的目的,导演对影片中的一些细节进行了精心的设置,在蒋介石的照片、姥姥的锦旗、福顺身上的中华民国国徽等滑稽可笑的细节中,政治权力遭到嘲弄、调侃和讽刺。此外,影片也讽刺了作为将军的“父亲”,通过描写“父亲”的失势和政治的炎凉,对国民党政权进行了尖锐的讽刺与批判。
三、人文关怀
王童电影关注现实,着意写人,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和人文情怀。不论是影片《看海的日子》中的妓女白梅,还是影片《策马入林》中的土匪何南,王童在影片中都为他们倾注了浓厚的人文关怀。
影片《看海的日子》讲述的是一位沦落风尘、以卖淫为生的妇女白梅为争取自由,恢复人的尊严而努力的故事。影片透露出一种理想主义色彩,完成了从“神女”到女神的人物形象塑造历程。白梅是创作者心中理想化的人物,“原著作者与编导美化白梅,是为了藉着她勇敢的面对苦难,开创命运,彰显生命的意志……传达出作品关怀人生的积极意义”。影片呼唤观众关切像白梅一样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物,“传达出为小人物向上苍请命的意图,悲天悯人的情怀十分动人”。影片《策马入林》塑造了一位凶狠毒辣但又有些许良知和人道精神的土匪何南。显然,导演对以何南为首的土匪甚至比对农民寄予了更多的怜悯之情。王童在接受《南方网》记者采访时曾说过,《策马入林》“这个片子看似是个一般的武侠片,也在讲村姑爱上一个盗匪的故事,反复在说这个事情,其实我心里是想把恶人都变好,影片中的恶人也不是那种大恶,还是有一些‘人道’在里面。”
影片《稻草人》《香蕉天堂》《无言的山丘》也不同程度地表达了导演对人的关怀,给社会底层以博大的同情,给负面人物以豁达的包容。影片《稻草人》既没有正面描写太平洋战争,也没有塑造反抗日本侵略的台湾民族英雄,而是展现在战争和日本侵略背景下,在极端恶劣生活环境下陈发、陈阔嘴兄弟一家卑微地活着的生存状态。影片并没有把人物简单地分为“好人”和“怀人”。一方面,导演对陈发兄弟一家寄予深厚的悲悯之情;另一方面,导演以人道的宽宏、过人的气度和胸襟,给予负面人物极大的慈悲与包容。影片《香蕉天堂》中的“门栓”和张得胜尽管从身体到精神受到极大的政治摧残,但“荒诞和侮辱并没有摧毁人的存在价值,《香蕉天堂》的政治讽喻并不虚无,它最终高举着人性作为政治悲剧的救赎。”而阿珍一家体现了农民身上所具有的优点:善良、淳朴。影片《无言的山丘》表现中国底层人民那种无论遭逢什么样的乱世都能艰难求生、希望永不磨灭的民族韧性,探索了底层人民之间纯洁、崇高的爱情、友情及兄弟之情,寄托了导演悲天悯人的情怀与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可以说,影片中从阿柔、阿助、阿屘到成仔、憨溪,甚至于日本人红目、富美子,都寄予了导演深切的同情。
四、身份认同
王童电影对人的关怀,具有哲学意味上的终极关怀意义,他在其影片中进行自我反省,对台湾以及生活在台湾的“外省人”进行追问: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将要到哪里去?尽管台湾历来是中国的一部分,但由于其地理位置独居岛屿而被海峡两地分隔,以及其飘忽动荡的历史和不断更替的政权统治,使台湾文化处于一种无根的状态。许多台湾电影或多或少地探讨身份认同这一文化主题。如李行的《原乡人》通过肯定主人公钟理和对“原乡”即祖国大陆的眷恋、向往表达了创作者对社国大陆身份的认同;侯孝贤的《童年往事》中祖母不断地寻找返回大陆的路,表达了上一辈人对大陆身份的认同。王童电影也不例外,甚至在这方面走得更远。
影片《香蕉天堂》中的主人公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中不断更换自己的名字,并因此闹出许多笑话。影片开始,门栓以何九妹的名字入伍,但由于执着于自己的身份,所以在军官点名时他会无动于衷,这正是源自于“门栓想象身份认同太强,以至于失去变化、操控符号的能力。”因此,当我们听到门栓以“明明是块肉嘛,哪是把米呢?”这句话来反驳张得胜的“偷鸡不成蚀把米”时,我们就不足为奇了。影片通过主人公身份的不断被改写,既揭示了历史对人性的异化,也体现了创作主体及台湾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焦虑。
影片《红柿子》绝大部分是王童的童年经验,因此回忆成了本片的叙事模式,过去的生活片段成了本片结构。本雅明通过对柏格森哲学的研究发现了记忆中潜意识材料的重要性,他指出经验“与其说它来自回想过程中被明确捕捉到的东西,不如说来自于积淀在记忆中的那些往往未被意识到的材料”,即对于经验来说,重要的不是“意愿记忆”,而是“非意愿记忆”。“非意愿记忆”是记忆主体在意识以外的记忆,不受主体意识的主宰,常附着于日常生活中琐碎、不起眼的事物。影片由大陆记忆和台湾记忆两部分组成,前者使用黑白胶片拍摄,而后者使用彩色胶片拍摄。虽然大陆记忆是黑白片,但唯有院子里的柿子是醒目的红。红色也是这部电影的重点色,贯穿整部作品,从姥姥床头上的红色寿字、姥姥寿宴中的大红寿字与红色桌巾、齐白石的画到姥姥的新衣等。影片中这些抢眼的“红”犹如呼应着黑白片中的红柿子般,成为过去的召唤,表达导演潜意识深处对家乡的怀念,对大陆身份的认同。影片片名之所以叫《红柿子》,王童解释道:“红柿子是非常中国、非常传统的一种物品,而且在中国的习俗中代表吉祥如意。”。可见,红柿子在影片中已成为家乡的转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