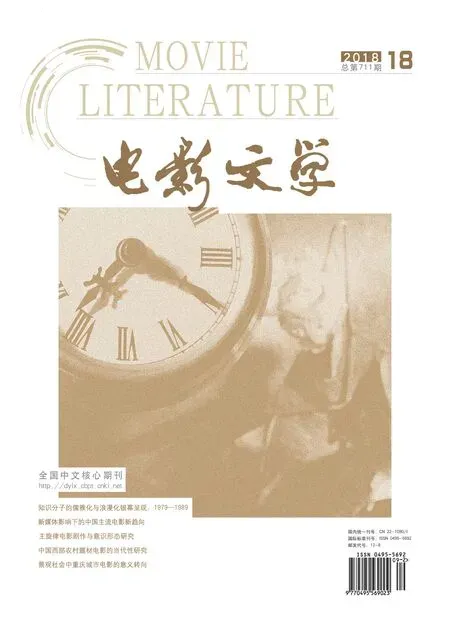复调文本:对贾樟柯电影的知觉现象学分析
2018-11-14曾胜
曾 胜
(浙江传媒学院 文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迄今为止,贾樟柯一共拍摄了九部剧情长片。纵观贾樟柯电影,不难发现,贾氏电影具有“复调文本”的特征。贾樟柯曾坦言:“我还期待电影的叙事和视听能发生非理性的‘碰撞’,让电影很多方面(影像、音乐、时空)发生互补的关系,让电影自身起化学反应,使剧本里的戏剧性得到客观立体的展现。”贾樟柯在其电影中极力营造出一个信息含量密集而意蕴含混暧昧的复调文本,这不但使贾樟柯的电影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而且将整个中国艺术电影推到一个新的高度。
一、贾樟柯电影的复调文本
贾樟柯电影的复调文本特性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视听知觉的多层并置。如视觉上的文字(字幕)、Flash动画、绘画图像、电影电视画面;听觉上的各种方言、流行音乐、地方戏曲、时事新闻等,这些源自不同媒介的信息常常在影片的视听空间中立体化混合存在。二是叙事结构回环重合。贾樟柯常常刻意安排一些观众熟悉的人物角色在不同影片中串演,形成一种回环结构,从而将贾氏所有电影文本连缀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三是人物关系的镜式结构。贾樟柯在设置剧中人物关系时,喜欢两两对应,互为阐释,使人物塑造更加生动深入。四是纪实与虚构的杂糅交错。在贾樟柯电影中,现实与幻觉、职业演员与普通人物、实录与调度、自然实景与人工搭景时常混合使用,使贾氏的电影文本常常显得蕴意丰富而又扑朔迷离。
贾樟柯电影的复调文本能够较为真实地呈现当代中国躁动不安的社会现实和普通人复杂的生存境遇。贾樟柯的电影与其早年的生活经历密切相关,复调文本是他对人生的一种体验与表达方式。贾樟柯并不完全认同第五代电影导演回避现实的“寓言化叙事”,他曾坦言其《小武》的拍摄就是“因为觉得自己有一种不满,有一种生命经验,非常多的人的生活状况被遮蔽掉了,若干年后想想大多数中国人是怎么生活的,如果你从当年的银幕上寻找,全是假的,全是谎话。这样看来,我觉得电影真的是一个记忆的方法。贾樟柯认为电影不该诗化生活和神话苦难,或过于追求叙事上的戏剧性和传奇性,相反,他大力倡导用镜头直面当下社会现实。另外,贾樟柯电影的复调文本也是对人的知觉审美经验的一种回归。克拉考尔认为:“电影按其本性来说是照相的一次外延,因而也跟照相手段一样,跟我们的周围世界有一种显而易见的近亲性。当影片记录和揭示物质现实时,它才成为名副其实的影片。”贾樟柯电影的复调文本实践与克拉考尔的电影观不谋而合。
二、“含混”的知觉现象学
知觉本是人与生俱来的一种生存能力,但长期以来,特别是在近现代,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们片面强调身心之间的二元对立,并且过分依赖工具理性和客观主义,从而导致人们对实际经验和生活世界的忽视,引发了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双重危机。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则强调知觉的身心交融,从而摆脱了传统意识哲学身心二分的窠臼,为阐释和构建人们的审美经验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被知觉的世界不是科学意义上的物体的总和,我们与它的关系也不是思想者与思想对象的关系。”因此,知觉的特性就是身心交融,身体是知觉的基础,人通过身体来体验和把握自己的生存世界。人的语言表达、人与他者的共处、人与自然的关系,都是建立在身体知觉的基础之上。总之,梅洛-庞蒂认为人在世间存在的本质特征就是身心的“含混”关系。同样,贾樟柯也认为生活的本质就是一种“暧昧的、混合的状态”,其电影的复调文本特性就是对这种暧昧和含混的生活的一种回应。
三、知觉现象场——人的存在处境
贾樟柯电影的复调文本与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之间相互验证,艺术与哲学之间呈现出一种奇妙的互文本现象。
(一)身体——“道成肉身”
在贾氏电影中,人物角色的身体永远都是他长镜头关注的焦点。在电影《三峡好人》的片头,贾樟柯用了一个长达三分钟之久的长镜头来展示举家搬迁的库区移民群像。这个长镜头犹如一幅新时代的“长江流民图”人物画长卷,它因为真实地记录了中国底层民众的精神状态而广受赞誉,被学界称为神来之笔。在《小武》中,贾樟柯用一个长镜头跟拍小武裸露着身体慢慢走向空荡荡的澡堂,一边有点跑调地唱起了流行歌曲《心雨》。裸身歌唱并洗浴,这是对小武接受爱情“洗礼”而净化身心的一种隐喻。贾樟柯电影中还经常出现舞蹈的长镜头,无论是优雅的民族舞蹈还是热烈的探戈或迪斯科,通过舞者身体所迸发出的激情与欲望,充分表达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内地青年身处单调闭塞环境的困顿以及对现代生活的向往。性爱是身体的重要体验,《世界》中的女主人公赵小桃洁身自好,在小旅店睡觉都要穿上雨衣,并拒绝与男友发生婚前性行为,把贞操视为自己最后唯一的资本。贾樟柯在此并非为了宣扬某种婚恋和性观念,而是强调爱情是在身体知觉基础上灵与肉完美结合的产物。
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反对传统意识哲学的身心二元论和心“尊”身“卑”的观点,认为身体是某种主客一体、心物交融的东西,“我的身体不是一个客体,而是一种手段,一种组织。我在知觉中用我的身体组织与世界打交道。由于我的身体并通过我的身体,我寓居于世界。身体是知觉定位在其中的场。”梅氏之所以强调身体知觉的重要性,是为了强调人的处境意识,因为我们是通过自己的身体参与到在世的存在,一个人的身体经验往往就是他对世界的理解,也即所谓“道成肉身”。人的身体并非纯粹的生理机器,任何意义的产生都不能没有身体知觉的参与,贾樟柯电影对人物身体的关注,就是他对当下普通人生活意义的一种思考。
(二)他者——“在世共在”
贾樟柯电影强调对现实生活做客观真实的纪录,同时,为了避免由此产生的叙事松散拖沓,他特别重视叙事结构的安排。比如借鉴中国传统绘画中的二联画、四联画的方式,如《三峡好人》里的借“烟”“酒”“糖”“茶”四个民间人际交往的礼品物件来黏合情节;或者借鉴中国传统戏曲的折子戏结构,如《天注定》里的四个故事就分别与“林冲夜奔”“苏三起解”“骂阎王”等“凶戏”对应;或借鉴中国传统章回体小说的结构,如《二十四城记》分别用诗句来连缀几个人物故事。
除了借鉴这些传统叙事手段,贾樟柯还特别善于运用人物交相对照的镜式结构,使人物之间相得益彰。《小武》中的小武与小勇曾是一对难兄难弟,但后来小勇欺世盗名,摇身一变成了当地“知名企业家”;而重视情义、“盗亦有道”的小武则因为靠“手艺”(盗窃)为生而成为“严打”的对象。贾樟柯不无嘲讽地设置了这“一正一邪”的人物关系,二人如同镜像,互为表里。《三峡好人》中的男女主人公三明和沈红,因寻妻或寻夫不约而同来到三峡库区,最后三明终于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妻子,而沈红却在与丈夫相逢之后竟成永别。贾樟柯通过三明与沈红两人的得与失、取与舍,生动阐释了何谓“好人”。贾樟柯这种镜式结构的人物关系设置,除了让人物塑造更显丰满生动和叙事结构更加紧凑有力外,还折射出了当下中国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和常见的一些社会问题。在生活中,一个人的身份往往如同镜中影像一样重叠交织,难以辨析,生活的本质有时就像电影《小武》的原名一样含混不清:“靳小勇的朋友,胡梅梅的傍肩儿,梁长友的儿子,小武”。
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认为自我与他者的问题实际上就是一种身体间性或曰交互主体性的问题,人与人之间是通过身体知觉而共同在世。身体间性意味着我与他人共处,因此没有绝对的自由和孤独,“只要我们活着,我们的处境就是开放的。”个体生命的存在意义不是来自于这个个体本身,而是来自于这个个体与周围其他个体的差异性,这就是人与人之间暧昧的结构性关系。
(三)语言——“并置共鸣”
除了通过设置镜式结构的人物关系来营造一种含混暧昧的复调文本,贾樟柯还善于运用声音进行多层次的立体叙事。方言是贾樟柯非常重视的语言元素,因为方言不仅仅表明地理位置,同时还涉及人物的社会身份与欲望诉求。贾樟柯电影对山西城镇、重庆三峡和广东沿海这三个地区有特殊的偏爱,这不仅是因为上述地区乃当下中国经济活动最为活跃的地方,同时也是中国从北到南三个重要的方言区,能够集中体现当下底层普通人的真实生活状态。《山河故人》就集各种方言如山西话、四川话、上海话,甚至英语于一体,生动再现了全球化时代中国人口的大迁徙。
贾樟柯对语言的迷恋还表现在对复调音轨空间的营造上。众所周知,如果电影的音轨与画面不对位就很容易造成突兀的效果,导演一般对此都慎之又慎。但贾樟柯却特别偏爱混录音轨或音画不对位的手法,使原本干净单一的音轨变成了一个容纳不同声音来源,各种声音与视觉空间进行错位或并置的复调空间,从而逼真地再现了当下中国社会动荡嘈杂的生活场景,在相当程度上还原了普通人生存处境的含混与暧昧。这种复调视听空间几乎成为一种“贾樟柯式”的电影签名,极具个人风格。如《站台》中的一个场景:村里的高音喇叭首先播出了一则时政新闻——“创建文明工程和大兴文明新村”,随后是一个私人广告——“谁要割猪肉,到我家来”。两种声音在高音喇叭中交错出现,时政新闻以标准普通话播报,代表政府的工作要求;而私人广告则以方言播报,代表农民的利益诉求,音轨中这两种声音的并置共鸣可谓极具时代和地区特色。
贾樟柯对音乐和戏曲也是情有独钟,善于借鉴流行音乐和经典戏曲来辅助叙事。如《三峡好人》中酷爱模仿周润发的“小马哥”,不仅时时哼唱电视剧《上海滩》的插曲,甚至连手机铃声都设成了这首曲子,这个细节生动再现了当时港台流行文化在内地引发的喧嚣与骚动。而《天注定》里则分别运用《林冲夜奔》《苏三起解》《骂阎王》等戏曲为剧中人物造型和叙事服务。这些流行歌曲或戏曲不仅标志着社会变化和时代变迁,同时也是一种对人物塑造和人物动作的内在评价。
语言是存在之家。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认为语言并非一种简单和被动的思维工具,而是和身体知觉一样,是人的一种在世存在方式。语言经验就是身体经验的一部分,因此,语言与意义的关系,其实就是身体与世界的关系。在现实生活中,语言与意义之间并不完全一一对应,相反,它们是一种含混的共谋关系。正如沉默也是一种富有含义的表达,贾樟柯电影中的人物多保持某种静止和沉默的姿态,使本该在时空中流动的影像也突然变成了平面和静止的图像,故有学者称贾樟柯电影中“沉默的大多数”为一种“人形标本”:“静止的人不再具有活动的主动性,任由摄影机榨取他肉身的形象,像一个人类学的标本被钉在了镜头里。这种‘人形标本’镜头具有强烈的死亡象征,它是对‘死亡’的模仿,是对一切终结的想象,是对人被钉在历史的时空中不得动弹的隐喻。”身体的任何使用都是一种原始的表达,贾氏电影复调文本中的这些沉默的“人形标本”,实际上已经具有文化人类学的意义,是当下中国底层普通人身体知觉备受压抑的真实写照。
(四)自然——“野性自然”
为了还原生活的复杂、含混与暧昧,贾樟柯常常有意识地安排一些人物角色在不同影片中进行串演,以此制造一种陌生化的间离效果,并将其所有影片连缀成为一个整体,共同营造出一个人物与情节重叠,多层叙事空间立体交错的复调文本。如《小武》中的主人公小武在《任逍遥》中摇身一变为放高利贷者,他甚至向贩卖盗版光盘的斌斌点名索要贾樟柯的电影《小武》,令人忍俊不禁。在《站台》里戏份不多的农民工三明,到《三峡好人》中则担任了前往三峡库区寻妻的男主角,接着又出现在《天注定》中,此时的三明已从三峡接妻子回家了。角色的串演让人不断地重温贾樟柯的电影,使贾樟柯的电影之间呈现出一种复杂而暧昧的互文本效应。另外,演员赵涛作为贾樟柯的妻子及其多部电影的御用女主角,也是形成互文本效应的一个重要原因。贾樟柯并不掩饰自己对复调文本的苦心经营,他坦言在自己的作品中,“他们(人物)之间是有关联的,只是同一条船,同一条河流,摄影机落到了不同的人身上,就有了不同的故事。我其实是刻意在建立我个人电影之间细微的联系。如果有一天重放我的电影,我觉得次序是《站台》《小武》《任逍遥》《世界》《三峡好人》《天注定》,我可以把他剪成同一部电影,放一个九小时的什么呢?叫《悲惨世界》!”
贾樟柯电影复调文本的陌生化效应还体现在纪实与虚构杂糅的叙事手法上。《三峡好人》缘起于为在三峡创作的画家刘小东拍摄的一部纪录片,当地惊心动魄的城市拆迁和底层大众卑微的生存状态深深震撼了贾樟柯,于是他决定拍摄《三峡好人》这部剧情片。该片大部分镜头都是在三峡库区实景拍摄,如江上船只、岸上废墟、迁徙人群。这种方法还延续到后来的《二十四城记》中,该片将口述史与剧情扮演相结合,真假不分,虚实并置,在电影复调文本的实验上更是大胆。《二十四城记》邀请了四位明星加盟,由于职业演员与普通工人在影片中交替出现,观众很容易形成纪实与虚构的双重视阈或叠映的观影心理,这种叙事上的吊诡使观众惯常的观影经验受到了“戏弄”,乃至有人愤怒地称此片为“伪纪录片”。
“其实我在整个创作过程里面会寻找到一些有点宿命或者有点神秘的东西,当进入到创作状态之后我会跟我生活中发生的事件产生一种神秘感的连接。”贾樟柯电影喜欢选择一些体形或力量巨大、难以为人驾驭的景观作为故事发生的背景,如火车、高速公路、三峡大坝、飞机和兵工厂等。这些景观代表了一种神秘的力量,人类在其面前显得特别渺小无力。贾樟柯还喜欢在其影片中增添一些魔幻色彩,使其电影复调文本充满隐喻而更显神秘,如《三峡好人》中酷似火箭的烂尾楼、空中飞过的UFO、片尾的走钢丝者、酷似外星人的废墟消毒员等。而《世界》里的微缩景观“世界之窗”和多次出现的Flash动画,也给影片带来一种后现代时空高度压缩的超现实主义意味。
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认为自然是一个超越理性意识的神秘世界,是我们存在的土壤,我们与自然完全粘连在一起,难以分割。在梅洛-庞蒂看来,通过身心交融的知觉,人与自然之间是一种可以相互转化的可逆性关系,而非征服与被征服的对抗性关系。当然,梅洛-庞蒂并非一味地反对科学理性,而是强调感性自然是包括科学理性在内的一切认知活动的基础,“被知觉的世界是所有理性、所有价值及所有存在总要预先设定的前提。这样的构想并非是对理性与绝对的破坏,而是使它们降至地面的尝试”。
四、结论:还原“生活世界”
贾樟柯所有电影都围绕着大时代变迁中的个体生命这一目标展开,他关注的不是历史事件本身,而是历史事件背后被人们忽略的日常生活和个体生存经验。复调文本表明了贾樟柯尊重现实时空的原初性和完整性,他尽量客观地记录和展示它们,在其电影文本中努力还原出一个粗粝、沉闷、含混又暧昧的生活世界,而这也是现象学的宗旨——“还原事物本身”。
贾樟柯的电影复调文本推动了电影审美经验的知觉现象学变革,其最突出的审美价值就是强调通过身体知觉进行“审美介入”,“梅洛-庞蒂在关于知觉作为一个综合体的讨论中,对审美投入做了进一步的论述,这种综合体在我们对对象的感觉把握中达到了一致和统一。这样一种综合体包含了‘作为知觉和行动领地的身体’,但超越了直接感知到的东西,而达到一个整体,即最终作为世界本身的一种完整性。在关于‘看’的描述中,梅洛-庞蒂将这种身体介入的观点延伸到艺术。”这种介入的美学直接挑战了以往孤立、静观的审美无功利说,从而走向一种审美经验的统一。复调文本不但是贾樟柯对中国电影的贡献,而且也创造了世界艺术电影的新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