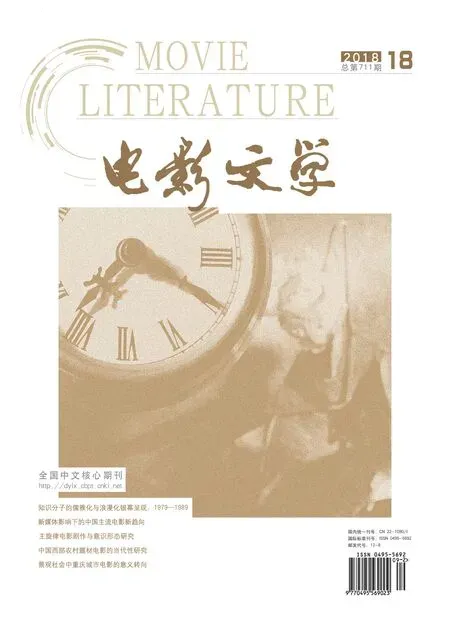浅析尼古拉斯·温丁·雷弗恩的美学风格
2018-11-14王晓利
王晓利
(内蒙古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80)
从执导低成本犯罪电影《末路狂奔》开始,丹麦导演尼古拉斯·温丁·雷弗恩凭借一系列拥有极致暴力美学特征的电影获得了广泛关注,自此,他连续拍摄了《末路狂奔2》《末路狂奔3》《血流不止》《恐惧X》《维京英灵殿》《布朗森》《亡命驾驶》《唯神能恕》《霓虹恶魔》等影片,并因此得到了“丹麦昆汀·塔伦蒂诺”的赞誉。其中,《亡命驾驶》(2011)获得了第64届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奖,他也因此成功跻身好莱坞导演之列。雷弗恩所执导的影片充斥着犯罪、杀戮、鲜血等令人战栗的暴力元素,运用独特的视听语言与叙事方式营造出冷淡疏离、残酷血腥、梦幻迷醉般的观影体验。
一、雷弗恩电影的外在暴力
尼古拉斯·温丁·雷弗恩所执导的电影带有强烈的个人特色,视觉语言与叙事方式独树一帜。尽管雷弗恩执着于暴力美学,并因此被称为“丹麦昆汀·塔伦蒂诺”,但是他与昆汀·塔伦蒂诺、斯坦利·库布里克、罗伯特·罗德里格斯等导演的风格不尽相同。作为一名出生在丹麦、生活在美国的导演,雷弗恩的导演风格既受到好莱坞电影的深远影响,又有不可磨灭的北欧烙印,他所营造的故事氛围更接近超现实主义的黑色童话。
雷弗恩痴迷于视听语言的暴力表达、阴郁昏暗的光线、强烈的对比色调、缓慢摇动的镜头,时而紧张时而冷静的复古音乐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冰冷与温暖、安静与激烈、缓慢与疾驰混合的奇异美感。这种视觉和听觉的极端刺激无疑是暴力的、宣泄式的,脱离了暴力美学的常规范式,成为另类的暴力美学表达。
(一)光影的运用
雷弗恩执导的电影中,人物与景物往往处在光影交界之中,一半阴暗一半光明,甚或大部分处于阴暗之中,沉沦于无尽的昏暗,看不到清晰的轮廓,伴随着摇晃的镜头,偶尔有光影一闪而逝,在人物或景物的边缘打上一层朦胧晕染的光。雷弗恩喜欢摄影,因此他的电影总给人以相片般沉静的光影感受。这种对于光影对比的执着,出现在他执导的每一部电影当中,将影片的黑暗主题烘托得淋漓尽致,映衬着人性的黑暗与昏聩以及乍现的闪光。
《布朗森》根据英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罪犯迈克尔·皮特森的故事改编。故事原型的身上充满了不可思议的矛盾和悖论,他出身上流社会,却天生暴力成性。人生中不停地犯罪、判刑、关入监狱,又因为在监狱里暴力犯罪而不停地更换关押地点。这样一个反社会人格的罪犯,却擅长诗歌、艺术,出版了十余本著作并获得了柯斯勒奖,他甚至关爱青少年的成长,呼吁他们不要犯罪,还参与了保护动物的公益活动。这种矛盾感引起了雷弗恩的兴趣,他用自己标志性的镜头语言,在电影《布朗森》中塑造了一个漫画式的“布朗森”的形象。电影的开篇是一片黑暗,黑暗中,布朗森忽然出现,此时光自上而下,在布朗森的脸上打出凹凸的阴影。整个画面有着油画般的细腻质感,给人以中世纪画作般的感受。黑暗当中,布朗森开始对着镜头介绍自己,伴随着一系列镜头的快速切换,布朗森以各种姿态出现在镜头当中自我陈述,最后,屏幕再度陷入黑暗。整个过程都在黑暗当中,仅有笼中微弱的红色光源,有时甚至连动作都看不清,黑暗中的留白有着东方式的含蓄意蕴,飞溅的红色鲜血使红色的灯光都有了黏稠的质感。影片中,微弱的光大多来自上方或斜上方,使人物身处黑暗,融入黑暗,景深则直接淡入黑暗之中。如果镜头推远,光则往往来自远处,使镜头延伸的范围内陷入黑暗,产生遥望窥视之感。
同样,《亡命驾驶》中也有着类似的光影效果。深沉的黑暗中,昏黄的光线照不到镜头远处的景物,留下大片大片沉落的阴影。阴暗的走廊、背光的室内,室外永远像连绵的阴雨天,即便偶有阳光,太阳也懒洋洋地挂在天际,将光线几乎平射般投入车厢中。电影中大段的飞车追逐段落,有很大一部分镜头处于车内,车外的光不停划过,人物的脸部便有了闪烁不定的高光,刻画出清晰的轮廓,却将表情隐藏在暧昧的光线当中。有时,镜头固定投射在车内某处,便有光影自车内的黑暗中缓慢滑过,轻抚过人物的手背、手臂、衣服、椅背,此刻一切静谧,流动的光影里细微的动作,便是所有情绪的表达,极致的安静、极致的缓慢,带来剥离了时光的艺术美感。
(二)色调的运用
雷弗恩毫不避讳自己是色盲的事实,他坦然地说正是因为他只能看到对比强烈的颜色,才会让他的电影有如此浓烈的视觉风格。在雷弗恩的电影中,最常见的便是冷冽的蓝色和浓郁的红色,而这两种颜色往往同时出现,带来极其强烈震撼的视觉冲击,甚至就连电影开篇的字幕都选用明艳的粉红、紫红、柠檬黄、湖蓝、天蓝等色调。
《亡命驾驶》开头,镜头缓缓掠过一张展开的地图,边框是蓝色的,窗外,楼体上闪烁着红、黄、蓝三种颜色的灯光。黑暗中行驶的车辆,窗外闪过的灯光大多数是蓝色的,车内投射的光是黄色的。夜色湛蓝,车辆的反光是蓝色的,衬衫是蓝色的,就连室内的光也是灰蓝色的,修理厂背景中墙围是鲜艳冰冷到极点的天蓝色……在这无尽的蓝色当中,红色是最耀眼的点缀和衬托。超市墙壁上鲜红色的遮雨棚、商店外面鲜艳的美国国旗、餐馆的玻璃上是红白交错的方格、大片蓝色光影中的红色灯光……除此之外,还有暖黄色的阳光与灯光,绝非正午接近白炽的光,而永远是黄昏般的暖黄色,阴影斑驳。
《霓虹恶魔》中,镜头中色调的对比更是到了极致,雷弗恩对于蓝与红等色彩的痴迷,以及对冷与暖色调的运用也到了令人瞠目的地步,灯光与色彩糅合在一起,将影片中时尚界的纸醉金迷表现得淋漓尽致,令影片呈现出夜晚霓虹灯般的梦幻与迷离。同样是电影的开篇,金色粉末闪烁着光芒不断飘落,金色粉末散去后,身穿蓝色短裙的杰西躺在长椅上,脸上涂抹着夸张的妆容,脖颈上大片触目惊心的深红色“鲜血”沿着手臂蜿蜒而下,在地面上汇聚成小小的“血泊”……镜头逐渐后退,露出绿色背光、粉红色灯带、不断亮起的闪光灯以及拍摄中的摄影师。影片中,处处可见对比鲜明的夸张色彩,带来超现实的异化感。
《唯神能恕》对于红色的铺洒几乎令人窒息,黑暗当中,压抑的红色灯光和兽头墙饰令人十分不适,镜头转换间,红色、绿色、蓝色随之切换,或同时出现,但以红色调居多。这部饱受争议的影片有着截然相反的两极评价,许多人表示这是一部令人厌恶的电影。雷弗恩对此并不介怀:“我总是说,如果哪天我的片子能讨所有人的喜欢,那我就不再拍电影了。”
(三)镜头的运用
雷弗恩喜欢在电影中运用摇动镜头或平移镜头。大量静止的画面令电影产生近似凝固的氛围,带来压迫感和紧张感,伴随着缓慢的摇动镜头,突变往往在一瞬间发生,猝不及防之下效果十分震撼。雷弗恩对电影的剪辑十分干脆利落,镜头切换凌厉,粗暴有效,毫不拖泥带水。
以《布朗森》为例,镜头多数时间是静止的,以旁观者的角度静静观看,聆听布朗森的讲述。平静的镜头语言中,布朗森夸张的肢体语言、放肆的笑声与冷感的视角产生了对比效果,使布朗森的形象有一种荒诞的滑稽之感。布朗森的脸在镜头中是略带灰蓝色的惨白,除了他“自述”的镜头外,有一个镜头也曾经反复出现,就是布朗森推着车走过的镜头。这时候的镜头,跟随着布朗森微微平移,其余时间里,镜头便安静地“仰视”着电影中的人物。片中对于人物的特写,大多如此,镜头呈仰角状态,以低于片中人物的角度“仰视”。这种视角,既可以凸显布朗森的彪悍魁梧,也对银幕前的观众施加了压迫感,使观众不得不跟随镜头,屏住呼吸,“仰视”银幕。同时,《布朗森》电影画面的构成呈现出对称状态,当布朗森“自述”时,他位于镜头的正中间,而当他以片中人的身份出现时,往往处于镜头的一侧,另一侧是黑暗与光的组合,或是呈稳固对称形状的建筑构造。某几个镜头中,布朗森与旁边黑白色调的景物呈现完美的对称结构,竟然带有些许“禅”的意味。
《亡命驾驶》的镜头运用也十分特别,静止画面中,镜头的视角多数略低于人物或景物的主体,是一个轻微的仰角。即画面中出现人物时,镜头略低于人物的眼睛,视线大致在人物的肩颈处。而画面中是车辆时,镜头大致位于车头的位置。镜头在车内时,微微晃动,带来颠簸感。其他时间,靠镜头的推近或拉远表现人物的内在情绪,展现环境的逐一变化。慢镜头的应用也是《亡命驾驶》的独特之处,作为一部有飞车追逐场景的电影,却伴随着浪漫悠长的音乐,多次以慢镜头展示画面中的场景。
到了《霓虹恶魔》中,超现实主义风格体现在几何结构的运用上。镜头中的景物多呈现几何形状,冰冷、完美、对称、连续,三角形、长方形、多边形以及艺术结构大量出现,在为画面增添现代美感的同时,也使气氛冷漠、疏远、冷淡到了极致,就如同雷弗恩镜头中的时尚圈,冷漠无情,择人而噬。
(四)声音的运用
雷弗恩非常重视电影中的音乐,每部电影的音乐效果都可圈可点。《霓虹恶魔》中的电子音乐,《亡命驾驶》中的怀旧音乐等,无不经过精心设计,契合画面与情境,达到了极其完美的烘托效果。值得一提的是,精简的语言和低缓的语速也是雷弗恩电影的特色之一,剧本中的台词相较其他电影来说十分简化,为电影留出大段的空白,低缓的语速令电影气氛更加沉郁,与电影本身所要呈现的氛围很契合。例如《亡命驾驶》中,“车手”带着一男一女去抢劫,留守在车上的“车手”等到了拎着大袋子的女劫匪,两个人平稳呼吸后,略带紧张地望向店铺门口。此时,电影中是没有任何声音的,数秒过后,在这种焦灼的安静当中,突然响起了一声枪声,伴随着枪声,走出店铺大门的男劫匪踉跄着跌倒在地,“车手”与女劫匪满脸震惊。没有之前的声音留白,突如其来的枪声便很难做到如此震撼。
二、雷弗恩电影的内在暴力
除了视听语言的暴力美学外,雷弗恩电影文本层面也呈现出暴力美学的特征。作为暴力美学的绝对推崇者,雷弗恩将视听语言层面的暴力发挥得炉火纯青,与此同时,电影的文本与叙事便显得不那么重要,甚至略显单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雷弗恩不重视文本的表达,相反,在努力构筑视听暴力美学的同时,他通过暗喻等手段将电影的主旨囊括其中。雷弗恩的每部电影,视听语言符码中都有其相对的文本意象,包括灯光与色调的运用,都建立在文本内核的基础之上,正因为有清晰的文本意指,才形成了视听语言的能指,因为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讲述的是一个怎样的故事,才有明确的视听语言的铺排设计。
在暴力的表象之下,舒缓的镜头和拂掠的光影带来一种别致的浪漫。与其他崇尚暴力美学的导演的区别就在于,雷弗恩的电影带有浓重的北欧式浪漫情调,梦幻的光影之中,一切仿佛就是一场梦,整个故事被迷蒙的色彩和光晕解构为黑色的童话,或许残忍冷酷、血腥暴力,却带着一抹极夜里灯光般的脉脉温情。
三、雷弗恩电影对暴力的消解
暴力与美,并不是无法共存的直观感受。对暴力的叙述与探寻,也有其深层的意义。观察暴力,不意味着向暴力妥协。表现暴力,也不意味着认同暴力。
雷弗恩在访谈中说:“说到观点,我想表达的是,暴力并不可怕,生活中时时刻刻都有暴力,真正可怕的是纵容暴力和对暴力的逆来顺受。这不仅仅助长了暴力而且使得暴力更加泛滥。”雷弗恩在电影中,通过冷静客观的镜头语言、刻意留白的剧本台词、舒缓淡漠的情感意境,拉开了观众与暴力的距离,以一种旁观者的冷静姿态体验暴力,同时消解了暴力。
直面残酷,才能看清残酷的本质;凝视暴力,才能识破暴力背后的软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