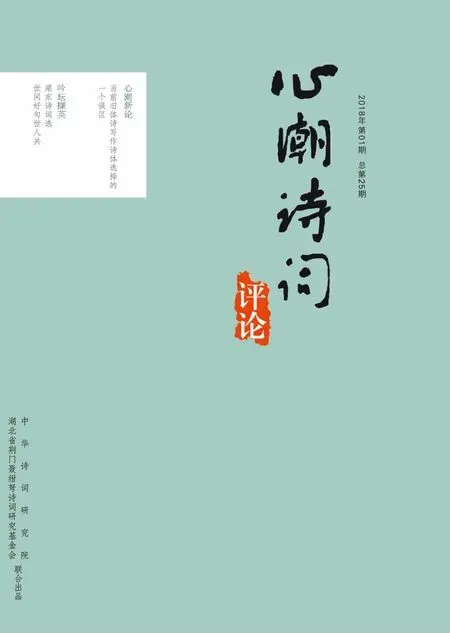“另类”的诗坛:当代诗词的存在空间
2018-11-14王巨川
王巨川
我们说旧体诗词作为一种另类的存在,主要是较之于一直处于主流地位的现代新诗而言的。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全面以西方为楷模而开启的现代文化的狂飙突进,使“舶来品”(主要基于形式而言)白话新诗立意把古典诗词作为批判对象,以此来确保白话新诗在开创时能够快速立足根基,在十余年的“新”与“旧”的诗歌形式博弈中,古典形式的传统诗词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其创作也逐渐进入一种边缘化、个人化的沉潜状态,同时也失去了诗坛独领风骚的主体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面对全新的时代和百废待兴的社会,旧体诗词在学术研究、高等教育等方面依然无法进入主流的叙事序列,仍旧是“少数人”作为个人化喜好、圈子酬唱的文化形式,甚至是某种“政治待遇”的体现。虽然旧体诗在诗坛上也有过勃兴时期,但终究被视为革命主流的新文化运动所抑制,不能与新诗比肩作为当代诗歌的一部分。正是在这样的状态下,旧体诗词随着创作群体的逐渐扩大、诗歌数量的迅速增加,由此在主流诗坛之外又形成了另一个“诗坛”。相对于大众化的新诗,在这个诗坛中有较为特定的创作群体(新文学家如茅盾、老舍等;学者如聂绀弩、胡先骕、苏步青等;革命家如毛泽东、周恩来、陈毅、董必武等),也可以说旧体诗词在当代诗歌视野中创造着中国诗歌的“另类的现代性”,即有学者所说的“在位于特定历史的形态中的一个想象和实践的进化过程”。
在这个视角观照旧体诗的发展,可以看到共和国建立后的旧体诗发展并非一路平顺,伴随着国家发展的不同时段,旧体诗词的创作也呈现出不同的叙事内容和审美倾向。基本而言,在当代文学史的视域内,旧体诗词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十七年的颂歌时期、文革后的反思和发展时期、新世纪的全面勃兴时期。在这三个阶段中,旧体诗词的发展各有特点和内涵。笔者以为,到了新世纪,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提出的全面复兴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倡议,为当代旧体诗词的繁荣发展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存在空间和创作机遇。
一、共和国初期旧体诗词的内涵及存在状态
共和国的建立,是中华民族发展进程和所有中国人的一个重大事件,当人民大众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后,那种由衷的幸福感、喜悦感、自豪感成为全体的共同情绪,表现在文学作品中必然是充满了溢美和歌颂。因此,在共和国建立初期到“文革”之前的十七年间,歌颂新中国成为诗歌创作的主要内容。旧体诗词的创作也不例外,大多数的创作以讴歌新中国、新社会成为诗人们的共同目标,如“祖国前途无限好,千红百紫斗芬芳”,“红旗到处飘扬,广大人群里,歌声洋溢,男女老幼,真个是、人人兴高采烈”(《念奴娇》下阙)之类,这类诗歌作为文学艺术作品而言大都流于政治化、口号化、公式化,内容多为歌功颂德、粉饰太平,艺术上罕有颖异之处,但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份子,这种带有浓重时代特色的作品中洋溢着喜悦和幸福,毕竟中国遭受了几十年的战火纷扰终于和平统一了,这种喜悦和幸福通过直白的语言和歌颂的热情表达出来,也就不难理解了。其中,作为旧体诗词创作大家的聂绀弩,在创作中也把歌颂祖国、歌颂新中国作为主要内容,如他在五十年代创作的写劳动生活的叙事诗《削土豆种伤手》:“豆上无坑不有芽,手忙刀快眼昏花。两三点血红谁见,六十岁人白自夸。欲把相思栽北国,难凭赤手建中华。狂言在口终羞说:以此微红献国家。”诗中同样表达了新时代下的劳动人民对国家的献身热忱之心和歌颂之情,这一类表达在当时的旧体诗词创作来说,从艺术水准而言已经算是上乘之作了。
这一时期的旧体诗词创作虽然数量较多,但是能够公开发表的并不多见。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五四以来的以新诗歌为主流的思想观念仍然以其强大的惯性延续着;另一方面是因为毛泽东写给臧克家的《关于诗的一封信》公开发表。1957年1月,刚刚创办的《诗刊》在第一期上发表了毛泽东同志的十八首旧体诗词,同期又刊出了毛泽东致臧克家的一封信,其中有这样一段话:“这些东西,我历来不愿意正式发表。因为是旧体,怕谬种流传,贻误青年。”又说:“诗当然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这封本来很正常的私人信件,却因为它的公开发表而在当时对旧体诗词的发展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副作用,被当做是党的文艺政策加以贯彻执行,从而使得旧体诗词只是作为“少数人”抒发情感、寄托思想的一种文学载体,没有能够在更广泛的空间中得以发展。同时,许多人面对旧体诗词的态度是一种高高在上的“政治待遇”,即“新诗只是文学创作,旧体诗则是政治待遇。”王学泰就回忆说朱德老总出版了一本《朱德诗集》,在1966年的“文革”中竟然成了他的一条“罪状”,造反派荒谬地批判他说:“毛主席出了诗集,你也出版诗集,简直是与毛主席分庭抗礼,平起平坐。”
1960年代,一大批老干部、学者被打成右派,或身陷囹圄,或放逐山野。在逆境之中,旧体诗词成为他们表达个人心志的一种形式。如被发配到北大荒的聂绀弩,在无可奈何的境况下,以旧体诗调侃自己,将鲁迅、周作人始创的杂文体诗发挥到新境界。其《散宜生诗》表现了诗人遭遇冤屈后二十年来的苦难历程,记录了被迫劳动改造的各个侧面,例如《搓草绳》《锄草》《削土豆种伤手》《地里烧开水》诸诗都生动描写了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劳动情景。他擅长以诙谐解嘲的笔调,化辛酸为一笑。如《推磨》一诗云:
百事输人我老牛,惟余转磨稍风流。
春雷隐隐全中国,玉雪霏霏一小楼。
新闻出版业转型升级,从主体的视角来看,包括传统新闻出版企业的转型升级和新兴互联网企业的转型升级。目前,新兴互联网企业在知识付费领域的高调表现,令诸多出版企业望尘莫及。而传统出版企业尽管经过了这么多年的转型升级推进,仍然没有在数字出版的市场化、产业化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转型升级需要持续地优化完善体制机制,按照现代企业治理结构开展经营管理,加速高新技术的应用,建立健全独立、通畅的数字产品渠道才能最终达成提质增效和融合发展的目标。
把坏心思磨粉碎,到新天地作环游。
连朝齐步三千里,不在雷池更外头。
推磨本是极平凡单调的劳动,在他笔下,毫无沉闷枯躁之感,反而能联想翩翩,比喻新奇,看似嬉谑,实则沉痛。颈联用一三三句法,拗折崛健。其它妙句如:“这头高便那头低,片木能平桶面漪。一担乾坤肩上下,双悬日月臂东西”。以白描手法写挑水,真实地表现了知识份子的劳动体验。
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结束,旧体诗词能够公开发表的并不多,大部分都是政治领导人的一些诗词,以时事与游览之作为主,但此时期在思想内容上趋同,大多是赞颂建设成就与大好形势,有意追求风格、具抒情性之作不多。1961年老舍随作家艺术家访问团到内蒙参观访问,写了《内蒙之行》《内蒙风光》《内蒙即景》《内蒙古东部纪游》等组诗。描写草原风光、民情风俗、劳动生活、建设成就和民族团结。其中不乏表态式的套话,但也有不少作品表现出老舍一贯的真诚、风趣和明丽的特点。茅盾在这一时期创作的旧体诗词大都属于“新台阁体”,具有强烈的政治性,表现了诗人强烈的政治人格的艺术投射。主题或歌颂或批判,或雅正平和,或义正词严。如《观北昆剧院出演〈红霞〉》(二首)、《曲艺汇演片段》(四首)、《歌雄心更雄》等带有浓重时代特色的政治诗。这些诗鼓吹和歌颂了大跃进的时代精神,具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再如歌颂和弘扬中外民族和国家之间的政治友谊的诗《祝日本前进座建立三十周年》(二首)、《听波兰少女弹奏肖邦曲》(二首)、《访玛佐夫舍歌舞团》《西江月·为日本蕨座歌舞团作》等“新台阁体”诗词,平正典雅、铺张扬厉,多骈偶,喜藻饰,呈现出一种世界大同的太平气象。其中有些诗也体现了茅盾精湛的古典诗艺功底,如作于1958年《观朝鲜艺术团表演偶成》二首(《扇舞》和《珍珠舞姬》)就是典范。这两首七律属对精工、诗语艳丽华美、诗风婉约动人。“素袖轻扬半折腰,连环细步脚微挑。低徊画扇百花绽,炫转长裾万柳飘。”“回黄转绿幻霞光,宛约翩跹仪万方。凤管徐随皓腕转,鵾弦偏逐细腰忙。”的写实的功夫体现了茅盾创作中一贯重写实的艺术情趣。茅盾创作的另一类是批判的,主要是批判当时国际上的“修正主义”思潮,如《无题》《壬寅仲冬感事》《满江红·一九六三年新年献词》《阅报偶赋二律》等等,这些批判性的政治诗词嬉笑怒骂、纵横捭阖,笔锋劲健犀利,有时难免显得夸张和漫画化。它们和歌颂型的政治诗词一道,红黑相间,构成了茅盾“新台阁体”诗词的一体两面。
随着政治空气的缓和,有些知识分子又开始作旧诗,如陶今雁《夜过彭家桥有感》诗云:“何须冻馁梗胸怀,工罢桥头意快哉。十里荷风吹汗去,一湖灯火映潮来。”表露的是劳动锻炼之余的轻松之感。1961年春,在中国科学院工作的学者胡先骕作《水杉歌》,被誉为亘古未有之科学诗。诗之开篇云:
记追白垩年一亿,莽莽坤维风景丽。特西斯海亘穷荒,赤道暖流布温煦。陆无山岳但坡陀,沧海横流沮洳多。密林丰薮蔽天日,冥云玄雾迷羲和。兽蹄鸟迹尚无朕,恐龙恶蜥横駊娑。水杉斯时乃特立,凌霄巨木环北极。虬枝铁干逾十围,肯与群株计寻尺。……
缅想当时地质年代的景象,水杉屹立其间,是何等雄伟。作者极尽描写之能事,继而描述水杉习性、地质变迁及今日之发现后,末云:“如今科学益昌明,已见泱泱飘汉帜。化石龙骸夸禄丰,水杉并世争长雄。禄丰龙已成陈迹,水杉今日犹葱茏。如斯绩业岂易得,宁辞皓首经为穷。琅函宝笈正问世,东风伫看压西风。”以此象征社会主义必将战胜资本主义。胡先骕将诗寄给陈毅副总理,陈毅推荐《人民日报》发表,并加《读后感》:“胡老此诗介绍中国科学上的新发现,证明中国科学一定能够自立且有首创精神,并不需要俯仰随人。”
1966年“文革”浩劫开始,大批诗集付之一炬,旧体诗倍交华盖运,只把毛泽东诗词作为教材,并且被谱曲演唱。在中国诗歌发展的链条上,毛泽东诗词充任了承继传统和连接现代的巨大桥梁,弥合了文学时空一度出现的间隙“断层”。对于诗人毛泽东为推动旧体诗词的发展所作出的独特贡献,著名文学评论家张炯先生10年前就著文指出过,“为旧体诗词在新中国诗坛争得一席之地并使之堂堂正正地拥有广大读者和作者的正是毛泽东。他以批判传统文化的猛士的身姿和伟大革命家的至高无上的权威,肯定了旧体诗词的历史地位和生命力,并且以自己辉煌壮丽的旧体诗词创作,实际地为走向僵化的旧的诗歌形式注入蓬勃而新鲜的活力,使文坛和诗坛耳目一新。”
还有一些学者教授,即便在遭受“四人帮”打击、失去人性尊严时仍对党对国家抱有希望,他们有的诗即反映了这一心态。如复旦大学苏步青笔下的顽龙:“铁爪锈多秋雨后,银鳞伤重暮风寒。”咏物寓意,透露了知识分子受摧残的心情。武汉大学胡国瑞教授的诗:“健饭忍为伏枥马,循常得脱服盐车。”寓感慨于旷达,意蕴弥深。与聂绀弩为好友的高旅,此期间作《时事十七首》,对个人崇拜与专制主义作出最为愤怒的控诉:“未举抗疏已逆鳞,判他永世不翻身”;“动辄人头千万颗,葫芦滚地不嫌多。”对人妖颠倒的时代作了冷静而又无比愤懑的批判。一批有思想头脑的中青年作者,偷偷学作诗,表达对这一场悲剧的思考,吐露人生遭遇的心声,发泄其愤懑,不乏抗争精神。既有直抒胸臆、豪放昂扬之作,也有曲折隐晦、含蓄深厚之作。诗词在此时逐步回归文学的自觉性,力争摆脱政教意识的束缚。
二、新时期旧体诗词的复兴及其文化精神的张扬
钱理群在《论现代新诗与现代旧体诗的关系》一文中认为“本世纪旧诗词的写作,尽管从未中断,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发展是不平衡的。就我们现在的认识而言,似乎存在着三个创作的相对高潮:一是20世纪初的辛亥革命前后,一是1940年代抗战时期,一是接近世纪末的‘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后的消化时期。”
1976年的天安门诗歌运动,敲响了“四人帮”覆灭的丧钟,拉开了新时期文艺的序幕,同时也展开了旧体诗词的复兴时期。应该说,天安门诗歌运动在当代文学史中是具有重要地位的,史学家们认为“追溯新时期文学的潮头,1976年4月,震惊世界的天安门事件产生的天安门诗歌事实上已经吹响了新时期文学的前奏,拉开了它悲壮的序幕。”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也称天安门诗歌运动“挖掘了埋葬阴谋文学的坟墓,揭开了新时期文学的序幕”。值得注意的是,天安门诗歌运动中创作旧体诗的大部分作者并非文学圈中人士,而是普通的干部群众。这足以说明,每当剧烈事件撞击人们心灵的时候,那种真情实感是可以通过传统的诗歌形式予以表达的。如“哀思念总理,誓言动天地。鬼喊欲出笼,九天有霹雳。”从“誓言动天地”的悲壮场景中,不难看出群众已是怒火满腔,震天撼地的霹雳要响了,这是对“四人帮”的讨伐,也是对这班鬼贼的严厉警告。“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人民悲伤,而魔鬼啤叫,人民哭泣,而豺狼狞笑,此诗前两句已是愤火喷薄欲出,而后两句则已是阵前的宣誓,冲锋的怒号了。这一类诗,悲至深,愤更烈,并已由极度的悲愤转化为同“四人帮”战斗到底的决心和行动。“悲歌献一曲,万里化雷声”,就是这些诗的特点和效能的生动概括。虽然其中一些作品并不符合旧体诗词的格律要求,但是情真语挚,语言凝练,既有直抒胸臆,也有婉曲含蓄,风格多样,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准。
如果说当代旧体诗在天安门诗歌运动之前还处于零散的个人创作的话,那么在天安门诗歌运动之后,旧体诗词的创作势头就一直没有减弱。1978年1月,《诗刊》发表了毛泽东给陈毅的信中说到:“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赋也可以用,如杜甫之《北征》,可谓‘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然其中亦有比、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这种对诗要用形象思维,要用比兴两法,标志着官方话语重视诗词艺术自身价值的回归。10月,北京成立了以萧军为首的野草诗社。与此同时,在无编制、无经费,甚至没有固定办公场所的情况下,各地诗社也纷纷成立。1981年在广州由李汝纶主编的《当代诗词》创刊,以“公心、铁面、法眼”为用稿原则;1983年南京《江南诗词》创刊,面向群众,发行量一度达到两万份。1984年在长沙成立了以教授专家为主体的中国韵文学会,研究与创作并重。1987年5月31日,中华诗词学会在北京成立,这对于当代旧体诗坛来说是一个大事件,中华诗词学会是建国后第一个全国性的诗词团体。其后有27个省市在诗社的基础上成立了诗词学会,并创办报刊,出版书籍。1990年中华诗词学会编印了《中华诗词》第一辑,1994年7月出版了有正式刊号的双月刊,之后改为月刊,成为目前发行量最大的诗歌类刊物。其办刊宗旨是:“切入生活,兼收并蓄。求新求美,雅俗共赏”。中华诗词学会每年举办一两次全国性的中华诗词研讨会,为当代旧体诗词的创作及理论建设起到了推动作用。
随着社会发展的逐渐多元化,思想的禁锢已经完全解除,上世纪末旧体诗词的创作也从后台转到前台,全国到各省市官方性质的诗词协会、学会纷纷成立,多达四百余家,民间的诗社组织更多。全国各社团、学会出版的诗词报刊近百家,诗人词家队伍和读者队伍迅速扩大。
三、新世纪旧体诗词发展与传统文化复兴
新世纪以来的旧体诗词,应该可以说是近百年来发展的黄金时期,社会的全面开放,文化的多元汇集,为旧体诗词的发展提供了全新的舞台空间,也为旧体诗词的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新鲜养分。同时,旧体诗词已经不再是少数人的“政治待遇”,越来越多的创作者加入到旧体诗词的创作群体之中,使得旧体诗词的创作呈现出多元化、多层级、多视野、多探索的局面。这种局面的开创,一方面是以中华诗词学会为主导的全国性旧体诗词创作学会犹如雨后春笋般成立,并由此吸引了大批热爱旧体诗词的创作者;另一方面,在国家层面开始大力倡导传统文化的复兴,也促使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以及社会各个层面对传统文化中的古典诗词开始重新关注,由此带动了旧体诗词的创作热情。中央文史馆诗词研究院的成立,更是在学术研究上带动了当代诗词的有序健康发展。可以说,旧体诗词伴随着二十一世纪的开启,进入一个黄金发展期。
应该说,就像抗战时期旧体诗词呈现出的勃兴状态一样,旧体诗词在新世纪的勃兴发展同样与国家对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复兴的倡导是联动的、不可分离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政治性因素的影响。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在国家的层面上对传统文化的重视逐渐增强,比如2006年5月24日刊发于《人民日报》的《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关于深入学习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大力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的意见》中明确提出:“要充分挖掘利用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积极推介经典名作,引导人们在欣赏品读中受到民族优秀文化和传统美德的熏陶。”这个意见从全民精神建设方面指出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对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意义。在《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中,对中华传统文化有了明确的定位:“五千年悠久灿烂的中华文化,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国脉传承的精神纽带,是中华民族面临严峻挑战以及各种复杂环境屹立不倒、历经劫难而百折不挠的力量源泉。”同时,在传统文化复兴的实施方面做了明确说明:“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和传统经典、技艺的传承。在有条件的小学开设书法、绘画、传统工艺等课程,在中学语文课程中适当增加传统经典范文、诗词的比重,中小学各学科课程都要结合学科特点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高等学校要创造条件,面向全体大学生开设中国语文课。加强传统文化教学与研究基地建设,推动相关学科发展。在社会教育中,广泛开展吟诵古典诗词、传习传统技艺等优秀传统文化普及活动,努力提高全民族的人文素养,树立良好社会风气。办好世界中华传统文化论坛。”钱光培在《在世界文化同一化中的中华诗词》中说:“在今天的世界背景下,重振京剧,重振民族民间艺术,重新认识和评价中国古典文学,特别是中国古典诗词,并使它们重新融入现代中国人的生活中,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从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上,把中华优秀文化纳入到国家发展的整体规划之中。他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充分运用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积累下的伟大智慧,并强调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思想引领下,从国家到地方、从高等院所到社会基层都掀起了一股股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潮。特别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意见》指出: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大战略任务,对于传承中华文脉、全面提升人民群众文化素养、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本尼迪克特认为:“各个民族的人民都遵照文化目的,一步步强化了自己的经验,并根据这些文化内驱力的紧迫程度,多种异质的行为也相应地愈来愈取得融贯统一的形态。一组最混乱地结合在一起的行为,由于被吸收到一种整合完好的文化中,常常通过最不可设想的形态转变,体现了该文化独特目标的特征。”旧体诗词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重要的一种文化形态,在经历了百余年边缘化的迷离、彷徨过程后又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和创作空间。这是因为在传统文化的各个文体中,诗词是最具有传统文化内涵的一种形式,不仅内嵌着中华民族的“和合”文化思想,并且在艺术层面“诗歌与书法、绘画等艺术相融合,将汉字在形、义、音各方面的美结合得天衣无缝,并将汉字的美发挥到了极致”。而当代旧体诗词在百余年的发展中仍然是对中国传统诗词的承传,其内核也同样是继承着中华民族文化思想脉流生生不息。基于这样的理解,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当代旧体诗词的创作与发展,必然会在民族国家对传统优秀文化复兴的整体框架中蓬勃发展。
四、结语
新的历史发展必然要求打破某些僵固化的对立情绪,从而在和谐共生的空间中协同发展。对于新诗与旧体诗词的关系问题,是一个老话题,也是一个久而未决的问题。在新世纪的诗歌发展空间中,一直以来存在着新旧诗学的对立状态应该顺应时势地进行“和解”处理,这就需要研究者和创作者在新的历史机遇中重新展开包容和开放的心态,在“异质”和“同质”的迥异中寻求和解的路径。
现代认知已不再寻求某些“分崩、离析”或宗教的迷幻,而希望达到东方型认知顶点的类似“涅槃”之境界。中国文化与文学历来具有“整体和谐”的特点,这种“整体和谐”,是在破坏与建设的过程中,在各种进进退退和经验教训的过程中,逐步积累并渐趋平衡而造成的。主流与边缘、离散与团聚印证着百余年新旧诗学的精彩生命历程。时至今日,现代新旧诗学应该在诸多问题中突围而出,由分而“和”,由“和”而生,既能保持各自诗学形态的独特性又能促动中华民族文化在当代的有机整合,真正实现多元共存、异态共生、互补共荣的中国现代诗学生长态势,彰显现代诗国的勃兴与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