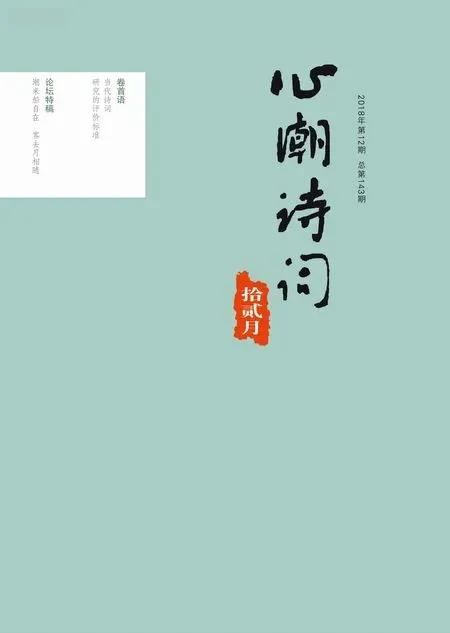现实主义与理想情怀
——当代诗词创作形态及其作品批评刍议①
2018-11-14
当代诗词在几十年的繁荣发展中,已经形成较为稳定的创作群体以及审美范式,涌现出许多优秀诗人及作品,比如我们所熟悉的老一辈诗人聂绀弩以及青年诗人姚泉名、李子老师等人,他们是撑起当代诗坛的臂膀和血液。但与此同时,当代诗词也与其他文学形式一样,由“快车道”发展进入了亟需调整、规范的阶段,“全民化”参与的诗词作品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审美趋同、形式泛化、语言俗白、立意浅薄等流弊,这些问题都需要从事诗词研究的学者们加以关注,在审美观念、形式规范等方面给予学理性探讨,引导当代诗词创作能够在继承传统的同时更好地融入当代文化精神、现代人文风貌及个人理想情怀,由此创造出更具有生命意味、现实深度和文化底蕴的诗学风貌。
本文结合诗词文本,对当代诗词的作品创作及审美形态进行剖析。文章中所选作品虽有挂一漏万、管窥之见的嫌疑,似不能代表当代诗词创作的全貌,但在一定范围内也具有普遍性意义,基本能够反映大多数诗词创作者们的文化审美观。笔者并在此基础上讨论当代诗词如何结合当代文化精神,以及诗词创作文化趋向和精神旨趣,旨在梳理当代诗词创作的类别或形态。
一、当代文化精神与诗词创作的关系
文化精神是一个民族国家在发展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文化体系中特有精神气质,代表着民族国家的文化身份和精神信仰。诚如张岱年先生所说:“精神本是对形体而言,文化的基本精神应该是对文化的具体表现而言。就字源来讲,精是细微之义,神是能动的作用之义。文化的基本精神就是文化发展过程中精微的内在动力,也即是指导民族文化不断前进的基本思想”。可见,文化精神对于促进民族国家发展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简而言之,笔者以为文化精神起码有两方面的基本特征:一方面,文化精神是民族国家生生不息的血脉,它引导着人们在文化传承中代代繁衍;另一方面,作为一种全民性的文化信仰与文化指导,文化精神又会在不同的发展历史阶段,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要求进行着调整和完善,每一历史阶段都会呈现出不同于其他各个阶段的文化发展要求。
那么,当代文化精神是什么呢?简单地说,就是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的文化形态。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改革开放开始,中国开启了国家兴盛、民族复兴的历史阶段。伴随政治生活的昌明盛达和经济发展的不断调整,当代文化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长期被忽视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国家未来发展、民族精神信仰的重要性逐渐凸显出来。从“继承民族优秀传统”到“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再到“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伟大目标,当代文化精神日渐清晰明确。而在博大精深、灿烂辉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当代文化精神即是这样一种在继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又要融入当代文化符码,从而创造出符合当下国家发展需要和大众需求的一种文化形态,它指导并影响着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可以说,当代文化精神的基本内涵需要呈现以下三个方面的基本特征:一方面是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紧密的内在关联,包括情感的、形式的和哲思的等;另一方面是它必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代表,具有引领和典范的作用;第三方面是它同时又是社会民众文化生活的精神家园,反映社会民众的精神诉求。它们之间并非是各自独立的,而是相互之间有着必然联系,相辅相成,相得益彰。那么,当代文化精神与当代诗词创作之间又有什么关联呢?他们之间的关系又如何理解?
中国作为以诗为内在文化精神核心的国度,在不断发展着的各个历史阶段创造出辉煌的诗歌成就,比如古代诗歌开端的“诗三百”、浪漫主义代表的“楚辞”、承前启后的高峰“唐诗”,以及创造了“汉语文诗文学发展的最高形式”的“宋词”等,都是我们今天需要继承并发扬的优秀篇章。王国维在他的《宋元戏曲史·序》中总结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可以看到,中国的历史长河为我们积累了深厚的诗学经验和理论基础。
因此,这里我们所谈的当下“一代之文学”,就是在二十一世纪正在走向国家富强与民族复兴的新时代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文学,当代诗词创作也同样处于这样的时代框架之内。因此,当代文化精神必然要通过诗词中表现出来,反之,诗词创作中也就不可避免地要呈现出当代文化精神的符码。比如冯峥嵘创作的《巫山红叶歌》中以“秋叶再红”来寄予中华民族复兴的精神,诗句呈现出气势磅礴、波澜涌动、内涵厚重的中华民族的文化底蕴:“江山旺气壮民魂,中华代有兴邦力。璀璨文明卓不群,每从宇内树奇勋。斯世图南医积弱,民心如沸事如焚。”姚泉名的《登明堂山》以探寻“汉武遗踪”和“嵚崖”“松响”等意象回望历史,“壮心争可哀”的抒发可谓是以古喻今的点题:“嵚崖何所若,攒若宝莲开。松响麒麟石,云生吴楚台。天随飞栈起,海驾烈风来。汉武遗踪处,壮心争可哀。”再如何少秋的《清洁工》以工整的古体形式和轻松的语言情调描写了早起辛劳工作的“清洁工”形象:“早起身披四月风,轻哼小调扫西东。虽无唢呐扶清韵,却有心花绽碧丛。茧手躬勤清秽物,襟怀坦荡对长空。长街净送晨行爽,一抹新阳照桔红。”这首诗虽然是关注社会普通劳动阶层的工作状态,但诗歌的视角在时间、空间的转换与人物形象的塑造中,以小见大,独辟新径,从而把当下社会中的新人物与新境界通过诗的意境展现出来,让人读来不禁耳目一新。
提举上述形式风格不同的诗歌,旨在说明不论从那一类形式、哪一个角度、哪一种思维去创作,诗歌都要能够保持与当代文化精神的内在气韵相关联。因为从现实意义来讲,如果二者不能有机结合起来,或者当代诗词创作无法表现当下的文化精神特征,则一定不会成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创作,就像艾略特曾经说的那样,“没有任何一种艺术能像诗歌那样顽固地恪守本民族的特征。”这里的“本民族的特征”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个民族国家发展历史阶段中的文化精神,它一定是既有传承因子又有现实主义价值的精神形态。
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当代诗词创作大体上分为两种类型:一方面,是具有大视野、大主题的宏大叙事,这一类诗词的内质是承袭着民族传统的诗教传统,以“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为创作思维,表现出“颂”“刺”“谏”的形态特征。因此,这种创作的视角有分为两个方面:一是站在形而上的立场中与国家民族的发展保持一致,对当下的大事件、大热点问题表现出极大的关注热情;一是承袭杜甫、白居易等一代传统士大夫关注现实、关心民瘼的诗学精神,深切体察民间风物、百姓疾苦;另一方面,是以创作者个体的精神体验为内核,在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中反观诗人自我内心的感受和经验。这一类诗作与传统诗教思维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又不似陶渊明式的“山水田园”风格。既有“出世”的飘逸又有“入世”的焦虑,是当代诗词中的一个创作形态。
二、形而上的诗学观与理想主义激情
传统文化观中的“文以载道”思维在人们的精神中亘古不变、历代相承。与西方以“模仿—再现”的诗学传统不同,中国传统诗学更加注重形而上的社会功用性,孔子提出“兴观群怨”,清人程廷祚也指出“诗人自不讳刺,而诗之本教,盖在于是矣。”“若夫诗之有刺,非苟而已也。盖先王之遗泽,尚存于人心,而贤人君子弗忍置君国于度外,故发为吟咏,动有所关。……岂若后世之为诗者,于朝廷则功德祥瑞,于草野则月露风云,而甘出于无用者哉。”白居易更是直陈诗歌应“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
在当代诗词中的创作形态中,以传统诗文观作为作诗内核的占有很大的比重,即采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诗人们以“不绝于天地间者”自居,诗文创作以“曰明道”“纪政事”“察民隐”为己任。比如聂绀弩早期的诗,他身陷北大荒农场改造时仍通过诗歌托物言志,“寄寓了对政治运动中错划、误判的看法和心情”。《锄草》《挑水》《削土豆》等诗都属于此类,总能在幽默、自然、平淡的诗句中寄予诗人关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其中,《锄草》写“何处无苗无有草,每回锄草总伤苗。培苗长恨草相混,锄草又怜苗太娇。未见新苗高一尺,来锄杂草已三遭。停锄不觉手挥汗,物理难通心自焦。”这种传统诗文观让许多心存家国情怀的诗人们即便身处逆境仍以诗为口,凸显出强烈的士大夫心态和满篇的“颂”“刺”“谏”诗作。
如果说聂绀弩的诗作表达的是上一代特殊历史状态中的所感所知,那么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诗人面对的是更为多元繁复的社会状态和国家复兴的历史阶段,诗的视野也同时进入一种纷繁复杂的多维度时空。如何寻找诗性的生长点?如何抒发时代节奏要求的诗歌?可以说,时代在发展,文明在进步,社会多元化与全球一体化让人类步入一个前所未有的生存空间。然而,作为中华民族传统精神内核之一的理想主义的家国情怀,在许多诗人内心深处却一直存在着,不论社会如何变化。诗人的身份也决定了他们必然要比社会普通人更加具有忧患意识、担当意识和反抗意识。同时,在某种意义上说,采用旧体形式创作的诗人们也比新诗作手多了一些“入世”的激情,或许是这种传统形式中内嵌的现实主义内动力因素使然,并且凸显出强烈的理想情怀。
人类赖以繁衍生息的精神之一便是内心深处激荡着的理想主义作为原动力。“理想”作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之一,其深邃的积极的思想魅力和乌托邦式的生命魅惑交织在一起,历来是传统士大夫与现代知识分子在“出世”与“入世”之间的最高精神追求。理想主义激情促使着诗人们用诗句表达对民族复兴、对国家发展的参与热度。如《巫山红叶歌》(冯峥嵘)、《贺珠港澳大桥通车在即》(李养环)、《江孜宗山古堡》(卢象贤)、《莲花山谒邓公铜像》(周学锋)、《南巡》(韩开景)、《港珠澳大桥》(华慧娟)、《致中印边界边防战士》(杨怀胜)、《喜迎十九大》(林向荣)、《军人之梦》(朱转娥)、《咏米神—袁隆平》(刘沐清)、《高原架线工》(王兴贵)等诗作,均以形而上的维度或抒发当下发生的热点事件,或情铸历史民族英雄的爱国故事,其诗学内核是以主流文化精神为主导,突显爱国主义情操。冯峥嵘的《巫山红叶歌》以奇特的想象、磅礴的气势和思通古今的笔触勾勒出巫山的气势,并以此表达诗人对中华民族复兴大业的坚定信念:
巫山横劈一江开,不尽江涛万古来。壁立林深猿啸急,峰回峡转水徘徊。西接高原连雪域,东瞻海气望蓬莱。远溯鸿蒙龙骨在,高撑碧落柱瑶台。方圆九峡三千里,洞壑纵横云雾起。奇峰缥缈绝凡尘,传闻自古有仙人。旦作朝云暮为雨,高唐一赋雅无伦。今日仙人何处觅?百丈阳台空寂寂。寻遍巫山十二峰,唯见江枫红欲滴。漫山烈烈似驱寒,高擎如炬报秋安。击石凌风生剑响,烘云照水卷文澜。巫山何以多红树?娇娆应是仙魂驻。昔闻红叶可题诗,倩谁题此江山句?君不闻、夔门水拍起罡风,自古名标天下雄。白帝城高霜磬冷,一声史唱入秋红。君不闻、屈祠云外楚骚声,秭归岩上柏松鸣。三滩舀尽西陵水,如何题得古今情?对此不由长太息,生生不竭思何极。江山旺气壮民魂,中华代有兴邦力。璀璨文明卓不群,每从宇内树奇勋。斯世图南医积弱,民心如沸事如焚。恰如良木经霜后,高华美质吐清芬。我以霜吟踏秋水,秋生颜色水生文。指看高峡平湖外,万千红树正缤纷。
全诗以巫山“秋叶再红”的意象贯连,其中“江山旺气壮民魂,中华代有兴邦力”“斯世图南医积弱,民心如沸事如焚”等诗句无疑是诗人意欲表达的爱国主义热情,具有激昂向上的理想主义精神品质,充分表达出诗人现实主义的理想情怀。
在对当代国家事件、热点问题的书写中,诗人们的关注视点大多集中在“颂”的形态而少有“刺”与“谏”,这似乎已经成为诗人们当下创作的共识。比如写中央军改和强军建设的《改隶调整感赋》《圆梦》《老兵》《军人之梦》《破阵子·强军梦》;写国家建设的《港珠澳大桥》《贺珠港澳大桥通车在即》《参观江汉运河》《中卫印象》《兴凯湖引水工程感吟》《高铁》《八声甘州·高速随想》《八声甘州·游长江三峡并远观大坝》;写对外发展的《丝绸之路颂》《观丝绸之路亭口车辙感一带一路》;颂怀伟人及革命先辈的《莲花山谒邓公铜像》《瞻仰深圳邓小平塑像》《赋陈德将军》《抗日名将录之邓世昌》《瞻韶山毛主席遗物馆》《西江月·有感习主席为农民香包捧场》等诗作都是以“颂赞”为主调,对中国改革开放及迅猛发展的抒怀之作。这一类形态的诗作并非当代诗人的新创,早在上世纪建国初期的五十年代,诗歌领域中的“颂”风便盛行一时。不论新体诗人还是旧体诗人的创作,都表现出一致性的歌颂热情,似乎应和了传统中“君上有令德令誉,则臣下相与诗歌以美之”的风范。然而现代社会发展已呈多元并存态势,社会矛盾也日渐突出。诗人们如果仅仅以“颂”为主调,而忽视社会中凸显的矛盾与人们生活中的困苦,则并非是合格的诗人,其诗作也不能起到“闻之者足以戒”的“言志”目的。
相比较而言,在关注现实、关心民瘼的诗作中,能够深切体察民间风物、百姓疾苦的作品却少之又少,在众多的诗作中,《咏萧县“水泥妹”》一诗读来倒是别有一番苦涩的滋味,诗中对为救夫而负重女子的充满情感的描写,如果不严格纠结诗的结构、格律等传统律绝规则,仅看诗作抒发的理想情怀则多少有一些杜诗的气息与激愤之感:
千古爱情奇闻多,难尽悲欢惹嗟哦。今有惊魂乡妹子,身背水泥究为何?灰衫灰裤婵娟罩,垢面难辨婵娟貌。百斤压在弱肩头,救夫哪管丑还俏。眼中射出坚毅光,一袋一袋负重扛。有梦焉知疲和累?只盼夫君命延长。药费如兽噬人盛,首饰家俬已卖净。唯凭苦力多挣钞,任他泥汗漉头颈。步履沉沉腰已弯,却念爱人命如悬。一步心中一念想:愿他多陪我几年。孩儿一双逗人爱,小辨却无花儿戴。不是妈妈不心疼,只想桌上多个菜。饥时徒自墙脚蹲,馒头就水和泪吞。淮水能载愁几许?可载我愁去几分?形若雕像目若呆,前景渺茫莫能猜。恨不将身替郎痛,三生石可证情怀。曾经是郎心上宝,亦宠亦娇日日好。五载相欢太匆匆,为甚病魔击郎倒?何故天教大难临,挺将玉姿似高岑。且凭柔骨擎天起,几人爱如此般深?爱纵深,意纵厚,怎奈天价医难就。一介民女情如山,强撑能否夫君救?呜呼!含悲衔恨问青天,底事浑然不见怜?但祈贫黎皆康健,不求富贵惟愿能平安。
全诗以叙事为主,语言俗白,把“水泥妹”的形态与境遇表达的清晰明畅,最后落笔“怎奈天价医难就”是诗人意欲表现的重点,由此点题升华为“含悲衔恨问青天,底事浑然不见怜?但祈贫黎皆康健,不求富贵惟愿能平安”的期许,达到了现实与理想的高度融合。周达的《咏黄花岗木棉》一诗借“黄花岗木棉”的意象歌颂先辈的革命精神,“簪缨”“碧血”“烈炬”等代表英烈形象的词汇连接后面的“先贤遗梦埋千古,我辈何颜说大同。惟有木棉终不负,年年岗上照人红。”使全诗有了丰富的意喻,在“颂”中有“刺”有“谏”。
从诗的形式来看,对普通人的关注似乎新诗体更能写出温度来,如张先州的《砌砖工》,把普通建筑工的劳动场景嵌入进对儿女、父母的真情实感表达:
一桩桩心事
种在砖头的缝隙里
如雨的汗水浇灌
梦里生根发芽
儿女的路
在瓦刀划过的弧线上延伸
年迈父母的病
在抚平灰浆中疗养
日子在一天天敲打中
结实起来
墙,一高再高
错落有致的诗体就像垒砌的“墙,一高再高”,“女儿的路”“父母的病”都是“一桩桩心事”,然而生活是在一天天地像砌砖工垒砌的“墙”一样“结实起来”,错综的笔法和深邃的意象叠加在一起,使诗歌在现实与理想的贴合中独具陌生化的美感。另一首同样写建筑工人的旧体诗《土建工人赞》,虽然也是抒发对底层群体“位卑犹有梦飞扬”的礼赞,但因形式与语言的双重限制,读来似乎缺少意境化的陌生效果,少了一种幽深的意境:“晨餐风露晚披霜,一片丹心系建房。涂料铺开多彩路,土方筑起万重墙。三轮车奏平凡曲,满手茧凝荣耀光。无畏缁尘经岁苦,位卑犹有梦飞扬。”
再看梅早弟的《清洁工》:“底层身处未徬徨,默默无言四季忙。两只车轮推日月,一枝竹帚扫炎凉。几番风雨雷惊顶,数度须眉汗滞霜。但使鹏城添靓丽,何辞污垢染吾裳。”诗中可见用词是有了斟酌和锤炼,身处底层的身份并没有让清洁工“彷徨”,依旧默默地奉献着,“炎凉”是说社会状态,“风雨雷惊顶”“须眉汗滞霜”是写清洁工的状态,然而最后的“添靓丽”“染吾裳”的起调却又落入了俗套。
由此可见,在形而上诗学观统摄下的诗词创作,诗人极容易进入一种观念至上的陷阱中。因此,在书写国家发展、民族复兴进程中宏大主题(包括社会热点、政治事件等)的价值评判的诗之“颂”“刺”“谏”要避免空泛、虚无的概念化、模式化应景之作,从而把宏大主题中不同事件的丰富细节和多元价值完全遮蔽掉了。
三、向内转的“小情调”与现实化精神诉求
在当代诗词的创作中,还有与形而上的宏大叙事主题创作有所不同的是我称之为“小情调”一类创作。这里的“小情调”并非指称诗坛流行的那些打着“抒发个人性灵”名义而拘泥于自娱自乐、自艾自怨、自言自语的小文人诗歌。这一类诗歌大多是从“大我”的姿态回归“小我”的内心感受,以诗人的一时一感为抒发点,追求诗人自我内心对某一情绪的即时性感受,视角是向内转的精神关注。王乾坤在谈到诗歌的个人化自由创作时认为:“文学的存在理由不是直接干预社会,其本业不在直接的社会改造,而在文学性回归,艺术审美的回归……如果文学的创造者将这种回归理解为一种对于时态的逃避情形,而恰恰可能是与美背道而驰,因为这种逃离只是意味着畸形偏安,而不是自由”。
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一类“小情调”的诗作与传统文人的“避世情绪”和上世纪八十年代新诗思潮中的“个人化”写作又有所不同。所谓“个人化”写作,是一些诗人对“政治化”“观念化”大行其道的反驳,是对群体性公共发言者的“疏离”,以自我内心的性情感知为主导,从而强调“诗贵性情”(沈德潜)的创作路径。这种观念也让许多诗人因此“误解了诗与现实的关系,认为诗与政治、现实无关,只需按照自己的个人视角来打量世界即可,也就是说不客观、全面地把握世界,而只是抓住自己所感受、体验到的一个或几个侧面来揭示自己对世界的认知”,从而进入自我划定的一山一水的小天地之中。可以说,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个人化”写作在疏离政治性话语、颠覆崇高性藩篱的同时,并没有远离现实和抛弃理想,也正是如此才让新时期以来的诗歌精神指向有了生命的意味和理性的深度,“从浅层的自我表现(诗的个人化)流向深层的自我表现(向意识深层进军)”。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遗憾的当代诗词创作场景,不论是宏大主题叙事还是个人化自我抒情,都存在着空洞无物、无病呻吟,寻章摘句、风花雪月、模山范水、歌功颂德、人云亦云的写作之风盛行。当然,在这样普遍流于形式的诗词环境中,也会有一些相对不错的作品,虽然很少。
从当代诗词的“小情调”写作来看,一方面是诗人自身以这种“田园式”的形态表达情感寄托的手段,如“池边杨柳未萌芽,室内山茶已绽花。许是楼高近瑶界,春光早进老农家。”(《农家新居》)“曲岸分明镜未磨,游鱼惊起野天鹅。螺峰弄影秋光里,一叶轻舟剪碧波。”(《题星火水库》)“绿是春兰红是花,柴扉半掩旧篱笆。客惊黄犬迎人吠,燕剪紫薇依水斜。几缕闲思融笔砚,满腔雅趣共邻家。炊烟小院送香晚,一醉乡情诗酒茶。”(《乡归》)等诗作。黄全知的《村雪》:“寒氛连夜锁烟波,吹落梅花赠素娥。百步犹闻香蕊淡,初妆自带玉颜酡。邻家稚子尝新雪,隔岸田翁拍短蓑。悄探西畴棉絮下,麦芽应比去年多。”通过雪降大地的姿态描述,畅想“瑞雪兆丰年”的年景。这类创作大多是以诗人自我对世界的感知为核心,把对“大我”的关注转向一种适度的“小我”状态,更多地是追求诗歌的意境与语言的锤炼,尽量避免盲目抒情与宣泄的混乱情绪。
另一方面,向内转也是当下许多诗人在处理诗歌与社会关系、现实关照时所采取的一种方式,即以“逃避姿态”或“个人化”写作来揭示自己对现实的理解和变化。因此,诗人在内敛化的田园抒情与精神扣问写作中,内隐的依然是在身体出世后的精神入世情结,因而诗歌内核中总会或显或隐的凸显出现实主义的理趣。
黄曙楚的《乡归》是一首抒发个人情趣的诗,把诗人回归乡里的情思通过“花”“燕”“旧篱笆”“黄犬”等乡间常见事物烘托出来,寄予了浓浓乡情与闲思雅趣:“绿是春兰红是花,柴扉半掩旧篱笆。客惊黄犬迎人吠,燕剪紫薇依水斜。几缕闲思融笔砚,满腔雅趣共邻家。炊烟小院送香晚,一醉乡情诗酒茶。”侯明的《游福永凤凰山》、罗金龙的《秋登大雁塔放歌》是诗人登山、登塔时的感受,与前一首不同的是,两首诗在情感的视角上有着较为一致的落点,即对现实的阐发。我们看原诗为:“凤凰山上觅仙途,幽处喈喈鸟自呼。芳草牵人花色暖,琼林布荫叶光敷。近攀玄石叹高绝,远眺白云知不孤。更待修持生两翼,乘风一举出青梧。”(《游福永凤凰山》)“乘风来上最高楼,认得题名在上头。一局江山存气象,百年事业壮春秋。栏杆拍遍情何已,枫叶堆成韵欲浮。好是长安形胜地,重开丝路写风流。”(《秋登大雁塔放歌》)通过诗歌可见,前一首是在写景寄情中自喻“凤凰涅槃”的壮志,而后一首则是以登“高楼”、看“江山”来凸显“指点江山”的豪气。
还有许多诗人的创作是“以物寄怀”,即通过对某种物像的感悟而抒发自己对现实的态度。比如王连生的《木棉树》:“老树孤高秀出林,丹霞万朵入云深。三千里外天风涤,数百年间海雨侵。此日满城同仰首,当时一面早倾心。落花亦带英雄气,触地还传叩石音。”以木棉树的“孤高”喻指历史的轮回与自己的心境;曹治果《读〈西游记〉札记》是一首用俗白语言写出的“打油诗”:“一路西天屡劫灾,百般请得救兵来。神仙摆下玩猴阵,哪个妖精无后台。”这类诗大多是借某种事件或情绪,揭示当下的某种状态,有“以古喻今”的目的。《读〈西游记〉札记》这首诗就是借孙悟空“屡劫灾”来讽喻现实社会中的“后台”现象。
当然,这种“向内转”的诗歌创作能够避免大而空、口号式的弊端,但如果诗人的精神生活不能完全脱离于世俗生活之外,而又在精神锤炼与情绪沉淀中无法把握现实社会的变化规律,或者不能理解丰富多元的事物发展过程。那么,在“出世”与“入世”的矛盾中也极容易造成诗歌创作内涵空泛、抒情无趣或者言不对物的现象。比如刘洪云的《悟萍》,诗人的本意是写“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塘中青莲,写青莲在“浮尘”中的“清明”“风华”与“寂寞”,借此抒发诗人在尘世间被俗事所累的心态,然而偏偏要提气写出了“水险由他三尺浪,风高任尔百帆横。云开雾去纵零落,偏有秋心莲长成”的句子,看似豪迈的气象却因脱离写意的情境,不仅没有达到诗意升华的效果,反而完全破坏了清淡舒缓的诗境。再如向言强的《月亮湾》:“灯光灿烂映檐楹,玉殿琼楼颂太平。昔日伟人挥手处,一轮皓月照新城。”虽然其意是对城市发展新貌的颂扬,但这种貌似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颂歌”却是既无诗性又无内涵的口号诗,基本上是脱离现实的失败作品。不仅诗词创作如此,即便新诗也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如马向虎的《矿工》一诗:“矿工/一束光/跌落千米地下/在黑暗的惊恐中抖索//矿工/一咬牙,一甩肩/用汗水拯救出深锁经年的光明//一池清水/冲走战斗后的疲惫/穿上阳光回家”。这首以“矿工”为抒情主题的诗歌虽然以看似意象丰富、内涵深刻,但并没有产生陌生化的效果,反而使人读来索然无趣。可以说,这种随意抒情的现象在当代诗词创作中大行其道,即便是我们不考量诗词写作的遣词、用典、联句及气韵转合等作诗基本因素,也应该以老老实实的态度认真探求自己内心的真切感知,切合自己周围的现实生活状态。
四、对当代诗词批评的一点反思
中国人历来重视反思,比如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荀子也说“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一般来说,对文学作品的批评,无外乎是基于研究者的学理性知识或者对于当下创作的一种感知和判断,这种感知与判断同样也是一种反思的过程,虽然不一定会全部正确,但总归是在众言多元思想中的一种反思性自省。
应该说,当代诗词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它在传统形式的规约下蹒跚前行、步履艰难。时至今日,正处在传统与现代的关键转型时期,如何在继承中创造新时代的新诗词形态,是每一个创作者与研究者的历史使命。我以为,对于当代诗词的传承与创新,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加大力度:
首先,对于当代诗词创作中的代表诗人及其优秀文本,研究者应该下大力气去研究和推广,而对于其中所出现的种种问题,研究者也应该力图做一深刻的剖析和正确的引导,而不仅仅是一味地表扬、跟风地颂赞。
其次,突破当前所谓研究学科的壁垒,不论是古代文学研究学者,抑或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学者,都应该以客观、开阔的视野面对当代诗词的创作与研究。在当前国家大力倡导优秀传统文化回归的契机下,特别是我们的教育促使许多学者并不能融通古今学养的现状中,更应该各自发挥一己之特长,共同把古今学科的优势发挥出来,为当代诗词的创作与发展做好指路标、垫脚石工作。
再次,对于诗歌创作者及其作品而言,应该从作品的外在形式和思想内涵两方面入手构建一种有效而务实的美学评价体系。在举贤排差的基础上,对当代诗词的立意之境界、情感之真诚、思想之深刻、态式之严谨、美感之悦目、文风之趣味等条件加以系统研究。我们无意做某种形式上的“权威”,但我们应该以此来引导当代诗词的良性发展。
不可否认,诗歌创作是一种极具个性化的艺术创造。但是,我们不能也不应该以“个性化创作”的理由来拒绝人类对美的共性的认知,因为美的标准是人类精神审美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共同遵奉的范式,就像我们传统文化中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与西方“你想别人怎么对待你,你就怎么对待别人”的“同理心”一样共同属于人类的“道德金规”(Golden Rule)。诗歌创作也会有人类共同认同的“道德金规”,只是这个“道德金规”我们还没有建立起来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