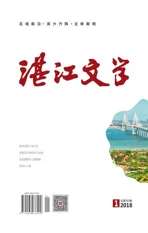超越底层的“底层写作”
——评王学忠的“平民诗”
2018-11-14赵金钟
◎ 赵金钟
八年前的一个春节,我集中阅读了一些“打工诗人”朋友寄来的“打工诗”。那些在某些追求纯艺术的诗人看来还有着些许稚嫩或粗浅的诗作,却深深地打动了我,令我落泪。它促使我思考着一个问题:艺术的标准到底在哪里?“底层写作”或者说“打工诗歌”,能不能或者说有无资格为诗歌写作提供一种标准?
今天看来这些问题应该不成为问题。这些来自于生活前沿与底部的写作,直接表达着与生存现状胶着共生的状态,非常质感地向我们传递了生活的真实和精神的真实,是关于生存的切肤体验的血淋淋呈现。它给诗坛带来了一股新鲜之风,给风行了20余年形而上探索之风的当代诗坛吹入了一股略显拙重却极具穿透力的活鲜气息。一句话,它给新诗创作提供了一种新的写作路径。这是值得肯定的。
从大的格局上看,王学忠的诗歌创作属于这一写作路径。他是一位下岗工人,时代的转型将他和大批产业工人“甩出”了工厂、车间,抛向了社会的各个角落。但他们没有沉沦,而是为了生存,以各种姿态坚毅地与命运抗争:
这是一群丑陋的劳动者
像一簸箕不闪亮的石头蛋儿
撒在古城的闹市、社区
钉鞋、修车、卖菜
(《劳动者》)
作为下岗工人,王学忠品尝了生活的所有艰辛,他摆地摊,蹬三轮,和所有“不闪亮的石头蛋儿”一样,游动在城市里。然而,与那些“石头蛋儿”不同的是,生活的苦难没有阻断他对“缪斯”的钟情,在辛勤忙碌的工作之余,他创作了大量的诗歌。这些诗歌“写在地摊前、饭桌旁和骑自行车进货的路上……”他写作了许多基于自己“第一体验”的诗作,表达了下岗工人的辛苦劳作与对于命运的抗争。正如其妻子英儿所说:“学忠的诗,是社会底层人们匍匐在地上的呐喊、呻吟,字字句句都流淌着酸涩的泪水,鸣响着对假、恶、丑的鞭笞。”[1]
诗歌是心灵的艺术。但这里的“心灵的艺术”不是自绝于物质世界的“独立体”,而是生活逼入诗人心灵产生震动之后所形成的“情绪凝聚”。成功的诗不可能是他者思想和体验的嫁接,而应“是作者在客观生活中接触到了客观的形象,得到了心底跳动”,并“通过这客观的形象来表现作者自己的情绪体验”的结果[2]。因而,“第一体验”永远是诗歌最可宝贵的“血肉”资源。它反对不经过“作者自己的情绪体验”,而只是根据现成的思想理念或政治条条去机械地演绎。一些诗人的创作之所以苍白无力,或流于口号,原因即在于此。学忠诗歌的可贵之处在于,它们建立在“第一体验”即诗人切肤体验的基础之上,是诗人“挑战命运”的心灵回声。
基于他的生存现实,学忠写了许多关于“苦难”的诗。如写农民工的苦难:“喝罢元宵汤”,“民工们已经起程/若一波波奔腾的春潮/似一阵阵喧嚣的烈风/……/向一切需要力量的地方涌动/……汗珠子是廉价的雨/殷红的血随时可以牺牲”(《中国民工》);写三轮车夫的苦难:“蹬得动要蹬/蹬不动咬牙也要蹬/就像做了一回上弦的箭/只有折了/句号才算画得完整”,“出门时把力带上/忧愁丢在家中”(《三轮车夫》);写小商贩的苦难:“大道上冷冷清清/行人的眸子里/转动着惊恐/卖菜的躲进墙角/修鞋的藏入了楼洞/风风火火的三轮车夫/鼠儿似的没了踪影/诶,那是谁家的小女孩儿/抱着半袋花生米哭得好痛/脚边是折了的秤……”(《这座城市很干净》)……凡此等等,不一而足。然而,学忠最令人感动的似乎还不是这些,而是一种难能可贵的自立与超越。阅读他的的诗歌,觉得他是一个有思想、有追求、有担当的人,决不是一般的“下岗者”,更不是一个软弱妥协的人:“不过,当你退下来之后/诺大的肚囊内/留下的,或许/只是一腔发不出声音的悲叹……”(《照相机》)——这是他对“照相机”命运的感慨。“照相机”跟随着首长,“考察”,“赴宴”,登临黄山、长城,俯瞰长江、黄河,的确“风光”过、“伟大”过,然而那只是陪着别人“露脸”,没有自己的脸面和“心脏”,所以,“忙碌”过后只能是空虚与悲哀。诗人实际上对“影子”与“歌手”们发出了批评与警示;“小妹呀,请不要/埋怨远方的诗人哥哥无能/只会怀抱诗笺,呜呜哭泣……”(《诗为陌生的小妹而哭》)——这是对无助弱者的同情。被同情者为四川一位名叫徐文英的难产女子。她在被家人送往医院途中,遭公路管理人员拦截达半小时之久,致使婴儿窒息腹中,母子双亡;“我是一株纤弱的小草/蜷缩在襁褓中/嘴上没有怨言/咽进肚里的/是天空滚动的雷鸣……”(《我是一株纤弱的小草》),“我多么希望有一天/柔弱的身子变成一根长刺/给那些玩弄者血与痛的还击……”(《我不是软绵绵的柿子》),“我真想从匍匐的地上/猛然站起/绊倒那些春风得意的小子/摔他个哼哼唧唧……”(《凳子》),这些掷地有声的诗句表达的是对不公命运的抗争及心中自有风雷的坚毅,传达出不妥协、不服输的硬汉子精神。
王学忠的诗一般不纠缠于对苦难与不公的展示,而是始终蕴含着一种超越,跳过所写事象本身,表达一种具有哲理高度的思考,甚或是一种关于社会结构和民族命运的思考。他的诗歌总是潜存着含泪的愤怒与无奈的幽默。这种写作风格不同于一般打工诗歌对民工命运的正面抒写,它往往更能体现诗的深度与诗人的成熟。《这座城市很干净》《笑》《猫儿盖屎》《胖子》《戴锁的鹦鹉》《凳子》《雪中的污物》《浮萍的苦衷》《扫帚》《小鸡的命运》《牛》《也许……》《红头苍蝇》《我是一棵纤弱的小草》《感悟》《照相机》《猪言狗语》(十六则),等等,是具有这一风格的优秀之作。它们简直就是“社会哈哈镜”或“官场现形记”,读来有一种痛快淋漓之感。
《这座城市很干净》可与《猫儿盖屎》互读。它们共同的主题是对“掩盖”与“隐瞒”的嘲讽。“掩盖”与“隐瞒”是我们这个时代常见的顽疾,它们弥漫于社会的各个角落,成为人们习以为常的思维方式与行为规则:“这座城市很干净/刚刚刷过的油漆味儿正浓/纵横交错的交通指示线/若白天鹅的羽翼扇动/似乎拍一拍巴掌/便扑楞楞飞向天空……”(《这座城市很干净》)诗作所揭示的是“市容大检查”时期的掩盖情形,表达的是对于街道、交通的混乱与肮脏状况的反讽。如果说,这里所讽刺的还只是官僚主义的一般作风,那么《猫儿盖屎》则深入到了社会的肌理,刺向了某些人的灵魂深处:“屎拉得很臭/盖屎的动作很麻利//躬一躬身/虎一样的神态/很坦然/隔壁的紫丁香/送来几缕清馨的馥郁//舔舔屁眼儿/一切皆已结束/一张猫脸/若一轮璀璨的旭日//旭日冉冉/似乎谁也不知/这块飘溢着紫丁香馥郁的地方/掩埋着一摊猫屎……”(《猫儿盖屎》)。在这里,诗人的厌恶、痛恨之情溢于言表,淡淡的幽默携裹着尖锐的讽刺,给诗歌带来了极大的张力。的确,一个人掩盖可气,一群人掩盖可恨,而倘若一个民族染上了掩盖之疾,则就可悲、可怕了。诗作以“猫”、“屎”、“虎”、“旭日”、“紫丁香”等意象入诗,雅俗相携,动静互映,既增添了诗的形象性,又扩宽了诗的表现空间,读来韵味无穷。《胖子》《红头苍蝇》等也是挖掘社会痼疾的力作。《胖子》的主题是《这座城市很干净》与《猫儿盖屎》的延续与拓展,它批判的依然是社会生活中的虚假和瞒骗:“瘦子的骤然发福/引起了许多人的猜测”,有的说“这孩子也有了出息”,“也有的说,那小子的胖脸纯属伪造/就像市场上不法商人的猪肉/明显有注水痕迹/也有的说,那胖乎乎的肥脸/是他自个儿用手打的……”“怀疑的目光像剑、像箭/一齐投向/那位倒背着双手/在人群中游来晃去的胖子……”(《胖子》)熟悉现实生活的人,一眼就能看出诗人想要表达的意思。《红头苍蝇》也有着一个深刻的主题,它是当今时代某类人物的画像。他们自私自利,肮脏透顶,却官服加身,人模人样:“闹哄在茅厕里/欢唱于垃圾中/嘤嘤,嗡嗡/俨然一付乡绅模样/摇着蒲扇/晃着脑袋/炫耀着那点血腥的红”。“那点血腥的红”就是贪官污吏手中的权力,正是凭借着“那点红”,他们蝇营狗苟,肆意妄为,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己乐,天下乐/己宁,天下宁”!(《红头苍蝇》)他们才是和谐社会的真正祸害。
将你扎得结结实实
是为了让你清扫垃圾
可你却坐在空调室里
与小姐聊天儿
聊杨令公、岳鹏举
聊皇帝的七十二妃……
嬴政那年的污物
至今仍堆在墙角
袁世凯拉的大便
仍然冒着浓浓热气……
太阳从东头挪向西头
似乎在例行公事
你抬起头看了看窗外
却想起了由谁接班的问题……
(《扫帚》)
这首诗对社会问题的揭示相当深刻。它表达了对历史文化结构、法制建设等等问题的深层思考。全诗使用了隐喻手法,延续着诗人一贯的诙谐中携裹着讽刺的风格,读来让人感慨良多。“扫帚”是用来清扫垃圾的,主人将它“扎得结结实实”,目的是让它好好地将“垃圾”打扫干净,而它却“坐在空调室里”,“与小姐聊天儿”。由于它的不作为(主人还得好生供养它),以致“垃圾”遍地,甚至“嬴政那年的污物/至今仍堆在墙角/袁世凯拉的大便/仍然冒着浓浓热气……”。这是何等的荒唐可笑。然而放眼现实,它又是对生活的逼真写照:一批批贪官污吏,损公肥私,祸国殃民;一茬茬不法分子,唯利是图,伤天害理……不正是“扫帚”不扫造成的恶果吗?更要命的是,养尊处优的“扫帚”并非“清静无为”,它还在思考着“由谁接班的问题”。它要像嬴政当年所设计的那样,把这一宝座永远传递下去。如此看来,这首诗所思考的问题就相当宽广和深刻了。
1、英儿:《诗为弱势群体而歌》,王学忠《挑战命运》第17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2、胡风:《略观战争以来的诗——在文协扩大诗歌座谈会的报告发言》,胡风《胡风评论集》第5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