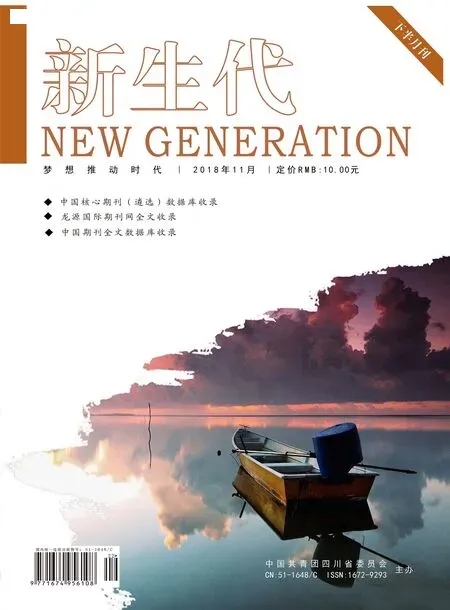平民非虚构写作的真实性
2018-11-13吴美惠广西师范学院文学院广西南宁530000
吴美惠 广西师范学院文学院 广西南宁 530000
在大众媒介时代,文化的多元化和传播方式的广角化,为社会公众提供了个体创作的平台,赋予了读者更广泛的阅读机会。就畅销书而言,自2010年以来,“非虚构”作品深受读者喜爱,而在非虚构创作中,平民非虚构写作异军突起,成为非虚构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如秦秀英的《胡麻的天空》、姬铁见的《止不住的梦想:一个农民工的生存日记》、吴国韬的《雨打芭蕉:一个乡村民办教师的回忆录》、马宏杰的《西部招妻》《最后的耍猴人》等。平民非虚构作品的创作主体并非专业的作家或者职业的艺术工作者,他们是来自社会各阶层的普通百姓,有农民、打工者、乡村教师、图片编辑等人,这些作品的创作者来源于社会各群体,亲身体验真实的社会生活,在作品中立足真实的人物事件,客观冷静地呈现人物事件,同时又从个人日常生活经历出发,客观记录个人的见闻感受,将普通百姓的平常生活融入社会时代背景,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审视历史知荣辱共进退。
“非虚构”不等同于完全真实,而是以真实客观为基础进行艺术加工创作,“非虚构写作”也存在着虚构。当我们谈论非虚构文学的“真实性”问题,可以从“写作主体的真实观、文本主体的真实态、接受主体的真实感”者这三个维度来探讨“非虚构文学”的“真实性”,并紧扣住非虚构文学作为文学的本质给予我们诸多启示。[1]平民非虚构写作作为一种文学创作活动,其选材来源于社会生活,通过语言符号的媒介进行创作,最终形成的作品也将面向广大读者。
一、平民非虚构写作的选材
在选择题材上,创作主体面临着“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问题。而平民非虚构写作主体选择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事实,无论是历史事件还是正在发生的事件,都以“生活真实”为基础。他们对过去或者存在的社会生活进行记录,不是完全重现现实生活的点点滴滴,而是对现实生活的艺术加工处理。在写作对象的具体操作上,平民作家由于出生和生活经历等因素,主张重回民间社会底层,侧重关注普通百姓的群体性事件和公共问题。在《止不住的梦想:一个农民工的生存日记》里,创作者即是一个打工者,他以农民工的视角,用日记体的方式记录下外出打工者的生存现状和工作环境,通过描写身边打工者的工作和日常生活,展现了农民工群体外出谋生的艰辛以及由于情感缺失导致在生活上的不良习惯。秦秀英的《胡麻的天空》完全是基于真实的大自然而作,她亲身触摸天地万物,以图文并茂的手绘图作品,描绘自然界的各种景物和生活中的亲人朋友和家畜,每一幅图片的内容都是作者亲身体验的客观真实,配合文字阐述自身对社会生活的感受体验。吴国韬的《雨打芭蕉:一个乡村民办教师的回忆录》刻画了一个忠厚老实的乡村民办教师形象,叙述中国社会进程中的细枝末节以及底层社会人民的生活状况和精神面貌。这些作品主要选取容易被历史忽视的事件,关注并记录下特定的社会阶层和群体在特定历史时期生活的生活面貌,通过作品还原当时社会现状和社会群体的生活原生态。
创作主体的创作意图与其人生经历密切关联。《西部招妻》的作者马宏杰从小家境贫困,是自幼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穷苦孩子,童年生活的环境和身边的人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因此他在《西部招妻》的序言中说过,我关心那些生活在底层的人。《胡麻的天空》的作者秦秀英是个普通农民,1947年出生她只念过一年半小学,超过60岁年纪的她在儿媳的指点下开始做自然笔记,起初儿媳只是为了让她排遣寂寞,把在公园里照的各种植物的照片放在电脑里,让秦秀英画。画完后,儿媳还让她标上花名、日期、地点和天气情况。虽然将近岁的秦秀英才开始查字典学文化,但她熟悉自己所画的那些朝夕相伴的植物、家畜等,于是她在68 岁就出版了《胡麻的天空》,图文并茂地讲述了一个农民的世俗人生和我国农村六十多年的自然与人文生态的变迁。[2]《雨打芭蕉:一个乡村民办教师的回忆录》的作者在乡村工作生活二十余年,他亲历社会发展变革对乡村的影响,他将自己的艰难岁月和人生世事以平实的口吻记录下来,以作品来见证人生经历和时代变迁。
二、文本主体的“真实态”
文本主体的“真实态”是指平民非虚构写作以平实质朴的语言,强调主体的“在场性”,叙述真实的历史或者人生经历。由于平民都是熟悉社会生活底层的非专业作家,他们的创作很少经过文学艺术的雕琢,故他们选择的文体灵活多样。卡波特认为:“非虚构小说将不会被纪实小说所混淆,它是一种既通俗有趣又不规范的形式。它允许使用小说家所有的手段,但是它通常包括的既不是有说服力的客观事实,也不是诗人高度的艺术虚构,这种形式是可以通过探索达到的。[3]《胡麻的天空》就是突破文学形式的束缚,采取图文并茂的方式进行创作。作者以手绘图搭配文字解读农村生活,手绘图简单易懂且栩栩如生,文字浅显通俗,质朴无华,两者珠联璧合,既对乡村的庄稼和家畜进行生动具体的解释说明,又加强了作品的真实感,展示了农村生活的本色。在《止不住的梦想:一个农民工的生存日记》中,作者采用日记体形式,用白描手法,真实的自我叙述写下农民工的日常生活场景,记录他们每天平凡而残酷的生活。每一个场景都朴素凸显农民工的工作处境和作为普通人的情感需求,充满了真实浓重的生活感,具有田野文献的标本价值。在《西部招妻》里,马宏杰坚持以“我”的视角追踪事件的发展,通过第一人称的叙述角度,描写身边的所见所闻,尤其注重事实相关的细节。如“聪梅母亲家的被子居然多年没有洗过,脏的看不出原来的颜色,只为了省一块钱买油盐酱醋”。在质朴的语言中,展现了底层人民因贫困而节俭生活的场景,可以看出底层人民的生活状态。
平民非虚构写作并非对客观社会生活的机械描摹,,而是渗透着创作主体对社会生活的情感态度,在非虚构写作中,平民作家以出客观冷静的视角审视社会,表现自身的真实体验和现实情感。以作品《西部招妻》里的一段“在场性”叙述进行分析。“下午快3点时,家里回来一个小男孩,一进门就管老太太叫奶奶。这小孩十岁左右,是老太太的孙子,他一进屋,看到大人们在说话,就小心翼翼蹲在炕头,伸手往炕下摸着什么,然后拿出一片泡菜叶子,很兴奋地放进嘴里就吃。老太太发现后,用手指点着他的头,骂他贪吃,孩子解释说’我饿了’。在这里,一片泡菜叶子,对孩子来说都是奢侈的小吃”。[4]看似平淡的叙述中,透过作者的语言看到了西部乡村农民的生活穷困潦倒贫穷限制他们日常生活的正常饮食,小孩子每天也只能吃两顿,甚至连农村最常见的泡菜也是孩子心中的美味佳肴。在如此艰难的生活境况下,善良的心与金钱的诱惑形成的冲突,使作品字里行间充斥着一种无奈的苍白感。马宏杰深入农村,触摸底层民众的疾苦,关注农民的辛酸,代农民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是务实的民间话语立场,更贴近底层民众的审美视野与文化期待,他以“在场”性的叙述话语,为读者展开西部乡村普通农民的辛酸与苦楚,激起了有过苦难生活经历的读者的阅读热情。
三、接受主体的“真实感”
读者能够从平民非虚构作品中看到真实性的社会生活,能激发他们对现实生活的审视,引起读者的共鸣,这便是接受主体的“真实感”。在盛行文化快餐的时代,为何平民非虚构作品深受读者青睐呢?美国“国家公园之父”约翰·缪尔或许能给我们解释。他曾说过:“当人们从过度工业化的罪行和追求奢华的可怕冷漠所造成的愚蠢恶果中猛醒的时候,他们用尽浑身解数,试图将自己所进行的小小不言的一切融入大自然中,并使大自然添色增辉,摆脱锈迹与疾病。”[5]在城市化进程和工业发展中,人们逐渐失去亲近自然接触自然的机会。中国进入快节奏的信息高速传播时代,社会公众经常来不及对信息的真伪做出辨别,就被迫遨游于信息海洋里,面对浩如烟海的信息,人们渴求真实却逐步丧失对真实能力的判断,尤其在娱乐至死的流行文化和金钱挂帅的消费主义时代背景下,许多人远离了真实的生活,失去对生活真实感的触摸。尤其是中国都市一族,他们渴望走出城市,拥抱真实的自然。而对于乡村生活的人,每天接触自然界,原野田园就在身边,就在眼前。当创作题材唾手可得,客观真实摆在眼前,即使是非职业化的作家,也能记录真实的生活场景,唱响对自然的热爱之声,体验个体生命之美。
在平民非虚构写作中,基于真实的社会经历和社会环境进行创作,以客观冷静的主观真实体验表现情感,以朴素的语言符号叙述生活,往往能满足社会公众对内含真实感的非虚构作品的期待视野。首先,许多历经磨难的读者由于生活经历和社会实践活动形成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在非虚构作品中能找到曾经苦难的岁月,能激起读者在艰难困苦中奋斗的回忆。其次,平民非虚构写作聚焦社会底层群体,主要是农民、打工者等,侧重关注城市化进程中的乡村,展现近乎真实的农村和农民,代替广大穷苦百姓发出自己的声音,为广大读者再现现实版的中国底层人民生活,使读者认识农民的真实面貌。《西部招妻》的作者马宏杰说过,记录常见的百姓生活场景,希望观者能从这些本真而平凡的图片中,品味普通人的生存状态。
读者对非虚构作品内容的信赖感来自于对“真实性”的期待,而这种“真实性”也正是“非虚构文学”区别于虚构文学的最大特点。平民非虚构写作满足了读者对真实的期待,但非虚构文学既要做到真实感又要有文学的可读性,往往使创作主体难以把握“非虚构”尺度。这要求平民非虚构写作的创作主体要保持真诚的态度关注事实本身,在创作过程中考虑到事实本身与文本真实的距离,兼顾读者的文化差异、受众水平等影响文本传播的因素,尽力将创作动机和意图达到读者的期待,使创作者与接受者在非虚构写作真实性的共识上达成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