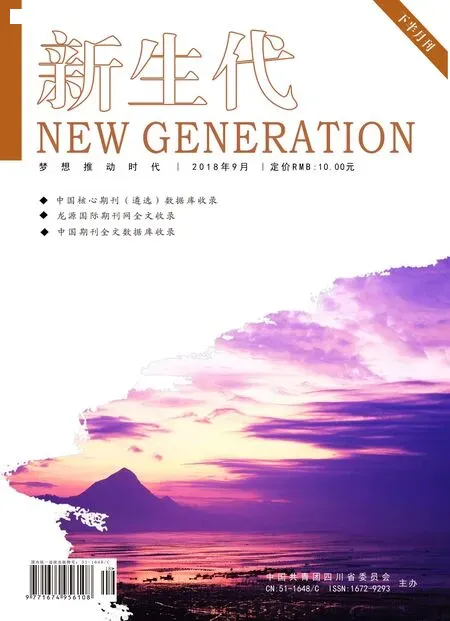陈淳论“情”
——“心之动”
2018-11-13曹晶晶上海师范大学上海200234
曹晶晶 上海师范大学 上海 200234
陈淳是朱门忠实的拥护者,正如全祖望在《宋元学案》中所说:“卫师门甚力,多所发明”。他曾两度侍学于朱子,由于两次侍学的时间间隔长达十年之久,使得在第一次授予他“根原”二字,教诲他探求“上达”之学的朱子,第二次时明确指出他所缺功夫在于“下学”。这样的为学经历,使得陈淳形成了“下学上达”一以贯之的心性学思想,而“情”在其中至关重要。
一、心具性与情
陈淳的人性论以“性”、“心”、“情”构成,认为“大抵人得天地之理为性,得天地之气为体,理与气合方成个心”。“性”,“天之所命、人之所受”,是天对人的命令。陈淳说:“性即理也。何以不谓之理而谓之性?盖理是泛言天地间人物公共之理,性是在我之理。只这道理受于天而为我所有,故谓之性。”他又说:“性命只是一个道理”,所以在陈淳看来性、命和理本质上是一物,但是所指不同。气化生万物,包括人,而理不离气,所以理赋予人身便是命,人身所接受到的理便是性。天命只是元、亨、利、贞,成为性则为仁、义、礼、智。所以性无恶全是善的,而性和命一样,都全是善而无恶。
而对于心性问题,张载首先提出“心统性情”,但他没有再加论述。朱熹认为张载的“心统性情”与程颐的“性即理”“颠扑不破”。因此朱熹对“心统性情”详加论述,在此基础上,朱子提出去人心,存道心。这一点陈淳同样认为“知觉从理上发来,便有仁义礼智之心,便是道心。若知觉从形气上发来,便是人心”,这与朱熹的思想是一致的。但是在对“心”的具体描述上,陈淳认为“心只似个器一般,裹里面贮底物便是性。”他继承邵雍所说,“心者,性之郛郭”,所以气聚而成个心之体,心里面的全是性。“心”只是承载“性”的一个容器。指出“性字从生从心,是人生来具是理于心,方名之曰性。”
陈淳虽然也承认“心”在“静”的状态下,里面全是“性”,即全是“天理”,因此此时的心是纯善的。但是由于“心是活物,不是帖静死定在这里,常爱动。心之动,是乘气动。”这就不同与朱熹认为所说的“形既生矣,外物触其形而动于中矣。其中动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俱、爱、恶、欲。情既炽而益荡,其性凿矣。”这就是说作为活生生的人,必然会与外物相感而“动”。这是的动首先是“心动”,心感于物而动。动而生情,这是心动的本能。故陈淳在“心动”这一点与朱子侧重不一样,陈淳则更注重将“心”放在“动态”中来分析。
二、情之所由来
理学又被称为性命之学或心性之学,他们的终极关怀在于人的伦理道德,而将人的伦理道德上升到天理的高度,是其特色。陈淳作为朱子的弟子,思想来源主要继承于师训,但也多有创见。
陈淳认为:“心有体有用,具众理者其体,应万事者其用。寂然不动者其体,感而遂通者其用。体即所谓性,以其静者言也。用即所谓情,以其动者言也。”即陈淳继承朱子认为心有体有用,而体是性,是静的;接触外物而发出来的是情,是动的。正因为如此,陈淳认为“心”是一个容器,里面装着“性”,“性”即“理”。心便有了能知觉的能力,而这知觉如果是内心本性的恢复,那便是仁义礼智之心,即道心。“情”是“心”接触外物而产生的,有如是“性”便有如是“情”,这便涉及到“情”的善恶问题。
在《北溪字义》中,他说到:“在心里面未发动底是性,事物触着便发动出来是情。寂然不动是性,感而遂通是情。这动底只是就性中发出来,不是别物,其大目则为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性”是“理”,理即天理,必然全然是善的,“情”是由“性”而发,其大目只是喜、怒、哀、惧、爱、恶、欲,但同时也存在是否中节的问题。所以他认为“情之中节,是从本性发出来便是善,更无不善。其中不中节是感物欲而动,不从本性发来,便有个不善。”即有个不从本性上发来的情,是感物欲而动,这是不善。意味着从性发来的情是善的,但也有不从性上发来的情,这是不善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来,陈淳较之朱子对人的情的中节与否更为严格,他试图强化情由性所发出,性只是仁义礼智,所以所发出的情也必然合乎中节,全是好的。所以他的阐述中透露出只有合乎当然之则的情才可称之为情,但是他也认为“心”不是一个死寂不动的,而是会动,且“乘气动”,这便避免不了情发而不中节,出现不善的情。因此在《北溪大全集》中他这样说:“情之善是从本性正面发来,其不善是发差了,是感物蹉了性之本位而然,非从本性中来也。若便以理与气合言之,则性即是天理。然理不悬空,必因气赋形生而寓其中。”所以情善与不善,在于是从本性发出,还是从气所发出。而人所得“气”之不同,所以形成的“质”有差别。故其情感发出便有偏盛,不能都中节。
陈淳论“情”,在于引导“情”的中节。对于理学家来说,修身即为修心,以此来恢复本性,所以感物所发之“情”是否中节便意味着修身的程度。而陈淳注重“情”的中节,这也是对朱子思想的继承以及对师门的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