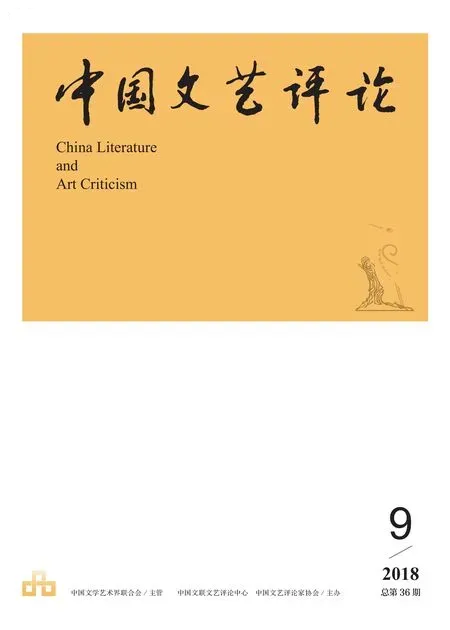从《经典咏流传》看歌曲的经典化方式
2018-11-13陆正兰
陆正兰
歌曲是人类最古老的艺术体裁之一,它具有艺术审美功能,亦是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群体、集团之间的交流媒介。随着文化产业的发展,当代歌曲作品生产数量迅猛增长,各种风格的歌曲层出不穷,如何在这些众多作品中引领大众,尤其是青年受众?如何选择有文化价值的经典歌曲,并让这些经典作品走入人心,做到真正流传?本文试图以近年一些成功的歌曲类电视节目为例,探讨经典与流传之间的关系,以及歌曲经典化的特殊方式。
一、社会选择与歌曲的经典化
经典,即一个成熟文化从历代积累的大量文学艺术作品中选出少数公认的精品。经典化,指经典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断更新。经典化离不开两个环节:社会选择与历史保持。对任何艺术品,文艺评论家、传播机构、接受者大众等都可以参与经典的社会选择与历史保持,但几方起的作用不同,且在历史不同时期的侧重点也不一样。
比如历史上的文学经典主要依据精英批评家们的挑选,就像六朝钟嵘的《诗品》,在122名诗人中挑出上品12人,靠的是比较,依据标准是仿汉代的“九品论人,七略裁诗”。而当代文化对经典的选择似乎有些变化,多了另一种经典化的方式,即“群选经典”。正如学者赵毅衡所论:“群选经典的名家,是群众需要的文化世界的提喻,大众无法接触全部艺术家,于是他们选择一人或某几个人,作为文化的替代性提喻,而每个时代面对一个新的文化,会需要自己的提喻。”当前这种大众群选经典化,主要靠投票、点击、购买、阅读、观看方式,以达到积聚人气和数量的连接。它们和精英式的批评相比,往往更注重从人到作品,而不是从作品到人。这两种经典化方式有时会互相抵触,但它们在当代社会共存,都对文化的传播发生作用。
然而,并非所有的艺术门类都遵循一种经典方式。艺术门类的不同,同样制约着经典的产生。歌曲经典化,既不同于精英批评家的挑选,也不完全由大众的群选决定,它与其他艺术门类的区别在于:声乐教学虽然是学校的一科,但学院派批评价值有限。媒体机构的批评可能在某种特定时期对某种特定种类起作用,但商业化包装(例如今日的网络媒介,排行榜,歌单)成功的把握并不大。因此,大部分歌曲的流传,主要靠媒体引导,歌众选择,靠歌众自觉传播,因而成为经典。
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央视创造传媒联合制作的诗词文化音乐节目《经典咏流传》,是一个值得分析的佳例。《经典咏流传》是一台大型文化节目,自2018年大年初一推出第一期以来,至今已有多期,每期都获得受众的好评。它以生动、时尚的形式,复活了中国独特的歌诗传统,传播中华诗词文化经典,吸引了中国青少年的眼光。它之所以获得成功,是由词曲作品、传播机构、演唱者以及接受者大众等的合力决定的。
首先,词曲是一首歌的意义中心。《经典咏流传》中反响很热烈的歌曲之一是《苔》。这是一首300年前清代诗人袁枚创作的无名小诗,并不列在我们所熟悉的唐诗宋词的经典目录中,演唱者也不是为人熟知的明星歌手,而是普通的乡村教师梁俊和他的学生,以朴实的曲调,演绎了“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的境界。一首小诗穿越古今,靠的是被普通民众挑选和演唱,靠的是“苔花”的提喻功能。正是在这个时代语境下凭借大众情感的经典提喻,传达了当代社会中普通大众身处平凡却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这首歌完成了一个时代的提喻功能,因而广为流传,成为新的经典。
其次,传播机构媒体的推广也非常重要。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作为影响力极大的传播媒体渠道,它鼓励歌众往优秀传统文化和价值观方向释义。新释义场的构筑,的确会创造歌曲的“新解”,而大众所喜爱的歌星的演绎会有助于歌众传播,它推动了一首经典歌曲变成无数个歌众口中、心中的歌,他们自己的歌,这样一首歌就变成了广为流传的歌。
其三,演唱者的身份会提升歌曲的传播效应。《经典咏流传》中有一首东汉刘桢的诗《亭亭山上松》:“亭亭山上松,瑟瑟古中风。风声一何盛,松枝一何劲。”由体育明星孙杨选择在节目中演唱,这与孙杨在游泳场中自强不息、勇敢拼搏的年轻表率形象很匹配,从而加深了歌众对此歌的接受和理解。需要强调的是,明星的加入使节目注入了时尚性,但并不代替文化产品原有的品格,只是附加给文化产品一种临时的“标志”,并加上社会价值、社群价值。不可否认,被加上时尚因素的歌,流传更为顺畅。时尚的过程是一时的,而流传的过程是历史的。
最后,歌众的接受和传唱是歌曲意义实现的最重要一环。一首歌创作出来的意图,就是希望被更多人接受并广为流传。可以有从来不发表的抽屉诗,却不可能有不被人唱的抽屉歌,因此我创用一个名词“歌众”:“歌”是名词也是动词,它的双性特征,决定了歌众的二重性——歌曲的接收者不仅是歌的听众,还是歌的再创造大众。一般艺术的受众,能动性只表现在“掏腰包”上,费斯克所说的“能动观众”,说的只是电影观众有用脚选择、用钱包选择的能力。歌众才是真正的能动接收者,因为歌曲的经典化是他们传唱出来的。
因此,一首歌之所以流传,取决于多方力量,还需要歌曲特殊的传播方式。德勒兹(Gilles Deleuze)与心理学家伽塔利(Felix Guattari)在名作《千高原》中提出文化的“块茎状模式”传播说。这种模式不同于一般传统文化传播的“树状模式”:“树状模式”有根、有胚芽、有基干,此后发出枝叶,但有权威性的源头,可追溯根源,可回溯发展途径,回向意义的权威源头。“块茎模式”在地下蔓延,随处可以冒出头,另成一个体系,另成一个意义源头。而“块茎状模式”反等级、反体系,是动态的、异质的。传播分途蔓生,各个节点可以成为新的意义之源,重新长出意义。
从上面分析的两首歌曲可以看到,歌曲的经典挑选和传播方式是典型的“块茎式”。歌曲的源头意义、权威性并不能完全主宰歌曲意义传播的旁侧再生。不仅每次新歌的挑选发行,每个歌手的演唱,每一台节目都是在新语境中创造新文本,每个歌众的歌唱,甚至哼唱,也是在创造新文本。歌曲的这种“块茎式”的传播方式,决定了歌曲的经典化只能通过歌众选择。古今中外,各种媒介机构、各种精英一直在试图引导歌曲经典化,但歌曲这个艺术门类的特殊性质,决定了它的文化机制不可能根本改变:如果歌众不跟上,媒介机构推动力就会削弱。一首歌的经典化需要多方合力,尤其是歌众的应和。正如克兰指出,“如果一个文本的话语符合人们在特定的时间阐释他们社会体验的方式,这个文本就会流行起来。”歌曲的流传,正好符合这个规则。
二、“歌不附体”与再语境化
经典化的另一个环节是历史保持。对歌曲来说,历史保持落在两个层面上,一是物质载体,二是语境载体。物质载体可以长久保存,例如歌本、唱片、磁带、卡拉OK带、CD、VCD、DVD、MV光盘、数字下载等,它们为歌曲经典化的历史保持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支持。语境载体虽然也具有物质性,却是临时的、“现场”的。常见的语境载体有电影、电视剧、歌剧、电视节目、广播节目、现场演唱会、网络观看等。语境载体对一首歌曲流传的最初阶段起很大作用,但是歌曲流行过程一旦开始,各种语境载体就多多少少开始淡出,就形成了“歌不附体”现象。
对语境载体来说,歌不附“体”现象是传播的必要机制。歌曲流行虽然起始于最初的语境载体,但要保持它的流传,就必须不断投放入新的语境,依靠新语境与旧语境的对比展开实现成功流传。
其中有些电影插曲和歌剧单曲,完全脱离原来语境,成为某演唱会中的一首歌,或者直接在群众中单独传唱、流行。最典型的是《义勇军进行曲》。它最初为1935年电通影片公司发行的电影《风云儿女》主题歌。这首歌曲出现在影片结尾,配合主人公阿凤等觉醒了的中华儿女步伐坚定投入抗日救亡运动的场景。后来成为中国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各种国际活动的仪式歌曲唱出来的时候,歌曲所传达的意义已经很不相同。原电影已经被忘却,抵抗武装侵略的语境也已经遥远,而民族尊严和骄傲的情感还包含其中。
还有一类歌曲得益于“半不附体”,它们虽然也脱离了最初的语境载体而单独流传,但还与原语境若即若离,歌者听着都依稀记得是某电影的插曲。比如《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是20世纪50年代电影《冰山上的来客》插曲,它带有新疆塔吉克舞蹈风情的曲调让人们依稀想起电影的某些情节和画面。《四季歌》原来是周璇在电影《马路天使》中唱的插曲,此歌的流行既与这个始发点有关,也由于脱离了原载体获得了新的生命。
这种一再的“再语境化”,使歌曲获得丰富的意义,突破时间障碍,流传为经典。比如,学堂乐歌时期李叔同根据美国歌曲重新填词的《送别》,20世纪60年代被电影《早春二月》用作插曲,80年代被电影《小城旧事》再次用作主题曲。《难忘今宵》原是为晚会所作的结尾曲。后来在1987年的春节,由著名歌手李谷一作为晚会压轴歌演唱,从此家喻户晓,成为人人传唱的经典歌曲。此歌流行了三十多年,已经成为一个情感象征,成为大大小小各种晚会的结束歌曲,从最大规模的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到个人的生日晚会,一次次出场,一次次不同的语境,衍生出一次次不同的意义。对春节晚会来说,难忘的是全世界华人共享祖国昌盛、人民安康的美好祝福。而对于一个人的生日晚会来说,难忘的是亲朋好友的聚会和又一个生日年岁的到来。
在《经典咏流传》节目中,我们也听到了很多这样的老歌,比如再次听到《滚滚长江东逝水》等老歌,这些都是原语境存留,与“歌不附体”结合,生成成功经典化的例子。歌曲传唱,就落在多重语境的控制之中,其意义越来越丰富。“块茎模式”是共时传播,“歌不附体”形成了经典歌曲动态的历史保存:歌不是保存在哪一场物质载体CD上,也不是保存在哪一场晚会的语境载体中,而是不断在新的物质与语境载体中复活蔓生。
三、“老歌翻唱”与歌曲的“共同主体性”
“老歌翻唱”是最重要的音乐流传机制。最早最具规模系统地更新载体的“老歌翻唱”,当为中央电视台组织的大型文艺演出《同一首歌》。此栏目于2000年1月27日创立,持续了五年之久,一直以现场和电视直播的形式亮相,人气指数和收视率一直据先。据央视国际《2005年播出节目一览》统计,就2005年1月7日至8月12日,不到八个月的时间内,总共组织了29场演出,平均每场演出在18首歌以上。这些音乐中大多数属于老歌翻唱,也有正在流传或者意图推向流传的音乐。2005年,中央电视台《同一首歌》栏目组配套出版了一套音乐丛书共六本。后来,中央电视台的《歌声飘过30年》《歌声飘过80年》,也都是老歌翻唱式的经典选择,它们都收到了很好的社会文化效果。
这些老歌被歌手们在台上复活,又被文字文本和VCD文本再次记录。就如《同一首歌》栏目的组织者所说,意图在于“在歌声中回忆过去的好时光,在歌声中品味现在的好日子”。对不同的歌众来说,老歌新唱确实将时间空间化了。男女老少,不同时代的人可以汇聚在同一首歌的场景里。
同样值得探讨的,是2005年的电视节目《超级女声》,可以说是当代典型的、最具冲击力的一种“老歌翻唱”。“超级女生”的成名,并没有沿着过去歌星成名的套路:量身定歌,凭借一首新歌一炮打红。她们一路唱来的音乐大多是旧歌,也基本属于“老歌翻唱”,这一点并未被评论界真正注意。在她们演唱的音乐中,几乎包含了现有歌手的各种翻唱形式,这里做个简要分析。
1. 民歌翻唱:李宇春选唱的《山歌好比春江水》,周笔畅选唱的《青春舞曲》,周笔畅选唱的《乌苏里船歌》等,吸引了很多民歌爱好者。
2. 影视音乐翻唱:黄雅莉选唱的《橄榄树》(台湾电影《欢颜》插曲),张靓颖选唱的《一帘幽梦》《在水一方》(琼谣影视剧的音乐),满足20世纪80年代一批成长于琼谣小说中的纯情男女。在此之前,歌手许茹芸曾推出过爱情电影主题曲翻唱合辑《云且留住》,以独特的唱腔重新诠释了早年琼瑶电影的主题曲,反响积极。
3. 跨性别翻唱:纪敏佳选唱的《天堂》,原为蒙古族歌手腾格尔演唱。张靓颖选唱的《真心英雄》,原为香港歌手成龙演唱。
4. 西方音乐翻唱:张靓颖选唱的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
,这首歌来自于当代著名音乐剧作曲家安德鲁·劳伊德-韦伯(Andrew Lloyd-Weber)创作的音乐剧《艾薇塔》(Evita
,作于1976年),由蒂姆·莱斯(Tim Rice)作词,可谓当代西方经典音乐。李宇春选唱的Everything I Do
,是美国电影《狮子王》(Lion King
)中家喻户晓的经典插曲。这些歌似乎更针对“白领阶层”。5. 不同风格音乐翻唱:李宇春选唱舞曲风格的《我最摇摆》《请你恰恰》,超级女生合唱的无伴奏风格的《半个月亮爬上来》《彩云追月》,纪敏佳选唱的戏曲风格的《说唱脸谱》等。
6. 不同时期不同歌星的代表音乐翻唱:周笔畅选唱的《龙拳》,是RAP歌星周杰伦的代表作之一;张靓颖选唱的《好大一棵树》,是实力派歌星那英的代表作之一;张靓颖选唱的《乡恋》,是老牌歌星李谷一的代表音乐之一;张靓颖选唱的《小城故事》,是邓丽君的代表音乐之一;周笔畅选唱的《流星雨》,是台湾偶像派组合F4的代表音乐之一;还有周笔畅选唱的《两只蝴蝶》,是网络音乐代表作之一。
7. 几种主题歌曲的翻唱:张靓颖选唱了颂歌《我和我的祖国》《爱我中华》,李宇春选唱了情歌《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超级女生群唱了励志音乐《明天会更好》《同一首歌》等。
在这些老歌翻唱中,一个能指指向另一能指,这个不断延伸、无限衍义的意指过程,也是歌曲在歌众不断传唱中特殊经典化的过程。最终歌曲必须由歌众自觉传唱,在歌众的不断老歌翻唱中得以形成,得以保持。老歌的不断翻唱,不仅巩固了此歌的经典地位,也在流传的过程中滋生新的文化功能。如果没有成功地利用这几种历史保持和翻唱方式,哪怕在一代人中成功流行的经典歌曲,也会在世代更替中,从经典中消失。
没有一种艺术门类能像歌曲这样,给予歌众以如此大的自由创造可能,而唱歌也是歌众自然的文化需要。伯明翰学派的斯图亚特·霍尔在《电视话语的制码与解码》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三种解码”理论。霍尔认为,意义生成过程,取决于观众的三种不同解码方式。第一种解码立场:“主导霸权式解码”(Hegemonic Reading)。观众与电视制作生产精英的编码立场完全一致,完全明白无误地接受电视剧制作机构意图中的意义,观众自己没有独立的立场。第二种解码立场:“协商式解码”(Negotiated Reading)。既不完全同意,又不完全否定,观众既接受社会文化中主导意识形态的权威,又看到自己的具体利益所在,但拒绝完全接受制作精英机构意图。第三种解码立场:“对抗式解码”(Oppositional Reading)。观众明白电视制作精英要借电视传送的意义,也明了电视文本各层次意义,却选择以完全相反的立场解码,“读出”针锋相对的意义。
霍尔理论指出文化产品的接受方式才是最后意义的实现。这个理论对歌曲研究有重要意义。三种解码对别的艺术门类可能足够多样了,却不够说明歌曲流传的多样化。
歌的接受,歌众的传唱,一开始是模仿,不久就变成自我表达、自我创造,而自我表达不可能完全遵循“制作精英”规定的模式,而是就自己的身体条件、感情需要、精神追求予以了改造。这样在歌曲流传过程中就出现了不同于霍尔三种解码的第四种解码方式,即“创作式解码”(我建议英译为Creative Reading)。这种“创作式解码”不再是艺术专家的领域,面对歌曲这种最普泛的共同客体,歌众创造并分享世界,成了每个个体生命自觉和不自觉的一种努力,从而构筑共同主体性。唱歌属于个人,却不存在纯粹个人的歌。歌者总是在交流,而且有意无意地加入并形成了共同主体性,来推动一首歌的经典化。
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理想地体现了这一共同主体性。其核心是人与人之间通过语言行为相互理解。歌唱作为一种人类最自然的表意行为,看似独自歌唱,实际上却是通过同唱一首歌,获得了“歌众群体”。他们不必形成合唱,即使相隔万里,从未相逢,却通过共同主体性,用各自不同的方式完成一个意义,这不是一般所说的“集体主义”,而是各个主体自由意志的贯通,它并不要求整个社群取得统一意志,相反,它必须依靠主体各自的主观意愿,提供不同的再创造,才能形成。就像《经典咏流传》中广为流传的一些歌曲,它能唤起一批人群心灵的共同响应,并且使他们自觉自愿地唱起来。“个体之主体性只有在共同主体性里才成为现实的东西;共同主体性也只有在众多的个体主体性发挥中才成为现实的东西。”这是哈贝马斯理想的共同主体性。歌曲取得的共同主体性,在这里得到非常生动的表现。就像他的论述:“语言行动不只是服务于说明(或假定)各种情况与事件,言语者以此同客观世界中某种东西发生关联。语言行动同时服务于建立(或更新)个人关系。”的确,能够把个人与共同主体相关联的艺术品,才是真正的经典。
这样一种理想的主体借“经典化”沟通的模式,首先在歌曲与歌曲传播方式中有活力地展开,并为努力探寻“共同主体性”的文化工作者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观察及实验场地,对有同样追求的其他艺术门类来说,借鉴歌曲传播模式,吸引大众积极参与,或许是经典化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