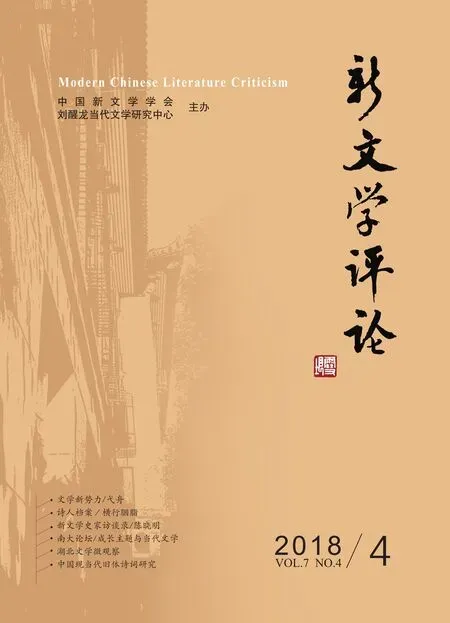吕志青《黑屋子》的前世今生
2018-11-13罗义华
◆ 罗义华
首先得承认,《黑屋子》有一定的阅读难度,这种难度,与其说是吕志青在肉体/精神、个体/群体、现实/抽象、世俗/宗教、历史/文化等多维视域中探究与表达时代文化症结的复杂方式让人却步,倒不如说是文本中艰难幽深的心灵探索令人猝不及防——小说对现实与人的灵魂的深度介入,就作者自己而言是前所未有的。吕志青在《关于〈黑屋子〉(创作谈)》中指出:“好小说似乎应是这样:它与生活的联系是如此紧密,可又不大容易被生活拉下水。”我以为,这句话本身暗示了小说的创作难度:黑屋子以对当代人心灵之境的窥测,敞开了一条透析当代文化与精神状态的路径;黑屋子隐约在形而上与形而下之间,无处不有无时不在,关乎你我众生;黑屋子有它的前世今生,小说重构了它的光谱。这种难度表明:《黑屋子》包藏了吕志青的野心,从《南京在哪里》甚至更早起他已蕴蓄多年,终于沉重一击。
一、 在敲打中呈现“现代撒旦”之恶
毋庸置疑,黑屋子正是小说的核心意象,通奸(或曰出轨),尤其对通奸的追溯、追究,以及所谓拯救,则是小说的中心事件。但是,小说一开端就抓住人心的不是黑屋子,不是通奸与拯救,而是齐有生探究所谓“真相”而不断敲打臧小林的细节与逻辑。
黑屋子是一点点敲打出来的。从发现一种端倪到反复质疑,从软硬兼施逼迫臧小林交代真相到两人一道实地勘察通奸发生的地点与细节,从肉体的通奸到精神的出轨,敲打是一个循序渐进、逐步深入的过程。为了抵近臧小林精神与情感层面的黑屋子,发现所谓最后的“真实”,齐有生不惜以上帝的名义、儿子的生命来裹挟臧小林,将其置于一种精神、肉体的双重不归之路。正是在这种层层深入、令人窒息的敲打中,心怀救赎意识的臧小林选择自杀(向死而生)以实现其最后的“洗耻”与“赎回”。可以说,整部小说始终贯穿着一条敲打的逻辑,敲打构成了小说叙事链条上的推进器。
推究起来,敲打行为具有如下三层意义:(1)在齐有生与臧小林的敲打关系结构中隐含有深刻的历史内涵,那就是男权中心主义的深固存在与女性自身意识的残缺及对男权的依附。(2)齐有生对臧小林的敲打,具有自我敲打的功能。在臧小林被敲打得体无完肤以至于灵魂、肉体双重消亡之际,他自己也走到了无路可走的悬崖边上。齐有生最终跳楼身亡说明他并未真正走出那所小黑屋,只是进入了一个更深、更大、更黑暗的黑屋子。(3)在近于一种残酷展示的敲打过程中,读者,或者说是小说的隐含读者,因为齐有生与臧小林关系结构的普泛性与隐喻性,而承受了来自精神层面的猛烈敲打。齐有生以“拯救”的名义将道德力量转化为一种权力并带来了触目惊心的伤害,因此,敲打本身就是一种僭越行为,这种僭越表征了历史、现实中权力与道德的转换关系,小说借此确立起一个“现代撒旦”的形象。吕志青在《〈黑屋子〉赘语》中指出:
我眼里的“现代撒旦”,或者我的词典里的“现代撒旦”,它是这样一种角色,它绝非一团漆黑,相反,它具有着某种“正当性”。而这种“正当性”,往往是由它所处的历史和现实的环境所凸显出来的,即它是在对历史和现实的批判中产生的。我眼里,历史上和现实中所出现的大大小小的“拯救者”,有许多都可归入这一类。它们当然是恶的力量。但不是一般人口头上的那种纯然一体的、漆黑一团的存在,而是具有某种“正当性”。这一点,从基督教文化中也可以找到佐证或寻得来源:撒旦最初是天使长,它的职责是专为上帝巡查、报告人世间的种种劣迹和罪行,在这个过程中它逐渐变得愤世嫉俗,随后异化成上帝的对立物。而我之“现代撒旦”,则主要侧重它的僭越方面。二十世纪的许多重大灾难,都由这僭越造成。但这并未结束。历史仍在现实中继续。齐有生不过是出现在家庭这个最小单位、这个社会细胞中的僭越者而已。他祭起上帝的旗帜,俨然上帝。
借助于基督教的救赎与涤罪命题,小说将敲打行为转化为一种自我拯救的过程。齐有生首先确立了一种道德姿态:尽管在婚前他也曾有过出轨行为,但婚后他即对臧小林坦白了一切,关键还在于,“真实”的想法是如此强烈执着,这么些年来,他对她从未有过丝毫的隐瞒,他以赤子之真面对她,“世界广大,世事纷繁,他所冀望的,无非也就那么点东西,如豆芥之微”。但是她却背叛了她,并且一直隐瞒与欺骗了他22年。即便现在,他所得到的“真相”也只是冰山一角。问题还在于,倘若臧小林真要如其所愿获得“重生”的话,她怎能不经受惩戒并在惩戒中回到最后的“真实”中来?正是在赎罪的逻辑链条上,齐有生占据了自己作为受害者与执法者的道德高地——惩戒只是手段,最严酷的惩戒行为也不过是为了上帝,儿子的生命和幸福——这个道德高地赋予了齐有生敲打的合法性、正当性与必要性。如何才能祛除这些罪孽呢?辱骂与殴打是不够的,离婚也不能“注销”耻辱与仇恨;忏悔是不够的,向公众坦白自己出轨行为的“负耻生活”也是不够的;“拯救需要血”,孙的血也是不够的,需要臧小林自己的血,她必须“向死而生”。小说一面于此探讨了自我救赎的可能性,一面在这种自我救赎过程中着力渲染与凸显了“现代撒旦”之恶。其复杂性在于:一方面,臧小林最后的“向死而生”,既有性别权利格局中女性的牺牲属性,也有在赎罪链条上的最后解脱意味,就小说文本形态而言,这两重因素的比重是含混莫辩的;另一方面,“现代撒旦”的敲打行为具有某种正当性,尽管“它们对人的影响和摧残,远非一般意义上的恶的力量可以相比”。这会令相当一部分读者面临这样的挑战:对臧小林与齐有生的行为及其结局,很难做出一种清晰简明的价值判断与情感选择,同情、怜悯、憎恨、厌恶混杂其间,又似乎都无济于事。
二、 拯救的难度
小说的中心事件,是对通奸(出轨)行为的追问、追溯和追究,以及所谓的拯救,小说由此形成了一条贯穿始终的逻辑链条。小说真正让人绝望的是,随着剧情的推进,几乎所有的人物都犯有通奸(出轨)行为或征候。齐有生婚前出轨,在敲打过程中又与沈慧同床共枕,臧小林则隐匿了长达20余年的奸情。许建平、厉大凯、老冯、老费、老穆、老柴这些男人,有的执行所谓“光源氏计划”,饲养小女孩;有的主张换偶游戏,搞同性恋;有的与妻子闺蜜私通;有的在婚姻殿堂里出出进进。他们的妻子都几无例外地与人私通。年轻一代小孔、小潘也都有出轨行为,更年轻的沈慧从16岁起就不断与人发生关系。关于通奸、爬灰、换妻、同性恋、艾滋病等问题的讨论,构成了小说叙事的狂欢。在多数情形下通奸行为并没有带来多少羞耻感,恰恰相反,它似乎成了两性关系的润滑剂。通奸制造了第三者,老费只有在第三者附体的情形下才能满足;齐有生、臧小林同样如此。
通奸(出轨)的本质是背叛、隐瞒与欺骗,它与忠诚、真实背道而驰,是在身体、精神层面的双重沦陷。小说表明,通奸(出轨)行为折射出人类心灵世界中的黑屋子,而你看到的永远都只是冰山一角,还有无限多样的“真相”你无从发现。这种行为具有足够的普遍性与含混性,因而带来了时代文化的总体象征意义——可以说,从未有人赋予通奸(出轨)如此深刻而丰富的时代性、集体性。至此我们得以窥见小说家的用心:在通奸故事的喧哗之下隐含有对时代文化的隐忧与愤怒,是在愤怒之下的重击。语言的迷宫、话语的喧哗,不过是一种欲盖弥彰的伎俩:当作品中所有人物都在不同程度上发生通奸(出轨)行为时,它本身就构成一个隐喻,一种话语,指向人际关系从根本上的失真与道德人伦的大面积坍塌。
但是,小说的旨趣并不止于通奸(出轨)事件本身,进一步说,通奸(出轨)事件及其所呈现的人际关系失真与人伦失范都只是作为问题提出的,作为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小说巧妙引入了宗教元素。在《圣经》中,犯有通奸罪的人必当惩戒,这种惩戒自带拯救的意义。小说从通奸出发,提出与确立了一个拯救命题。
小说表明,拯救的难度首先就在于,它是与“真相”相对而言的,而“真相”往往难以发现,更何况已经呈现的“真相”很可能不过是另一种“真相”的掩盖。如果不是恰好与许建平妻子有过共事经历,如果不是因为一种近似于本能的直觉,齐有生就没有可能发现臧小林刻意隐瞒了22年的奸情。从这个意义上讲,齐有生的残忍与冷酷,不过是在另一维度上表明了探究“真相”的难度。其次,拯救起于身体,指向精神,但肉体出轨容易洞察,精神出轨隐秘难测;身体上清洁容易,精神上还原不易。齐有生、臧小林、小米等人希望借助于宗教来实现拯救,这个选择本身就凸显了拯救的困境。拯救的难度还在于,它自身往往构成一个陷阱。齐有生也曾一度怀疑自己探究“真相”的意义,因为在很多情形下,“真相即污秽,真实即耻辱”。当他以上帝的名义来要求臧小林彻底清洁自我时,拯救就变成了一个循环往复且无限延伸的陷阱。这里面的一个悖论在于:谁能拯救以拯救者面目出现的“现代撒旦”,如果他不能自我拯救的话。问题还在于,当背叛、隐瞒与欺骗成为一种普遍性行径并从个人、集体上升到时代文化的范畴,拯救何以成为可能?
如果不能在宗教层面理解臧小林与齐有生向死而生的意义,拯救的代价不过是死亡与牺牲。在小说尾端,文本的叙事节奏突然冷静下来,在激愤、挣扎、撕裂、狂躁、暴虐之后,一种含混着悲凉、疲倦的气息弥散开来。齐有生曾对沈慧说:“做不了牺牲,就做愚人。”沈慧的结论是“你只有把自己弄得面目可憎、滑稽可笑、含含混混,才能够含含混混地活下去”。我宁愿相信,许建平的不知情是一种假装,生命尚存的许建平、老冯、沈慧或许都代表了齐有生自我拯救的可能性。读者尚需判断:在齐有生、臧小林的向死而生,老冯最终的隐忍宽谅,许建平的不知情,沈慧的“含含混混”过活等多种情形之间,我们到底倾向于哪一种选择?每一种情形都隐含有向死而生的意味,又都伴生着那种难以祛除的不确定性。在他们向死而生的路上,吕志青埋下了隐患与忧伤。
三、 结构的三种元素
吕志青在关于《黑屋子》的创作谈中指出自己对毕加索关于心灵图景的说法情有独钟,“具体说到我的写作,我希望在我的小说的内里,在其结构上,显示出一种隐喻性;而在其局部,在整个叙述的表面,则希望尽可能地靠近生活的外表,甚至是非虚构的外表”。这提供了进入小说文本结构的阐释路径。在我看来,《黑屋子》的结构性元素主要有三个方面:人物、《圣经》、黑屋子。三者绾结纠缠,构成一种多线条、多声部、多层面的复调结构。
其一,从人物上看,齐有生与臧小林之间的故事构成一条主线,许建平、老冯、老费与妻子、情人之间的故事则成为副线,主副线既总体平行又有所交叉;在众多人物中,齐有生和藏小林成为主要声部,其他人物则成为次级声部。小说由此获得了一种多线条、多声部的结构特征。
人物始终是小说的灵魂,《黑屋子》的灵魂就是齐有生。《庄子·齐物论》有云:“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这或许就是“齐有生”名字的出处。齐有生有这样一层觉悟:“他们每一个,包括老汤、老柴,都像是他的一个侧面或者一种可能,反过来说多半也是一样。他是一棵树,他们就是他的枝丫。同时,他也是别人的枝丫。枝丫间当然有近有远。”由此,我们可以窥见小说的命名意图:齐有生具有生命总体的特征,许建平、厉大凯、老冯、老汤、老费、老穆、老柴、小朱、沈慧等则是其生命形态的各个侧面。上述诸人在不同程度上参与到关于通奸、乱伦、爬灰、换妻、同性恋、艾滋病等问题的讨论中,他们的见解总体上丰富了齐有生的思想世界。
老费尸沉江底,因道士作法乃得以从江底腾身而起,又或者他在下水之前早就死了,出现在人们面前的老费不过是一具躯壳罢了。这是小说叙事链条中极为荒诞的地方。或许在吕志青看来,当现实充满谎言、背叛与死亡时,谵妄之言就产生了“真实”的意义。换一个角度看,臧小林在其自杀之前早已死去。老汤只是行尸走肉,老穆还在等死。当齐有生平静地对儿子说要杀死他的时候,齐有生自己也早已死了。几乎所有人都已经丧心病狂,都在已死半死将死之间。小说两次写到同一个细节:老费身上只剩下短裤衩和脖子上的一条红领带,该如何理解这个细节呢?短裤衩是用以遮羞的最后物件,红领带则是一种被勒索的符号,指向社会制度、文化、心理结构,是我们无力解脱的具有体制性特征的象征物。小说这一情节的意图或许就在于:在剥去我们的外衣之后,我们只剩下混乱的性与由体制带来的身份属性,两者媾和于赤裸的身体之上,即为通奸之表象。
再看厉大凯。小说在开端从茶余饭后的通奸故事出发,引出关于忠贞、诚实、背叛、绝对与相对的话题。小说借厉大凯之口指出:当今人们的爱情和婚姻,差不多只剩下了两种形式:“要么生活在由谎言和欺骗编织起来的虚假的幸福中,要么是陷在谎言和欺骗被揭穿后的真实的痛苦里。”可见,作者从一开始就设定了谎言与幸福、真实与痛苦之间的悖论,齐有生、臧小林的故事就是对这一悖论的展开。小说还借厉大凯说出:文化本来是一种元气充沛的精神创造,但现在文化的生命与灵性被杀死、肢解,“除了一堆零杂碎,什么也不剩了”。“事情已经迫在眉睫,森林黑暗,已从三面包围过来,泥沼,恶臭,应有尽有。怨忿,仇恨,越积越多的暴戾之气;懦怯,战栗,沉思,发愁,牢骚越积越多,心灵比身体更困乏。被黑暗囚禁的人无法不渺小。”厉大凯还指出,这世上最重要的学问是心灵学,这个说法为我们指明了一条理解黑屋子的路径。
再看老冯。小说借助老冯的观点,批驳了时下中国那种半身不遂的自由主义,认为它经过扭曲变形已简化为一种赤裸裸的荷尔蒙,成了一种萎靡不振、下流无耻的东西,它带来的不是生机,而是死气沉沉的腐败和腐朽,道德上的羞耻,美学上的羞涩,正一并失去。人们竞相堕落,竞相成为一种没有生命、没有灵魂的非实体的存在,成为一种早已死在罪中的人。小说最后借老冯之口指出:在我们这代人身上,多少都带着这种可怕的东西,比如触及灵魂这个词,我们固执地寻找真相,而忽略了我们自身的残缺与凶残,“伤我们最深的,正是我们最热爱的。主义,女人,都是如此”。这里或涉及20世纪中国知识界的文化人格问题,小说因此将悬置在精神层面的黑屋子赋予一种历史的、在场的属性。
所有人物既具有独立性,也都服务于齐有生,都在其敲打真相的进程中各尽其职。臧小林对于齐有生而言,就是作为敲打对象和照见其生命的黑暗处另一种“真相”的镜子而设定,与许建平、老费、老汤、老冯等人相比,臧小林的身份设置决定了她是齐有生之外唯一不可替代的人物,是齐有生走入黑屋子的必然途径。臧小林与齐有生的表亲身份,带来了爱情与婚姻的难度,她背叛、隐瞒与欺骗22年的事实则与这种难度构成一种反讽,这种反讽加重了人际关系失真与道德失范的危机,这也使得其后的拯救行为更见残忍与悲剧性。在齐有生和臧小林之间,自始至终贯穿着一种对抗与妥协交替出现的对话;而在许建平、厉大凯、老冯、老汤、老费、老穆、老柴、小朱、沈慧等人那里,则是一种多种声音混杂在一起的价值喧哗。如果说前者是两个主要的歌咏者,后者就是一个小歌队。如果前者是一件主乐器,后者就是一个小乐队。二者交织成一部隐含矛盾冲突的混声合唱或者一部协奏曲。
其二,《圣经》既提供自我拯救的场所,也提供拯救的逻辑链条。如果《圣经》仅仅提供一种教义而形成一种批判并最终导引一种皈依的力量,这样的写作就是无效的,至少是了无新意的;它就成为一种可有可无的附会,并带来作品整体结构的支离破碎。果真如此吗?首先,《圣经》在叙事链条上的功能很值得注意。在《圣经》中,通奸是一项重罪;在律法时代,犯了奸淫的人必遭受严酷的惩戒,即为涤罪。在《黑屋子》中,作为中心事件的起始,通奸的出现,为基督教的出场、在场,提供了充分的逻辑。
如前所言,齐有生借助于《圣经》确立了自己作为受害者与拯救者的双重身份,随着在拯救陷阱中越陷越深,他逐步僭越而成为一种隐形的上帝——“现代撒旦”。可见,对于齐有生而言,宗教并没有成为一种拯救性力量并带来最后的皈依,小说更着眼于它在功能上提供一种批判与审视的镜像,一种话语。实际上,在相当程度上,齐有生只是需要上帝这面镜子,照见臧小林与自己幽深、阴暗的角落,这种照见又产生了进一步敲打的空间与路径。二者之间也是一种悖论。伴随着齐有生对“真相”的持续追问、追溯、追究,一场赎罪行为逐步变成了惩罚和折磨,并最终走向了并未带来新生的死亡。
《圣经》还提供了从个体到时代的“原罪”视阈。按照现代观念,齐有生与臧小林的近亲结合从一开始就是乱伦行为,作为这一行为的结果,他们的女儿未能成活,儿子一出生就有着忧郁的眼神,从他幽深晦暗的瞳孔中,齐有生常常看见那个夭折的小女孩:小小的一个女孩,坐在一眼枯井底下,仰面朝上,等着谁来搭救,眼神忧郁无望。这实际上已经提出了关于原罪的救赎命题。问题还在于,小说中的原罪不仅为每一个个体所负载,还隐秘地指向了历史文化的深处。小说重复出现了所谓“敌基督”的说法:利用基督反基督,这种重复叙事强化渲染了“现代撒旦”惯用的伎俩。恰恰是《圣经》照见了吕志青的人间情怀:作为起点的个人拯救,指向了我们终将面对的时代的、集体的原罪及其拯救。
其三,黑屋子意象既在一个总体象征的层面统摄全篇,又贯穿小说的叙事链条。这是小说结构艺术的与众不同之处。关于这一点,吕志青强调说:黑屋子不只是作为一个意象出现在文本中,它还担负有结构上的功能。在小说叙事链条中,黑屋子是贯穿始终的中心意象,齐、臧故事作为主干按历时时序步步推进,其他部分作为另一条线索则以碎片化的方式进入,二者联结于黑屋子。这种联结,既有表面的,即结构上的联结,又有内在的,即精神上的联结。从结构上看,从旧友相聚引出“黑屋子”话题,到找寻、建造、体验黑屋子,黑屋子始终是小说叙事链条上的关键环节;从精神上看,从物质意义上的黑屋子到个体精神中的黑屋子,再到时代文化结构中的黑屋子,这一核心意象的内涵与外延在不断滋生裂变,这就提供了精神意义上的隐秘线索。这两条线索,表里相依,共同结构了小说文本。
从《南京在哪里》开始,吕志青逐步养成了一种从现实喧嚣烦扰的细节不动声色地进入历史、文化结构的能力。《黑屋子》在写法上延续了这种细致绵密的“织锦法”,但更为复杂精密。正是因为上述三个层面的结构功能,小说形成了一种多线条、多声部、多层面的复调结构,看起来喧哗、分裂、对峙、错位的各种元素,最终被巧妙地绾结在一起。这种结构方法在当代文坛上,若非绝无仅有,也极为罕见。
四、 黑屋子的前世今生
回到黑屋子这一中心意象。几乎在接触这部小说的一刹那,我想到了它与梁启超、鲁迅等人的精神联系。

比较而言,吕志青的黑屋子既在形而下层面接近梁启超,又在形而上层面靠近鲁迅,它表明了吕志青的传统与个人才能。每个人都有一个黑屋子,大家又共处于一个巨大无形的黑屋子之中。吕志青的贡献在于重新赋予黑屋子以黑色的时代文化元素,这个问题涉及中国当代写作进程中的黑色光谱。与“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中的红色光谱不同,新时期文学开始更多探索红色光谱之外的可能维度,黑色光谱慢慢浮出历史地表,它首先集中地出现在朦胧诗群的创作中。顾城曾出版诗集《黑眼睛》,他的《一代人》诗云:“黑夜给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北岛的诗作也充满了黑色元素,许多作品直接以黑夜、夜色以及某些混沌难辨、暗色调的元素为意象和色彩,其中“夜”的意象就出现在近60首诗中。在《黑屋子》出现问世之前,吕志青写作了小说《黑影》《黑暗中的帽子》等,彰显了他对黑色元素的兴趣。
吕志青笔下的黑屋子有三种形态。首先是自然形态的黑屋子。黑屋子的原型最早出现于许建平的儿童记忆,小说由此牵引出黑屋子这一中心意象:在川湘鄂西交界的地方,某个偏僻的村子里,一个老祠堂的后面,紧靠背后的院墙,有一间不太大的小石屋,从前专门用来拘禁犯了奸淫的男女。这个黑屋子虽然被人扒掉了,但是,黑屋子勘察队伍还是找到了另一所关着一个女精神病患者的小石屋。其后厉大凯等人更是筹划设计了一间与世隔绝的让人体验拘禁的黑屋子。这都是自然形态的黑屋子。
精神形态的黑屋子则存在于每一个个体的内心。为什么一个曾经关押过女人的黑屋子引起了所有人的兴趣,又为何那么多人排队去体验黑屋子,因为人人心中都有一个黑屋子!柳洁如、臧小林都藏在自己的小黑屋里。齐有生带着臧小林去实地勘探,或许就是为了“占领那被她隐藏起来的黑暗区域”,伴随着勘探进展,齐有生也的确进入了“前所不知的黑暗区域”。齐有生认为臧小林无法安宁,是因为她怀揣“灵魂中的黑暗秘密”,而这些秘密是阴暗、阴森的。齐有生与藏小林只是两个彼此熟悉的陌生人,孙则是在阴暗中损害他侮辱他的人。齐有生与臧小林的第一个孩子背上了近亲繁殖的恶果,交由医生处理:回到其由来之处——无边的黑暗里。教堂里的十字架有着黑暗的底子,牧师的声音总是如同从遥远的暗夜深处传来。齐有生的无数的念头总是从黑暗中迸出来。肮脏的、湿淋淋的地老鼠总是生活在阴沟里。厉大凯认为当今男女情爱关系就像一个黑暗的森林。老费之死不过是被带入了一个广大无边、永沉黑暗的黑屋子。齐有生从小黑屋里走出来时,他记起了脑海中的一幅画:商场的大厅,来来往往的顾客,地板下立着死人、幽灵。要到其中一块方格地板突然从哪里掀开,他们才会发现,他们一直是与死人和幽灵共生共处在同一世界。齐有生由此觉悟:每个人都有另一个自我,藏于地下,藏于黑暗,藏于一间小黑屋,一直为他们所不知。
小说告诉我们,世界是阴暗的,黑屋子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在自然的、精神的层面之外,还有一层与时代文化相关的黑屋子。齐有生在敲打臧小林之始,曾有过一个噩梦:一个陌生男子站在一幢老宅的后门口,和他谈着鬼魂和鬼城。小说借这个陌生男子之口指出,所谓“鬼城”,不是丰都,而是“一般意义上的鬼城”,这令齐有生疑惑不解:这世界原本就是一个鬼域、鬼城?到处鬼影幢幢,没一点真实气息?从噩梦中醒来的齐有生突然意识到:这世界不重要,宇宙不重要;国家、政党、民主、自由,这些大字眼,全不重要;对你唯一重要的,只是那么一小点东西,如豆芥之微,那是人境与鬼域的区别。这个梦就点出了黑屋子的另一种面向。小说总是在有意无意之间通过笔下人物的对话与思考来点击现实,从而实现自然的、精神的、文化的三重黑屋子之间的沟通链接。

五、 结语

这正是《黑屋子》的价值所在:在不失却先锋姿态的同时,保持一定的对现实的热度。其隐喻指向,不仅仅是一种形而上的存在主义精神图景,也包含了更为丰富、复杂乃至于暧昧的当代中国图景。本来老生常谈的话题被小说赋予新的内涵:肉体的与精神的、个体的与群体的、现实的与抽象的、世俗的与宗教的、民族的与世界的。种种元素融会贯通其中,这让小说文本产生了沉重的力量。黑屋子触及了这个民族及其每一个个体的隐秘世界,它带来了普遍的隐痛,实际上,隐痛就一直在那里。现在吕志青以其看似波澜不惊而绵密有致的文字改写了黑屋子的光谱,提出了拯救陷阱这一时代命题,让我们深陷其中。

注释
:①吕志青:《关于〈黑屋子〉(创作谈)》,《钟山》微信平台2016年5月10日。
②吕志青:《〈黑屋子〉赘语》。
③吕志青:《〈黑屋子〉赘语》。
④吕志青:《关于〈黑屋子〉(创作谈)》,《钟山》微信平台2016年5月10日。
⑤吕志青在《关于〈黑屋子〉(创作谈)》中谈及:“刚刚完成的这部小说,感觉它在结构上也有点像是一支协奏曲:一件主奏乐器,加上一个小乐队;或者,一男一女两个歌唱者,后面站着合唱队;它们融合在一个共同的主题中。”《钟山》微信平台2016年5月10日。
⑥吕志青:《黑屋子》,《钟山》2016年第3期。
⑦吕志青:《黑屋子》,《钟山》2016年第3期。
⑧吕志青:《黑屋子》,《钟山》2016年第3期。
⑨吕志青:《黑屋子》,《钟山》2016年第3期。
⑩笔者在思考与写作过程中曾与吕志青本人有过数次对话,此处关于黑屋子的结构功能的观点,主要来自吕志青本人在对话过程中的相关陈述。特此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