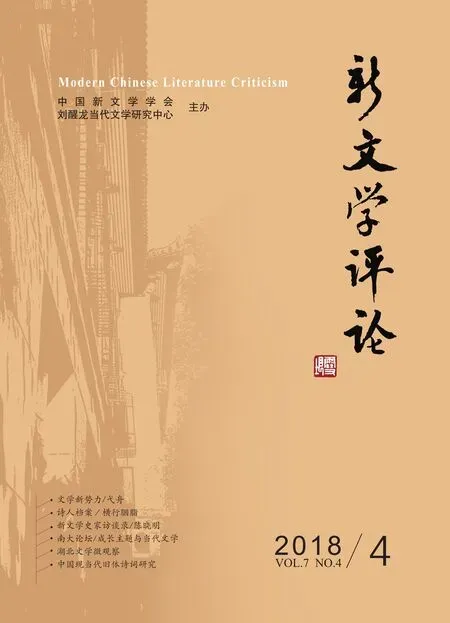生命召唤、乡土栖居与写作在场
———论刘益善文学创作的意义
2018-11-13李俊国
◆ 谭 华 李俊国
近代学者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序》中说:“凡一代之有一代之文学。”刘益善以近半个世纪的创作实践,六百余万字的文学产量,诗歌、小说、散文等题材的全面参与,集诗人、小说家与编辑等于一身的经历,成为“一代之文学”(中国乡土文学)的典范和标本。刘益善的文学创作总体属于乡土文学。文学创作的冲动,文学梦想的构建以及对现代人的基本价值的呼唤与坚守,召唤他回到乡土,“面向事物本身”,成为乡土、乡村和乡民的“译作者”。在诗意的栖居中,故乡风景得以展开。在他的操心下,民族的秘史、经验的日常、接地气的风俗等纷纷现身。在“小而精,实而韵”的写作中,油然升起“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的怀乡情感,由此生发出带有现代性震荡感的原乡情结。在文学梦想的召唤下,在“三乡”(现实的故乡、情感的故乡、精神的故乡)大地的栖居中,作家通过作品人物在场性、作家感知在场性、作家精神在场性,开启了写作的在场性。
一、生命召唤:梦的召唤、往日的召唤、思想的召唤
从现象学哲学而言,“召唤”一词是海德格尔经常使用的一个大词。它是唤起此在现身世界之中的呼声。米兰·昆德拉将此词运用于小说的诠释。在《小说的艺术》中,米兰·昆德拉将“召唤”作为勘探小说内在逻辑的方式。他将召唤分为四个层次:游戏的召唤、梦的召唤、思想的召唤和时间的召唤。本文借用米兰·昆德拉的理论,意在把握作家创作动机的内在逻辑及其与文本的关系。
“召唤”在文艺学上相当于创作动机,它是一个古典文艺美学的问题,也是一个现代文艺心理学的问题。米兰·昆德拉认为小说是“梦与真实的混合”,“是使想象爆发的地方”。雨果认为“理想是艺术的动力”。弗洛伊德则认为创作家的创作动机来自“白日梦”。梦的召唤是刘益善进行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动机。这种创作动机的形成与他的作家梦有关。刘益善从小就有当作家的梦想。“小时候我除了爱听祖父讲故事外,还喜欢听说书艺人讲评书。”上小学六年级时,老师对他作文的表扬激励了他,也培植了他。“那时(初中时期),我梦想着将来能当个大作家。今天,这个梦还没有醒呢。”“文革”开始了,他“回乡当了农民,除了种田,我还当过民办教师,由于我喜欢文艺,还为大队文艺宣传队写过快板、唱词、对口词、渔鼓、道情等”。1969年,他便开始发表文学作品。后来在工农兵推荐上大学时,他被推荐到华中师范学院生物系。由于他文笔不错,有幸改进梦寐以求的中文系。作家梦就像“前面的声音”一直在召唤他向前走。相较于中国其他作家,刘益善的作家梦持续而热烈,“激情”而又“迷狂”,近似尼采的“超人”意志,福柯的“疯癫”文明,巴赫金的“狂欢”精神。其精神烈度、生命厚度和欲望强度不仅标识出中国乡土写作的精神特征,也标识出中国许多作家对文学的热情。
“往日的召唤”是作家的另一创作动机。强烈的作家梦,激发了创作愿望,创作愿望在“现在”又唤起了他对往日经验的回忆。文学创作便因对“最近诱发性的事件和旧事的回忆”而引发。在刘益善的作品中,“最近诱发性的事件和旧事的回忆”留下的痕迹随处可见。金水河畔,两年农民生活,“写成了组诗《我忆念的山村》”(刘益善《〈我忆念的山村〉后记》);西部的游历、长江边上的生长、乡村的生活汇聚成《三色土》;向警予烈士在武汉牺牲五十一周年激发出传记体抒情长诗《向警予之歌》;有感于毒品的泛滥,作家创作了《吸毒者》。刘益善的创作就像“白日梦”激发创作家一样,是“最近诱发性的事件”的记录,是“旧事的回忆”的“替代品”,“是往昔之井的启发与命令的结果”。书写记忆可以说是乡土写作的常规和套路。但中国一些作家由于乡土生活经历单薄,写作完全被套路所拘,反而失去了章法。湖北的乡土文学向来有一个特点:看似无套路,其实有章法。现代文学时期的废名,当下的刘益善、晓苏等都擅长“以小取胜”。小而多、小而精、小而有韵不仅是他们的写作特征,也应该成为中国乡土写作的标准。
召唤刘益善进行文学创作的还有一个重要动机——思想。米兰·昆德拉认为“思想的召唤”使小说成为“精神的最高综合”。汪曾祺也认为“小说里最重要的”是“思想”。刘益善文学创作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通过他的创作,我们不难发现他对思想的强调与重视,对人性的思考与表达。他为人民代言,为农民代言,为弱者代言。他关注留守儿童,关心农民工、“失足妇女”、“犯罪青年”、“吸毒者”,提携文学青年,“不赶热闹”,“不作秀”。他的作品往往蕴含着思想内涵和内在精神。他的小说往往在“讲述一个故事”,“描写一个故事”中“思考一个故事”,“讲述一种道理”。《国道边的人家》讲述了从20世纪50年代土地改革到80年代的分田到户,农村土地几易其主的历史,思考其间乡村历史与乡民人性的荒诞性。《一枝梅》则从一个女人的历史,思考拯救与复仇、“规训与惩罚”、“爱欲与文明”、真相与历史的关系。

二、 乡土栖居:故乡、怀乡、原乡




虽然卡夫卡说,比如现在,人的根早已从土地里拔了出去,人们却在谈论故乡,但刘益善以扎实的生活基础,炽热的故乡情感,浓郁的家国情怀,执着的文学梦想,对故乡历史现实的全方位书写显示了乡土文学的创作实绩,成为区别一般乡土写作的典型特征。
三、写作在场:人物在场性、作家感知在场性、作家精神在场性




作家精神在场性还体现为写作主体对“共名”的社会现象、事件等做出迅速反应,产生个体“共鸣”,继而用文学创作对此加以呈现。比如作家对过度包装、假钱泛滥、农村留守儿童、分田到户后成分取消、乡镇企业贪腐等“共名”的时代问题产生过“共鸣”。这类作品往往通过作家自我的声音在文本中的呈现,作家思想价值观念在文本中的凸显,显示作家精神的在场。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正是市场经济东风劲吹的时候,“别一种生财之道”弥漫社会。针对这种“共名”的社会现象,作家将生命的眷注转化成写作的冲动,创作了《1994年的标底》。小说写一乡村建筑队为拿下乡镇建筑工程,偷拍拍卖人二乡长的奸情,以此作为要挟,靠不正当竞争,成功中标。诗歌《历史的公正结论》是作家对天安门事件平反、抓捕江青反革命集团等重大历史事件做出的快速反应,传达出“拥护、欢呼、赞成”的时代主旋律。作家精神在场性不仅仅在于作家的“共鸣”,还在于作家的文学发现。精神在场若只止于“共鸣”,那么其创作则有做时代留声机之嫌。优秀的作家,其精神在场总伴随着文学发现。文学性和它们之间构成了“一体两翼”关系。阅读这类作品,读者不仅有身临其境之感,而且会获得“教谕”。比如中篇小说《远湖》,作家将自我的温爱、关切、思索熔铸在故乡的“秘史”与现实里,打捞出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一段段多元的人生,一部部多义的历史,一片片荒芜的风景。吃喝嫖赌的劁猪佬肆意欺凌被后爹所卖的弱女子,勤劳和善的王家三兄弟谦让媳妇,因换亲所迫一对情侣不得不劳燕分飞后又终成眷属,“响当当的贫农一夜间变成坏人”,地主分子刘老五也是有情有义、勤劳善良的人,历史也有为民除害与谋杀并存的悖论,生趣盎然的远湖如今成为一片被修饰过的土地。
写作在场性是刘益善文学创作区别于一般乡土写作的“元叙事”。它不是“制作的美丽”,不是“二道贩子”的“叫卖”,而是作家的“硬功夫”。写作在场不仅反映了作家扎实的乡土生活基础,而且彰显出作家对于复杂的社会现象看似拙朴、实则机智的智性驾驭能力。

注释
:①李俊国:《小说之“小”:刘益善小说的“微叙事”》,《新文学评论》2015年第1期。
②米兰·昆德拉著,孟湄译:《小说的艺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14~15页。
③米兰·昆德拉著,孟湄译:《小说的艺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14页。
④伍蠡甫、胡经之:《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莎士比亚论》(中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43页。
⑤刘益善、傅炯业:《乡村生活与文学情结——刘益善访谈录》,《语文教学与研究》2002年第14期。
⑥刘益善:《刘益善文集·散文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98页。
⑦刘益善、傅炯业:《乡村生活与文学情结——刘益善访谈录》,《语文教学与研究》2002年第14期。
⑧米兰·昆德拉著,余中先译:《被背叛的遗嘱·纪念斯特拉文斯基即席之作》,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版,第61页。
⑨伍蠡甫、胡经之:《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创作家与白日梦(弗洛伊德)》(下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8页。
⑩米兰·昆德拉著,余中先译:《被背叛的遗嘱·巴奴日不再引人发笑之日》,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版,第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