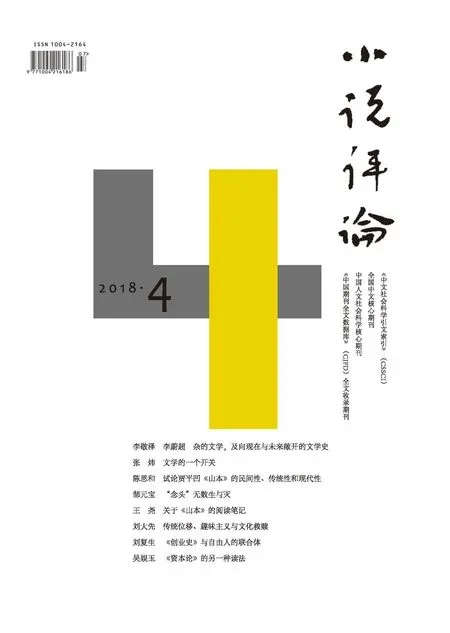《山本》的死亡叙事及其文学史意义
2018-11-13韩蕊
韩 蕊
《山本》阅读时冲击力最大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其中的死亡场景,文本一反常态——作家一贯的创作常态和中国小说的审美常态,超细致书写了整个当代文学都极少见的如此大量、如此多样又如此无意义的死亡。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死亡已经成为这部小说的叙事方式甚至终极目的。作家就是要用死亡定位人生的意义,也用书写这众多死亡时内蕴深厚的云淡风轻来表达对于那个时代的憎恶和对于生命的热爱。
一、无意义的死亡与多功能的叙事
《山本》中所有人都命如草芥,生存脆弱,就像秦岭山上的花草树木,在大自然的风霜雪露中生长死亡,外来的祸患在生存个体毫不知情的情形下没有任何预兆地突然到来,而相对于摧毁树木植物的灭顶天灾,老百姓遭遇的却是人祸,身处弱境的山民自在状态的生命顷刻间的消亡显得愈加惨烈。
《山本》的结局,除了陆菊人、宽展、陈先生、蚯蚓和剰剩等涡镇中日常生存状态最柔弱者,几乎所有的人都死了。无论是叱咤风云喧嚣一时的各路英雄枭雄、有名没名的士兵土匪,还是有钱的财东掌柜,抑或普通的镇民山民,都在这几年间死于非命,乱世之中寿终正寝已是奢望。而在对这众多死亡的描述中,作家写得几不重样又合情合理,为财死,因仇亡,遭灭口,遇误杀,受连累,挨惩罚,作战死,带冤死……刻意书写这种种死亡的背后是作家独特的哲学思考和深厚的情感寄托。
核心人物井宗臣在游击队内部斗争中遭陷害被自己人欺骗打死摔下悬崖,井宗秀被不知名凶手刺杀。主要人物也是预备团主要成员杨钟大腿中枪失血过多而亡,陈来祥搬运大钟因成员一个屁大家失手被铁钟压死,参谋长蔡太运生病被俘虏医生打针害死,保安队长史三海得性病又被捏碎生殖器刀捅而亡,井宗秀的美人计一石两鸟,使五雷被手下王魁打死割掉生殖器,王魁被打入粪窖子后割头。战场上死亡最多是简单中枪的,还有炸药炸死的,泥石流淤埋的。如果被俘虏,死法更惨酷,游击队长程国良被抠眼割舌割喉后枪杀,游击队员绑树上让豺狗吃肠子鹰啄眼,三位姓周的队员被铡死,红军战士被吊死,两名保安队员被活砌在城墙里,五个预备团员死后还被锯脖子。
俗话说“扛枪吃粮”,大部分士兵当初当兵是为了生存盲目地跟从,因为参加得草率又缺乏明确的信念,各个队伍里的动摇分子便不少。“什么国军呀土匪呀刀客逛山游击队呀,还不是一样?这世道就靠闹哩,看谁能闹大!”“当红军当逛山,还是他蒋介石的兵冯玉祥的兵,谁不是为了吃饭!”对于普通山民而言,进政府保安团、作逛山土匪或参加游击队区别不大,都是为糊口而扛枪。正义邪恶敌我双方没有区别,稍有风吹草动,或是生命受到威胁或是面对利益诱惑,便极容易倒戈。红军与土匪联合行动,却有二十七名战士反水了。对于叛徒的惩罚历来是最严厉的,冉双全叛变预备团被枪杀,邢瞎子因害井宗臣被剐,叛徒三猫被剥皮蒙鼓,宗秀媳妇偷情被谋杀而掉进井里,薛宝宝叛变与怀孕的媳妇一起被报仇的游击队员枪杀……问题是看到这种本应“大快人心”的复仇结果,读者没有丝毫的阅读快感,反添不少感慨和唏嘘,正如文本中的陆菊人也忍不住劝说井宗秀的不可过于残忍。
城池失火殃及池鱼,更多的无辜山民镇民也遭非命。莫郎中给人治病因误解而被枪杀,茶行崔掌柜咬舌自尽尸体被扔入河里,山民逃跑坠绳下崖被砍断绳索摔死,杜英逃跑途中遭蛇咬而死,井宗秀小姨子被掐死,孙举来被推入水潭灭口,唐建为父报仇够不到阮天宝便砍死阮父吓死阮母,自己被讥性无能而上吊,吴掌柜家遭土匪抢空气得吐血而亡,岳掌柜遭土匪绑票家人不赎被石头砸死,井掌柜掉进粪尿窖子淹死,李掌柜因儿子被杀而自残跳城墙自裁,杨掌柜被风吹断的柏树压死,大量镇民被传染霍乱病死,被最后的攻打涡镇的炮声炸死震死。相较于前面的争斗和仇杀,这些生命的逝去更是令人唏嘘不已。
预备团最初成立是为了防御土匪抢劫,保护涡镇安全,也算是子弟兵。镇民当时是一片拥护,但接下来的纳钱纳粮又使老百姓苦不堪言,队伍纪律涣散渐渐地也发生了与土匪类似的扰民事件,甚至反而危害镇上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兵匪几乎没有了区别。事情的发展并没有按照镇民所期许的那样,当权者为自己的名利争斗,特别是与保安队为敌并开始作战时,预备团完全偏离了成立时的初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双方名义上都是保老百姓安全,但都给老百姓带来灭顶之灾。故事讲述近一半时,杨钟攻打保安队时战死,杨掌柜慨叹“唉,只说有了预备团涡镇就安生了,却没想到死了这么多人!人死不起呀,再不敢死人了啊!”却不知死人只是刚刚开始。
秦岭山中争斗的各方面力量均谈不上是与非,红军和游击队亲民性上好一些,但初期的队伍也并不纯粹,极易被山民们与保安队、预备团、土匪逛山等混为一团。从预备团到保安队再到游击队,阮天宝走过的路就极具典型性,私利使昨天还是并肩作战的战友,今天就成了刀枪相向的敌人,对战斗力的急需和审查制度的缺乏又使曾经的敌人转眼变成了同志。于是个人恩怨与团体目标纠结在一起,最终酿成公报私仇的惨烈结局。阮天宝利用游击队内部斗争陷害井宗臣,置之死地而后快,似乎终究是血浓于水,预备团不仅让道放井宗臣部队通过,与其相约打假仗,井宗秀最后还为游击队的兄长保了仇,红军则最后攻打预备团的炮轰涡镇,总之,秦岭里打成了一锅粥!正义与邪恶只在一念之间,善良与残忍并存于一人之身,哪一方是正确的?谁又是没有一点错误的?结果不是甲战胜乙,也不是正义战胜邪恶,是两败倶伤,杀人,被杀,被敌人杀,被自己人杀,杀人者和被杀者角色迅速转换,最终一切归于尘土。从文本故事内容的最后结局看,所有人的死亡基本上都是无意义的。
然而,从《山本》的整个叙事结构看,死亡成为贯穿全文的一条主线,对情节发展具有重要的推进功能。正是因为被土匪祸害,才成立预备团,于是交战死人,复仇死更多的人,往复循环,除了作家有意留下的陆菊人等几个艺术形象之外,几乎所有的人物出现就是为了完成各自最后死亡的使命与结局。每个人的死法也成为塑造其个性的必不可少的手段,如井宗臣的沉痛,井宗秀的反讽,程国良的悲壮,陈来祥的黑色幽默,杨掌柜的厚重,史三海的恶毒等等;更是作家表达全书创作意图不可或缺的叙事方法,地主周财东被长工灌煎油,长工又被保安队七八个刺刀戳死,这些已经不仅仅是肉体消灭,而是变态地虐杀,杀人不是目的,宣泄私愤引起他人恐惧,以震慑后来者似乎才是需要的效果。《山本》里种种鲜血淋漓血肉横飞泯灭人性目不忍视的场景比比皆是,什么使人如此凶残?是人性本恶还是社会环境抑或生存地位造就?
二、死亡苦难与生存批判
中华民族历来有“重生轻死”的传统,大多数人一面赞赏“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英雄风骨,一面借口“好死不如赖活着”而苟安于乱世。死亡在中国是讳莫如深避之唯恐不及的沉重话题,有各种回避“死”的代称,文雅的如崩、薨、仙逝、殁了等,近代以来正面人物用“逝世”“牺牲”,幽默者用“见马克思了”,民间常用“去世”“过世”“老了”“走了”“上山”“入土”“驾鹤西游”等词汇代替。在今天安乐死也还只是为少数人能够接受,哪怕明知结果是植物人,亲人也要倾尽全力抢救,这些无不是出于对生的极度渴望。人们以死于家中床上为幸事,夭亡横祸是不正常不吉利的,死在外边的人不允许进村停放等无不表现出对于死亡的忌讳。人们也以夺取他人生命为终极惩罚方式,俗话说杀人不过头点地,但千刀万剐等各种酷刑自古有之,开棺鞭尸挫骨扬灰则是泄愤到极致了,还带有对于死者遗属及家族的侮辱。
从某种意义上说,《山本》就是写人如何死的,是一种极端的残酷体验。死亡如驱散不尽的雾霾一样漂浮在秦岭山间,阅读时便如鲠在喉艰于呼吸,而贯穿全文的黑色便是作家表现死亡最集中的审美意象,也是读者产生压抑感的重要缘由。黑色的美学意味是肃杀、寒冷、阴暗、神秘、恐惧,与死亡有千丝万缕的对应关系;死亡最能显示人性中黑暗的一面,它如黑夜一般,既囊括一切又了无一物,是睡过去便不再醒来。秦人尚黑,《汉书·郊祀志上》中曾有这样的记载:“今秦变周,水德之时。昔文公出猎,获黑龙。此其水德之瑞。”而五行之中水德对应的标志颜色正是黑色。秦人又认为祖先是“女修吞卵”而生,即颛顼的孙女吞玄鸟蛋而生秦的先祖大业,秦人便尊崇玄色,所以秦国从春秋战国一直到一统天下都崇尚黑色。宫廷多用黑色,老百姓更喜欢黑色衣服,手织粗布染料简单,干活耐脏不易退色。涡镇就是如此,文本一开篇就交待镇名来自黑河和白河的交汇,街巷上所有的木板门面都刷成黑颜色,与其相配的树皮也是黑的,猪狗都是黑的,鸡也是乌鸡,乌到鸡骨头都是黑的;预备团装备是黑旗黑衣黑裤黑裹腿,夜线子应该念黑线子,护送首长走的是黑沟,一阵刮黑风,碰到一条黑蛇,吃的黑熊掌,茶行经营黑茶而盈利,陆菊人养的是黑猫,还有涡镇之魂的黑色皂角树等等,黑色意象促成了整个文本的沉重、压抑与肃杀感,若没有麻县长的秦岭动植物志做调剂来舒缓节奏,满目的黑色真要使小说难以卒读了。
民间有云“死者为大”,正如《三国演义》里诸葛亮祭奠战争中双方战士的亡灵,《山本》也在庙里设了往生排位对死者进行超度。人在年少时不怕死也极少谈论与死相关的话题,自有远大的前程和饱满的希望充盈眼际,随着岁月的洗礼和阅历的丰富,年长智者便能够看得通透,于是多少沧桑感怀化为一声“天凉好个秋”的长叹。《山本》写的不是战争,充斥文本表层的无意义残酷杀戮背后,是作家深深的悲哀和对正常生活的渴望,读者看到的是表层的杀戮,感受的是其背后作家深深的悲哀。
人文关怀是贾平凹作品一以贯之的情感脉搏。他曾慨叹贫穷使人残忍,《山本》书写如此大量无意义的死亡,更是显现出人穷命贱,其批评的笔触直指民族劣根性。文本借杜鲁成愤慨“涡镇人心咋这烂么!”井宗秀假托阮家浮财给大伙儿分钱时,镇民感觉像是在做梦,感慨“镇上咋只有一个阮天宝啊?!”而当保安队攻打涡镇时,“镇上人自己手打自己脸:这是弄啥哩,保安队来打的是预备团,咱倒是跟着遭殃了?!他们怨恨起井宗秀不该去县城抢枪不该烧阮家房杀阮家人啊!”其功利、自私、贪婪可见一斑。可恨之人又有其可悲可怜之处,涡镇人一直寄希望于出一个官人罩着他们,陆菊人盼望着“镇上总得有人来主事,县上总得有人来主事,秦岭里总得有人来主事啊!”将自己的人生交到他人的手上便难免被害被杀的命运。漫长的封建社会老百姓没有主体意识,陕西民间歌谣就是典型例子:“好皇上坏皇上总得有个皇上,没皇上这个世上它就乱汪汪;坏婆娘好婆娘总得有个婆娘,没婆娘这个日子它就太恓惶。”天子子民、清官意识可谓是积淀长久的集体无意识,直到今天我们不还是希望有个好领导吗?当井宗秀开始在镇民家门上挂鞭子时,大家将这视为一种荣耀,都盼着赶紧给自家挂,好让女人们去为井宗秀服务。鲁迅曾说“然而自己明知道是奴隶,打熬着,并且不平着,挣扎着,一面‘意图’挣脱以至实行挣脱的,即使暂时失败,还是套上了镣铐罢,他却不过是单单的奴隶。如果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那可简直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对弱者的欺凌和对强者的奴性,矛盾而协和地统一在涡镇人的身上。
作家知识分子的反思与批判精神还集中表现在对于井宗秀的人物刻画上。从开始替父还债的仁义感恩到知晓胭脂地预言后的逐渐膨胀,从对陆菊人倾心尊敬到恼怒不屑,从施美人计消灭五雷到买岳家房地再到救韩掌柜开布庄,初期的聪明心计变成了残忍阴险,谋害妻子、活人砌墙、杀人灭口、剥皮剐刑、特别是每天骑马巡街和挂鞭子,已经完全是君临天下的感觉。最终被刺杀身亡极具反讽意味,英武一世却死得无声无息,毫无壮烈或震撼感,加之尸体停放到庙里后又遭到炮轰,普通肉身的消亡显示出循环往复中的报应不爽和天理昭彰。井宗秀身上有《古炉》中夜霸槽的影子,只是在人性的底层滑得更深更远。《桃花扇》中有一段唱词“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每个人在努力向上的时候,多能律己向善,一旦获得成功拥有地位权利时则容易贪欲丛生,渐渐骄横跋扈,四面树敌,灭亡也就不远了。井宗秀亦是如此,作家的态度也从开始的欣赏认可渐渐转变为批评批判。
实际上,贾平凹关于人类生存的哲学思考早从《古堡》始露端倪,《古炉》渐成体系,至《老生》已臻成熟。张家老大牺牲个人利益带领古堡村致富却被村民无情报复最终入狱,古炉村发生文革并愈演愈烈亦与人性中自私贪婪紧密相关,老唱师串起的四个秦岭故事上演各种人情悲喜,《山本》是《老生》的再现和深化,世事沧桑中人事人生人性立体呈现,人的各种欲望在死亡面前没有正邪之别,敌我难分对错难分,胜者为王似乎成了唯一标准。而且因为故事时空的相对集中,动荡时代人性中的卑劣恰恰表现得最为全面彻底,其中批判思考也更为深邃。涡镇里只有善恶没有对错,只有悲剧没有崇高,底层山民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稍有权利者皆为自己名利争斗,整个镇子就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一片乌烟瘴气。作家心里是有悲哀的,他憎恶那个时代,然而文学作品还是要给人以希望的,正如《古炉》中有狗尿苔杏开善人蚕婆,《山本》里也有陆菊人、宽展、陈先生、蚯蚓和剰剩,相对于那些争斗不已而最终皆是无意义的死者,这些涡镇里看似柔弱的生命,也许正是秦岭山中最顽强的生存群体和对真善美最虔诚的守护者与坚守者,也正是通过他们,作家拨动着我们内心深处最柔软的那根心弦,大秦岭的茫茫苍苍也才有了无尽的美好与生气。
三、死亡叙事的新书写
十七年文学经常写到死亡,特别是革命和战争题材小说。由于文艺政策对作品正面教育意义、积极感情基调及明朗理想色彩的规约与强调,在正义必胜的指导思想下,小说或影视剧中的正面人物多是打不死的,身体多处中弹亦能奇迹般地生还,或是关键时刻有人以身相救。即便是最后的死亡,也称其为牺牲或壮烈牺牲,且这牺牲一定是有意义甚或意义重大的。如《董存瑞》的主人公、《红岩》中的江姐、《红色娘子军》中的洪常青、《英雄儿女》中的王成等等,他们为信仰牺牲生命而在所不惜毫不畏惧,“杀了洪常青,自有后来人”的视死如归,其精神和勇气是超出一般常人的,他们是被尊为革命先烈为我们所敬仰的。而在叙事手法上,小说会用高呼口号等激昂的语句升华其革命精神,电影中则出现乌云翻滚电闪雷鸣松涛阵阵江河奔涌,以烘托人民的哀伤与哀伤后更加坚定浓烈的报仇决心。与之相对的是敌人的死亡则以丑恶事物的消灭为定位,基本上是非个体的面目模糊的丑态百出的,“我代表人民宣判你的死刑”是当时枪毙敌人或叛徒常用的句子。“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是对此时期死亡叙事的最好概括,在具体描述上,则避免对于死亡场景特别是细部的入微描写。
新历史小说很大程度上纠正了十七年过于理想化的偏颇,试图从人性的角度写出有血有肉的英雄和凡人,但其间的分寸很难拿捏。莫言对民间英雄野性原生力量的膜顶崇拜少了些理性控制,苏童有对民间的知性智性反思但多关注个体命运,余华由先锋小说对人性的冷漠怀疑转向脉脉温情的民间认同等等,大多呈现出对个体生命生存与死亡的深度思考,整体格局显得不够宏阔,而且从民间视角切入便极少进行大规模的死亡叙事,也缺少一种全局式的把控。总体来看,此时期关涉到死亡叙事的作品,表达更多的是对底层小人物或蓬勃或坚韧生命的向往与感慨,带有敬佩感、认同感和一线暖意,欠缺的是作家对于生存苦难的理性反思和关怀悲悯。
《山本》的新书写首先表现在死亡叙事呈群体性大格局。死亡在文本写作中居核心地位,既是关照对象,亦是叙事线索。前文提到当代文学中几乎没有哪部小说书写如此之多的死亡,中国人对死亡的态度的避讳,使《山本》面临巨大挑战,极容易因其可以进入限制级的惨烈暴力引起阅读障碍。恰是作家深厚的写作功底和深入的哲学思考化解了这一难题,文本没有就暴力写暴力,说的是死亡,其关节点则在死亡之外,或曰死亡的对立面——生存,所以阅读者会在体会残酷之后不是纠结于鲜血淋漓,而是跟随作家一起进入思考的时空隧道。此外,文本的大体量叙事使得其思考的普遍性意义更为重大和深远,在此基础上的批评和超越性也便呈现出大家风范。场面特别是大场面的书写是小说呈现大气象的主要原因,贾平凹从《古炉》开始用力于场景描写,至《带灯》手法已经全然谙熟,《山本》中大小场面比比皆是,其间人物的须发眉目、言行喜怒、节奏的快慢缓急、气氛的张驰有度,作家信笔写来,读者则如在目前。而场景叙写中最多的便是战斗和死亡,或小分队偷袭,或上百人作战,或惩戒叛徒,或滥杀无辜,作家皆不动神色地实录,各种惨烈景象让人不忍卒读。确非大境界者不能写,若无强定力者不可读。
其次是从人性关怀普世慈悲的角度,一视同仁地写每个生命的逝去。不同于莫言《檀香刑》中以浓墨细描各种酷刑为目的的暴力美学风格,《山本》中的死亡叙事是手段。作家直言“我写的不是战争”,如此众多的死亡场景,无论是大小战斗谋杀暗杀越货强奸,还是酷刑逼供短兵相接,抑或天降厄运亲人反目,面对涡镇人的各种死亡,作者的态度似乎无褒无贬不左不右,呈现出超越性的镇定冷静,是看得通透之后的貌似默然,或曰直面死亡的“零情感”。最典型者莫过于井宗秀杀妻一场,井宗秀不露声色地谋杀,作家则波澜不惊地书写,但又完全不同于新写实小说中无奈妥协甚至心灵鸡汤式的“零度情感”,《山本》的零情感看似没有人的慈悲心,后面却有深意,文本直面死亡的冷静与超越悲喜的淡然实际蕴藏着他对于涡镇人事的深入思考。作家关注点不在谁胜谁败,是把几方力量均看作是普通山民,都是有父母有儿女的血肉之躯,是一种超越具体人事的普泛化的悲悯。六十六年的人生履历,贾平凹业已看淡生死或曰死也是生的一部分,正如其作品被垢病总写粪尿等不洁之物,恰是作家认为这不洁是人人离不开的生活的组成部分。
最后是历史的眼光与传统文学的审美风格。如果说十七年小说作家对主人公需仰视才见,新历史小说作家基本与人物平起平坐,《山本》中作家的思考是远远高出其笔下人物的,但也绝不嫌弃他们,其中或倾心或反思或批评或悲悯,不紧不慢不温不火中自有一片通透超然与亲切自由。一如《古炉》以瓷器作为中国符号而通过小小古炉村暗喻中国,《山本》也不仅仅写秦岭几年间的人与事,它同样隐喻了整个中国,甚至可以将时限推得更远,历代战争是政治的产物,就参与其中的普通士兵而言意义很大了。《山本》不似其他作品死亡书写那样令人战栗,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作家对中国文学审美传统的继承。大面积的死亡却写得怨而不怒哀而不伤,作家借鉴了中国古典小说的叙事结构框架,用三分胭脂地将整个故事写得一切皆有定数,如“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闹世事”“宝黛还泪神话”一样成为天地间一段孽缘,增加了人命天定的规律性,冲淡了现实世界的悲剧感,作家不是哀怨感伤,而是以更宏大的气象,写出历史的走势。因为秦岭依旧的苍苍茫茫山高水长,任何人事不过是过眼云烟,终究成为大山中的一撮尘土或历史上的一个标点。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贾平凹:《山本》,作家出版社2018年,第162页、411页、211页、218页、233页、497页。
⑦鲁迅:《南腔北调集·漫与》,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