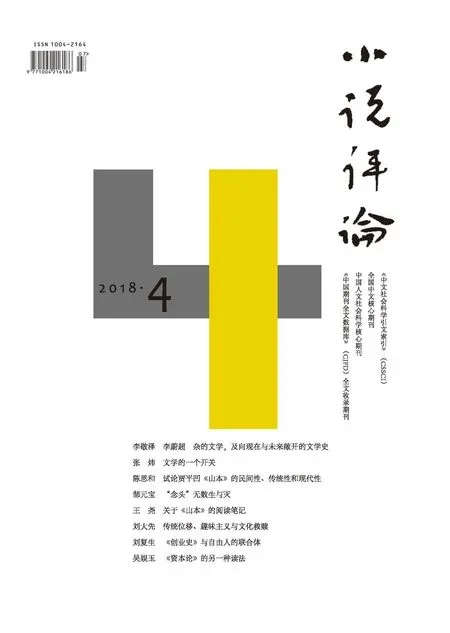杂的文学,及向现在与未来敞开的文学史
——对话李敬泽
2018-11-13李敬泽李蔚超
李敬泽 李蔚超
李蔚超:
今天,我想从批评说到您的文学创作。我记得一位作家开玩笑说,经常和您同台开研讨会,您对作品的褒贬态度,需要费一番思量去琢磨。当然,有人会说那是“中国式研讨会”的外交辞令——
李敬泽:
哦那不是外交辞令,是很认真的。我只是不习惯那么暴土扬尘地对某个作品表态。同时我也觉得,研讨会就应该研讨,应该是一个多端的对话场所,作为经常在会议开始时致辞的那个人,他应该谦卑,他不应该把自己弄成关于某个作品的唱诗班的领唱。李蔚超:
在您的批评文本中,我同样看到了意义的多义性或衍生性,与其说是“李敬泽式”修辞的多义性使它摆脱了时间的纷扰,不如说您把意义交付给过往文学自身有待言明的历史性,谁想恢复那种意义的直接性的企图,都会沦为神话制造术。我认为您的批评是一种感悟式、不命名、不造神、与时间同质的。简单说,您把“新”的作家、作品、文学观念带进文学场,但您并不去参与“经典化”的过程,我不知道我说得对不对。李敬泽:
你真是有学问,我都快被你绕晕了。对“经典化”这个词,我本来也无感。我觉得这是教授们的阴谋,他们把阴谋搞成了阳谋(笑)。“经典”,加上“化”,充满了等级、权力的气息,披着大主教的袍子。曾有人建议我仿照哈罗德·布鲁姆,像他写《西方正典》那样写一本中国现代传统下的类似的书。我没有他那样的本事,但是我也认真想了一下,发现我面临着比他还大的难度。当然《西方正典》在西方,比如美国,也并不那么“正”,布鲁姆之所以要写它就是要和政治正确、“憎恨学派”吵架,也是吾道甚孤,倔老头子一个。我不知道他老人家是否喜欢特朗普,特朗普和他有共同的敌人,他们是否因此就是朋友?这是一件有意思的事。在中国,当下的文化语境下,确立一个现代的正典谱系面临更多的断裂和冲突,你可以说它已经有了啊,各种版本的文学史啊,但文学史也还要重写,乃至重写的重写,远没有水落石出。在这个问题上,还是耐心一点,是不是“高峰”人民说了算,时间说了算。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中有一个很特殊的问题,大家很少谈到。研究了半天体制,教授们也想不起研究自己这个体制。每个大学都有中文系,中文系里有一个当代或现当代文学专业,当代文学被现代文学看不起,更被古代文学看不起,然后就得证明我是学术,就要历史化,就要写当代文学史。对此我并无异议,我自己编《中国现代文学丛刊》,一上来也要昭告天下,以安众心:这是一本学术刊物而不是评论刊物,一定要有学术品质,即使是当代也要做成学术。但是,这个当代文学史是敞着口的,一敞就敞到了2018年的今天。这个问题一开始就存在,关乎当代文学这个学科是否成立,所以很多学者重兵防守,做了很多工作。现在看,问题似乎不大了。但我有时觉得,问题只是被搁置了而已,实际上,这个“敞口”不仅涉及历史哲学和历史编撰,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些活人都还活在这个敞口里。新时期文学到现在也不过四十年,但现在的作家却很可怜,文学史随时准备审核他们、收编他们,狮螺壳里做道场,要在这个尺度非常有限的文学史叙述中找位置,定方向。有时场面很是滑稽,比如最近一次会上,一群人严肃认真地讨论余华、苏童,先锋文学是否终结等等问题,我忽然觉得这是滑稽的,余华苏童都才五十多岁,龙精虎猛,刚才还一起吃饭,一转身我们大家就一起把他们历史化了,立成了航标,他们再想乱动简直是跟我们大家过不去。
这也涉及到当代文学史怎么写的问题,我有时觉得我们是急于下结论、打封闭。好好的胳膊腿,打了封闭就血脉不通。我们上次曾谈过历史意识问题、总体性问题,我认为文学一定要向着总体性敞开、向大历史敞开、向中国1840年以来的现代进程敞开、向文明的未来命运敞开。一些朋友一谈这个总体性就花容失色,但同时,他们一直致力建构一个文学自身的总体性,搞出它自身的一小套宏大叙事。
这种既敞口又封闭的当代文学史对当代文学会有什么影响?这恐怕也是当代文学史的特殊问题,你研究先秦两汉,就算有影响也是层层传导、无迹可寻,你做的是当代,一直做到今天,你不仅仅是把今天归档,你的叙事和逻辑也一定会形塑人们的今天和明天。我们每年都随着当代文学的延伸自我“作古”或“被作古”,天长日久,中国作家关于文学的所谓“历史意识”就特别强,它通过中文系、学院、大学等体制化力量,变成了此时此刻作家们的强迫性焦虑。
当代文学史始终存在着一种危险,它面对古代现代本来是谦卑的、不好意思的,但拼命的自我确立也可能演化出一种狂妄傲慢,把文学变成了一个自足自律的“小世界”,好像它独有一个自我完成的历史逻辑,看不清也要发明出来,否则当代文学史怎么写?由此带来的不仅是学术问题,它还会反过来影响活的文学的发展,它不仅关乎如何认识过去,还内在地影响着我们的自我认识和战略战术,规约和限制着我们对未来的选择和行动。
——怎么扯到这儿来了。好吧,我想我的那些文字的确是与时间同质的,它的方向是现在和未来,仅此而已。
李蔚超:
我想,“经典化”这个学院气场十足的词,可能触动了您对文学现场、当代文学史研究现状的一些思考。其实,当代文学学科在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问世之前,大家也经常提出或接受一种质疑——我们是否可以为“当代”撰史?理由也包括您说的那一点,一位作家、一部作品,去今不远,是否经得住人民和时间的检验?是否能“经典化”?洪老师的“当代史”之所以令人信服,就是他将50-70年代的文学进行了“历史化”研究,在历史结构中观察文学的生产、作家的身份、文学的评价与传播等等,当然,这一切的前提在于那三十年是一段相对闭合的历史。然而,80年代至今的当代文学则无法轻易如法炮制,一旦急于截流出一个水库,闭合某段时间使之“历史”化,就会出现类似您所讲的问题。说真的,我不相信作家真的会面对“文学史”写作,他们可能有“影响的焦虑”,有成名的焦虑,有名垂青史的焦虑,但是,我不相信他们会面对文学史去写,他们只能背对着历史向前走。
李敬泽:
哈是的,很少有作家会天天琢磨怎么跻身文学史,在里边占一章或一节,而影响的焦虑也是正常的。问题的要害不在这里,而在于,某种延伸到现在的历史叙述会内在地影响他,会让他不知不觉地把自己放到这个叙述的延伸线上去,进而自觉地进入这个叙述逻辑的“下一场”。但这种叙述其实必定是非常相对、非常有限的。我也认为,洪子诚老师倡导的历史化方法很重要,当代文学特别是十七年的研究由此获得了坚实的学术基础。但对我这个学术门外汉来说,敞口问题依然是个问题,这是当代文学史的阿喀琉斯之踵。我们所作的这个当代文学史,至少从新时期开始、或者从90年代开始,它就是处于一个未完成的、动态的过程中,“历史化”面临着特殊的困难。我想洪老师讲的历史化应该也不是把2018年的文学历史化,但如果2018年不能历史化,你又何以有信心把1998年或2008年历史化?
当代文学史可能需要为自己发展出一种足以应对这个敞口的历史意识、方法和规范。怎么办?我也不知道。最近又读了一遍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如何将当下纳入历史,如何以历史的方法解读当下,我觉得马克思的路径我们可能还没有认真地往下走。
李蔚超:
这也是我对您的批评集《见证一千零一夜》着迷的原因吧,我不知道,您是否视之为自己的批评代表作。在我看来,这本书是一种新鲜的“月记体”,是回到字面意义的“史”,又记言又记事,按时间顺序记录了新世纪前三年的文学现场,由您遴选的作家、作品、现象,在今天看来,就是一部独特的李敬泽的“文学史”。您的意思是,这些作家、作品好,值得记一笔。李敬泽:
我也比较喜欢这本书。当初《南方周末》来找我,说他们想开一个专栏,叫《每月新作观止》,不知怎么就想到了我,此前我也不认识他们。那时《南方周末》影响很大,我当时也还年轻,有时间又有力气,就答应了下来,一写就写了将近三年。作为批评家,有计划地持续做一件事也只有这么一次,虽然这计划本不是我的计划。我从来没有想过这是李敬泽的“文学史”,当时没这么想,现在也没这么想。但是我喜欢你这个说法:字面意义上的“史”,和刚才所说的史不同。古代的史官做春秋,后来做起居注,都是在时间之流的“此时”记录他认为有意义的事。但是,虽然写的是此时之事,他心里却是有史的。也就是说,在他看来,今天是、而且应该是历史的延续甚至回归,他拥有一套确定不移的标准,据以筛选、整理和阐释事实,把今天归档,归入传统和过去。但是,我认为当代文学属于中国现代的宏大历史过程,它正在向着未来生成,我要做的,固然是注视此时,但不是为了把它归档。我心里并没有那么一套秩序井然的文学史,我的学理准备和知识准备非常非常不足,我很佩服有的批评家,他看到一个作品,马上就能由此追溯到当代和现代的哪个哪个作家上去,我没有这个本事。我是野狐禅,我看到一只兔子不会想到考察兔子的祖宗,它和它祖宗的关系也许重要,但我考察不出来,我关注的只是兔子和树的关系、和猎人的关系、和风吹草动的关系,以及兔子自身的状况。我如果是一个史官,也是力求对现在和未来负责而不是对过去负责。这本书是否像你说的那么好我自己也没什么把握,它已经十多年没有再版了,现在被你这么一说,等我看看哪家出版社愿意再出一版。
李蔚超:
嗯,当代文学史的书写显而易见也离不开那条律例——“所有当代书写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好的历史化研究和文学史写作理应携带鲜明的当代意识和观照。李敬泽:
是的,当代文学史的写作有天然的敞口,这是它的困难。但是,这个敞口可能恰恰意味着我们能够由此产生一种向着当代、向着未来敞开的复杂的批评精神,在这里,历史不是封闭的,而是正在被能动地创造。李蔚超:
批评家的集子,大多少不了一些即时文章、“场合”稿,在我看来,《见证一千零一夜》的写作、体例不太常见地携带了“文体意识”。时隔多年读批评集子,选哪个,评论谁,最能看出批评家的识见,《见证一千零一夜》里,您谈到的作家大多文学生命比较旺盛。李敬泽:
我的“场合”稿也不算少。但《见证一千零一夜》里,还真没有什么凑合苟且,作家和作品应该都是我当时喜欢的,而且觉得有意义有意思的。一方面,尽管开专栏是被动的,但真写起来,我把它当作个人的主动的批评行为,我自己的菜园子还不能随我的意,还要讨大家高兴?另一方面,这个专栏当时影响不小,你也会对自己有比较高的要求。我刚才说了,我其实至今也没有充分的学理准备,对此我完全不自信,但我是个好编辑,有一件事我比较自信,我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才华。李蔚超:
《见证一千零一夜》里,我发现您关注的一些文学问题的最初端倪。比如对报告文学,在操作这一文体时,作家过于不自律的主观叙述,可能背离了求“真”务“实”的初衷,于是,您提到了“非虚构”文体——这距离您作为主编主导《人民文学》杂志推出“非虚构”栏目,还有8年左右的时间。比如,您对“70后一代人”命名的迟疑,问,难道我们每过十年就要用年代为作家命名吗?很遗憾,现在还是这样取名的。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这一方面证明了我们并不陌生的结论——今天的文学还在90年代的延长线上,问题的起源、我们提问的方法,都是一脉相承下来的。另一方面,不得不说,很多文学问题,我们至今含混未决,面对文学现场,我们也没有提出更多十分新颖的问题。李敬泽:
哦是的,我常常感到太阳底下没有什么新事。N零后的搞法现在还在搞,确实反映了我们正在一个乏味的轨道上滑行。比如最近大家好像热衷于谈论70后作家,他们夹在中间,不上不下的很焦虑啊。不过我的感觉,这和当初谈论“60后”时也没什么区别,提出的问题、基本的理路是重复的。演员换了,剧本没变。当然,代际问题虽然通常生产不出什么东西,但大家对这个生产过程还是乐此不疲,它使我们回避真问题,忙于鸡毛蒜皮。经验的表面差异真的那么重要?李白比杜甫大十几岁很重要吗?或者鲁迅比老舍大多少岁这里边有真问题吗?再过一百年,你和我在后人眼里稀里糊涂都算一代人了,这里真的有那么多话可说吗?在这个时代,余华面对的问题,和徐则臣面对的问题,和张悦然面对的问题,真的有多大差别吗?李蔚超:
《见证一千零一夜》在风格化的美文式语言上,说这是一本散文集亦无不可。也许,我们的辨析文体的意识和世间一切规则一样,削足适履在所难免。我记得在梁鸿《梁光正的光》的首发式上,您评述她的写作,提出了一个观点——一个写作者最初的文体、写法,对他这一生的写作是有影响的,这就好像弗洛伊德的理论,琢磨琢磨总有点令人梦醒心惊的道理。李敬泽:
就文学创作来说,很多事都是天经地义地那么顺口说着。比如,小说、散文、诗歌、评论,这些文类以及其中更加细分的诸体,这本身就隐含着对你的规约和规训,文类之间的关系和由此形成的秩序是一种复杂的建构。现代以来,小说、散文、诗歌、评论都经历了一个建立合法性的过程,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当然是最大的赢家,这个时候你选择做一个小说家,不仅和你的才华禀赋有关,也不仅和风尚习俗有关,这本身就意味着你进入了一个资源更丰沛、更具文化势力的场域。在这方面,研究的不多,一个人选择什么文类通常被默认为一个给定的事实,没有更多的话可说。在这个意义上,鲁迅是最有意思的,他几乎是自己为自己创造了一个文类,就是杂文,他已经是小说家、是散文家、是学者,他觉得还不行,他要写另外一种文叫“杂文”,这是很有意思的,最近学术界对此也有一些很有见地的分析。我自己的评论常常被人谈论文体,人家大概也是觉得没什么别的好夸。对我来说,怎么写的问题确实一开始就是一个重要问题,你知道,我硕士也没读过,没受过什么学术训练,人家老说我的文章没有论文腔,其实是想有也有不成。写评论也不是非要写,立了个志要当评论家,而是种种因缘,信马由韁写起来了。所以,这确实是未经规训的“野狐禅”——远藤周作有个庵号叫野狐狸庵,我很喜欢,请人也刻了一方印。我又是个编辑,写评论的时候难免特别在意那些现场性、感觉性的东西,更像一个读者;另外,很重要的,我的评论主要是给报纸写,报纸的编辑女士们很高兴,她们总算找到了一个说话让她们和她们的读者听得懂的批评家。所有这些因素加在一起,随心所欲而逾矩而炫技,辞达而已乃至辞胜于理,就写成了这个样子。
当然,就个人的气质禀赋而言,我这个人什么“家”也不算,但如果你说我是个杂家,我倒是夷然受之。我对越界的、跨界的、中间态的、文本间性的、非驴非马的、似是而非的、亦此亦彼的、混杂的,始终怀有知识上和审美上的极大兴趣,这种兴趣放到文体上,也就并不以逾矩而惶恐,这种逾矩会甚至成为写作时的重要推动力。
我有一个根深蒂固的定见,现代以来,我们一大问题是文类该分的没有分清,不该分的分得太清。什么叫该分的没有分清?你看看每年的高考作文题就知道,我们根本就没想清楚考的到底是什么,是文学还是文章?如果是考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大家都来写文学散文,那么在一个现代社会你有什么必要强行培养亿万文青?如果是考一般意义上的文章,那么这种文章的目的何在?它的文化功能何在?它的实用的、伦理的、审美的规范又在哪里?这些都没有想清楚。作为考试来说,还真是远不如八股文。
另一方面,不该分的分得太清。太知道什么是小说、什么是散文、什么是诗、什么是评论,小说越来越像小说,散文越来越像散文。这个被像的柏拉图式的抽象理念又是什么呢?不过是一些很Low很简陋的清规戒律。按照我们这样的理念,《战争与和平》都要删掉三分之一,因为它不像小说。
李蔚超:
您做批评时,是不大下判语的,大多发问式地提醒作家、读者,这里是不是还有如何的可能?大家一起去想吧。现在的您,时时宣布退出批评行当,专心当作家,我觉得即便您说,我要写作啦,我不要做文学批评,您还是隐隐有找个前文本对话的习惯,在对话中使智慧曼衍开来。《青鸟故事集》、《咏而归》把历史视为前文本,借题发挥,浇一己之块垒;《会饮记》中,您在文学生活中遇到的每个人、每件事,一场研讨会、一本书、一次展览,都可以是您对话的对象,就连你自己,作者李敬泽也索性设一个第三人称“他”,这个自己跟那个“他”对话,今天的自己和彼时的“他”对话,自我的不同面向也在对话中徐徐打开——就像您的批评文章里,常常借巴赫金的理论倡导一种对话的、众声喧哗的小说。李敬泽:
嗯,我的理论功底不好,和你们这些年轻批评家没法比。80年代有一阵子读卢卡奇比较多,由卢卡奇又比较细地读了马恩的文艺理论。90年代早期,游手好闲,读了一堆巴赫金、本雅明、福柯,那时福柯的译本大陆很少,都是花高价买的台湾版。这都是很喜欢而且读进去了。这两年读柏拉图对话,也觉得气息相合。我想,对话确实是一个根本问题,对我来说,这是思维习惯、感受方式,是想象力和理解力,也是与世界、与自我相处的方式。就批评而言,我觉得这更是内在于批评行为,关乎批评的根本意义。批评家也就好比苏格拉底,他坐在这里,以尽可能多的方式打开文本,把读者带进一场活跃的对话中去。批评家不是法官,或者说,他即使是法官,也是那种审慎明达地引导着陪审团的法官。至于《会饮记》,我不太倾向于把那里的“他”确切地设定为另一个“我”,或者说我没有打算限制他界定他,他不是我的镜子,如果是也是“风月宝鉴”。他也不是我牵着的狗,大部分时间我是放开了绳子随他跑去,当然,现在看,我还应该给他更多的自由。但是,你说的对话性是显而易见的,我希望“他”是柏拉图对话里的那样一个戏剧角色。——读柏拉图的对话你会看到,戏剧真是希腊文化的隐秘核心,戏剧是理性的变体,或者理性就是戏剧的变体。在这个意义上,新时期文学以来,中国文学最内在的艺术事件,不是什么先锋之类,而是对话的、戏剧的精神的停滞或者说早衰,这样一种精神,在我们这里还没来得及建立就被PASS过去了,没有经过拉伯雷、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等等,直接就跳到了卡夫卡、博尔赫斯。
李蔚超:
上次在北大采薇阁的读书会上,中文系的“90后”同学纷纷给您的《青鸟故事集》和《咏而归》命名,认为这是一种“杂”文体,是一种“集结了叙事、虚构、议论、抒情、说理甚至俏皮话与插科打诨的综合性文体”。博士后路杨的发言,在我看来颇有见地,她认为鲁迅的杂文、《酉阳杂俎》和《咏而归》的审美性在于“内在的紧张感所带来的特殊的阅读快感,这与多种文体与风格在文章内部的杂糅状态及其在形式层面上的角力有关”——这多少解答了《咏而归》妙趣横生的可读性来源。在我的观察中,您一直不崇尚“纯”的文学,好多年前,您在《人民文学》的卷首语中谈到,小说生长自喧哗的市井而不是冰封的古堡,您期待着“子部的复活”,您是否在召唤着与“纯文学”不同的、之外的“杂文学”?李敬泽:
我确实不喜欢“纯文学”这个说法,那是因缘际会的建构,早就站不住脚了,很多人都谈过,我完全赞成。这个说法现在有时还在用,是因为我们这些从五四新文学一脉下来的人现在面临着自我指认的困难。我以前讲过,我们现在都不知道自己叫什么了,纯文学?严肃文学?高雅文学?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网络文学界谈起我们会说他们是传统文学,我说你们才是传统文学好不好?当年胡适陈独秀鲁迅他们在忙什么呀,不就是宣布新文学诞生,把你们归到了旧文学吗?与“纯”相比,我喜欢这个“杂”字,它让我想到鲁迅的杂文。对这种杂文在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中的意义,我们还没有充分认识。大家说了或者不好意思说的,都觉得鲁迅那么伟大,他要是继续写小说多好啊,写长篇小说多好啊!实际上我们都认定长篇小说更伟大,鲁迅需要长篇小说的伟大来证明他的伟大。但我觉得,长篇小说这件事,鲁迅写了固然好,不写也没什么,我很怀疑鲁迅真的打算写长篇,他从他的生命体验、从他的文化境遇包括当时的媒体条件里——没有那个时代报刊的发达就不会有杂文——还从更深远的、从汉到魏晋的脉络里,为自己开辟了一条新的文章之道。鲁迅的“杂”其实是回到诸子的,一种现代的诸子之道,从他的小说、散文,那个非驴非马令人困惑的《故事新编》,到《野草》到杂文到小说史,我觉得鲁迅并不认为这是在做着几件各自分明的事,不是现代文类分工下的多种经营,这是一种诸子式的包罗万象、纷然杂陈。所以你看,鲁迅对周作人、林语堂他们搞晚明是不以为然的,这里固然有人际关系、气质不合的原因,但更重要的,周作人他们是要建立一个现代散文的法统,往前边找合法性,圈出一块地来说,这就是散文,而鲁迅对这个不感兴趣,在他看来这未免小了,他是要回到韩愈之前,回到“子部”。
有一次磨铁出了一套年轻人的小说,请我去站台,说顺口了一张嘴就说了一个“子部的复活”。那些年轻人算不算“子部”另当别论,但我自己很喜欢这个说法,一直想写一篇文章细谈。现代的文学散文,周作人他们起了很大的建构作用,经史子集,他们实际上是独取集部,而且是集部的晚明。而鲁迅后无来者,他是走了“子部”。后无来者也是正常的,集部人人可走,子部可不是人人能“子”的。但是现在,我确实认为有一种子部复活的前景,在互联网背景下、自媒体背景下,现在最重要的书写不在我们这些传统的散文家这里——我是不是又要得罪人了?此处删去几千字(笑),而在很多公号文章、很多自媒体的书写里,他们有“杂”而“子”的气象。当然他们有他们的问题,但你别忘了,每一代都是在自己的限制、问题和对堕落的诱惑的抵制中做出真正的创造的。
李蔚超:
那次读书会上,您和丛治辰及同学们谈到一个话题,即中国缺乏现代散文理论——现代小说是舶来品,西方的小说理论集装箱式进口到中国来,十分畅销,而散文则没有与之对应的理论。我回想了一下古代文学理论,刘勰体大思精的《文心雕龙》,开启的是古人的“文章学”,确立一种本质——“道”,随后谈文体变迁,由雅而变,然后说行文布章,这都算不得现代散文理论。我们今天怎么去谈散文才好?作为写作者,您如何去在散文中自觉地思考这个文体的问题?我想请您多聊几句这个话题。李敬泽:
确实是这样。我前几天还和一个朋友说,你做做散文理论吧,这里边的空间特别大,最宜跑马圈地。或者说,我愿意用另一个词,就是“文章学”。中国古代的文章学是笼盖四野的,特别是韩愈之后,道乌乎不在。但是在现代转型中,这个文章的道统崩溃了,你看周作人他们最恨韩愈,各种冷嘲热讽。然后要做一个现代建构,重划疆界,确定一个现代的、文学的散文范围,实际上是对韩愈的反方向收缩,韩是载道,周是言志。结果就是把庙堂江湖一股脑划出去,过去诏书、奏折都是文章,《曾文正公全集》里收一大堆公文报告,现在这个都不算了;史书划出去,传记划出去,各种实用的交际性的书写也划出去,不断划出去,剩下一个叫散文。这个是干什么用的呢?他们往上找了晚明小品,往外找了ESSAY,这基本上就是个人经验和情感的书写,就这么形成一个新的小传统。当然实际情况比这里说的更复杂,后来还有延安之后社会主义文学实践对这个小传统的改造等等。但总的来说,散文在现代文学中的地位是极尴尬的,从范围上说,它已经由“日不落”退缩成岛国小邦,从传统资源和艺术资源来说,它把文统道统一扫光,只搞出个袁中郎、张岱、兰姆,和现代的小说比起来寒酸薄弱至极。它给自己留了一块地,个人生活和经验情感,但这块地是不是全归它也很成问题,小说在这块地上也开花结果,而它在艺术资源、艺术空间上远不能与小说抗衡。从现代到当代,专业的散文家寥寥无几,散文只合业余写,它是“余事”,小说之余、诗之余、生活之余,“余”成这个样子,也说明,它的本身还没有足够地成立。
所以毫不奇怪,谈起小说,谈起诗,我们都有一大套理论,都有极为复杂的省思,谈起散文有什么好说的呢?谈谈真诚和真实?这些话说了一百年,到现在也没分清真诚也不等同于真实。作为文学的散文书写并没有完成现代转型,推而广之,从混沌凿、文章裂之后,广义的文章学、文章之道也还没有完成充分的现代转型。所以你看,文风问题到现在也还是个大问题,高考出题还是不知道怎么出才好,一年一个路数,孙悟空七十二变总还有个孙悟空在那里,我们的高考题就只有七十二变眼花缭乱,没有文章本体。
回到文学散文,极大的困难,就在于作为一种现代艺术形式,它没有足够的自律性。文学当然做不到、也不应该绝对自律,但一定要有相对的自律性,它的内部规律、内部规定性,否则就漫无边际、不能成立,就和其他事物没有边界没有区别了。小说、诗都是相对自律的,你能够就小说谈小说,就诗谈诗,可谈的话很多,但散文很难,这种难一定程度上和我们现代早期的建构有关,四四方方切豆腐,切了这么一块,后来发现切得太小了,切成一粒豆腐丁了,不够一盘菜的。但另一方面,散文缺乏自律性可能也是正常的,因为它的前身前世就是笼盖四野、茫无际涯。一切书写文明都是这样,中国更突出一些。我不知道,你或许可以考察一下,在欧美语境里,大概除了小说和诗,一般并没有专门把散文列为一个独立自洽的艺术门类。
当然,欧美没有不意味着咱们不可以有。恰恰我觉得,我们现在需要一种广义的文章理论,把庞杂的万物生长的常态的书写活动都容纳进来。对人类生活来说,小说不是常态,诗也不是常态,但文章是常态。文与章,这是中国文化和中国传统的根本发意,我们需要在更广大的视野里对现代中国之文作深入的理论思考,也只有经历这样的思考,作为文学的散文才能获得它的艺术自觉。
李蔚超:
一次,我和刘大先闲聊《咏而归》的观感。他说,您的文章之法是水银泻地,自然而然,无迹可寻,我只有无话可说地同意。我们酸溜溜地探讨了半天怎么能练就这样一幅笔墨,结论,这真不是“认真”两字能达到的。当时我说,您的见识是传统文人式的,以古观今,文章里面看家国。您还有都市市民的享乐趣味,早年您挺喜欢王朔小说,现在您爱听郭德纲相声。您读书偏好史书和文人笔记,颇染上些士大夫的闲情逸致。您是否同意我们的看法?李敬泽:
我不知道。周作人说,他身上有两个鬼,绅士鬼和流氓鬼。我不如他,身上鬼更多,闹得很。“文人士大夫鬼”可能有,我自己有时也这么说,但你也别全信。我自己也搞不清都是些什么鬼,比如至少还有一个反文人士大夫的鬼,我就是个农家后代,泥腿子的底子,喝咖啡就大蒜我装什么高人雅士?传统文人那种气质风格在新时期以来广受推崇,以至于现在很多人拿这个当饭碗。但凡是中国人又有些文化,身上难免藏一个“文人士大夫鬼”,年轻时看不出来,别急,到了时候就会冒出来。我自己也曾种种毛病冒出来,但现在反而特别警惕,这很容易搞出一身油腻的酸腐气,再进而就是装神弄鬼,拿肉麻当有趣。我有时也自称文人,那是开玩笑,或者是为了回避问题——我的问题是,当批评家也不是个标准的批评家,当散文家也不是个标准的散文家,直到现在,自称批评家或散文家时还是常常难为情——是真的不好意思,但你总得有个身份吧?好吧好吧,退无可退,只好说我是个文人,我在它的本义上用它,以文为生的人。同时我也喜欢文人的另一重隐含的气息,它不是专业分工下的专家,它是业余的驳杂不纯的。但严肃地说,我不觉得我是传统文人,我也不打算向那个方向修炼。我并不认为在21世纪做一个传统文人有什么意思和意义,当然,从根本上说,这也不可能。好像有老师说汪曾祺先生是最后一个士大夫,我不是很同意。汪先生是个现代文人,不是传统文人,他早年的东西是现代派,他搞京剧还是现代派,他在生活上和创作中都深度地卷入了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实际上,他的意义完全在于他在这个过程中参与提供了一些重要的美学方案。至于炒菜写字等等,那和唐装盘串儿差不多,有趣而已,不必认真。他哪里是什么士大夫,他是“拾垃圾者”,或者说,是本雅明意义上的文人的变体。
好吧,我一直喜欢“拾垃圾者”这个意象,我自己,如果是文人的话,我希望也是一个本雅明意义上的文人。这样的文人,他的内在方向是空间的,不是时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