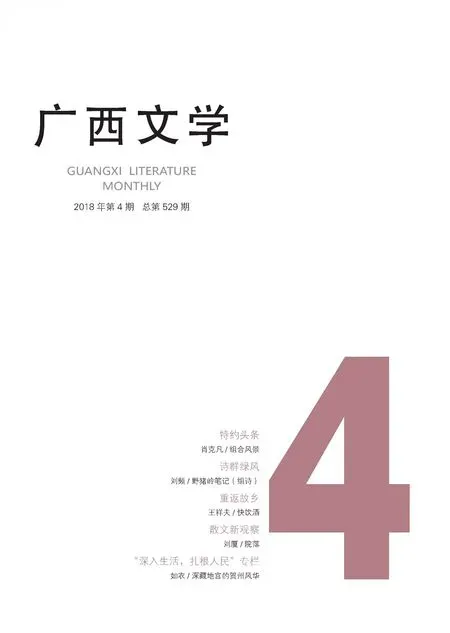空旷处,野马奔驰
——陆辉艳《心中的灰熊》阅读札记
2018-11-12庞华坚
庞华坚
1
她的句子,准确、直接,像一把镰刀,不留情面地递向生活中高过头顶的茅草。茅草倒下,遮掩了脚下更多的生活细节,但是茅草倒下,眼前更加辽阔——她找到了她的空旷——自己的世界。
读陆辉艳的《心中的灰熊》,既感慨她掌控情绪的能力——冷静、客观,又赞叹她持续挖掘生活的本事——深入,抵达生死,更欣喜她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诗歌,得以校正、推动和稳定自己的创作步伐,从而呈现出来的与众不同和从容。
2
“悬崖抱奇崛,绝壁驾崚嶒。”陆辉艳不少诗歌正是这样:意象奇崛,又隐喻丛生。
“哦,天空低垂/它占领杂草丛生的土地,犹如躯体/长年累月,为我的灵魂所租用/秋天的鸟雀跑到山顶的背面/不久将传来消息:它们啄去巢穴——/那停放我将来作为尸体的地方”(《状况》)。天空、杂草、秋天的鸟雀、山顶的背面、巢穴、尸体,一连串意象,瞬间转换,构建出的场景和氛围直接把人按住,让人气都喘不过来。但是当你再读一次这些句子时,不得不承认,真好。
《南方信札:“并不是这样……”》也是这样一首诗。“你所爱之人,正在别处的土地/你擦拭所有的门/每一扇门后面,都有一双手,为你拔去门闩/都有你的悲伤在无限扩散,仿佛涟漪……”时间置换中,因了思念,仿佛对方存在,仿佛两个人就在一起,一举一动,都在温柔和悲伤之中,而事实上并非如此——“你写一封语无伦次的信/信上说到四月花开——你看,这些花开得多么明亮/不会使人想到花圈,世界末日因此/而减缓它的来临”。这种差不多是不可捉摸的转折,奇崛却并不显得唐突,而是顺理成章。这样的转折,给人以阅读的冲动,新奇,新鲜,余韵悠远。
我一直认为,诗歌给予我们的,可以有忠告、告诫、批评、个人观点,但是诗中更应有一条线,有一股引领的力量,让阅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和阅读后,有回味、想象、延伸、扩展和自我判断的余地。诗歌由诗人写出,由阅读者终结。诗人不是“教父”,写诗的人如果在诗里先入为主、自以为是去教导别人,做“法官”,可笑,心术不正,甚至居心叵测。
3
读一首好诗,可以让人击节赞叹。《心中的灰熊》里确有不少我认为可以击节叫好的诗。比如《礼物》(大自然的告诫和给予)、《我们喝过的水》(感恩)、《最好的风景》(死亡里的温情)、《拍照》(贫穷人的生活,难得的幽默)、《发言》(准确的叙述,格言般的)、《大苹果》(无法言说的生活感慨)、《木匠》(卑微人生)、《缺席》(对死者的尊重)、《环》(命运的飘移和虚实把握)和《如此》(爱情深觉和变幻)等。
整体而言,这是一部失败、平庸之诗比较少的诗集。之所以如此认为,我觉得诗人始终在场是关键原因。《心中的灰熊》的诗,大部分以第三人称出现,在场者似乎隐蔽着,不在场,但是一行一行读下去时,诗人分明又无处不在。而第三人称,反而让诗人得以处于一个合适的观察的位置,客观地深入现场。无论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她就在现场,以一个人或者一群人的形象切入事件内部,然后还看到她从事件中走出来,这非常见功力。一开始,她好像一个冷静、理智的旁观者,你以为她不参与,但是她的决绝和态度,一目了然,不容置疑。她参与,但不做评判,只负责呈现。她只是以句子为镰刀,割倒生活的茅草,让我们可以看得更远,走得更远。
在场感,对诗人和读者都是一个评判标准。
诗歌在场者,有幸接近事件的真实、本质,闻得到诗句之犁翻开泥土的新鲜气息,领略得到诗歌本身散发出的檀香味道,那味道一定会持续敲响你锈迹斑斑的大门。而站在远处遥望的——也可能是不得不站在远处遥望,要么是初窥诗歌门楣之人,有心无力接近,要么是对诗歌保持足够警惕,对诗歌另眼看待的人。他们不在讨论之列。他们尚未具备能力、资格讨论和分享好诗的阅读和想象快感。
4
野外,大片白茅草,拼命摇晃,像命运。
命运,这不可推倒的定数,是陆辉艳诗中挥之不去的命题。写命运,且不说像陆辉艳这样年轻的诗人,这世间又有几个人能把命运呈现得让世人信服?面对复杂、神秘的命运,需要牢固的定力、个人的清晰判断、娴熟的语言把握能力和足够自信,才能写出味道浓烈、意蕴丰沛的命运之诗,否则很容易陷入武断、判断和虚无之中。在我看来,陆辉艳深谙其中三昧。她不动声色,凝练、准确,对不可穷尽的世界进行探索,对个性生命沉浮切入内里去理解,寂然不动又如意自信。这需要功力,更需要灵性和宽容。陆辉艳写命运,是以自己的目光、生命与命运保持着不远不近、不偏不倚的距离。她看到、感受到的,是自己视野中的真实,是她的真实和真诚。
真实和真诚,对于一个作家、诗人而言,讲起来容易,做起来太难。但是,一个诗人的目光,不是平视和俯视,难道只朝着天上吗?只会仰望走路的人,走着、走着,一定会踢到石头、撞到墙壁。真实、真诚、平视和俯视,很多时候甚至是我结交诗友的标准,我实在不喜欢、看不顺眼那种只会仰望的诗人。陆辉艳的诗,视角是平的、低的,这让她得以看到人世间的痛苦、隐约的幸福、刻骨铭心的爱情和命运之舟的去向——
《木匠》:站在近处,得以看到木匠缓慢无比地打的墨线,看到木匠简单、粗糙,无比漫长又瞬间消逝得无影无踪的人生。
《在南宁港空寂的码头》:我们身边,包括我们自己,无时无刻不在变迁,来自内外的强大的覆盖与毁灭(或新生),不为谁左右,坦然面对泥沙俱下和沧海桑田——历史的脚步声渐去渐远,几十年时间,犹如弹指一挥间,沉沦和埋没的,何止眼前的建筑、河水和草木,也许,眼前的一切早已物是人非!
《环》:生与死的联结,死与生的无奈,几代人,千百年来,谁能奈何命运?“我的奶奶,终身被/一种看不见的环牵制/直到她进入棺木/变成一堆白骨。”
《父亲深夜来到我家》:“……命运,像这片不走运的土地。/父亲,但我怎么能怪你。/我也同样被生活狠扇耳光,/被它那只巨大的手,往嘴里灌满黑色泥浆。”饥饿、不祥、大雪……依然如悬于头顶的太阳,既催发又摧毁生命。“我们该做些什么?假装什么也没发生/置之不理,土地上的亏损、债务,苦难/梦想熄灭。直到接受这一切,直到——/丢弃那假装的面具、踩碎,/重新穿上鞋子。”
又如《迁徙》对居无定所的拷问等,命运啊,狗日的命运!
5
一个人心智的成熟与否,成熟得早与迟,和经历的关系太大了。命运如大风,吹醒死亡,也吹醒新生。岁月如一片无边无际的原野,人像原野上一棵草,风吹草摇,漂泊无着。孱弱可以转换成坚定,但有时也是不得已为之。陆辉艳以书写死亡和灰暗的方式,转换成生的渴望和信念。《心中的灰熊》的第一辑和第四辑分别完成了这样的使命。
《心中的灰熊》第一辑里的诗歌,色调几乎都是灰暗的,凝固、寂寥,仿佛所有冰冷聚集于此,无从化解,读得无比郁闷。虽然如此,但是,作为读者的我又不愿从诗人营造的氛围中走出来。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作为一个读者愿意承担这意外之重?我是不愿意放弃这样的吸引。比如《缺席》:“他挪开那上面的物件:/一个骨灰坛,盖着黑色绸布/‘坐这儿,这儿’/他的声音压低,充满悲伤/右手按在胸前”——读这样的句子,你除了一个个字读下去,你愿意释卷吗?又如《手铐》:“这匆忙、拥挤的生活/不得不爱,不得不接受/举起双手,各拽一个吊环/哦,耶稣受难的姿势/座位上,一个坐在妈妈怀里的孩子/仰起头,指着那些晃荡的吊环/突然大声说:/看,好多手铐!”——小孩总能洞悉真相,而笑得最大声,笑得溢出泪花的,只能“是那些手抓吊环的人”。——读这样的句子,你除了一个个字读下去,你愿意释卷吗?
在写死亡方面,陆辉艳算得上是一个颇具勇气的人。在这本诗集中,她几乎可以称得上是不厌其烦地呈现死亡了。我甚至觉得,这本诗集第一辑的第一、二首之所以放在诗集的最前面,只是为了不从开始就直面惨淡生活,不面对死亡,而有意为之的。这对于一个年纪尚轻的诗人而言,意味着曾经有过什么经历,需要承担着什么样的重负,自是不言而喻了。这些诗,在平静文字的掩护下,波涛汹涌,读来让人惊心动魄,纠结无比。
“坐在她生前坐过的条凳上”“嗑着她夏天种的红瓜子”,六个儿女各怀心事,代表各种感情,只有她的小儿子在“她左手的中指上,那儿/发现一个细小的,缝衣针留下的小洞”。这是《丧事》中的细节,这首诗和其《迁徙》有异曲同工之处。在死亡面前,在“我”和“别人”面前,在渺小和阔大面前,在“自己”和“别人”的关系面前,死亡算什么?悲凉、悲愤和无能为力又算什么?
在《奶奶》中,衰老和死亡仿佛是一首歌中的主、副歌,主、副歌不停高低起伏,反复回旋,诉说着阴与阳的变化,诉说着正常和不正常思维的互换;《状况》中以死亡来进行转折形容和隐喻,简直是神来之笔。当然,写死亡并不是最终目的,死亡之下是生命的升起,是温暖的重整旗鼓。死亡换一个角度来看,不也是生命的另一种形式吗?比如《今天是安静的》,以浅埋死亡的方式,让“我活了过来”,“在午后,寒冷的空气里/它们成全过我的繁盛,衰落,今天更是如此”——这首诗的温度虽然不高,但是总算有了些许暖色。第一辑的最后一首《土地有它自己的脾气》也是,“那些死去的因此又一次活过来,重新生长”。诗人以此来结束生死杂陈的这一辑,给了阅读者期许,更给了诗人重新成长的勇气。
不过,在第一辑里,有几首并不容易读进去,哪怕反复读,我还是不太能理解诗人的表达,奇怪的是又无法不喜欢那如岩石缝中逸出的气息,那是死亡的气息,无解的气息,贴着泥土不知道是什么味道的气息。比如《空缺之诗》和《只差一步》。另《强迫症》一诗的意象很好,意象的转换显得稍快,从最后两句的急促看来,诗人似乎急于作判断了。
6
《心中的灰熊》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用简单的语言、句子营造复杂的意象。在这个时代,学会用自己的语言写作,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至少对于中国诗人来讲,是一样难得的好品质。尤为难得的是陆辉艳不但会用简单的语言准确地写作,而且能够化于无形,化于句子的节奏中,而节奏又掩盖了准确的诗句,不动声色地推进诗歌的节奏,起伏明朗、富于音乐性。《回到小学校园》就是这样一首在结构和节奏上都尤其明显的诗歌。
保罗•策兰说过:“在所有丧失的事物中,只有一样东西还可以触及,还可以靠近和把握,那就是语言。是的,语言。在一切丧失之后只有语言留了下来,还可以把握。但是它必须穿过它自己的无回应,必须穿过可怕的沉默,穿过千百重死亡言辞的黑暗。它穿越。它对所发生的一切不置一词,它只是穿过它。它穿过并重新展露自己,因为这一切而变得‘充实’。”
确实如此。
7
诗人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奔放、热情,甚至狂妄得可以吹牛皮。此话虽然言过其实,但很多诗人比较开朗也是事实。有时我想不通,是谁给了诗人这样的性格和自由?因为写诗,需要丰富的想象力?难道写小说、写散文不需要丰富的想象力吗?但是每一个诗人心中,都有一头渴望奔跑的小兽,我觉得存在。让诗行奔跑起来是必要的,但是陆辉艳同时还能让自己沉潜,不急不缓地写,张弛有度,这就不简单了。如 《出塞》 《穿行》《魔蝎•十日》等的不乏“粗犷”,而《绿萝》《多么静的夜晚我在此》 《短歌Ⅰ、Ⅱ、Ⅲ》等又尤其寂静:喧哗里有平和,荒芜中有生命勃发的巨大力量,孤独而非孤寂的况味,身处阔大而不遗失立足之地的清醒。
8
在陆辉艳的诗歌里,天地大爱的诗歌占大多数,比如《真相》等。爱情诗其实也不算少,只是被她有意无意遮蔽着了。虽然遮蔽,但是仍然掩盖不住字里行间爱的流动。比如《南方信札:隔阂》《南方信札:“并不是这样的……”》《如此》《隔世》《这些时日》等。“……时间对于我的培养是/不理智。我知道深藏于内心的旷远/将因你的缺席而终止/冬天的孩子在树梢枝头发芽。你说爱他”——这得有多绵长而无奈,才借助得了一片树叶讲出爱啊!“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是爱,“只可意会,无法言传”也是爱。爱,就像岁月的苍老,古今相似,从没放弃过有计划、按步骤地行进。在岁月的苍老中,相爱的人,最终到达的,是天长地久比肩而立,还是时光悠长的背景?不知道。只知道至少有爱那时,醉意降临,物我两忘。
9
读陆辉艳的诗歌,常有这样的想法:我们还在寻找出路和长途奔忙时,她已从远处归来,安静地回到她多年前随手缔造的茅草屋子,生火煮饭,汲水养牛,和水井边一棵野草再度屈膝而坐,长夜倾诉。
想想,这应该是天意和上天给予她的酬谢。祝福她诗路畅顺、花草茂盛。
然后,我又想到了另一个问题:诗歌在世俗生活中,特别是现在——一个不属于诗的年代,尴尬又不可或缺地存在着,写诗有什么用?作为一个喜欢读诗、写诗的人,我相信,诗就像那些废墟上不知不觉长出来的几根草、一朵小花,它们看似在边缘、微小、被忽视,却又不知不觉滋润着我们的目光,给沉寂已久的心灵带来生命的活力。辛波丝卡讲得好:“我偏爱写诗的荒谬,胜过不写诗的荒谬。”实际上,与此同时,我还记起了她讲过的另一句:“诗人总有关起门来,脱下斗篷、廉价饰品以及其他诗的装备,去面对——安静而耐心地守候他们的自我——那白皙依旧的纸张的时候,因为到头来这才是真正重要的。”我猜想,陆辉艳看过这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