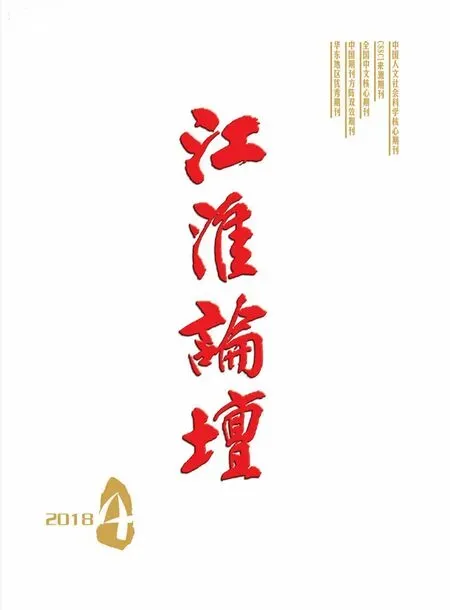荀子“法后王”说续辨*
——兼及其所蕴含的礼治精神
2018-11-12刘亮
刘 亮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北京 100875)
荀子“法后王”说,见于《荀子》的《不苟》《非相》《儒效》《王制》《成相》等篇。从其文义释读到思想阐发,前贤今人之所以高度关注,是因其说实为探究荀子思想中礼法制度与君权关系的一个有效角度、讨论荀子礼治思想之基本特征的关键切入点。
一、前贤观点
针对荀子“法后王”说的研讨可溯至汉代。司马迁《史记·六国年表》云:“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将后王解读为近世之王,法后王为取法近世之王。杨倞承袭此说,释《不苟》篇“百王之道,后王是也”云:“后王,当今之王。言后王之道与百王不殊。”释《非相》篇“欲观圣王之迹,则于其粲然者矣,后王是也”云:“后王,近时之王也;粲然,明白之貌;言近世明王之法,则是圣王之迹也。夫礼法所兴,以救当世之急。故随时设教,不必拘于旧闻。而时人以为君必用尧舜之道,臣必行禹稷之术然后可,斯惑也。”17世纪以来,中外学者对此多予质疑,并提出新说。新说暂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观点,试图通过在历史过往中探究所“法”之对象,来明确“法后王”含义。依照对象之异,大略区分如许:(一)刘台拱、汪中、猪饲彦博、王念孙、杜国庠、吴茹寒、李涤生等持“文武”说。论其理据,杜国庠先生列举《成相》的“文武之道同伏戏,由之者治,不由者乱”,李涤生先生则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恰与《非相》“后王之迹”粲然可知相一致。 (二)物双松、钱大昕、久保爱、冢田虎、朝川鼎、郭沫若、冯友兰、熊公哲等持“周王”或“周道”说。朝川鼎以《非相》“知周道”以及“禹汤有传政而不若周之察也”作为依据,郭沫若则将“周道”说建立在他对荀子世界秩序思想的理解上,他主张荀子的“宇宙观或世界观是一种循环论。一切自然界和人事界的现象虽然是千变万化,但变来化去却始终是在兜圈子,结果依然是没有变”。(三)章太炎先生持“法《春秋》”说,旨在彰显荀学与孔学的传承关系,以申“尊荀”旨意。其云“綦文理于新,不能无因近古”,言“法后王”是针对典章制度的创新,大凡创新,对旧制又不免有因循。(四)刘师培倡“守成之主”说。 其言“‘後’、‘后’古通。后,继体君也(见《说文》);盖开创为君,守成为后,开创之君立法草创,而成文之法大抵定于守成之君;如周之礼制,定于周公、成王是也。《荀子》所言后王,均指守成之主言,非指文武言也”。(五)韦政通、张亨等学者持“积累”说。张亨先生解释称,“经过历代的累积,当然是后来居上,粲然大备,照理说只要取法后王就够了”。 (六)梁启雄、李中生、周群振、陈礼彰等学者,提出以“不变之法”变“可变之法”说。梁先生释《天论》篇“贯之大体未尝亡也,乱生其差,治尽其详”云:“荀子法先王,又法后王。大概在道理原则上他是掌握着不变的道贯,这是‘原先王’;可是,在法术和政教上他是随时灵活地变革的,这是‘法后王’。”李先生认为,荀子主张稳定不变的道贯与某些重要的具体礼法是不可变的,而不重要的具体礼法,则可循道贯而变。周先生提出“以先王所示之价值理念为宗纲,以后王所成之具体实务为榜样”。陈礼彰先生亦承此说,谓“永恒不变的道理原则以先王为法,与时俱进的文物制度则以后王为法”。此种观点尚有未尽详之处,如,为何先王后王分而论之,却不言径自依据先王治道而变革当世之法;由此可变的、不可变的规则所组成的结构,可否进一步推知“后王”乃至“法后王”的精确内涵与外延等。(七)廖名春先生提出“成王康王”说。其言“周之礼制,亦即周道,其基本框架成于周公、成王之时”,而成王、康王作为“西周盛世之君的代表”,即荀子所谓“后王”。这一类释义的具体观点虽各有异,然综合而言,皆将“法后王”指向先代圣王的各类治道法度。根据此类师法往昔圣王的释义,又能够 (直接或间接地)推出“法后王”说对特定旧制的保守态度、重视历史经验等特征。
第二类观点,释“后王”为荀子所处时代的天子。如吉联抗释《王制》之“后王”为“当代的帝王”等。这类释义可体现“法后王”对荀子所处时代特殊性的肯定,以及(近于法家诸子的)是今非古、“世异备变”之倾向。
第三类观点,将“法后王”视作对未来的期许,仅是理想状态,不存于历史或当下。章学诚称“法后王”有“欲来者之兴起”之意。罗焌先生援引《正论》“天下归之之谓王”以及《正名》“后王之成名,刑名从商,爵名从周,文名从礼”,提出“后王所定礼制,非袭三代之礼…… (后王)非商周之王……乃指后世为天下归往之王,非谓后世以君位世及之王耳”。赵俪生先生亦主张“荀子的‘法后王’,并不是已经找到哪一个新的崇拜对象,他只是说,过去对周制和文、武、周公的崇拜太过了”,言荀子“后王”之说乃是对周制的否定。根据此类释义,“法后王”之说有排斥一切旧制度的倾向,而成一种极具革命性的学说。
根据上述聚讼,“法后王”释义的细微差别,亦将招致其所蕴思想的相为天渊。故针对其说的研讨,释义问题最为基础,必先予明确。
二、再释“法后王”
讨论“法后王”含义,需留意不同角度:
首先,“法后王”应指向原则、制度层面,如前贤所指出。“法后王”之“法”,意为取法或师法。法,古字有作“灋”者,《说文》云:“灋,刑也。平之如水。从水,廌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去。”有效的刑法,内容须具备概括性,针对的定是一类具备某些构成要件的行为、事态,而非特定的、独一无二的行为或事态。循着这一特征,“法”字引申为取法、师法之意,表示按照某种原则处置某一类事态。如《孟子·公孙丑上》云“则文王不足法与”,《韩非子·五蠹》云“不期修古,不法常可”,等。《荀子》文中各处“法后王”之“法”,即属此种含义。取法、师法的对象,为适用于某一类事态的概括性原则,即使面对“后王”的任何特定的举措,也只有从中提取出能够适用于具有相同特征的事态的概括性原则,方可言取法、师法;反之,纯粹特殊的、完全无法提取概括性原则的特定举措,则无取法的价值。亦即“法后王”所“法”之对象,是针对处理具体事态所循的成文或不成文(惯例性)的,抑或在具体事例中提炼出的具有概括性的原则 (如典章制度等),而不论这些原则处于政治、经济、文化等人类社会的哪一方面。《王制》“道不过三代,法不贰后王”中,“道”与“法”互文修辞,即在强调(此处用作名词的)“法”所处的原则、制度层面,及其所具有的概括性。
其次,对《荀子》而言,“后王”的礼法制度粲然可知。《非相》云:
圣王有百,吾孰法焉?故曰:文久而息,节族久而绝,守法数之有司极礼而褫。故曰:欲观圣王之迹,则于其粲然者矣,后王是也。
其明言“后王”之迹为“圣王之迹”(圣王的礼法制度、政治举措)中能够清楚知悉的部分。“先王”的礼法制度,则处于久而息绝的状态,无法详知。因此,对《荀子》而言,后王、先王的区别在文物制度是否可知。
再次,“先王”治道可经由“后王”礼法制度推知。对“后王”“法后王”的研讨不得不论及“先王”“法先王”的含义,因《荀子》提及“后王”的文本,明里暗里皆相对“先王”而言。“先王”即历史上那些文物事迹湮灭无闻的圣王,有如前述。其迹湮灭无闻,如何“法先王”?《荀子》的回应,是通过后王粲然之迹推知先王治道,然后再予取法。《不苟》云:
故君子……所听视者近而所闻见者远。是何邪?则操术然也。故千人万人之情,一人之情是也;天地始者,今日是也;百王之道,后王是也。君子审后王之道,而论于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议。
其言有“术”,可由已知信息推求未知信息:后王的礼法制度即属已知,且是探究先王等往昔圣王的途径。具体方法,可透过《荀子》的相关表述窥见。《不苟》《儒效》与《天论》各篇,均将此推知术建立在荀子学派变贯并举的史观上:一方面承认历史具体情势的变化,如《儒效》言及“万变”、《天论》言及“应变”等;一方面指出历史流变过程中有一以贯之的内容,亦即人类社会某些更为深层的、更为基本的秩序与原则,如《儒效》所谓“百王之道,一是”中的“一”。因而,推知之术就是在历代后王粲然可知的礼文制度中考求此类稳定的内容,再将后者推至先王的时代。此法颇为粗疏武断,其推得的先王礼法,仅限“百王之所同”领域内的少许重要原则。与上述推测相符的是,《儒效》云“法先王,统礼义,以浅持博,以古持今,以一持万……是大儒者也”,其以能持博之“浅”、能持万之“一”等形容可探究而得的先王治道,彰显后者地位紧要而篇幅简短。
最后,后王的礼法制度,不仅可据以推知先王之迹,且可径自指导当下各类政治举措。“法后王”的具体方法,颇似推知先王之法。《天论》云:“一废一起,应之以贯。理贯,不乱;不知贯,不知应变。”引文(基于前述变贯并举的史观)指出,文物制度中应对具体情势的内容需随具体情势的变动而变动。人类更为基本的秩序——保持高度稳定的“贯”,则需坚持。统揽《荀子》各篇,“贯”以其(在礼法制度的结构中所处)地位的不同,又可分为两种:一为“变”(随时势变动)的部分在变动过程中所遵循的更高级的、稳定的原则,如《礼论》“给人之欲”等;一为不同时代文物制度中始终稳定的具体内容,如《礼论》云“故三年之丧,人道之至文者也,夫是之谓至隆,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也”,此丧礼即属“贯”中的一项具体内容而非指导礼法变革的高级原则。面对变、贯二者,“理贯应变”是荀子因循损益各类既有礼法、原则的方法。理贯,是指考察、梳理礼法历时性流变中一以贯之的稳定内容;应变,是指礼法损益等应对当下具体事务之举;理贯以应变,即以稳定不变的高级原则指导当下具体举措,以应对新的具体情势。面对那些“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的具体条目,新举措亦应谨慎遵循——这就是“法后王”的具体方法。“法后王”的含义,则为从后王粲然可知的礼法制度中探寻稳定不变的部分,进而以后者为依据,指导当下各类举措。反之,违背或无视此一原则,托名先王而炮新规,非变更礼法制度的正确方法。如《非十二子》云“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韦政通先生释曰:“荀子并不以法先王为非,只是嫌其只知‘案往旧造说’,不能就先王之遗绪而知其统类,以充分发挥其功能。 ”韦先生所言“知其统类”,即指向此种以贯统变的结构。
根据上述讨论,可进一步明确“法后王”的某些特征:
其一,“后王”是过往的圣王,不是当代或未来的圣王。《非相》所谓后王之迹的“粲然”,是“以贯应变”的方法所决定的。具体言之,以贯应变首先需要明辨贯、变,贯、变仅能从历史上粲然可知的礼法制度中察见。《天论》明言“贯”的探求方法:“百王之无变,足以为道贯。”郝懿行释 “道”为“礼”,道贯即礼法制度之“贯”。“贯”既为历经漫长的时代流变而保持高度稳定的礼法制度或原则,那么,只有通过圣王那些清晰可辨的礼法制度,或因革典章的举措,后人才有分辨变、贯的可能。在此可知性的角度上,“后王”须是过往或当下的圣王。然,荀子却不认为其所处“当下”存在“圣王”——由《正名》所云“今圣王没,名守慢,奇辞起,名实乱”可证,故“后王”仅限于往昔圣王:盖(相对前儒所谓唐虞)礼法制度可知者多在近古,故言“后王”。前贤以“未来之王”界定“后王”,难点正在可知性上:未来圣王的礼法制度无从知悉,“法后王”与《荀子》所指责的“诬欺”(语出《非相》)、“造说”(虚构无事实根据的主张,语出《非十二子》)本质上又有何差异?而以“当代之王”释“后王”,又与前引《正名》之文正相抵牾。
其二,“后王”泛指故事粲然的列位圣王。该词有似西文的复数形式,而不以特定朝代或个人为界限。以贯应变的主张是将“礼法如何因革”这一重大问题,诉诸对历史流变过程的筛选:在这一有待考察的历史过程中,不同时期的典章与举措,内容愈充分、愈详细,“贯”也就越有可能被发现;在往昔圣王礼法制度可知可考的前提下,时间的跨度越大,“贯”也就越有可能被发现。是以,一个承载诸多礼法制度的时间纵深,是考求贯、变的必要条件。而“后王”的外延,应将礼法制度粲然可知的列位圣王悉数囊括:在礼法制度可知可考的情况下,放弃取法某一历史时段的圣王,是违背常理的。而《儒效》“道过三代谓之荡,法贰后王谓之不雅”与《王制》“道不过三代,法不贰后王”中,“三代”与“后王”皆文义互足,可印证此说:其泛言“三代”而不言“周”,盖虑及“后王”的时间界限未必狭如后者。他篇称美周制,可证周制属“后王”范围,却不足证“后王”仅限周制。如前引“欲知上世,则审周道”,“欲观千岁,则数今日”等,是为解释“以近知远”而列举极端,打出形象的比方。又如《正名》云“后王之成名,刑名从商”,“刑名从商”为“法后王”不限于周制的明证。“后王”不受特定朝代限制,更非特定人物,其限定因素应仅有王迹能够知悉。故如“本朝圣王”说、“周王”说、“周初列王”说、“文武”说、“周公”说等,以特定王朝或个人作界限,有将“后王”(在未有充足证据的情况下)拘于狭小外延的风险。
其三,“法后王”兼具因、革两方面意义。“法后王”的具体方法既为“以贯应变”,“贯”自属于对旧制旧物的因循,循旧的目的,却在于应对新问题。《儒效》云:“法后王而一制度。 ”“法后王”与“一制度”对举,以二者皆强调礼法制度的修建。立法改制(就其性质而言)既为创建新规则,又需取法旧制度,有如上述。此即章太炎先生“綦文理于新,不能无因近古”,以及牟宗三先生“就礼宪发展之迹,本其粲然明备者以条贯之,以运用于当时”所强调:若对旧制度全无因循,则应排斥师先圣、法先王后王;若现实无异于旧情势,则沿袭旧制即可,“法后王”同样失去价值。此亦前贤仅言革不言因,与只言因不言革诸说的难点:如赵俪生先生之“理想说”,是将“法后王”置于作为一个整体的旧制度(“周道”)的对立面上,“法后王”对“贯”的探求、对旧例的因循,在其解释中全然无法体现。
综上,“后王”泛指礼法制度或统治举措可供察考的往昔圣王;“法后王”是主张从这些圣王的旧制中发现稳定不变的原则,再以这些原则指导当下的行动。如果说荀子学派试图创建一学说系统,以为变动不居的各个时代始终如一地遵循,那么,“法后王”因其超越特定时代的普遍价值,或可成为此系统的一项重要内容。
三、“法后王”所蕴含的礼治精神
本文所谓“礼治精神”,是指(在今天看来)《荀子》礼治思想中那些具有超越特定时代之价值的原则与宗旨;所谓《荀子》礼治思想,是指《荀子》文本所彰示或蕴含的以礼义为价值评判基础的政治思想。
某种意义上,“法后王”一说所蕴含的礼治精神,突出表现为针对统治者损益礼法、颁布命令等一切统治举措而树立的“更高的原则”。与那些主张统治者 “不和于俗”、“不谋与众”(《商君书·更法》)的原则相比,荀子学派强调各类政治举措师法历代圣王,自含有以前述“更高的原则”约束统治者的意图。首先表现在力求“变外之贯”(历史上长期稳定的礼法内容)立于统治者支配权之外,使某些基本的社会秩序不因统治者变换不居的命令而损毁。此类不可改动的礼法所编织起来的规则、惯例系统,不论内容是否细致完备,(较全无此类规则而言)皆可于一定程度上为人民设置一相对稳定的、可供预期的规则框架,人民可据此框架规划生活。其次,探究“变中之贯”(具体礼法损益所循的高级原则)以指导各类统治举措,以求统治者能够遵循此类原则,而非全然放纵一己私意。这一为统治者树立更高原则的创举,盖因彼时代各国所流行的“变法”运动而起,以防传统礼法所贯彻的“仁爱”等基本宗旨于此一时代凋零。合此两点,“法后王”之说以历史过程对文物制度的筛选,来约束统治者依照己意篡换礼法制度;力求礼法基本的框架与精神独立于统治者意志之外,力避片面强调变法而无视变法行为本身亦应予规范,防止(一如法家诸子所倡的学说那般)使礼法制度沦为统治者弄权的工具。
进而言之,如何责成统治者在各类行动中遵循此种更高的原则?《荀子》将此问题置诸责成统治者遵循礼义的整体框架,此框架先以统治者是否遵循礼义来评判其统治的正当性,进而鼓吹对失去正当性的统治者予以征诛。
就前一步骤而言,《不苟》宣称“礼义之谓治,非礼义之谓乱”,统治的正当性仅源于遵循礼义,不符合礼义的统治,即使维持着某种秩序,仍当划归“乱”。此一判断标准,非对即错、非治即乱,无中间地带,与《慎子·威德》所谓“法虽不善,犹愈于无法”正相对立。在这一点上,荀子竟稍有近于西方自然法学“恶法非法”的性格。而慎子之说,流于无原则的推崇“法”(实为统治者的命令)的效力,使“法”濒于人主支配臣民的工具。
就后一步骤而言,《荀子》主张武力攘除丧失正当性的统治,意在以外部威胁迫使统治者遵循礼义秩序。如《正论》云:“汤、武非取天下也,修其道,行其义,兴天下之同利,除天下之同害,而天下归之也。桀、纣非去天下也,反禹、汤之德,乱礼义之分,禽兽之行,积其凶,全其恶,而天下去之也。天下归之之谓王,天下去之之谓亡。故桀、纣无天下,而汤、武不弒君。”以桀纣与汤武为例,言桀纣之流丧失统治的正当性而成独夫,自宜诛灭。以武力摧灭背离礼义的统治,成为荀子之说维护礼义秩序、责成君主遵循礼法的终极主张。
于是,荀子学派以“法后王”责成统治者守礼,以合乎礼义与否评判统治的正当性,以汤武革命除乱复治,勾勒出一幅礼义至上的秩序图景,成为其政治思想的精神所在。然而,这一思想构造远非绵密无缺:首先,“贯”的内容尚未清晰具体,招致那些“稳定的高级规则”在实际操作中易于为统治者随意剪裁取舍,而旁人难以判断监督。此种剪裁取舍,将使礼义成为统治者的粉饰而非约束,如梁启超先生所言“礼之名义为人所盗用,饰貌而无实者,吾侪可以触目而举证矣”。其次,除将汤武革命作为外部的责成因素胁迫统治者就范之外,在和平的政治运作中未能设置有效的制约力量。牟宗三先生评曰:“位愈高,控制之外力愈微,一旦将此超越之者拆穿而无睹,则君即成全无限制者;祸乱即从此生;而革命、独夫、自然天命之竞争,亦随之必然来矣。故古人对君除责之以自律外,盖无他道。”其言包含荀学在内的中国古代各派思想,终不能以和平方式责成君主遵守礼法,故不得不依靠自下而上的革命,或可遇不可求的王者之兵。传统社会是以无从逃脱和平与战乱相互交迭,陷于“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治乱循环。
总之,古今学者聚讼纷纭的荀子“法后王”说,实是主张以历史上高度稳定的礼义原则指导当下各类政治举措。其所蕴含的礼治精神,突出展现在为统治者的行为制定更高的规则上。其至关重要的价值,在于以遵循礼义评价统治的正当性、以武力攘除不正当的统治者等观点,共同建立起荀子学派礼义至上、君权须遵循礼义的思想结构。这一礼义至上的秩序图景,为先秦儒家政治思想的精华所在。
注释:
(1)观点转引自陈礼彰《荀子“法后王”说究辨》。
(2)《章太炎全集》第一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6-7。 “《春秋》约而不速” ,鄙意法《春秋》与《劝学》抵牾。
(3)韦政通:《荀子与古代哲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7:14-15。 韦先生虽与前文“周道”说重叠,然其强调“周道乃是百王之法累积损益而成,故后王足以代表百王之道”。他对积累的强调与单纯“法周道”说有所差异,故将其列入此处。
(4)丁福保主编《说文解字诂林正补合编》,台北:鼎文书局,1983,“法”字条目。
(5)“三年之丧”等具体条目能够稳定不变,是因有“不变易”的统贯精神。《礼论》对此多有说明。如“三年之丧,称情而立文,所以为至痛极也;……哀痛未尽,思慕未忘,然而礼以是断之者,岂不以送死有已,复生有节也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