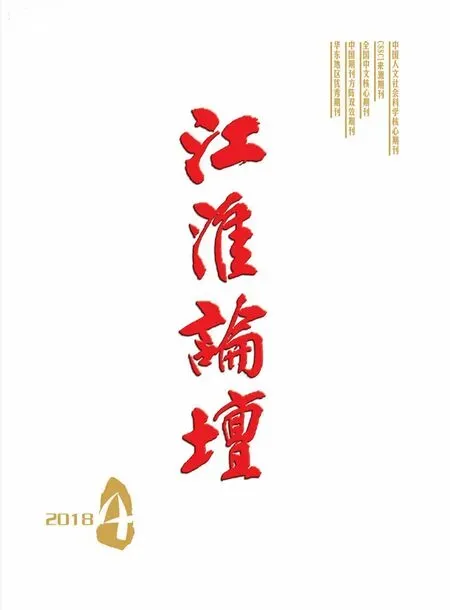从批判性思维的观点看公孙龙“白马论”*
2018-11-12杨武金
杨武金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北京 100872)
公孙龙(约 B.C.320—B.C.250),战国时期赵国人,著《白马论》,论证“白马非马”命题。《荀子》《吕氏春秋》《史记》等基本上都认为公孙龙的论证有理由、论证充足,不过,目的不纯,是为了“欺惑愚众”。冯友兰通过西方哲学或西方逻辑来看问题,认为公孙龙“白马非马”论片面强调白马和马的对立,割裂了自相与共相的关系。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公孙龙的“白马非马”论不是诡辩,比如曾祥云、刘志生就通过符号学的观点分析,认为公孙龙的“白马非马”论是“合理命题”,不是“诡辩命题”。周礼全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逻辑”条指出,公孙龙是根据“马”和“白马”这两个概念的外延和内涵都不同来论证“白马非马”命题的。从外延看,白马只是白马,而马还包含黄马、黑马等;从内涵看,马只名形,而白马既名形又名色。因而,他认为公孙龙虽然背离了日常语言的意义,但论证是严密的。从批判性思维的观点出发,考察公孙龙“白马非马”命题及其论证,公孙龙的“白马非马”论证虽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从根本上存在着形式方面或者非形式方面的逻辑错误。
一、“白马非马”论证
批判性思维是人们运用多种思维技巧和方法来质疑、分析和评价的认知活动。它以分析一个论证作为出发点,具体包括3个方面:一是这个论证从前提到得出结论的过程是否合乎逻辑,即推理的前提能否足够得出结论;二是这个推理的前提是否真实,有无虚假前提存在;三是所运用的概念是否有效。
首先,公孙龙关于“白马非马”的第一个论证。
《公孙龙·白马论》说:“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马非马。 ’”马是关于形体的名,白是关于颜色的名。关于颜色的名不是关于形状的名,所以,白马不是马。“马”这个名,是就形(实体)来说的,而“白”这个名则是就色(属性)来说的。因此,公孙龙得出结论“白马非马”。具体推理过程如下:
马是名形的,
白是名色的,
名色不是名形,
———————
所以,白马非马。
这个推理通过进一步整理后,可得:
马是名形的,
白不是名形的,
———————
所以,白马非马。
从三段论推理的格式来看,上述推理属于第二格的三段论,即区别格的三段论。结论否定,前提中有一个否定,形式上没有问题,推理是充足的。问题在于,小项即结论的主项在前提中是“白”,在结论中是“白马”,整个推理存在“四概念”或“四词项”错误,即偷换概念了。要避免这个错误,需要把前提中的“白”等同“白马”。这就进入了公孙龙关于“白马非马”的第二个论证。
其次,公孙龙关于“白马非马”的第二个论证。
《公孙龙·白马论》说:“马固有色,故有白马。使马无色,有马如已耳,安取白马?故白者非马也。白马者,马与白也。马与白,马也?故曰:白马非马也。”马本来就有颜色,所以才有白马这个名。假如马没有了颜色,那就只有马而已,又何言求取白马?所以白马不是马。白马这个名,是马和白的结合所规定的。马与白的结合,难道是马吗?所以,白马不是马。“白马”这个名或概念是由 “白”和“马”共同构成的。也就是说,既然“白马”这个概念在内涵上既名色又名形,而“马”这个概念在内涵上仅仅名形,因此,公孙龙得出结论“白马非马”。
但是,如果“白马”这个概念名色也名形,那么通过有效推理只能得出和公孙龙完全不同的结论。也就是说,从白马这个概念既名色也名形只能推出白马这个概念名形,即白马是马,而不能推出白马这个概念不名形,即白马非马,否则就会出现“白马马也”且“白马非马”的逻辑矛盾。推理过程如下:
∀x(Wx∧Hx→Hx)(白马是马)
这个推理属于命题推理中的联言推理。其中,W 表示“白的”,H 表示“马”,x表示变量,∀表示全称量词“所有”,∧表示合取量词“并且”,→表示“推出”。整个推理的意思是说,对任何对象x来说,如果x是白的并且x是马,则x是马。同理可得,对任何对象x来说,如果x是白的并且x是马,则x是白的。
但是,公孙龙的结论是绝对推不出来的,因为∀x (Wx∧Hx→¬Hx)(白马非马)(其中,¬表示否定词“非”)是一个无效的推理形式。也就是说,对于对任何对象x来说,如果x是白的并且x是马,则“并非x是马”这个结论是推不出来的。
再次,公孙龙关于“白马非马”的第三个论证。
《公孙龙·白马论》说:“求马,黄、黑马皆可致;求白马,黄、黑马不可致。使白马乃马也 ,是所求一也。所求一者,白者不异马也。所求不异,如黄、黑马有可有不可,何也?可与不可,其相非明。故黄、黑马一也,而可以应有马,而不可以应有白马,是白马之非马,审矣! ”如果有人要马,可以给出符合条件的黄马或者黑马;但是如果要白马,就不能给出黄马或者黑马了。假如白马是马的话,那么要一匹马和要一匹白马就是一回事了。既然要一匹马和要一匹白马就是一回事,则白马和马就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如果要白马和马没有什么区别,那么给出黄马、黑马,有时是可以的,有时则是不可以的,这又作何解释呢?可以与不可以,其不相同是明显的。所以,同是黄马、黑马,可以说是有马,但不可以说是有白马。这白马不是马的道理,可以说已经非常明白了。这里,公孙龙认识到了,在外延上,马可以包含黄马、黑马,而白马只是白马,不能包含黄马、黑马。但是,公孙龙由此得出“白马非马”的结论却是错误的,整个推理是不充足的。具体推理过程如下:
黄、黑马都是马,
黄、黑马不是白马,
————————
所以,白马不是马。
这个推理属于三段论第三格的AEE式,大前提是MAP,小前提是MES,结论是SEP,整个推理是一个无效推理。大项P在前提中不周延,而在结论中变得周延了。更直观地说,上述推理的小前提倒过来说就是“白马不是黄、黑马”,于是推理就变成了:“白马不是黄、黑马,而黄、黑马是马,所以白马不是马。”白马不是黄、黑马,难道就能说不是马了吗?不是黄、黑马,还可以是别的颜色的马啊!显然,公孙龙的结论必须假设“只有黄、黑马才是马”或者“马就是黄、黑马”这样的虚假前提才可能被推导出来。
然后,来看公孙龙关于“白马非马”的第四个论证。
《公孙龙·白马论》说:“马者,无去取于色,故黄、黑皆所以应;白马者,有去取于色,黄、黑马皆所以色去,故唯白马独可以应耳。无去者,非有去也,故曰:‘白马非马。 ’”马对颜色没有去此取彼的选择,因此黄马、黑马都可以认为是马;白马对颜色有去此取彼的选择,黄马、黑马因其所具有的颜色而被排除,因此唯独白马可以认为是白马。对颜色没有去此取彼选择的马,并非对颜色有去此取彼选择的白马。因此,结论是“白马非马”。推理过程如下:
马没有去取的要求,
白马有去取的要求,
—————————
所以,白马非马。
这个推理是三段论第二格的EAE式,大前提为PEM,小前提为SAM,结论为SEP。这个三段论的结论否定,前提有一个否定,因此,整个推理能满足充足性,是有效推理。但是仔细分析中项的含义,就会发现推理存在“四概念”问题,即存在偷换概念的错误。“去取”在大前提中的含义是“去”所有的颜色和“取”所有的颜色,而在小前提中则是“去”除白色以外的所有颜色和“取”白色。于是,整个推理准确地表达出来就是:“马是去除了所有的而没有取任何的颜色,而白马是去除了白色以外的所有颜色而取白色,所以,白马非马。”推理中的偷换概念情况是明显的。
最后,来看公孙龙关于“白马非马”的第五个论证。
公孙龙问:“以有白马为有马,谓有马为有黄马,可乎?”就是说,“你方将有白马视为有马,那么将有马说成是有黄马,可以吗?”客方回答说“未可。”即“有马异于有黄马”,有马和有黄马不一样。这时候,公孙龙论证说:“以‘有马为异有黄马’,是异黄马于马也;异黄马于马,是以黄马为非马。以黄马为非马,而以白马为有马,此飞者入池而棺椁异处,此天下之悖言乱辞也。 ”这段话翻译为现代汉语就是:“既然有马与有黄马不一样,所以有黄马与有马也就不一样;有黄马与有马既然不一样,因此,黄马不是马。那么,你方既认为黄马不是马,而又主张白马是马,这不就如同飞鸟进到了水池而棺椁分置两处的情况吗?这实在是矛盾而混乱的言辞啊。”既然“黄马非马”,那么,同理也可以说“白马非马”;如果既说“黄马为非马”,又说“白马为有马”,不就自相矛盾了吗?主客论辩过程中所用到的推理情况,可以做如下分析:
客方回答推理:
有白马为有马,
(有马异于有黄马),
——————————————
所以,不能说“有白马为有黄马”。
公孙龙的反驳:
有马异于有黄马 (假设客方的隐含前提为真),
所以,异黄马于马,即黄马为非马,
———————————————————
因此,白马非马(与客方的前提“有白马为有马”矛盾)。
公孙龙在这一反驳中的错误,关键处是从“异黄马于马”推出“黄马为非马”,将“异于”(不一样)和“非”(不是)等同,出现了偷换概念的错误。他的结论只能反驳“有白马不异于有马”(有白马与有马没有差异),却不能反驳“有白马为有马”(白马是马)。
综上所述,公孙龙虽然看到了无论从内涵上还是从外延上讲,白马和马这两个名之间都存在着差异或不同,认识到了矛盾的命题不能两立,但他的上述论证整个来说却存在诸多逻辑错误。这些错误的存在使得公孙龙的论证或者在从前提推导结论的过程中缺乏充足性,即前提的真不能传递到结论的真;或者由于使用了无效概念或者虚假前提,从而使得论证的成立得不到保证。
二、“白马非马”论题
批判性思维是从分析论证开始的,但对于一个论证来说,其论题最为重要。在反驳论题、反驳论据和反驳论证方式三者之中,反驳论题是最主要的。所以,批判性思维需要考察一个论证的论题即结论是否合理。
“白马非马”这个违背常识的论题,很可能在公孙龙之前就有人讨论过。《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记载:“兒说,宋人,善辩者也。持白马非马也,服齐稷下之辩者。”宋人兒说就坚持“白马非马”命题而常与别人辩论,并曾经把稷下学者辩服。《战国策·赵策二》记载:“夫刑名之家,皆曰白马非马。 ”刑名之家即名家,他们都说“白马非马”问题。这也就是说,很可能公孙龙之前就已经有人提出了“白马非马”论题,而公孙龙坚持这一论题,并进行了论证。
如前所述,从公孙龙的论证逻辑来看,既然可以得出结论“白马非马”,当然也可以得出结论“白马非白”,即白马既非白也非马。《公孙龙·白马论》说:“以‘有白马不可谓无马’者,离白之谓也;不离者,有白马不可谓有马也。故所以为有马者,独有马为有马耳,非有白马为有马。故其为有马也,不可以谓‘马马’也。曰‘白者不定所白’,忘之而可也。白马者,言白定所白也,定所白者非白也。 ”认为论敌“白马是马”的主张,是一种把“白”从“白马”中撇开来的说法。而公孙龙则持“不离”的主张,即不把“白”撇开来,也就是“守白”。“不定”在某个具体事物上的一般的“白”,忘记它也是可以的,但“白马”的“白”则是“定”在了具体事物上的“白”,这个“白”不是一般的白,而只能是“白马”的白。于是,白马就是白马,而马就是马,白就是白,白马非白并且白马非马。概念的外延之间只存在同一关系和全异关系,不存在其他的关系。
公孙龙主张“白马非马”,是其正名政治意图的体现。《公孙龙·名实论》说:“天地与其所产焉,物也。物以物其所物而不过焉,实也。实以实其所实(而)不旷焉,位也。出其所位非位,位其所位焉,正也。”“物”是天地及其所产生的一切事物。“实”是事物自身所固有的质的规定性。“位”是事物的本质所规定的位置、界限,是质和量的统一,相当于“度”。超越了“度”的界限叫“非位”。保持“度”的界限叫“正”。于是,正名的结果和标准是“其名正则唯乎其彼此焉。谓彼而彼不唯乎彼,则彼谓不行;谓此而此不唯乎此,则此谓不行。其以当不当也。不当而当,乱也。”彼、此之名都要有所专指。如果称呼那个东西为 “彼”,而“彼”不专用于那个东西,则“彼”的称呼就不能成立;称呼这个东西叫“此”,而“此”不专用于这个东西,则“此”的称呼也不能成立。把这认为恰当,是不恰当的。不恰当而认为恰当,是逻辑混乱。因此,正名的原则就是,“故彼彼止于彼,此此止于此,可。 彼此而彼且此,此彼而此且彼,不可”。称那个东西为“彼”,又专限于那个东西,称这个东西为“此”,又专限于这个东西,这是可以的。“彼此”之名既是彼又是此,“此彼”之名既是此又是彼,这是不行的。公孙龙正是为了实现“位其所位”的政治主张,才提出“唯乎其彼此”的正名标准,才有了“白马非马”的论题。正如钱穆所说:“惠施喜欢把异说成同,公孙龙却喜欢把同说成异。”公孙龙的政治主张和政治目的,使得他喜欢把“同”说成“异”,于是就有了“白马非马”的论题。
总之,公孙龙“白马非马”论证,完全可以说是其《名实论》中“唯乎其彼此”的正名理论的一次具体应用,当然也是其《指物论》中“物指”(相当于“白马”)与“指”(相当于“马”)之间关系的一个举例说明。也就是说,公孙龙的“白马非马”论题,重在强调一名一实的正名理论,让每一个实际存在的事物当然也包括政治生活中的每一个人都要做到“位其所位”,最终目的是为“正名”的政治主旨服务的。
三、“白马论”的论证方式
如前所述,批判性思维就是要在充分质疑的基础上提出问题,进而细致地对问题进行分析并最终解决问题的思维或认知活动。批判性思维虽然是一种认知活动,但认知活动未必就是批判性的,只有反思性的思维活动才是批判性思维。反思性的思维是在质疑的基础上进行的认知活动。公孙龙的“白马论”部分体现了批判性思维的反思性特征。
“白马论”的论证是以设主客问答的方式进行的。“客”代表问难的一方,从人们惯常理解的角度出发,针对公孙龙的论证漏洞不断提出疑问。“主”代表公孙龙的观点,对问难者的提问一一给予回答,从不同角度论证“白马非马”这个论题。事实上,“客问”不过是公孙龙的设计,完全是公孙龙为了自己论证上的便利,所列举出来的一般常识中会问到的问题而已。不过,有些问题还是十分尖锐的,确实与人们常识中会问到的问题相符合。例如,“以马之有色为非马,天下非有无色之马也。天下无马,可乎?”马有了颜色就成了“非马”,但是世上没有无色的马啊,那世上就没有马了?问题非常尖锐。公孙龙充分考虑到了论敌的基本观点,这是在对自己观点进行了深入反思的基础上才能做得出来的。由此可见,公孙龙的“白马论”体现了批判性思维的反思性特征。
公孙龙在论证中熟练地应用了归谬法。归谬法的论证过程是:首先假设某个命题成立,然后由这个命题推导出明显的矛盾或者显然荒谬不可信的结果,从而下结论说所假设的命题不能成立。如前所述,公孙龙在论证中,首先假设客方的观点是正确的,“有白马为有马”、“有马是有黄马”等等;然后顺着客方的观点进行推理,最后得到“白马非马”与“有白马为有马”相矛盾的结论。显然,从所假设的前提出发,却得到了矛盾的结论,因此,所假设的前提不能成立,即“有白马为有马”不能成立。
公孙龙论证的根本问题是,他的立场和目的有问题。批判性思维不仅仅是一种技巧,更是一种态度和精神,其核心是求真、公正和反思。公孙龙的“白马非马”论证虽有较强的反思性,但公正性和求真性不足,其正名理论完全是为了贯彻自己的政治立场。“善于发现别人论证的缺点而将其一棍子打死,以使自己的理论免受严格考察,这是有批判性思维技巧的学阀,越这样就越阻挡认识的发展。 ”
《不列颠百科全书》中记载了古希腊的智者学派,被同时代的人批评为“不是追求真理而是在辩论中用不正当的手段达到取胜的目的”。诡辩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目的不纯,为了取胜完全可以忽略求真或者求公正。爱利亚学派的芝诺,为了论证自己的哲学观点,别出心裁地为“阿基里斯(古希腊跑得最快的人)追不上龟”、“飞矢不动”等虚假论题进行论证。公孙龙的“白马非马”论证,也类似地是为了实现其“位其所位”的政治目的而进行的诡辩。如荀子所言,诡辩者的论证虽然也“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但最终目的是为了“欺惑愚众”。在诡辩者的心目中,由于取胜被放在了第一位,而求真或者求公正被放到了次要的位置,故,他们在论证中也就不可避免地会存在着如前所述的“推不出”或者“偷换概念”等等诸多逻辑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