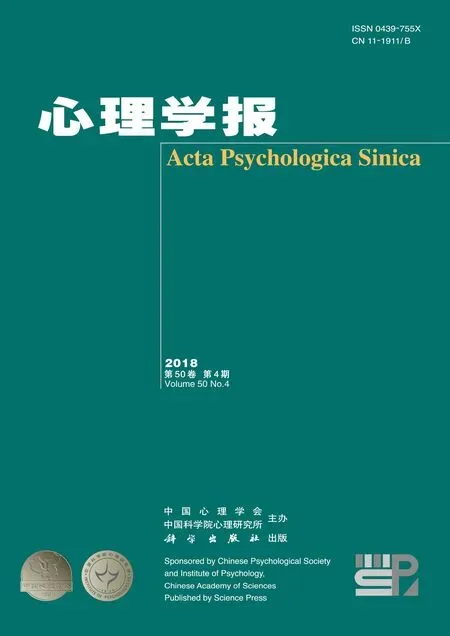身体与认知表征:见解与分歧*
2018-11-11叶浩生麻彦坤杨文登
叶浩生 麻彦坤 杨文登
身体与认知表征:见解与分歧*
叶浩生 麻彦坤 杨文登
(广州大学心理与脑科学研究中心, 广州 510006)
对于身体的不同理解促使认知心理学形成了不同研究取向。经典认知心理学视身体为不同于心智的生物物理实体。认知表征则成为沟通心智与包括身体在内的外在世界之间联系的“桥梁”。在经典认知心理学那里, 心智是一种运算, 运算的内容则是认知表征。认知表征是符号性的、抽象的, 与身体的构造和感觉—运动通道无关。身体似乎仅仅是认知表征的“载体”或“容器”。具身认知则强调了身体在认知过程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具身认知中的“温和派”视身体为心智中的身体, 认知在其根本上是一种身体经验。因此, 认知表征不是抽象的, 而是身体格式的, 是身体特定感觉–运动通道提供的具体身体体验。心智是一种运算, 但运算的内容不是抽象符号, 而是具体的身体经验。具身认知中的“激进派”则主张彻底抛弃“运算”和“表征”。在激进派那里, 认知是被身体作用于世界的活动塑造出来的。认知是为了解决问题, 而不是为了形成认知表征。基本的心智不涉及内容, 换言之, 基本心智过程不涉及认知表征。认知在本质上是一种具身的行动。
认知; 表征; 具身认知; 身体; 心智; 生成论
1 引言
身体与认知表征关系的探索要求我们首先了解身体(body)的基本涵义。什么是“身体”?怎样理解“身体”?传统上, “身体”在心理学研究中并不处在中心地位。毕竟心理学是研究“心智” (mind)的科学, 身体在其中至多也就是个“生理基础”, 更多地属于生理学和神经生物学范畴。因此, 心理学没有必要给予“身体”以过多关注。然而, 随着具身认知的兴盛(Glenberg, 2015), 心理学家改变了对“身体”的看法。身体由边缘化的“生理基础”一跃成为心智的塑造者, “大脑并非供我们解决问题的唯一认知资源。我们的身体和身体知觉指导下的动作在达到目标的过程中完成了大量工作, 替代了复杂内部心理表征的需要” (Wilson & Golonka, 2013, p.1)。“身体”既然由过去的“边缘”成为现代认知心理学的“中心”, 那么就有必要厘清各种有关“身体”的理解, 为身体和认知表征之间关系的探讨奠定必要基础。
在认知心理学的发展过程中, 有关“身体”的理解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或者存在着这样几种观点:
第一, 基于二元论(dualism)的理解。自科学心理学创立到20世纪80年代末, 二元论观点一直在心理学中占据支配地位。二元论主张身体和心智是两种性质不同的实在1。身体属于物质范畴, 心智属于精神范畴, 两者分属不同研究领域。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心智不同于身体这一事实似乎显而易见、不证自明(McFarlane, 2017)。实验心理学的创立者冯特的“身心平行论”就建立在这样一种理解基础上。他指出: “心理现象不可能像结果对原因那样涉及身体现象……对心理现象的解释只能通过适当的心理现象来进行……” (Wundt, 2003/1894, pp.481−482)。身体由骨骼、肌肉、皮肤、血液、神经、体液和各种生物化学成分构成, 这是一个“物” (thing)的领域, 属于物理和生物范畴。心智则不同: 心智是身体的“灵魂”, 是肉体的组织和控制者, 知觉、记忆、学习、目的、动机、思维、情绪、气质和性格等构成了心智的主要表现。心智就其性质来说是“非物质”的, 属于心理学、认知科学等精神科学范畴。长期以来, 主宰心理学和认知科学的主流观点就是这样一种基于二元论的身体观。在这样一种视角下, 身体仅仅作为“有机体”而存在, 是客观世界众多物体中的一个物体。如果以这样一种观点看待身体, 则很难理解为什么心智是“具身” (embodied)的, 毕竟从常识上来看, 我们从意识上超越了身体: 身体在意识的控制下而不是相反。
第二, 基于现象学的理解。“哲学思维, 即现象学的思考一直在强调身体在心智中的角色” (Haken & Tschacher, 2011, p.79)。受梅洛·庞蒂身体现象学的影响, 从80年代末期开始, 一些认知心理学家开始重新思考“身体”在心智中的作用。现象学追求对客体的主观体验。达到的是主体的“纯粹意识经验”。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则将意识经验置换为身体体验, 认为组成心智的意识经验实际上由各式各样的身体体验构成(Merleau-Ponty, 2012)。残疾人的“幻肢”现象有力说明了这一点: 为什么肢体残缺的人仍然能感觉到缺失肢体的疼痛?疼痛的意识体验怎样产生的?如果残肢是疼痛感必要的生理基础, 那么残肢的缺失为什么不能导致疼痛感的消失?基于现象学的理解, 是因为残肢虽然不存在了, 但残肢的运动经验依然存在, 所以才有了疼痛的意识体验。在这里, 身体是经验中的身体, 并非由骨骼和肌肉等构成的物质实在。我们对于身体的意识是一种本体感受。这种本体感受的基础是身体经验, 是通过身体的位置和状态、肢体的动作和姿势而形成的。认知之所以是具身的, 是因为认知在本质上并非抽象符号的加工或运算, 而是由身体经验构成(Johnson, 2013)。退一步说, 即使认知是一种加工或运算, 那么它加工的也是特定感觉和运动通道提供的身体经验。“心理编码主要或从根本上利用的是个人身体状态和活动的本体感受和表征……” (Goldman, 2012, p.71)。这种经验是身体化的, 或者说是身体格式的(body-formatted)。视觉、听觉、触觉、和皮肤觉等特殊感觉通道提供了认知加工的素材。所谓身体意像(body image)、身体图式(body schema)就是基于现象学视角对身体的理解。
第三, 基于生成论(enactivism)的理解。生成论是近年来认知科学中激进具身认知的典型代表。它源于1991年出版的《具身心智: 认知科学与人类经验》(Varela, Thompson, & Rosch, 1991), 近年来已成为具身认知中一股强劲思潮(Hutto & Myin, 2017)。生成论主张认知并非大脑对外在世界的内部表征和表征的加工或运算, 相反, 认知是行动的制造者, 产生于行动, 服务于行动。认知源于有机体与环境的互动(Ward, Silverman, & Villalobos, 2017)。有机体是行为动作的有机体, 有机体通过独特的身体结构和身体活动作用于环境; 环境也并非独立于有机体的客观环境。环境是有机体选择和动作的结果。有机体的行为能力造就了它独特的生存环境。因此, 认知并非有机体被动地从客观环境接受信息, 然后把这种信息转换为对环境的表征。人们不是表征世界, 而是“生成” (enact)一个世界。身体作用于环境的活动决定了认知的性质和方式(Stewart, Gapenne, & Di Paolo, 2014)。从生成论的视角理解身体, 则身体既不是心智的“载体”或“容器”, 也不是一种身体感受或体验。“我们不像计算机: 机器总是耐心和愉快地等待着他人的开启和指令。我们则是由起伏不定、不断扩展的欲望和欲望激发出来的各种身体动作所构成……我们之所以有大脑, 主要是因为大脑要为我此刻关心的问题找到解决的方法” (Claxton, 2015, pp.37–38)。因此, 从本质上讲, 身体是一种活动。这种活动发生于自然环境, 也发生于社会文化环境。身体既是生物的有机体, 也是社会的有机体, 带有文化的深刻烙印(Ziemke, 2016)。
对身体的三种不同理解, 造就了三种对认知表征的认识, 也形成了经典认知心理学、温和的具身认知和激进具身认知三种不同风格的认知心理学(Gallagher, 2011)。
2 生物有机体的“身体”:认知表征的功能与作用
经典认知心理学视身体为心智的“生理基础”, 认为认知与身体是两种性质不同的实在, 心理学和认知科学的主要任务是探讨内部“心智”怎样从认知上真实表征了包括身体在内的客观世界(叶浩生, 2017)。从本体论上来说, 经典认知心理学认为存在着发生于身体之内, 但是性质上却独立于身体的内部心理过程。知觉、记忆、注意、语言、思维、想象、学习和问题解决等内部认知过程虽然需要一个具有中枢神经系统的身体来实现, 但是认知是功能性的, 包括大脑在内的身体仅仅是实现这些功能的生理底座。“符号的操纵和表征的使用是心智的主要工作” (Dretske, 1995, p.xiv)。认知心理学家的工作是揭示认知表征的内部机制。至于身体和外在行为, 那不是心理学关注的焦点。毕竟认知心理学之前的行为主义曾给予行为反应以太多的关注, 以至于心理学成为没有“脑袋”或“心理”的行为主义。为避免重蹈行为主义的覆辙, 认知心理学家利用了计算机科学的成果: 把大脑比作计算机。大脑的生理构造似乎可作为一种“硬件”来看待, 内部的认知过程则可比拟为计算机的软件。软件功能的实现虽然需要硬件的支撑, 但是两者之间是一种“离散”关系: 软件虽然运行在硬件上, 但硬件仅仅是一个“基础”或“底座”, 它并不能改变软件的性质, 而且软件可以运行在这个硬件上, 也可以运行在其它具有相同性质的硬件上。认知过程一旦被视为“软件”, 则可以脱离身体的束缚, 因为此时的身体仅仅是一种载体或容器, “载着”大脑, “容纳着”心智。即使认知发生于大脑中, 对大脑有着结构上的依赖性, 但彼此之间, 也不是一种必然联系。因为认知作为一种功能可发生于任何具有相同性质的载体上。“人工智能”的产生就是基于这样的理念。这样一来, 认知心理学家开始沉溺于从软件的视角看待内部心理过程, 专注于认知过程怎样“表征”了外在世界。古老的“二元论”在“软件与硬件”的旗号下, 从心理学的角度得到了印证。
“二元论”观念古已有之。古希腊、罗马时期就有了“灵魂”与“肉体”的区别。肉体被视为灵魂的“石棺” (sarcophagus)。早期基督教承袭的就是这样一种贬抑身体、崇尚灵魂的二元论观念。中世纪后, 主宰西方社会的宗教教义则不仅继承了贬抑身体的理念, 而且视身体为灵魂的“敌人”, 直接把灵魂和身体相对立。在长达1500多年的时间里, 灵魂和肉体的区别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 笛卡尔之所以能从认识论上确立二元世界的存在, 所依赖的就是这样一种早已深入人心的世俗观点。
近代法国哲学家笛卡尔被认为是从哲学认识论视角论证心物/心身二元论的第一人(Abrams, 2016)。作为近代科学的创始人之一, 笛卡尔反对神学教条, 试图从认识论上确立人类理性的权威。经过文艺复兴之后, 宗教权威日渐式微, 随之而来的是人们在意识经验起源问题上的困惑。如果真理的观念不是来自上帝的启示, 那么它是从哪里来的呢?笛卡尔的主张是: 意识经验起源于人类固有的理性。通过其著名的“我思故我在”命题, 笛卡尔确立了一个精神的“我”, 与之相对立的是“非我”。“我”是精神的, “非我”是物质的; “我”的特点是能思维, 但是不占有空间, “非我”的特点是占有空间, 但是不能思维。
笛卡尔塑造了一种心身分离的认识论观点。“他把心智视为非物质的实在, 且这种实在同身体几乎没有直接联系。他视人类的灵魂统治着心智, 指导着身体的活动……成为‘肉体渔船的领航员’ ” (Lindblom, 2015, p.23)。经典认知心理学在心身问题上的立场所体现的就是这样一种心身对立的认识论观念。
在经历了行为主义漫长的统治之后, 20世纪60年代心理学迎来了“认知革命” (Gardner, 1987)。行为主义视大脑为不透明的“黑箱”, 意识和心理因为缺乏客观指标而被行为主义所抛弃。心理学研究的是刺激和反应, 成为不需要“头脑”的行为主义。在这段时间里, 心理学家对这种没有“心理”的心理学感到不满, 但是苦于没有适当工具。计算机科学的发展给了心理学家有益的启示: 如果把大脑的生理构造比拟为计算机的硬件, 记忆和思维等认知过程视为计算机的软件, 用计算机模拟方法, 神秘的意识和心理不就有了客观指标吗?而且令心理学家感到欢欣鼓舞的是, 由于意识的神秘性和内省方法的使用, 意识和心理的研究总是带有主观色彩, 与自然科学的客观性相距甚远。如果认知等心理过程是软件性质的实在, 那么由软件的实在性就可以推及认知的实在性, 心理学家就再也不必为客观性而忧心忡忡了。因此, 在计算机科学的影响下, 心理学家开始用计算机软件的性质看待认知过程, 探讨内部认知机制怎样“表征”了客观世界。
经典认知心理学在“大脑有如计算机”的信念指导下, 成功地把研究重心由行为反应转向了大脑, 探讨处于刺激和反应之间的内部认知机制。认知心理学史家Gardner (1987)曾经指出: “如果人造机器可以推理、具有目的、修正其行为反应和转换信息等等, 那么人类确实也值得以同样的方式进行描绘” (p.40)。换言之, 大脑就是一台复杂的计算机, 同计算机的信息加工具有程序上的类似性。既然计算机科学的发展已经提供了那么过得硬的研究工具, 心理学家还有什么理由加以拒绝呢?
但是计算机科学发展史的研究表明, 计算机的原型并不是人的大脑。实际情况是, 二次大战期间, 英国科学家为了获得德国军事情报, 需要对德军电报进行破译。但是电报的破译异常艰难, 需要冗长、枯燥和令人厌倦的数字排列组合。为了减轻大脑的劳动强度, 这些科学家发明了一种机器, 让机器去完成这种枯燥的数字游戏。这种机器就是计算机的原型。从这个角度来说, 计算机并非根据人脑的工作原理设计出来的, 而是为了减轻大脑的负担, 从事那些繁琐、无创造性的工作。但是这样一种设计却被早期认知科学家奉为认知的原型, 以为大脑就像那些无创造性的机器。更为严重的后果是, 如果大脑像计算机, 认知过程是大脑的软件, 则认知发生的唯一场所是大脑: “认知始于对大脑的输入, 结束于来自于大脑的输出, 认知科学完全可以把它的目光放在大脑之内的各种过程……” (Shapiro, 2011, p.27)。换言之, 身体至多是个载体或“生理基础”, 其作用并没有超出“强身健体”的范围。在认识论上, 其意义微乎其微。
如果“人脑有如计算机”, 认知类似于软件性质的程序, 那么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就是, 认知过程处理的不可能是外在于认知的真实事件, 只能像计算机那样处理“符号”。计算机是一个物理符号系统。它根据人为设定的规则加工着来自于系统之外的物理符号, 如字词、数字、图形等等。这些符号本身没有意义, 它的意义是其所代表或表征的内容决定的。而且符号与它所表征的内容之间并无必然联系, 其表征和被表征的关系是人为的、武断的(Searle, 1990)。如果认知过程所处理的也是这种性质的符号, 那么就产生了一个严肃的问题: 认知表征与它所表征的内容之间的关系究竟是怎样产生的?换言之, 认知表征的意义是如何获得的?它同身体之间是什么关系?
依照经典观点(Fodor, 1975), 认知表征具有这样几个特点: 第一, 表征是发生于有机体神经系统内部的意像、符号和标记等等。计算机的逻辑运算决定了运算内容不能是具体的、琐碎的真实事件或事态, 只能是代表这些事件或事态的字词和数字等符号。认知过程本质上也是一种运算, 运算的内容同样必须符合这些要求。因此, 作为运算内容的认知表征并非外在真实事件, 而是一些神经性质的符号。这些符号内在于有机体的神经系统, 本身没有意义, 其意义是其“代表”或“表征”的内容决定的。其次, 认知表征虽然转瞬即逝, 但是其具有时间上的可识别性。这意味着, 表征具有实在性。它并非形而上学的虚构, 而是实实在在的存在于神经系统之内。它们就是心理的“内容”, 是认知加工的对象。再次, 各种认知表征独立存在, 通过一定的规则组成相应的事态, 表现为特定的心理活动。最后, 也是最重要的是, 认知表征具有情境的剥离性。这是高效认知加工所必须的。由于认知表征可以脱离具体情境而在有机体内部抽象运作, 因而认知表征既不受限于特定身体, 也不受限于具体环境。这保证了认知过程的速度和效率。人类思维之所以高效和灵活, 就是因为人类思维可以不受具体事物和情境约束。换言之, 人类思维依赖的是抽象概念, 同身体的感觉和运动系统无关(Mahon, 2015)。思维有自己的“语言”, 可以在抽象层面上运行。
认知表征的这几个属性使得认知过程完全脱离了与身体的关系。无论是表征的内容和形式都与身体构造和活动无关。它们仅仅是一些神经性质的“符号”。这些符号代表了某种内容, 却同这些内容之间仅仅存在“表征”和“被表征”关系。也就是说, 这些抽象的神经符号同承载它的身体之间仅仅存在微弱联系。身体只是生物“有机体”, 是认知表征等心智活动的载体。载体对于被载的事物是重要的, 没有载体被载的事物只能原地不动。但是载体终归只是载体, 载体并不能决定被载事物的性质。如果身体对于心智活动来说仅仅是个载体, 那么身体既不能影响心智的内容, 也不能制约心智的形式。事实果真如此吗?上个世纪80年代之后兴起的具身认知理论对这种笛卡尔主义(Cartsianism)观点提出了严肃质疑。
3 体验中的“身体”:身体经验在认知表征中的作用
法国现象学家梅洛-庞蒂早在1945年出版的《知觉现象学》一书中, 就通过对身体经验的强调而批驳了笛卡尔的认识二元论。梅洛-庞蒂主张, 认识的主体并非笛卡尔幽灵般的“自我” (cogito), 而是身体, 或者“身体–主体” (body-subject)。认识的主体是“我”, 而“我”就是我的身体: “通过交换的方式, 主体就是他的身体, 他的世界, 他的情境” (Merleau-Ponty, 2012)。梅洛-庞蒂指出, 组成意识内容的是三种通过身体获得的经验: 第一, 自我体验。自我体验并非超越身体的纯粹意识经验, 而是身体的位置、状态、动作、目的、需要和愿望等本体体验。其次, 客体的体验。这种体验是基于身体知觉而产生的, 客体的意义也是通过对客体的身体体验而产生的。再次, 对他人作为意向主体的体验。我们对他人的这一体验同样基于身体知觉, 是一种身体经验(Matthews, 2014)。
意识是一种身体经验的思想在具身认知兴起的早期是一种十分流行的观点, 即使在今日的具身认知心理学中, 这种观点仍然占据着较大的市场。它构成了具身认知阵营中“温和派”的基本观点。温和派认为(Barsalou, 2008, 2016), 经典认知心理学假定认知表征以语义记忆的形式储存于大脑, 同身体知觉和身体动作处于可分离状态。根据经典理论, 通过特定感觉通道(如视觉、听觉、触觉等等)形成的表征被转换为一种跨感觉—运动通道的认知符号。这些符号以语义形式表征着知识, 不依赖于任何特定感官和运动系统, 也就意味着同身体的形态和运动没有任何直接联系。例如, 有关“狗”的概念知识。从身体体验的角度认识关于“狗”的概念知识, 意味着这一概念的形成依赖于许多具体知觉形式及其与狗互动的身体体验。这些身体体验既有感觉的, 也有动作的和情感的: 我们通过视觉形成了狗的形象, 通过听觉闻知狗的叫声, 通过触觉摸到狗的光滑皮毛。如果我们有被狗追逐的经历, 提到“狗”的概念我们还存在着恐惧情绪。这一切都是通过特定感觉–运动通道形成的, 依赖于我们的身体体验和与狗的交往活动, 大脑中并不存在一个跨通道的、一般性的关于“狗”的知识表征。所有关于“狗”的知识表征都是具体的、鲜活的, 有着视觉、听觉、触觉和情绪感受等特定通道特征(Gallagher, 2015)。
温和派的主要代表人物Barsalou认为, 没有任何经验证据支持认知过程中存在跨通道的抽象符号表征。经典理论之所以坚持这一立场, 是因为抽象符号似乎完美地表现了知识表征中的形式主义, 支持了认知加工的符号操纵特征, 且有了这样一种假设, 智能就可以人工模拟, 为人工智能的探讨提供了充足理由(Barsalou, 2008, p.620–622)。
Barsalou提出了一个“知觉符号系统” (perceptual symbol systems)理论来取代经典认知表征理论的“物理符号系统” (physical symbol systems)理论。物理符号系统理论认为认知表征由跨通道(amodal)的抽象符号构成, 与特定的身体通道无关。但是知觉符号系统理论认为: “在解释经验时, 传统方法假定了符号操作的重要意义, 在这一点上, 它是正确的……知觉符号系统的理论观点保留了传统理论中的符号功能, 但是却使用(身体化的)模拟(simulation)和动力系统加以完全不同的解释……它主张在大脑中存在着一个单一的、多通道的表征系统。这个表征系统支持了各种不同的模拟方式, 而这些模拟均发生于知觉、内隐记忆、工作记忆、长时记忆和概念知识中” (Barsalou, 2008, p.622)。所以, Barsalou (2016)主张, 表征并非跨通道的抽象符号表征, 而是依赖于特定感觉通道, 其机制类似于一种“神经复用” (neural reuse)。
作为具身认知理论中温和派的主要代表, Barsalou保留了经典认知心理学的一些关键特征。就像经典观点主张的那样, Barsalou也认为认知也是一种“运算” (computation)。但是运算的对象不是抽象的, 跨通道的符号, 而是通过身体各种通道形成的认知表征。认知表征并不抽象, 而是一种模拟(simulation)或仿真过程, 是“另外一种心理事件、状态或过程的再体验” (Shanton & Goldman, 2010, p.527)。Barsalou使用模拟这个概念, 用以指涉通过身体通道获得的知觉、运动、情感和本体的身体状态的再生成(reenactment)。当身体作用于环境时, 大脑获得了不同通道提供的身体状态, 并进行综合加工, 使之成为一个多通道特征的认知表征。例如, 面对一把椅子, 椅子的模样, 坐椅子时的身体动作, 坐在椅子上的舒适和放松等等身体体验构成了关于“椅子”的认知表征。以后在适当的刺激条件下, 那些储存在记忆中的身体状态被重新激活, 模拟了在直接经验条件下获得的那些感觉和运动状态(Matheson & Barsalou, 2017)。因此, 认知加工中的认知表征并非不受身体制约的抽象符号, 而是通过身体感觉—运动通道获得的各种经验和感受的模拟物。这些模拟物从性质上来说是身体化的, 是被身体经验塑造出来的。
社会认知同样是基于身体经验而产生的模拟过程。社会认知是对他人心理状态的认识和理解。通过内省和反思等意识体验, 我们可以了解自己的经验和感受。然而, 他人的体验和感受隐蔽于我们, 是我们无从直接抵达的。那么, 我们是如何了解他人心理的呢?这就产生了所谓的“读心” (mindreading)问题。
在这一问题上,理论论(theory theory)主张大约在4岁左右的时候, 儿童才开始懂得他人的心理不同于自己的心理。一些人认为这种能力是天生的, 是人类进化的产物(Baron-Cohen, 1995)。另外一些人则认为这种能力是儿童发展的结果。在成长的过程中, 儿童利用常识对他人的行为进行预测, 并在实践中进行检验, 从而逐渐形成了有关他人心理的“理论” (Gopnik & Meltzoff, 1997)。两种观点都认为儿童利用“常识心理学”对他人的心理状态进行“理论般的”推测。这种推测就是所谓的“读心”。
模拟论(simulation theory)则认为儿童对于他人心理状态的理解并不是一种理论推测, 而是使用自己的心理资源去“模拟”他人的思想和感受。为了达到对他人的理解, 我把我放到他人的位置上, “穿上他人的鞋子走路”, 利用我自己的动机和情绪资源, 在我的心灵中产生一种“假扮的” (pretend)信念、愿望或策略, 以此达到对他人心理状态的理解。因此, 读心并非是一种“理论”, 而是自身心理资源的“再利用”。如果说我对自己心理状态的理解是“在线的” (on line), 那么, 对于他人心理状态的理解就好像是“离线的” (off line)。换言之, 我利用自己的心理资源模拟他人, 以此来体验他人的感受, 并以这种体验和感受解释他人的心理。这就是所谓的“读心”过程。
无论是理论论还是模拟论, 都假定了我们与他人之间的隔离属性。在社会认知过程中, 我们无从直接抵达他人心理内部。如果要达到对他人的理解, 就需要一个中介的认知表征。这个表征在理论论那里是一种“心理理论”, 在模拟论那里则是一种“心理模拟”。就像Keysers和Gazzola (2006)所说的: “就模拟的案例来说, 观察他人的行为和感受因而转变为一种在类似情境下我们自己的经验和感受的内部表征” (p.390)。但是这种内部表征的性质是什么?同身体有什么关系?是否是身体化的呢?这是理论论和模拟论没有回答的问题。
社会认知研究中的具身模拟论(embodied simulation)则利用镜像神经元的“镜像—匹配”机制解释读心过程中的内部表征。镜像镜像神经元具有双重特征: 它可以在指向一定目标的动作执行和动作观察两个阶段皆被激活。例如, 恒河猴在自己抓握食物时和观察其它个体抓握食物时, 其额下回后部所谓的F5区的镜像神经元都呈现出明显的电生理反应(Rizzolatti & Fogassi, 2014)。人类的研究也表明, 在理解手、脚、口部的动词时, 其主管这些动作的皮层区域也呈现出明显的激活反应(苏得权, 钟元, 曾红, 叶浩生, 2013)。这些事实说明对于他人心理的内部表征是身体化的, 个体使用自身的神经生理资源表征对于他人动作的理解和认识。认知理解同身体动作系统紧密联系在一起。我们用自己的动作去理解他人的动作。社会认知过程中对于“他心” (other mind)的理解建立在我们自身感觉—运动经验的基础上。同我们的身体密切相关。
4 互动中的“身体”:没有表征的认知
早期的认知心理学认为心智有如计算机, 心智的主要工作是认知表征的运算和操纵。温和的具身认知把认知表征与身体经验结合起来, 主张认知加工的内容是基于身体经验的内部表征。也就是说, 认知表征是身体经验。既然是身体经验, 当然离不开身体。但是, 温和派在强调了身体经验对心智塑造作用的同时, 却又保留了计算和表征。在温和派那里, 心智仍然是计算, 计算的对象是心智的内容, 即认知表征, 只不过这种表征具备了特定身体通道的属性。
激进的具身认知对于这种改良观点提出了激烈的批评(Dempsey & Shani, 2015)。他们主张“认知应完全限制在行动、情绪和知觉范围内” (Dove, 2016, p.4)。从生成论(enactivism)的观点出发, 激进具身认知主张(Hutto & Myin, 2013), 认知是一种活动, 其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 而不是为了形成心理表征。“有机体的活动 – 以特定的方式与环境的特定特征相互作用 – 足以解释基本认知中的大部分活动……总而言之, 并非所有的心智活动都需要个体去建构关于他们的生存世界的表征” (pp.4–5)。与其说认知是一种心理表征, 不如说认知是一种具身的行动: “思维并非某种可以脱离身体的东西, 相反, 思维是一种行动, 而这种行动受到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身体和大脑的强烈影响。换言之, 我们怎样思维依赖于我们具有什么种类的身体……认知的存在是为了指导行动。我们知觉是为了执行动作, 我们知觉到什么依赖于我们倾向于怎样行动……即使理解诸如自我、语言等最抽象的认知过程也可以从考虑它们怎样根植于行动而受益。这种对行动的关注同标准的认知心理学形成鲜明对比” (Glenberg, Witt, & Metcalfe, 2013, p. 573)。
激进派主张, 认知是一种扎根于环境和身体的活动。这种活动的方式为心智的理解提供了正确模型。认知语言学家Lakoff和Johnson (2015)曾经指出, 由于地球引力和直立行走的行为方式, 人类形成了“上”和“下”的概念。以这一对概念为基础, 人类发展出各种对抽象情绪和精神状态的理解。例如, 高兴为上, 悲伤为下; 意识为上, 无意识为下; 健康为上, 疾病为下; 美德为上, 堕落为下; 地位高为上, 地位低为下; 理性为上, 非理性为下等等。这些抽象概念的理解都离不开特定的身体构造和作用于环境的活动。无论一种认知方式多么复杂和抽象, 都可以从特定身体构造和作用于环境的活动方式中得到理解。
认知是具身的, 也就是说认知基于身体, 源于身体, 是被身体作用于环境的活动塑造出来的。Varela等人(1991)强调指出, 所谓的认知具身性(embodiment of cognition)就是依照身体的感觉—运动能力来定义认知。认知是一种具身的活动, 这种活动根植于身体, 扎根于环境, 与有机体的生物、心理和文化因素紧密联系在一起。所以对于心智的理解既不能离开身体, 也不能脱离环境。对于一个生命体来说, 它们的世界和它们的生存环境是其感觉—运动能力“生成” (enact)或“导致” (bring forth)的。认知心理学的任务是揭示有机体的感觉运动能力怎样造就了它们的世界, 而不是发现有机体怎样精确“表征”了世界。“我们知觉到的世界是通过复杂且又精致的感觉运动能力范型而构成的” (p.164)。
激进的具身认知赞赏生态心理学家吉布森的观点(Gibson, 1979)。吉布森在视知觉的研究中, 提出了一个“示能性” (affordance)概念。他利用其视知觉研究的成果, 指出知觉的形成并非感觉信息加工的结果, 而是直接的。换言之, 知觉过程并不涉及运算和心理表征。其次, 知觉是为了更好地行动, 是为有机体解决问题, 而不是通过感觉信息加工而形成认知表征。再次, 知觉具有“示能性”, 即被知觉的对象提供了怎样行动的可能性。示能性把知觉和行动视为一体: 知觉是为了行动, 行动促进了更好的知觉; 知觉在行动中产生, 行动决定了产生怎样的知觉。吉布森的“示能性”概念给了激进派有力的启示, 因而“吉布森近来成为具身认知科学的英雄之一……” (Chemero, 2013, p.146)
激进的具身认知强调两个主题: 具身的主题(Embodiment thesis)和发展性解释主题(Developmental- Explanatory thesis)。具身主题强调的是, 基础认知是一个具体的身体在特定时空中与环境的动力互动过程, 并非一定要涉及内容和表征。McGann, De Jaegher和Di Paolo (2013)指出, 认知或心理并非作为一种表征存在于个体内部。实际上, 认知或心理动力性地存在于有机体与环境的互动和耦合中。正如“握手”并不存在于你的手上, 也没有隐藏在你的衣袖里。“握手”仅仅存在于握手的过程中, 是两个不同的手互动的结果。另一个形象的比喻是“舞蹈”。“舞蹈”只有在舞者跳舞时才存在, 舞者停下脚步舞蹈就不存在了。而舞蹈是舞者与音乐彼此协调、相互促进的结果。“从生成论的观点来看, 心理活动恰恰就是这种动力构成的过程” (p.203)。在这样一种互动中, 并没有静止的表征指导个体的行动: 认知是为了行动, 行动促进了认知, 两者互动耦合、浑然一体。
示能性概念也展示出, 环境并非作为一个静态的表征而存在于有机体的大脑中。环境是动态的, 给特定身体构造和身体能力的有机体提供了各种行动的可能性。但是这种行动可能性依赖于有机体的身体构造和行动能力。认知就产生于有机体与环境的互动过程中。
从具身的主题来看, 身体在认知过程中扮演着构成性的(constitutive)角色(Kuhle, 2017)。传统认知心理学并不完全否认身体的作用。实际上, 在“生理基础”的名义下, 传统认知心理学对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等生理过程进行了大量研究。但是, 心理的生理基础名义下的身体作用探讨仅仅视身体为“因果性的” (causal), 也就是说, 身体的生理因素是认知形成的原因。然而, 具身主题强调身体的作用不仅是因果性的, 而且是认知过程中的构成成分。在空间知觉中, 身体和头部的转动是立体知觉形成的原因, 同时, 身体和头部的转动也是空间知觉的必要成分。社会认知的研究也证明, 蜷缩的身体动作导致了被试更倾向于赞同他人的观点(黎晓丹, 杜建政, 叶浩生, 2016)。在这里, 蜷缩的身体动作既是认知判断的原因, 又是认知判断的构成成分。
发展性解释主题强调的是, 有机体与环境互动的历史, 亦即个体发展史, 足以对现时的认知方式作出解释(Vernon, 2016)。对于一个具备学习能力的有机体来说, 恰恰是它的学习能力决定了环境展示给它什么机会。正如示能性概念所指出的那样, 互动中的环境特征并非客观的、绝对的, 而是相对于有机体特定的身体构造和运动能力。另一方面, 身体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其能力在交互作用过程中不断发生变化。认知恰恰产生于身体与环境的互动。古人云, “路是人走出来的”。智慧和技能都是一种行为倾向。这种行为倾向是被长时间的互动历史塑造出来的, “解释有机体现时心理活动结构的奥秘完全在于以往互动的历史, 与那种储存在内部的心理规则和表征没有任何关系” (Hutto & Myin, 2013, p.9)。
Vallée-Tourangeau, Steffensen, Vallée-Tourangeau和Sirota (2016)的实验证实, 创造性问题的解决并不取决于工作记忆等认知能力, 而是受到任务生态、个体动作历史等因素的强烈影响。在他们的实验中, 实验者首先测查被试的工作记忆能力, 确定被试的工作记忆没有显著差异。接下来, 被试被分成两组: 一组被试得到了平板电脑和电子笔, 另一组被试得到的是手工制作图形的各种材料。被试的任务是把17只动物放到4个围栏里, 每个围栏里的动物都必须是单数。第一组被试使用平板电脑和笔可以对问题进行数学运算, 但是如果限于数学运算, 这个问题是无解的, 所以第一组被试中的大部分人没有解决问题。第二组被试手工尝试着各种摆放方式, 最终大部分人找到了问题解决方法, 即两个围栏部分重叠, 同一只动物可以重复计算。第二组被试中没有解决问题的两个被试是在尝试的初始阶段就错误地把手工材料捆绑在了一起, 限制了随后的动作思维。这个实验有力说明认知过程并不是限制在个体内部。问题解决需要个体利用环境资源, 与环境互动。互动的方式影响了被试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体现了生成论的思维方式: 认知并非发生于有机体内部的认知表征, 而是身体动作与环境要求之间的动力耦合(Barandiaran, 2017)。
5 小结
“身心关系一直是哲学人类学与心理学的中心话题” (Fuentes, Hernández, Santasilia, & Fuentes, 2017, p.1)。从文章前面几个部分的论述中可以看出, 有关身体与认知表征的探讨实质上涉及的是身心关系问题, 而身心关系的讨论要求我们首先了解什么是“身体”。究竟应该怎样理解“身体”?在心理学中, 身体曾经仅仅作为生物有机体, 是心智的“载体”; 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促使心理学家视身体为心智中的身体, 本质上是一种身体经验; 而具身认知阵营中的激进派则把身体视为一种活动, 恰恰是这种身体作用于环境的活动塑造了认知。这三种观点的根本分歧在于身体在心智和认知的形成中究竟发挥了什么作用: 身体是“载体”或“容器”?是“身体经验”?抑或“身体活动”?这些对身体的不同看法促成了不同身心观, 也促成了不同取向的认知心理学。依照对身体的态度, 认知心理学或从更广泛意义上的认知科学, 大致可划分为所谓的“第一代认知科学”和“第二代认知科学”。第一代认知科学深受计算机科学的影响。在“大脑有如计算机”、“心智即计算”信念的激励下, 身体被视为一个生物—物理实体。从第一代认知科学家的视角来看, 身体至多也就是个有着七情六欲的有机体, 对于心智的作用止于“载体”或“容器”。第二代认知科学则在梅洛·庞蒂身体现象学、动力系统论、复杂性科学影响下, 视身体为认识的主体, 认为认知与心智首先是一种身体经验, “认知与身体和身体活动紧密交织在一起” (Costello & Bloesch, 2017, p.1)。至此, 认知从“离身”开始走向“具身”, 身体则由心理学的“边缘”迈向心理学的“中心”, 实现了认知心理学的“身体转向”。在第二代认知科学的初期, 视认知为一种身体经验的观点开始流行, 认知表征有了身体化的特征; 随着生成论的兴盛, 视认知为有机体与环境互动的观点占据了优势, “认知表征”开始被遗弃。
不同取向的认知心理学对于什么是认知表征也提出了不同见解, 彰显出各自对身心关系的信念。认知表征实际上代表了“心”是什么。经典认知心理学视心智有如“自然之镜”, 观察、表征着包括身体在内的客观世界。认知心理学的任务就是要通过认知表征精确地恢复这个世界。这样一种既定心智对既定世界的表征假设了存在着一个主观的、离身的“我”和包括身体在内的“非我”, 而“认知表征”则是两者之间沟通的“桥梁”。这种笛卡尔主义的二元论观点正是具身认知阵营所极力反对的。
“温和的”具身认知采纳的是一条“改良主义”路线。它并不想从根本上颠覆经典认知心理学的认知表征观。它保留了“计算”和“表征”, 但是重新对表征进行了定义。Barsalou (2016)指出, 表征概念对于认知心理学的必须的, 因为如果认知仅仅是一种不涉及内容的活动, 那么尽管这种活动受到知觉的引导, 但是由于身体活动和知觉仅仅是一种基本的认知操作, 因而无法解释抽象思维、概念学习和问题解决等高级心理过程。恰恰是因为人类具有抽象概念表征的能力, 才使得人类超越了其他物种, 彰显出杰出的理性能力(Binder, 2016)。
但是具身认知阵营中的激进派却要在认知心理学中掀起一场“范式革命”。他们所希望的并非修修补补的改良, 而是颠覆传统范式的革命。激进派主张, 基本的心理现象不涉及内容。换言之, 基本心理过程并不涉及认知表征。认知是一种具身的活动, 是为有机体解决问题, 而不是形成外部世界的心理表征。“这一观点的关键前提是, 认知不应该被理解为提供了外部世界的内部模型, 而是服务于行动, 根植于感觉运动的耦合。因此, 认知过程及其基础神经活动模式的研究主要参照的是它们在行动的产生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Engel, Maye, Kurthen, & Konig, 2013, p.202)。
无论是温和的“改良派”, 还是激进的“革命派”, 都强调了身体对认知的作用, 表现出对中枢神经系统之外身体的关注。这体现出第二代认知科学的根本特征。认知心理学家O'Connor (2017)指出: “心理学和社会科学的新近发展明显表现出对具身概念的关注。具身认知这一新兴领域连同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现象哲学为从理论上勾画人们怎样理解周遭世界提供了有价值的见解” (p.2)。但是正如本文前面论述显示的那样, 尽管具身认知已经几近成为认知心理学的主流, 但远没有形成统一的理论框架, “在认知科学中存在着许多研究纲领。这些纲领都打着‘具身认知'的旗帜……尽管有着一个统一的标签, 但是这些纲领是非常异质化的……” (Goldman, 2012, p.71)。从温和派和激进派的争论中, 我们甚至可以看出, 即使在反对经典认知心理学的符号加工理论方面, 具身认知阵营也没有达成一致的观点。因此, 具身认知距科学哲学家库恩所描述的成熟“范式科学”仍然存在着较大距离。未来有关身体在认知中的作用、表征是否存在等问题还需要争论的各方提供更为有力的实验证据。
Abrams, T. (2016). Cartesian dualism and disabled phenomenology.(2), 118– 128.
Barandiaran, X. E. (2017). Autonomy and enactivism: Towards a theory of sensorimotor autonomous agency., 409–430.
Baron-Cohen, S. (1995).. Cambridge, MA: MIT Press.
Barsalou, L. W. (2008). Grounded cognition., 617–645.
Barsalou, L. W. (2016). On staying grounded and avoiding quixotic dead ends.(4), 1122–1142.
Binder, J. R. (2016). In defense of abstract conceptual representations.(4), 1096–1108.
Chemero, A. (2013). Radical embodied cognitive science.(2), 145–150.
Claxton, G. (2015)..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Costello, M. C., & Bloesch, E. K. (2017). Are older adults less embodied? A review of age effects through the lens of embodied cognition., 267.
Dempsey, L. P., & Shani, I. (2015). Three misconceptions concerning strong embodiment., 827–849.
Dove, G. (2016). Three symbol ungrounding problems: Abstract concepts and the future of embodied cognition., 1109–1121.
Dretske, F. (1995).. Cambridge, MA: MIT Press.
Engel, A. K., Maye, A., Kurthen, M., & Konig, P. (2013). Where’s the action? The pragmatic turn in cognitive science., 202–209.
Fodor, J. A. (1975).New York: Thomas Y. Crowell Co.
Fuentes, P. M., Hernández, M., Santasilia, S., & Fuentes, F. M. (2017). The body as constitutive element phenomenology and psychoanalysis on our view of ourselves and others., 6.
Gallagher, S. (2011). Interpretations of embodied cognition. In W. Tschacher & C. Bergomi (Eds.),(pp. 59–70). United Kingdom: Imprint Academic.
Gallagher, S. (2015). Reuse and body-formatted representations in simulation theory., 35– 43.
Gardner, H. (1987).. New York: Basic Books.
Gibson, J. J. (1979).New York, NY: Psychology.
Glenberg, A. M. (2015). Few believe the world is flat: How embodiment is changing the scientific understanding of cognition.(2), 165–171.
Glenberg, A. M., Witt, J. K., & Metcalfe, J. (2013). From the revolution to embodiment: 25 years of cognitive psychology., 573–585.
Goldman, A. I. (2012). A moderate approach to embodied cognitive science., 71–88.
Gopnik, A., & Meltzoff, A. N. (1997).Cambridge, MA: MIT Press.
Haken, H., & Tschacher, W. (2011). The transfer of principles of non-equilibrium physics to embodied cognition. In W. Tschacher & C. Bergomi (Eds.),(pp. 75–88). United Kingdom: Imprint Academic.
Hutto, D., & Myin, E. (2013).. Cambridge, MA: MIT Press.
Hutto, D., & Myin, E. (2017).. Cambridge, MA: MIT Press.
Johnson, M. (2013).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Keysers, C., & Gazzola, V. (2006). Towards a unifying neural theory of social cognition. In S. Anders, G. Ende, M. Junghofer, & J. Kissler (Eds.),(pp. 379–401). Amsterdam: Elsevier.
Kuhle, L. (2017). The subjectivity of experiential consciousness: It's real and It's bodily.(1), 91–109.
Lakoff, G., & Johnson, M. (2015).(W. Z. He, Trans.).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of China. [乔治·莱考夫, 马克·约翰逊著; 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 何文忠译,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Li, X. D., Du, J. Z. & Ye, H. S. (2016). Bidirectionality metaphorical effect of Chinese ritual culture: Contractive postures make people humble.(6), 746–756.
[黎晓丹, 杜建政, 叶浩生. (2016). 中国礼文化的具身隐喻效应:蜷缩的身体使人更卑微.,(6), 746–756.]
Lindblom, J. (2015).. New York: Springer.
Mahon, B. Z. (2015). The burden of embodied cognition.(2), 172– 178.
Matheson, H. E., & Barsalou, L. W. (2017) Embodied cognition. In J. T. Wixted (Ed.),(4th ed.). New York: Wiley.
Matthews, E. (2014).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McFarlane, A. C. (2017).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is a systemic illness, not a mental disorder: Is Cartesian dualism dead?.(6), 248–249.
McGann, M., De Jaegher, H., & Di Paolo, E. (2013). Enaction and psychology.(2), 203– 209.
Merleau-Ponty, M. (2012).(D. A. Landes, Trans.). New York: Routledge.
O'Connor, C. (2017). Embodimen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knowledge: Towards an integration of embodiment and social representations theory.(1), 2–24.
Rizzolatti, G., & Fogassi, L. (2014). The mirror mechanism: Recent findings and perspectives., 20130420.
Searle, J. R. (1990). Is the brain a digital computer?.(3), 21–37.
Shanton K. & Goldman, A. (2010). Simulation theory.:527–538
Shapiro, L. (2011)n. Routledge.
Stewart, J., Gapenne, O., & Di Paolo, E. A. (2014)..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Su, D. Q., Zhong, Y., Zeng, H., & Ye, H. S. (2013). Embodied semantic processing of Chinese action idioms: Evidence from fMRI study.(11), 1187− 1199.
[苏得权, 钟元, 曾红, 叶浩生. (2013). 汉语动作成语语义理解激活脑区及其具身效应: 来自fMRI的证据.(11), 1187−1199.]
Vallée-Tourangeau, F., Steffensen, S. V., Vallée-Tourangeau, G., & Sirota, M. (2016). Insight with hands and things., 195–205.
Varela, F. J.1, Thompson, E., & Rosch, E. (1991).. Cambridge, MA: MIT Press.
Vernon, D. (2016). Reconciling constitutive and behavioural autonomy: The challenge of modelling development in enactive cognition.(1), 63–79.
Ward, D., Silverman, D., & Villalobos, M. (2017). Introduction: The varieties of enactivism., 363–375.
Wilson, A. D., & Golonka, S. (2013). Embodied cognition is not what you think it is., 58.
Wundt, W. (2003).(2nd ed., H. S. Ye, & L. X. Jia, Trans.). New York: Macmillan.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894)
[威廉·冯特. (2003). 人类与动物心理学讲义 (叶浩生, 贾林祥译).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Ye, H. S. (2017).Beijing: Commercial Press.
[叶浩生. (2017).. 北京: 商务印书馆.]
Ziemke, T. (2016). The body of knowledge: On the role of the living body in grounding embodied cognition., 4–11.
1 “实在”在哲学领域是一个经常使用但含义模糊的术语。一般来说, 它指涉的是独立于意识的“客观存在”。由于他人的意识和心理也独立于我们的意识, 因而依照笛卡尔的心物二元论, 就有了物质实在和精神实在之分。
Body and cognitive representation: Understandings and divergences
YE Haosheng; MA Yankun; YANG Wendeng
(Center for Mind and Brain Science, Guangzhou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What is meant by “body” here? There are many understandings about what the human body is, which promote a variety of research programs in cognitive science in general and cognitive psychology in particular. The classical information-processing model of cognitive psychology treated the body as a biophysical substance that is different from the mind as a mental substance. Therefore, as a science of mind, the body has always been ignored and relegated to the position of a “physiological basis” of the mind. The classical cognitive psychology is founded on the idea that brain is something like a digital computer in which the physical structure of the brain is like a hardware, and the cognition is a software. In other words, the cognition was assumed as a computation of a computer. Usually, computation is understood as the rule-governed manipulation of representations, therefore, it requires the assumption that the mind contains some cognitive representations of aspects of the objective world that is independent of our perceptual and cognitive capacities. The cognitive representations are abstract symbols and they are amodal and exist independent of structures and functions of the body. As if the body is only a “carrier” or “container” of the mind. In contrast, embodiment theories of cognitive psychology had tried to distance itself from the classical cognitive psychology, highlighting the pervasiveness of in cognition of bodily factors. Right now, there are many approaches and programs sailing under the banner of “embodied cognition.” A “moderate” or “weak” approaches to embodied cognitive psychology do not separate the body from the mind. They take the body as more in mind, and want to elevate the importance of the body in explaining cognitive processes.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moderates, cognition is in essence a kinds of bodily experience, and the nature of our bodies shapes our very possibilities for our thinking and feeling. For the moderates, cognition is still involved in mental representation and computable processing which are staples of classical cognitive psychology. However, the cognitive representations are not disembodied symbols, but are body-formatted or body-related codes. The “radical” or “strong” approaches to embodied cognitive psychology claim that cognitive systems do not rely on internal representations and computations. Human cognition should be explained without the ascription of representational mental states. Our cognition is essentially grounded in the brain as it is integrated with our body. The nature of our cognitive processes is determined by the specific action possibilities afforded by our body. Our cognitive system is for action, and about solving problems for the organism, not for forming cognitive representations. Cognition is essentially a embodied action.
cognition; representation; embodied cognition; body; mind; enactivism
B84-09
2017-09-16
* 广东省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重大项目(2016WZDXM022)。
杨文登, E-mail: yangwendeng@163.com; 麻彦坤, E-mail: myk1966@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