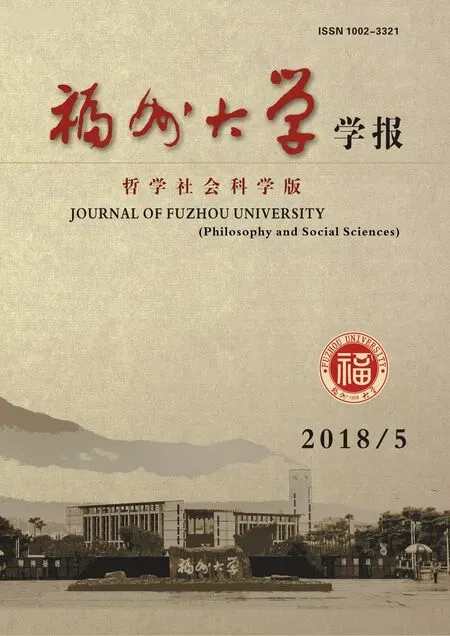家庭责任感与单流动家庭婚姻关系的维系
——基于对单流动家庭的质性研究
2018-11-08罗小锋何朝银
罗小锋 何朝银
(福州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福建福州 350116)
一、问题提出与相关文献
自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农村劳动力持续大规模地从农村流向城市。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4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7395万人,外出农民工16821万人,其中住户中外出农民工13243万人,举家外出农民工3578万人,[1]这意味着近80%的外出农民工是以分散流动的形式进行的。从家庭整体功能角度来看,劳动力的持续分散流动会导致家庭成员长期分离,这不仅会对农村家庭结构造成冲击,影响家庭功能的发挥,甚至会威胁农村婚姻家庭的稳定。
流动人口的婚姻家庭问题很重要且值得关注,[2][3]但从现有的文献来看,这一领域尚未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关于农村人口流动对婚姻家庭的影响, 以及流动人口如何维系婚姻家庭的研究不够系统,多散落在其他主题的研究中。关于夫妻单方流动对婚姻稳定性的影响,学界有两种不同的观点:(1)夫妻单方流动对婚姻的稳定造成了消极影响。[4][5][6]为什么农民流动会影响婚姻的稳定呢?有研究认为,流动青年婚姻观的变化、流动女青年经济的独立、流动导致农村青年夫妻差异性的增加,以及长期两地分居和交际网络的扩大导致婚外恋的出现。[7]外出或外出经历是离婚的导火线或动力,农民流动引发了婚姻危机,而在“外出”通向“离婚”的过程中,中国独特的城乡二元经济和社会制度发挥了重要作用。[8](2)夫妻单方流动并没有对婚姻的稳定造成消极影响。[9][10][11][12][13][14][15]何以在流动的冲击下农民的婚姻家庭依旧稳定呢?因为外出打工的丈夫给家庭带来经济收入,[16][17]并且农村婚姻解体的社会成本过大,[18]离散化的农民家庭之所以会呈现弥合效应,原因在于家庭的功能障碍得到一定的维护和修复。[19]
现有研究成果增进了我们对相关问题的认识,但相关研究仍有拓展空间:(1)已有研究多就事论事,缺少理论框架。(2)已有研究未能从理论上解释:为何在流动背景下少数农民家庭会不稳定而多数农民家庭却依旧稳定?本文的研究问题是:面对人口流动的冲击,多数单流动家庭婚姻是如何得以维系的?
二、研究设计
(一)资料来源
根据研究问题,同时考虑到研究内容的敏感性和调查对象抽样框的模糊,本文采用质性研究方法,用个案深度访谈法收集资料。
本研究采用目的抽样法来选择被访谈者,抽样考虑以下几个标准:(1)流动模式:丈夫单独外出妻子留守和妻子单独外出丈夫留守;(2)性别:男性和女性;(3)代际:第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
2008年暑假通过亲戚、朋友等关系在福州、厦门、东莞、龙岩等流入地城市及农民工的家乡深度访谈30个个案。2014年暑假、2015年寒假、2016年暑假及寒假,笔者及笔者的学生在河南、江西、安徽、山东、山西、福建等地访谈了30个个案,合计60个个案。
(二)分析框架
莱文杰(Levinger)较早使用婚姻回报、离婚障碍和婚姻替代建构了一个解释婚姻稳定性的模型。莱文杰模型的重大贡献在于,强调了一个事实:本想分手的不幸伴侣却因为离开的代价太大而选择在一起。[20]
普雷维蒂等使用婚姻回报、离婚障碍和婚姻替代性框架对人们为何维系婚姻进行了探讨,该研究从方法上和理论上拓展了莱文杰的研究。[21]
受上述研究启发,结合调研资料,本研究建构了一个框架来分析一方外出一方留守的单流动家庭是如何维系婚姻的,分析框架如下图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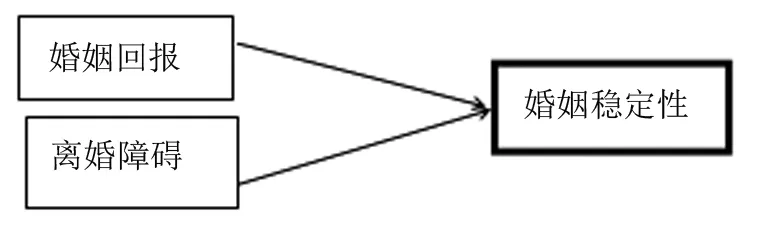
(三)概念界定
1. 半流动家庭是在人口流动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新的家庭形态。它的基本特征是家庭成员部分外出部分留守,由此一个家庭的成员空间上分隔于两地。本研究中的半流动家庭特指丈夫外出,妻子和其他家庭成员留守的家庭。
2. 婚姻稳定性。有研究从主观的角度将婚姻稳定界定为当事人对婚姻的态度或对婚姻持续的信心。[22]我们认为,当事人主观上的离婚想法未必会导致婚姻关系的解体,本文将婚姻稳定界定为婚姻当事人主观上没有离婚的想法,客观上没有采取行动去结束婚姻关系。
三、婚姻回报与婚姻关系的延续
访谈对象在回答婚姻何以稳定的原因时,不断提到夫妻之间“有共同的目标”“要互相信任”“互相理解”“沟通”“互相体谅”等等因素。既有研究表明,夫妻之间拥有共同目标、相互信任、相互理解、互相体贴属于婚姻的回报。
(一)留守妇女与丈夫拥有共同的目标
一方外出一方留守的单流动家庭多采取丈夫外出妻子留守的安排,这种安排多是夫妻共同商量的结果,是农民的一种家庭策略。这种安排服务于改善家庭经济状况,服务于让家庭这个整体过上好日子。共同的生活目标将空间上分隔两地的留守妇女与其丈夫凝聚在一起。
新劳动迁移经济学把家庭作为分析单位,认为人口的迁移是一种家庭策略。迁移行为不是由个体做出的,而是由更大的单位如家庭或家族做出。家庭通过做出部分家庭成员外出部分留守的安排,目的是为了多元化家庭的收入来源,实现家庭的规模经济;同时因为家庭成员通过迁移分属于不同的行业,家庭的收入风险因此分散。同时,外出成员和留守成员之间相互的支持有利于保持家庭的凝聚力。[23]
来自闽西的罗先生2000年外出打工,妻子严女士和儿子留守在家。罗先生外出务工的目标是为了让家庭过上好日子。在外出打工前,他与妻子在家务农,因为运气不好,种的东西要么产量不高,要么市场行情不好。总之,从事农业生产的效益很低,导致家庭无法过上好日子,他因此倍感压力。而要想提高家庭经济收入,就必须在农业之外开辟收入来源,他因此外出打工。(案例一)
问及打工的决定是谁做出的?罗先生说,“是夫妻两个人的决定。”严女士也表示,夫妻就丈夫外出打工的事情是经过商量的。
正因为夫妻之间有共同的目标,所以夫妻双方都能克服分居所带来的困难和不便,也能同心同德地在各自的领域中尽职尽责,共同把家庭经营好,夫妻关系也不会因时空的分离而受影响。如下文所述,夫妻关系不会受流动影响还因为他们彼此互相信任、互相理解、互相体谅。家庭作为一个群体,其凝聚力的强弱取决于夫妻共同的生活目标和人生理想……等等。[24]共同的目标意味着夫妻能齐心协力把家庭建设好,表明夫妻之间的凝聚力强。[25]夫妻之间共享同一生活目标利于婚姻的美满与维系。[26]共同的生活目标使留守妇女与丈夫愿意忍受孤独,愿意承受生活的重担。
(二)留守妇女与丈夫互相信任、互相理解
迫于改善家庭生计,留守妇女与外出打工的丈夫不得不过着时空上相互分离的分居生活。分离的夫妻关系虽然不易维系,但我们发现,多数访谈对象表示,分居生活对婚姻关系的稳定没有消极影响,原因就在于夫妻之间相互信任、相互理解和相互体谅。外出前就已经建立起来的信任,为留守妇女与丈夫婚姻关系的延续打下了坚实的心理基础,而相互理解和相互体谅表明夫妻各自为家庭所做的贡献得到对方的认可与肯定。
使得亲密关系易于保持的另一个特点是信任,期望对方会善待和尊重自己。[27]人们相信亲密关系不会带来伤害,并期望伴侣能满足自己的要求,关注自己的幸福。[28]如果丧失了这种信任,亲密伴侣也会常常变得猜忌与疑虑,以致损害亲密关系特有的开朗、坦诚和相互依赖。[29]
问及外出打工、妻子留守在家是否会对夫妻关系有影响时,罗先生说:“互相信任。”罗先生的妻子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要互相理解,你要理解我,我要理解你。你要相信我我要相信你,夫妻关系就不会受影响了。”(案例一)
另一位同样来自闽西的罗先生2004年以前独自外出打工,妻子张女士和家人留守在家。问及丈夫单独外出是否会影响夫妻关系的稳定,张女士表示:“没影响,老公够老实,我不会怀疑他做什么事,信任他不会做坏事。”(案例二)
张女士还提及另一个有助于婚姻稳定的因素,那就是夫妻相互体谅,“丈夫很体贴,会打电话回家,问我干活有没请人,叫我干活不要太拼命,他会拿钱回家,让我请人干活。”张女士也会表达对丈夫的关心,“我问他干活会不会很累,他说很累、很苦,肩膀扛柴扛到出血。这些苦事我都记得。”(案例二)
如上所述,外出打工的丈夫与留守妻子相互信任、相互理解、相互体谅有助于维系夫妻之间的亲密关系。有研究认为,夫妻之间相互信任是婚姻美满的要件之一。[30]中国人讲夫妻“恩爱”就是要有爱,也要有恩。“恩”字指夫妻之间互相关怀、互相体谅、互相感激和对等付出;有恩有爱是婚姻美满持久的一个重要方面。[31]
(三)留守妇女与丈夫之间良好的沟通
进城打工的丈夫和留守农村的妻子所处的时空不同,生活环境不同,接触的信息也不同,这些不同客观上会拉大夫妻之间的距离。但我们的调查显示,外出打工的丈夫和留守妻子大多能保持有效的沟通,这种沟通使得夫妻双方能及时了解对方的动态、共享信息、消除信息不对称所可能造成的误解与猜疑。
沟通可以让夫妻分享感情,通过情感的交流让夫妻感受到对方的关心与爱,能够加强夫妻关系,使夫妻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沟通也有利于夫妻分享经验、感受、思想和期待;良好的沟通有助于婚姻的美满。[32]婚姻的和谐程度与夫妻之间的沟通程度有关。[33]留守妇女与丈夫之间多样化的沟通策略,不仅可以更新和确认双方的身份和彼此在婚姻中的成员资格,而且可以消融再社会化环境不同所带来的差异,使夫妻能够同步发展。[34]
罗先生通过电话保持与妻子的密切联系,“一般一个星期左右会跟妻子电话一次,那时候通讯没有现在这么方便,有时候要推迟。”(案例一)
江先生独自外出打工期间会积极地与妻子联系与沟通,“一般一个星期会打一次电话,有手机的时候打得多些。一般聊家里的情况,田里的情况,父母小孩的身体如何,主要是关心家里,问候大家。”(案例三)
以上案主虽然在时空上与妻子和家人分隔开来,但这没有影响他们的夫妻关系,因为他们采取各种能动的策略积极有效地与妻子保持沟通,在沟通中夫妻相互向对方表达关心,这种沟通能够拉近夫妻之间的心理距离,增加夫妻之间的亲密感,增进夫妻之间的相互信任。正如费孝通所言,“空间距离和社会距离固然并不是完全相同的,尤其是在现代交通工具日形发达的情形中,书信电话都能传情达意,配合行为,空间的隔膜已不成为社会往来的隔膜了。”[35]
(四)留守妇女与丈夫相互爱对方
一些访谈对象将婚姻稳定归结为夫妻感情好。 例如,来自福建永定的江先生,2002年以前在厦门搞装修,妻儿以及母亲留守在家。虽然夫妻分居,但他认为这对夫妻关系没有影响,“如果我对老婆没感情,那么即使在家也一样。夫妻之间如果有感情,那么无论我到哪里打工都是一样。如果夫妻有感情,那么彼此的关系就不会受影响。” (案例四)
江先生的话语说明,夫妻关系是否会受流动影响跟流动前的感情基础是密切相关的。正因为流动前留守妇女与丈夫之间就有比较好的感情基础,所以他们的婚姻关系才不会受暂时分离的影响。外出打工的丈夫通过汇款回家以及通过电话进行沟通交流,使留守妇女相信丈夫的心还在家里。笔者在调研中发现,单流动家庭中的婚姻问题多因为夫妻感情出了问题,而这个问题在流动前就已经出现,流动后夫妻感情问题因空间分隔更不可能得到修复。“除了纯粹的性本能之外,恩爱之情也可以促使一对夫妻长久地呆在一起,即使他们的婚姻达到最初的目的。而随着精神素质对爱情的影响,夫妻之情自然也更趋长久。”[36]
四、离婚障碍与婚姻关系的延续
前文从婚姻回报的角度分析了单流动家庭婚姻关系得以延续的原因,然而,并非所有的婚姻都是依靠婚姻回报来维系的,一些单流动家庭能够维持下去是因为存在离婚的障碍。
以往关于婚姻维系的研究已经注意到离婚障碍的作用。在亲密关系的周围存在着许多障碍,这些障碍使得婚姻当事人很难逃脱亲密关系。[37]离婚障碍可能在离婚过程中扮演着关键作用,因为离婚障碍可以维持婚姻完整,并可能推迟甚至阻止离婚。[38]
访谈分析发现,部分留守妇女的婚姻关系之所以能够得以维持,与下述几个离婚障碍因素有关:首先是对子女的责任;其次是亲属的劝阻;再次是存在反对离婚的舆论。
(一)顾及子女
即使留守妇女与丈夫之间已经没有感情了,婚姻关系仍然能够延续下去,原因何在呢?部分就在于子女的存在,子女通过血缘纽带把父母联结在一起,一些留守妇女为了给子女完整的家,与丈夫凑合过下去。
关于子女在稳定婚姻关系中的作用已经有大量的相关研究。不少夫妇能够白头偕老靠的不是爱情而是爱情之外的其他因素,这些因素包括双方家庭背景、小孩的教育、经济上的顾虑等。子女是当事人离婚时的顾虑,有子女的夫妇比较难以做出离婚的决定。[39]
子女作为婚姻的特有资本会增加婚姻价值,从而起到稳定婚姻的作用。“如果一个婚姻保持其完整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婚姻资本积累起来了,婚姻的价值也就增加了。孩子是首要的例子,尤其是年幼的孩子。……婚后,当一对夫妇有了自己的孩子,特别是当孩子年龄尚小的时候,离婚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减少。不仅美国和其他一些富有国家的情况是这样,而且原始社会也是这样。”[40]
沈女士的丈夫2003年去厦门打工,在建筑工地上班,因夫妻长期分居以及丈夫没有尽到作为丈夫和父亲的责任,沈女士觉得有丈夫跟没丈夫一样。访谈中沈女士一直感叹人生的不公平,对丈夫极度失望的她曾在亲属面前提出要与丈夫离婚,但后来她接受丈夫回家,最主要原因是她担心两个儿子,“我就是看两个儿子的面上,只会看儿子的面。小孩是我生下来的,如果我不理,这会害小孩一辈子。”(案例五)
访谈中她不断强调自己对孩子的责任,“对于小孩的教育,我当时只会想尽自己的能力去做,能做到多少就做多少,做不到就没办法了。”
强烈的家庭责任感,强烈的母爱支撑着沈女士,正因为如此,她才能忍受抚育孩子过程中的艰辛。看到孩子的成长,她倍感欣慰,孩子的懂事让她觉得自己的付出是值得的。问及为两个儿子付出这么多是否值得时,她反问道,“我自己生的子女怎么会不值得呢?当然值得,我无论做什么都是为了子女,累到死都值得。”
无论是从婚姻的特有资本,还是婚姻的目的,再或是家庭结构,以及父母对子女的情感和责任感方面,子女都对婚姻的稳定具有正面的促进作用。
(二)亲属的干预
在中国,尤其是农村,婚姻不是当事人个人的私事,它是婚姻当事人所属家族的公共事务。费孝通很早就指出了这一点:“结婚不是件私事。……我说婚姻是用社会力量造成的,因为依我所知世界上从来没有一个地方把婚姻视作当事人个人的私事,别的人不加过问的。婚姻对象的选择非但受着社会的干涉,而且从缔结婚约起一直到婚后夫妇关系的维持,多多少少,在当事人之外,总有别人来干预。这就把男女个人间的婚姻关系弄成了一桩有关公众的事件了。”[41]
刘易斯和斯帕尼尔认为,来自家庭、朋友和教会的反对,离婚压力会使婚姻当事人选择保持婚姻关系的延续或婚姻的稳定。[42]
在整合良好的农村社区,每当婚姻遭遇危机时,由婚姻当事人长辈、亲朋好友构成的关系网络会极力加以劝阻,多以“为了孩子”“为了家庭”为由,说服当事人要互相忍让。经过亲友的调解,闹离婚的夫妻多半会放弃离婚的想法。[43]婚姻发生问题时,父母、亲友的劝和有助于婚姻的稳定。[44]
沈女士因丈夫不顾家曾在哥哥面前讲过要跟丈夫离婚的事,哥哥从抚育小孩的角度对她进行了劝阻。
2005年清明,沈女士的丈夫从厦门回来扫墓,与丈夫同一房的一位叔叔和其他亲属来吃清明晚宴,晚宴后,沈女士跟这位叔叔说:“我跟他出去厦门打工,他还跟其他女人在一起,经常躲避我,这样子我在这里住不下去了,这个房子呢,他也参与盖了,就每人一半。”沈女士顾家行为为她赢得了道义支持,而丈夫的不顾家行为则使其丧失了道义资本。鉴于此,这位叔叔当时表态,“房子都是你的,没有他的份。”
婚姻不是当事人之间的私事,而是两个家庭乃至家族的公事,当婚姻出现问题时,夫妻双方的亲属会及时介入。必须指出的是,作为婚姻外的社会力量而存在的亲属组织,若能在当事人的婚姻出现危机时进行必要的干预,是能够化解婚姻危机的。在沈女士的案例中,无论是娘家还是婆家的亲属都劝当事人以家庭为主,看在小孩的份上,维持这段婚姻。
(三)反对离婚的舆论压力
虽然受到人口流动的冲击,乡村社会仍属于熟人社会,熟人社会容易生成强有力的舆论压力,生活在熟人社会中的村民不能不顾及村庄的舆论。案例五中的沈女士放弃离婚念头的一个原因就是她在意自己的脸面,在乎村民的评价,“如果我不接受他回来,别人会说我一个女的那么强势。”
沈女士的话语清楚地表明,她所生活的村庄民风淳朴,仍然存在反对离婚的舆论,这构成了村民离婚的障碍。
五、 结论与讨论
上文我们对单流动家庭婚姻关系何以维系进行了深入探讨,研究发现,单流动家庭中的婚姻得以维系的原因,部分是因为婚姻当事人能从婚姻中得到回报,部分是因为在农村婚姻的解体依然存在种种障碍。婚姻的回报体现在夫妻拥有共同的目标、爱、互相信任、互相理解、互相体谅、有效的沟通等等。当然,婚姻的回报不是天然就具有的,而是婚姻当事人自身努力经营的结果。在丈夫外出妻子留守的分居过程中,婚姻当事人能够积极互动,这进一步增强了婚姻的凝聚力。离婚的障碍体现在对子女的牵挂、亲属对离婚的干预以及村庄反对离婚的舆论。如果说婚姻回报使婚姻变得有吸引力,那么离婚障碍则为婚姻筑起了防火墙。
已有研究在探讨半流动家庭婚姻稳定的原因时,多强调经济因素的作用。农民工家庭成员虽然长期不共同生活但仍然稳固的原因,是“农民工对家庭的经济支持”[45]。分离的核心家庭的维系是生存压力与传统伦理道德约束下的经济维系。[46]丈夫外出打工获取了经济收入,[47]家庭经济得以改善。[48]
上述学者看到经济因素对家庭维系的作用,却忽视了其他因素如情感因素在维系婚姻家庭稳定中的作用,有经济决定论的嫌疑。目前绝大多数的研究都高度强调中国家庭的合作特性,特别是家庭在应对社会变迁时所显现的“集体行动方式”。结果,中国家庭的公共层面,也就是经济、政治、法律层面,吸引了大多数学者的目光,但是其私人生活的层面却往往被忽视。[49]“虽然农村家庭生活里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维系,自50年代以来已变得越来越重要,可学术界却几乎仍然没有什么人对此进行研究。”[50]
物质虽然是婚姻家庭生活的基础,经济对于婚姻的维系作用固然重要,但必须承认的是单纯依靠经济因素还不足以维持婚姻的稳定。单流动家庭婚姻关系的维系不仅仅在于经济维系,还在于情感维系。留守妻子与外出打工丈夫在共同改善家庭生计的过程中,能互相信任、互相关怀、互相理解,通过各种方式加强彼此之间的联系,增进夫妻感情,增强婚姻回报,加强夫妻之间的连接纽带。家本位的文化使得外出丈夫与留守妻子能够共担家庭的责任。婚姻维系表面上是经济维系和情感维系,实质上经济维系和情感维系的背后真正起作用的是婚姻当事人对于婚姻家庭的责任。因此,婚姻维系本质上是责任维系。
注释:
[1] 国家统计局:《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5年4月29日, http: // w ww.stats.gov.cn/tjsj/ zxfb/201504/t20150429_797821.html,2018年3月5日。
[2] 杨善华、沈崇麟:《对未来二十年中国城乡家庭的展望》,见杨善华主编:《家庭社会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43-144页。
[3] 风笑天:《农村外出打工青年的婚姻与家庭:一个值得重视的研究领域》,《人口研究》2006年第1期。
[4][8] 张玉林:《流动与瓦解——中国农村的演变及其动力》,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83-85页。
[5][9] 郑真真、解振明:《人口流动与农村妇女发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22-126页。
[6][7] 石人炳:《青年人口迁出对农村婚姻的影响》,《人口学刊》2006年第1期。
[10][19] 金一虹:《离散中的弥合——农村流动家庭研究》,《江苏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
[11][17][46] 潘鸿雁:《农村分离的核心家庭与社区支持》,《甘肃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
[12][16][45] 李 强:《关于“农民工”家庭模式问题的研究》,《浙江学刊》1996年第1期。
[13][34][47] 叶敬忠、吴惠芳:《丈夫外出务工对留守妇女婚姻关系的影响》,《中州学刊》2009年第3期。
[14][48] 许传新:《西部农村留守妇女婚姻稳定性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15][18] 李喜荣:《农村留守妇女的婚姻稳定性探析——豫东HC村的个案研究》,《妇女研究论丛》2008年第6期。
[20][37] G.Levinger,“A Social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 on Marital Dissolution”,JournalofSocialIssues,vol.32,no.1(1976),pp.21-47.
[21] D.Previti and P.R.Amato,“Why Stay Married? Rewards,Barriers,and Marital Stability”,JournalofMarriageandFamily,vol.65,no.3(2003),pp.561-573.
[22] 叶文振、徐安琪:《中国婚姻的稳定性及其影响因素》,《中国人口科学》1999年第6期。
[23] Oded Stark and E. Bloom.David,“The New Economics of Labor Migration”,TheAmericanEconomicReview, vol. 75, No. 2(May 1985), pp. 173-178.
[24] 张新芬:《家庭凝聚力及其价值评价》,《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7 年第5期。
[25][30][32] 彭怀真编著:《婚姻与家庭》,台北: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第233,229,176-178页。
[26] 潘绥铭:《家庭、婚姻、性与社会性别》,郑杭生主编《社会学概论新修》,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75页。
[27] J.A.Simpson,“Psychological Foundations of Trust”,CurrentDirectionsinPsychologicalScience,vol.16,no.5(2007),pp.264-268.
[28] H.T.Reis,M.S.Clark,&J.G.Holmes,“Perceived Partner Responsiveness as an Organizing Construct in the Study of Intimacy and Closeness”,in D.J.Mashek & A.Aron (eds.),Handbookofclosenessandintimacy, Mahwah, NJ.Erlbaum,2004,pp.201-225.
[29] J.T.Jones,B.W.Pelham,M.Carvallo,& M.C.Mirenberg,“How do I love thee? Let me count the Js: Implicit Egotism and Interpersonal Attraction”,JournalofPersonalityandSocialPsychology,vol.87,no.5(2004),pp.665-683.
[31][39][44] 蔡文辉、李绍嵘:《社会学概要》,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3年,第2,100,101页。
[33] 蔡文辉:《婚姻与家庭:家庭社会学》,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3年,第185页。
[35][41] 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29页。
[36] [芬兰]E.A.韦斯特马克:《人类婚姻史》第三卷,李 彬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
[38] Chris Knoester and Alan Booth,“Barriers to Divorce:When are they effective? When are they not?”Journaloffamilyissues,vol.21,no.1(January 2000),pp.78-99.
[40] [美]加里·斯坦利·贝克尔:《家庭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393页。
[42] R.A.Lewis and G.B.Spanier,“Theorizing about the Quality and Stability of Marriage”,in W.R.Hill,F.I.Nye,and I.L.Reiss(eds.),ContemporaryTheoriesAbouttheFamily(vol.1),New York:The Free Press,1979,pp.268-294.
[43] 尚会鹏、何详武:《乡村社会离婚现象分析》,《青年研究》2000年第12期。
[49][50] [美]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8,2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