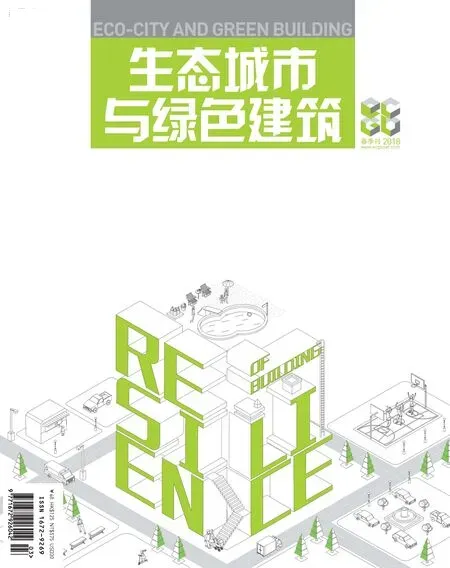自然、场域与技艺的共生
——伦佐·皮亚诺在世界文化遗产地的当代建筑解答
2018-11-02张乐敏张若曦喻苏婕ZHANGLeminZHANGRuoxiYUSujie
张乐敏 张若曦 喻苏婕 / ZHANG Lemin, ZHANG Ruoxi, YU Sujie
意大利建筑师伦佐·皮亚诺(Renzo Piano)以其对自然、场域、建筑技术和时代性的深刻理解,创造了许多经典的建筑杰作,得到国际建筑学界的普遍关注和肯定,其以时代与场所、技术与自然为主题的建筑设计理念对当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世界文化遗产地马耳他(Malta)首都瓦莱塔(Valletta)的城市之门重建项目中,皮亚诺通过对自然环境特征及传统文化进行重新诠释,以当代材料及形体进行创新,并把现代科学技术融入其中,成功打造了新的代表性作品。文章将对该项目的设计理念及实施过程进行深入分析。
1 背景概述
1.1 城市发展背景
瓦莱塔是地中海岛国马耳他的首都,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UNESCO)授予的世界文化遗产地。在1530年至1798年间,耶路撒冷圣约翰骑士团对马耳他的统治跨越了3个世纪,于1565年在一个伸入海中的石灰岩半岛上建设了瓦莱塔城,利用具有抵御海盗及外来侵略者的绝佳地理位置,围绕海岸自然地形建设了一系列雄伟的防御工事和护城墙,用以保护重要的海港区域和内部居住聚落(图1)。1798年骑士团被迫撤离后,马耳他相继成为法属、英属殖民地,使这座城市浸染了丰富的多元文化。在仅有0.55km2的瓦莱塔古城中,密布着16~18世纪共计超过320处历史遗迹,成了一座名副其实的城市博物馆。其中,瓦莱塔古城的防御工事,是圣约翰骑士团统治时期最重要的有形象征,也是历史、战争和多元文明交织的见证,在地中海地区的发展史上具有深刻的意义。
经过百年的历史洗礼,白色石灰岩块筑起的护城墙已被风蚀成黄色的古迹,有些仍耸立达百米,瓦莱塔中世纪构建起的原始城市形态也近乎完整地保存至今。然而在二战的空袭中,马耳他的部分街道及建筑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曾经雄伟的皇家歌剧院也沦为战争的牺牲品,只剩下场地上残存的遗迹。此后,瓦莱塔长期笼罩在乡愁思绪之中,直至1964年马耳他正式独立,政府才全面展开了严峻的重建工作。
1.2 项目概述
瓦莱塔的城市之门,作为古城唯一的陆路城门入口,同时也是贯穿城市的中轴大街的起点,从中世纪建城至今一直是瓦莱塔古建筑群的核心标志之一,在历史上经历了几次重建。此次对二战时被破坏的城门及周边区域进行重建,既是对历史上城市主入口意向的还原,同时也具有重塑马耳他新时代国家形象的意义。1990年代,公众对城门及皇家歌剧院遗址重建的呼声越来越高,最终在2008年该城市历史上最重要的重建项目“瓦莱塔城市之门(Valletta City Gate)”正式启动。伦佐·皮亚诺建筑事务所的重建设计任务包括3个部分:(1)重新恢复城门及设计护城河的外部空间,构建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新城市入口;(2)在紧邻护城墙的原城市广场上设计新国家议会大厦;(3)将皇家歌剧院遗址改建为一个露天剧场和文化中心(图2)。
在如此敏感又脆弱的世界文化遗产地建设当代建筑,不仅是对建筑师的极大挑战,也极大地冲击着市民对历史文脉所固有的保守理解:他们只希望通过恢复历史建筑原貌的古典风格来重现历史,因而抵制新的建筑形式及功能。伦佐·皮亚诺的设计通过对当地建筑和城市的重新理解和组织,将城门、皇家歌剧院遗址以及两者之间并不宽裕的场地充分组织起来。在不断的批判和争论中,项目于2015年完工并投入使用,为这个自二战结束至今一直饱受重建质疑和遗迹制约的地区,引入了新鲜的人潮和丰富的生活。

图1 瓦莱塔城市格局

图2 “瓦莱塔城市之门”总平面
2 城市之门——以场域塑造延续历史
2.1 空间重塑:场景的还原
城市之门自1633年建立至今共经历了5个时期,作为瓦莱塔的标志,不同的风格和形态分别代表着这个古城所经历过的不同历史及文化背景。最初的城门由意大利军队工程师设计而成,是瓦莱塔防御工事的一部分,出于防御需求,其仅为护城墙上的一个简单开口,更像是穿越城市壁垒的通道,由一座横跨在深邃护城渠上的木吊桥联结两侧,1582年木桥改为石桥。1632年由马耳他本土建筑师鼎力(Dingli)设计了第二代城门,虽然城门更富装饰性,护城桥也改建过多次,但仍沿用了由岩石筑成的桥基(图3)。18世纪末之后,城门陆续变换了第三代及第四代设计,其中护城桥作为入口空间序列的重要起始点,在多次重建中被一再拓宽,直至失去了最初的防御性形态,更像是一个城市广场。此外,第四代城门的现代主义风格因无法融入统一的城市风格而引来众多民众的批判,直接导致此后40年瓦莱塔再也没有尝试建设其他任何当代建筑。
皮亚诺认为,城市之门重建设计的首要目的是重现中世纪时期护城墙和壁垒最原始的纵深感和力量感,而只有恢复最初城门和护城桥的尺度、形态和规模,才能充分还原这组防御工事的历史感。因此皮亚诺在第五代城门重建方案中,拆除了增建的附加物,着眼于恢复第二代城门时期护城桥的尺度。在当代,城市之门不再需要具有防御性的实际功能,仅需表达入口空间的意向即可,对内则连接开阔的古城中轴大街,因此设计的城门仅是在古城墙上开设的8m宽的狭窄缺口,加强了城门防御性要塞的场景感(图4)。深邃的古护城渠、高大厚实的古城墙、狭窄的城门成为一个整体,再现了瓦莱塔古城中世纪时期重要的入口空间,经过窄桥步入城门,仿佛将人引入了另一个时空纪元,营造出独特的空间序列的体验(图5)。
2.2 新旧碰撞:时代的更替
出于对场所精神的重视,皮亚诺将文化、历史、文脉等因素作为技术、结构以及构造、节点设计的基础,其许多作品都具有很强的场所特性。城市之门的设计风格简洁而内敛,摒弃了一切冗余装饰,给人一种朴素的力量感。城门选用了原始护城墙中所用的本地材料——巨大的石灰岩块。这种石灰岩石材在马耳他早期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较硬的石材用于铺路,较软的易于加工的石材则被广泛地用作建筑材料。瓦莱塔古城也因此形成了统一而连续的城市风貌和建筑风格,随着历史的演变,建筑表面自然风化,显露出斑驳的时代印记。在项目中,皮亚诺采用了硬石材料,其色彩纹理与历史建筑风格统一,平整刚劲的线条更凸显出强烈的现代感,而新颖的技术和结构的运用也在设计中赋予了灵魂,充分发挥出材料的潜力。

图3 第二、三、四代城门景象



图4 皮亚诺设计的第五代城门“瓦莱塔城市之门”


图5 “瓦莱塔城市之门”鸟瞰

图6 石材及钢的材质应用

皮亚诺既充分考虑了自然、场所以及规划的因素,又强调让技术发挥最大效益以实现功能,充分分析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确定形式需求并与技术措施相结合。通过对新技术、新材料的潜力进行深入的探索,回应建筑的场所特性和文化传统,并将精美的细部构造处理变成其作品的重要特征。在设计中:城门两端各一把6cm厚、刚劲有力的“钢刃”刺穿古城墙并支撑新的城门,既将材质、颜色、尺度都高度统一的二者紧紧地缝合、串接在一起,也是旧与新两个时代的界定(图6左);两个25m高的巨大细锥形钢柱(图6右),既代表了古城中世纪延续至今的骑士精神,也彰显了该朴素缺口作为瓦莱塔城市主入口的地位。新旧之间的衔接与碰撞,是石块和金属在自然感、力量感和历史感语境中的对话,其中现代科学技术和各种材料潜力得到了充分运用及发挥,实现了建筑与自然的协调统一,现代建筑技术形式与建筑场所特有文化的结合。
3 新议会大厦——建筑技艺的本土对话
3.1 形体塑造:环境的映射
皮亚诺一直试图以某种方式实现建筑与周围自然环境的相适应,利用先进技术和工艺创造时代感,同时使建筑体现出自然特性是其设计的一个重要特征。新议会大厦选址于古城墙与皇家歌剧院遗址之间的自由广场,在整体建筑的体量考虑中,还原场地功能、为城市街区创造可渗透的路径和空间是皮亚诺最主要的设计出发点。根据“瓦莱塔城市之门”总平面可以发现(图2),紧邻巨大的城墙堡垒的新议会大厦由两个完整的大型体块组成,临近皇家歌剧院遗址的较高体块为主议会大厅,靠近城门的体块为国家议会、首相和相关部门的办公空间。两大体块之间根据周围的路径动线及与古堡垒的呼应关系,切割出一个三角形的中心庭院,作为建筑的主入口和人流汇集的空间。

图7 新议会大厦形体与古堡垒的对话

图8 建筑联结与空间组织

建筑整体应用当地石材,形体上延续了瓦莱塔古城墙的厚重感。建筑被分割成几个结实而又富于变化的石块,交错悬浮于空中,通透的地面提供了良好的视线穿透性,也吸引着人流靠近。转角处落地而高耸的塔楼,其刚毅挺拔的斜面使人联想到厚重的古城墙(图7)。在中轴大街上,建筑立面的厚实感和连续性,营造出城门内部良好的空间围合感,而穿过架空的底层,在看似不起眼的两个体块间的夹缝里,围合成了独立而宁静的小天地——中心庭院。豁然开朗的空间变化,也使迎面而来的古城墙堡垒尽收眼底,新旧建筑在材质、色彩和尺度方面实现了高度统一(图8)。形体的对话、视线的引导、空间的衬托,更凸显出古堡垒重要的历史地位和雄伟体量;而轻盈细长的钢制廊道,联结了两大体块,产生丰富多变的光影效果,使得整个空间充满现代感和活力。
新议会大厦的外部空间设计体现了皮亚诺对当地语境及场域的尊重,建筑开放包容的姿态,使其外部空间还原成最初的广场空间,成为多种公众活动的首选场所(图9)。皮亚诺认为,一座建筑其地面层的丰富性和活力度,是决定能否引入市民生活、促使该建筑的其余部分也富有蓬勃活力的关键。新议会大厦通过动线组织使地面层更好地回归于市民活动,这个开敞而灵动的公共空间,联结着中轴大街、中心庭院及周边的更多路径和遗迹,同时也是一个灵活的文化空间,成为举办各种展览的理想场地(图10)。中心庭院嵌套着另一个位于地下一层的绿化庭院,与瓦莱塔的旧轨道隧道打通,皮亚诺借重建契机,将这个被废弃用作车库的地下构筑物重新恢复使用,设计成一个特别的公共休闲空间。
3.2 材料应用:技艺的升华
天然的石灰岩石材在马耳他城市建造中扮演着主角,如果说皮亚诺的城市之门设计体现了石材的刚劲、厚重和力量,那么新议会大厦则体现了现代技术与传统工艺的结合,是对本土石材建造技术的一种全新的、充满活力和技艺的诠释,通过技术手段反映时代特征已成为皮亚诺作品的重要特征之一。

图9 新议会大厦及公共空间剖视图

图10 地面层与周边街道的空间对话与连结

图11 立面肌理与当地材质对比
皮亚诺主张从功能需求出发,用技术解决现实问题,用本土材料的创新体现建筑的时代感,同时通过形象的表达实现与环境的融合。议会大厦建筑表面选用了开采于马耳他戈佐岛(Gozo)的本土硬石。三层楼高的建筑表面共覆盖了7000块石材,这些石材为建筑塑造了完整而硬朗的体块线条、丰富的当地色彩和特色肌理。在设计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平整朴素的石材表面点缀着的菱形细石柱。在马耳他灿烂的地中海阳光照耀下,建筑立面在一天之中显示出丰富多变的光影效果。通过这种与自然的对话,庄重朴素的建筑显得生机勃勃。除此以外,皮亚诺经常从自然中发现一些形态,并擅长用建筑构件进行模仿,并与实际使用功能相联系,使建筑表现出仿生的状态,呈现出一种与自然和谐共存的视觉效果。根据皮亚诺的设计理念,这些由细石柱拼贴而成的线条表达了对古老街道肌理的尊重与回应。石材表面的形体切割和窗户开口,模仿了石材受到自然的海风及阳光侵蚀的效果(图11),既体现出对自然环境的谦逊姿态,同时也起到景观视线的引导作用,为建筑内部空间提供了完整的外部美景。

图12 建筑表面石材设计及构造

图13 瓦莱塔皇家歌剧院原貌及遗址现状
皮亚诺从科学技术的角度出发,捕捉结构、构造和设备技术与建筑功能、造型的内在联系,通过精心设计的外观和精美的施工,将高度复杂的工业技术通过艺术形式表达出来,从而达到技术与艺术的融合。在新议会大厦设计中,环境因素及能源利用方式被重点考虑。设计所采用的立面石材除了具有丰富的装饰效果外,还被赋予照明和能源控制的新功能,已远远超过了一般建筑外表皮的防护功能。这些精细的石柱均在意大利由CFF Filiberti公司通过数控机械切割而成,该公司负责本项目的工程设计及各石材单体的制造。在2014年的意大利维罗纳石材展上,CFF Filiberti公司展示了该项目中石材在技术和设计上的创新性应用(图12)。在功能方面,细石柱既体现了立面上的开窗变化,也充当了过滤太阳辐射的遮阳装置,通过控制太阳辐射和热量的进入,减少供热及制冷能耗。每个石柱单体都依照太阳角度进行设计,能够对渗入建筑的光线起到调节作用,身处其中的人们不仅可以感受光线、天气与昼夜时间的变换,同时也协助进行通风与换气调节。在此,石材不仅是整体语境的综合诠释,其创新性的应用也凸显了新建筑本身。

图14 剧场遗迹的再创造
技术进步是建筑发展的核心动力之一,其关键作用在于既解决了功能性问题,同时又是时代感的有力象征。在皮亚诺的设计中,外墙的石材与建筑不仅在结构上融为一体,在能源利用上亦是如此。包裹在石材内的40个地热井眼深入地下,直达140m深的岩石,比海平面还低100m,将被有效地用作建筑的地热交换器。除此以外,建筑屋顶覆盖了600m2的太阳能光伏板,作为建筑的主要能源,可以满足80%的冬季供暖和60%的夏季制冷需求。
在新议会大厦设计中,皮亚诺完美地诠释了其一贯的“高技派”特点。该作品不仅是一个将当地历史语境进行充分演绎的建筑,同时也是结合前沿科技的产品,外墙构造的做法不仅增添了建筑外观的美感,其高质量的工艺水平也表达了富有时代感的技术审美,再次展示出皮亚诺作品中新兴技术与古老材料结合的独有魅力。
4 皇家歌剧院遗址重建——历史与当代的共生
4.1 乡愁表达:批判的回应
瓦莱塔皇家歌剧院建于1862至1866年间(图13左),这座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建筑曾是国家的骄傲,但1942年在二战轰炸中不幸被摧毁,只剩下残存的外墙和柱基(图13右),此后一直保持着遗址的状态。歌剧院的重建问题引起了马耳他全国上下持续近60年的争议,也成为马耳他人的一块心病。1964年马耳他独立后,歌剧院遗址地的重建随即成为国家众多战后重建项目中的重点。最初政府希望在遗址上新建议会大厦,民众则希望重建一个能够体现古城中世纪辉煌的新歌剧院,而皮亚诺则提出了另一个想法:将现存的歌剧院遗址完整保留,并设计为露天的多功能剧场。毫无疑问,在原遗址的场地上采取“不建设”的处理方式,成为皮亚诺整体项目方案中最大的争议,也是导致公众反对的一个主要原因。
虽然皮亚诺和瓦莱塔市民都同样热爱这座古城,但如何在建筑上体现世界文化遗产地所独有的集体记忆?双方有着不同的理解。争论点围绕对歌剧院遗址的处理方式展开,即保留遗迹或制造一个复制品?皮亚诺认为“设计的目的并不是复制过去”。“在这个歌剧院场地上,现存的遗址已成为马耳他历史的一部分,已经像纪念碑一般存在着,既是历史的见证也是集体记忆尊严的象征,应当被保留下来。遗址将使人们真实地感受到战争的暴力及对城市的摧残,这在一般城市中并不多见。遗址背后的故事使其映上了高贵的光芒,与剧场的幻影结合,可以为这个城市的核心地区创造出魔力。”他在采访中说道,“我喜欢在这个能代表瓦莱塔的遗址上将过去和未来、历史和现代结合的想法……如果将这些遗址毁掉,在上面建设其他功能,这才是真正该受到谴责的事。如果将遗址保留下来,同时赋予其尊严、功能和用以展示艺术的现代设备,我认为这才会很棒。”
皮亚诺通过场域环境和功能来体现对过去的延续,实现新旧的联结。他认为,皇家歌剧院的遗址会为瓦莱塔带来更多的历史氛围,表现出对城市历史最基本的忠诚,而这是复制或新建一个歌剧院所无法比拟的。经过不懈努力,一座露天剧场的方案诞生了,皇家歌剧院残存的外墙和柱列最终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
4.2 功能植入:实体的超越
沉重的遗址部分是永久性的,轻巧的露天剧场部分是临时性的,在这两者之间、在遗址与构筑物之间、在历史环境与现代功能之间建立起一种和谐的冲突,虽然属于完全不同的两个语境,但却理所应当地可以实现共生。皮亚诺成功地说服政府打消了在遗址场地新建议会大厦的想法,除了出于保护遗迹及遗址环境的考虑之外,对场地及功能的理性分析也是重要因素。皇家歌剧院的遗址空间不足以容纳新议会大厦的巨大体量,甚至对于其他的实体文化设施而言空间也十分紧张。既需满足现代演出的一系列功能性要求,如预演排练空间、舞台设施等,还需考虑人流及舞美设备运送的可达性,若不花费大量的运行成本,该场地无法满足常规尺寸的现代剧场的使用需求。因此皮亚诺对于该场地的重建设计超越了实体的概念,遗迹被修复起来,设计利用钢结构对残留的柱列进行了加固,并作为剧场的功能性支架,用以支撑舞台荧幕系统、舞台设施和近1000个座位,使得遗迹与露天剧场安全地融为一体(图14)。
平时,该场地作为露天广场,既是公共的城市场所,也是展示遗迹、与历史对话的社交空间。在夏季,露天剧场发挥了重要的城市活动空间功能,可在此举行一季度的城市文化盛宴,包括歌剧、舞蹈、电影、音乐会等各式节目及活动。演出时,荧幕搭建在铁架上,用以隔离街道上来往的人群,而所配备的增强音效系统,使该历史场所也能达到与室内音乐会场地一样的效果。
在看似简单的场地中,瓦莱塔市民体会到了分享和包容所带来的收获,分享历史和文化,同时也分享生活。再次面对这些零落的遗迹时,公众难得地表现出了坦然和接纳,在皮亚诺的带动下,也通过不同形式的艺术再创造,给遗址带来了多彩的活力。在这个遗址重建设计中,皮亚诺以退为进,看似不作为但胜过作为,通过最少的改变达到最大的转变。可以说,在这个敏感又脆弱的世界文化遗产地,该项目是对皮亚诺所凝练出的当代性最好的诠释。
5 总结
在瓦莱塔城市之门项目中,面对起源于中世纪的世界文化遗产地,皮亚诺的设计表现出一种蓄意的谨慎。这个充分体现了当代性的设计作品,既没有古怪的建筑形体、鲜明的个性标志,也没有与语境对立的手法,却将艺术与人类学、社会与科学、科技与历史,这些看似碰撞而又交融的两面性巧妙地叠合而又清晰地界定出来,就像他在城市之门设计的那两把刚劲有力的“钢刃”,将新与旧串联的同时又强调了边界。
对于项目中的3个部分,皮亚诺分别采用了3种不同的表达方式来展现他对这个世界文化遗产地的深入思考和对话:城市之门设计体现了城门与自然环境的对话,以内敛而谦卑的姿态表达了对遗迹的尊重;新议会大厦设计体现了新旧建筑之间的对话,以当代性的精密技艺与消融于环境的场域表达来呈现若有似无的对比;皇家歌剧院遗址重建设计体现了历史和创新之间的对话,以历史的永恒和现代功能的灵动来实现古今的共容。在其中,也回应了皮亚诺“建筑关乎幻想和象征、语言及说故事的艺术”这一设计理念。皮亚诺在典雅的感官营造和精细的都市化实用主义之间实现了平衡,创造纪念性的同时,也将瓦莱塔散落的城市历史记忆和遗址充分融合,转化为一个能够抓住时代精神的功能性场所。用本地的语境发挥当代的幻想,最终实现场域的象征,皮亚诺的当代性思考及表达在这个世界文化遗产地特殊的项目中再次战胜了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