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谧胜景与诗意几何
——建筑师李兴钢访谈
2018-10-30范路FanLu李兴钢LiXinggang
范路 Fan Lu 李兴钢 Li Xinggang

天津大学新校区综合体育馆- 游泳馆/ 孙海霆 摄
从某种意义上说,李兴钢是一位对建筑秩序充满信念的设计师,正是这种信念,让他感动于路易斯·康的“世界中的世界”和景山俯瞰下的宏伟故宫。同时,李兴钢也是一位对生活充满感悟的建筑师,对于西方建筑、中国城市和园林聚落的个人体验,滋养出一种面向独特静谧和诗意的执着。感动与滋养,信念与执着,在他内心汇聚成“胜景几何”的思想。下面的访谈,描绘了李兴钢这些年的建筑思考和实践探索。
范路(以下简称范):在2015年的著作《静谧与喧嚣》中,您对自己的设计思想进行了一次系统梳理。其中很多文章并不是专门为该书写的,但能感到它们好像是围绕着一个方向展开?聚落也好,它们可以称为是基于同一思想观念和生活哲学的一整套中国(特别是传统的)营造体系,所以自然就会有很强的相关性。有意思的是,对于这些自己不同阶段的思考和学习,近两年我有一点融会贯通的感觉,想法越来越清晰,好像有一种“打通”的效果。
对于“胜景几何”的提法,它既是我实践的总结,也越来越成为了我思想性的工作目标。最近完成了一个200平方米的“微缩北京”——大院胡同28号,是个北京旧城更新项目,在这个改造性的小项目中,我觉得能够把以前对于城市和建筑关系的思考、对于园林和聚落的思考等都融会在一起,自己觉得还是很畅快的。
李兴钢(以下简称李):这本书是应王明贤老师“建筑界丛书”第二辑的邀请完成的。他要求以文字为主,但我没能力一下子写出那么多文章来。真正为这本书写的是第一篇文章,而后面的文章都是以前陆续写的,我按时间顺序编排,也是想反映在不同时间段都在想些什么东西。所以这么一个汇集,确实也有点总结的意思。
整理这些文章的过程也可以说是“自我认识”的过程。我以前觉得自己在不同阶段感兴趣的内容是在不断变化的:从大学毕业前一年开始,对中国传统营造体系中城市和建筑的关系特别感兴趣;然后到了2003年,开始对园林产生很大兴趣,后来把聚落也纳入到研究和思考的对象中。但现在我发现它们之间是相互关联的,好像是一个体系里面的不同表现方式。城市也好,园林也好,
范:您2014年的《UED》作品专辑以“胜景几何”为标题,而2015年的著作以“静谧与喧嚣”为题。这两个标题有什么关系,您的思考又有什么变化?
李:实际上,这两者不是变化的关系,而是深化的关系。这有一个发展过程。2013年,我们在方家胡同的哥大建筑中心(北京)有一个微展(图1)。这是史建和李虎两位老师组织的系列“微展”之一,每个建筑师需要为自己的展览取一个主题性的标题。我提出的是“胜景几何”,并写了一段阐释性文字,实际上是对我多年思考和实践的一种概括性总结。
在这么多年我的工作中主要有两方面的兴趣。一方面是中国传统如何当代化,比如对中国传统城市和建筑、园林以及聚落等的研究,希望能通过某种当代的转化,使那些有价值的传统,呈现于当下的思考和实践中。另一方面是对于建筑本体层面几何操作的兴趣:建筑的形式、空间、结构和建造等以几何为基本逻辑不断衍化而生成建筑。这两方面其实并非完全并行,但我希望在自己的工作中把它们结合起来。2014年初,《UED》杂志出了中英文两版作品专辑,我专门为此写了一篇题为“胜景几何”的文章,介绍了这个概念或思想跟研究和实践的关联。
方家胡同展览之后,又在中国建筑设计院做了一个续展。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青锋老师应邀为我们的院刊《设计与研究》写了一篇相关的评论文章。通过解读我的文章和作品,他指出“胜景几何”表达了自然、几何、诗意等多重含义,同时,他也提出了一些问题,比如我所思考的“诗意”,到底是怎样的诗意,是否海德格尔式的那种潜藏在神秘和敬畏背后的“黑暗与沉默”?而我所反复提到的“自然”,又是什么样的自然?面对他的提问,我也在思考,并一直想有所回应。
2015年,南京大学的鲁安东和窦平平老师组织了一个“格物”工作营。他们邀请国内十位建筑师或学者,让每个参与者根据自己长期关注的设计研究内容,针对南京特定的一个场地,来作出具体的回应和表达。在这个工作营中,我设计了一个装置作品——“瞬时桃花源”(图2),表达我的“胜景几何”主题,同时也回答青锋老师之前提出的问题。如果说“胜景几何”是一个思想理念的话,那作为一个建筑师,就要把思想转化为行动,趁着“瞬时桃花源”这个项目的机会,用具体的设计建造来呈现思想、回答问题,更是进一步深化自己的研究和思考。“格物”工作营中的“瞬时桃花源”是唯一真实建造的“设计研究”。
然后,2015年写的“静谧与喧嚣”这篇文章,实际上主要是关于“瞬时桃花源”的,但又不止于这个项目。它是把思想转化为行动之结果的一个描述,回答了“胜景几何”中的“胜景”,其确切所指是跟自然密切相关的空间诗性,并且如何被“制造”出来。其实,这就像康所说的,将“可度量”之物转化为“不可度量”的状态,是从物质性的手段到精神性的目标。而我认为跟自然紧密相关的这种“空间诗意”,是一个从喧嚣到静谧的过程,是作为体验之“主体”——人,从空间之外的喧嚣,通过一个叙事的过程,而进入空间内部,最后获得“静谧”的状态。“静谧”跟“胜景”、跟人的凝视或沉思有关系,是一种身心“沉浸”的状态。“胜景几何”所营造的诗意是空间性的,它必须通过空间营造而获得,而且人“浸入”空间还需要有一个引导的过程,这个诗意的胜景才会在人的心理上被放大,使人有强烈的精神感受。总之,在“瞬时桃花源”这个设计研究项目中,我完成了一次具体的“理念性”操作。
范:从操作性的角度来看,您心中的静谧胜景有何独特之处?
李:实际上,在“瞬时桃花源”项目里,我也进一步思考和回答了工具和手段的问题,就是用怎样的空间营造手段,来实现人们从外部世界进入内心世界的这一过程。我提出了“房”和“山”两类关键代表性要素。这里的“房”和“山”都是加引号的,是广义的。“房”对应了建筑,是人工的建造;而“山”则指代自然物。这里的人工物和自然物并不是二元对立、一成不变的,它们可以相互转化,也就是说“房”也可以变成“山”,“山”也可以变成“房”——房子做得好的话可以变成地景,可以像自然元素那样被视看和体验,或者那些本来的人工建造之物,经过时间的磨砺和各方面自然元素的加入,也可以变成一种特殊的自然物,比如说建于明代的南京老城墙,上面有很多经历长久时光所形成的“包浆”,有植物长在上面,还有荒废的老厂房的斑驳台基等,这些与自然元素“媾和”一体的人造物,已经可以被视为某种特殊的自然物,成为跟我们通常所指的自然之山类似的东西或者起到类似的作用。在建筑物层面,近年我们较多地聚焦在坡屋顶这种形式语言,它跟平屋顶很不一样,更为适应自然气候和构架建造的条件,有着更多天然的“自然性”,甚至具有某种文化性的意义。而从人的正常视点,坡屋顶是可以被看到的,下雨的时候,雨水会打在屋面上流落而下,雪堆积在屋面上成为动人的冬季之景,这些与自然元素的互动也使坡屋顶更兼具自然性和人文性的特征。所以,我们有多项实践作品是以坡屋顶为主要语言的,这是对“房”的具体操作(图3)。

图1:”胜景几何“微展(夏至摄)

图2:瞬时桃花源(孙海霆摄)

图3:瞬时桃花源(孙海霆摄)

图4:瞬时桃花源(孙海霆摄)
对于“山”元素,也有一系列的操作。这里面有不同的情况:首先一种是场地中本来就有纯粹的自然元素,就是真实的山、水、树木等,或者是原本人工物转化而成的“自然物”,比如“瞬时桃花源”中的老城墙和厂房台基废墟;而在更多的情况下是缺乏天然山水或人工遗迹的条件,这时就需要我们营造一种特殊的“人工自然”,当然这种“人工自然”可以同时成为被使用的空间,也即“山”转化为“房”。不管何种情况,人工物和自然物之间都要有非常密切的交互关系,而对于这种交互关系的营造——从方位布局的经营,“形”“势”的转化,到高、深、平“三远”视线关系的控制,以及空间框界下“景”之画面的生成和深远空间层次的制造强化等,造就了从“喧嚣”到“静谧”的空间诗意(图4)。
范:所以说人工和自然的互成是您心目中静谧胜景的核心气质?
李:是这样的,这是我思考的核心。
范:通过您的描述,能感受到两个气质不同的部分。胜景是静谧也是静态的,它倾向视觉和秩序感,是空间性的;但是,从喧嚣进入静谧的过程,或者说抵达胜景的旅程却是动态的,它更关乎身体和叙事,是时间性的。那么在设计中,您如何将两者统一起来?
李:确实是这样。我所追求的这种诗意空间,应该是两者兼具的。它既有动的部分,又有静的部分。从审美角度来讲,“相反相成”的两个东西结合在一起才有对仗,才会强化那种美感,在抵达深层次的、沉浸式的状态之前,也一定要有一个过程,才能强化体验的愉悦。童寯先生提出的园林“三境界”非常精辟,第一,“疏密得宜”,说的是空间布局;第二,“曲折尽致”,表明要有一个动态的过程去抵达;第三,“眼前有景”,便是视看胜景,是一种身心沉浸所带来的诗意状态。这三境界并不是三个独立的标准,而是相互关联而且递进的。我现在更愿意把这样一种动静结合的过程和状态叫做“身临其境”(是鲁安东老师给我的宝贵建议,我觉得很恰当):“身”代表体验主体——人的身体,“临”代表一种接近的过程,“境”代表一种身心一体、沉浸其中的诗意情境。
范:在《静谧与喧嚣》一书中,您提到自己多年的实践看似风格很多元,但背后却有内在的一致性。因为“文如其人,建筑也如其人”“不同的建筑之间有着非表面化的共性,是因为它们背后都站着我自己这个人”。那么,您的一致性或者说心中的建筑执念是怎样的?《周礼·考工记》的那种城市及建筑格局太“硬邦邦”了,园林才更“高级”,更符合我内心那种对理想空间的期待,但现在回头来想又并非如此了,我发现它们都不过是中国人思想哲学体系里的某一部分体现——所有那些东西其实都在里面,只不过以不同方向呈现出来,所以才会有那种贯通而统合为一体的感觉。
另一方面和我的工作环境、项目的情况相关。我所在的中国建筑设计院作为央企国有大院,主要项目来自全国各地,所以我的工作范围从东到西、从南到北跨越很大,地域和文化、社会、经济等各方面条件变化也很大,追求某种风格上的统一性,我觉得没有太大意义。所以,我可能更倾向于追求一种思想上的、内在的、立场的甚至某些策略上的一致性。我认为,建筑总是按照它内在的逻辑——地理、气候、历史、文化、自然、场地、使用等条件的规限——加上建筑师个人的把握和判断,而呈现某种“理想化”的唯一结果。所以设计的整个过程就是寻找某个“唯一答案”的过程。可能对于别人来讲并非唯一答案,但对我来讲就是唯一完美的答案——为特定的使用者营造理想空间。追求理想空间是人类的本能,建筑师工作的意义,就是面对不断变化甚至恶化的现实条件,为人们营造和实现理想空间。
李:这需要从两方面来说。一方面,每个人都有学习和成长的过程。实际上,我一直处在一种不满足于已有见识和经验的状态,这是一个不断学习和探索的、循序渐进的过程。因而从表面上看,我的作品没有特别高度一致性的风格。但人本身会有某种天然的一致性,于是我做过的思考和实践肯定就会有这种天然的一致性在里面。所以我说今天回过头来再看自己写过的文章、做过的作品,会有一点“贯通”的感觉。不是说我今天感兴趣于园林,前面对于城市和建筑的思考就没有价值了——当年我刚开始对园林发生兴趣进行一点研究的时候,觉得之前关注的类似
范:现阶段,您理解的理想空间和生活模式是怎样的?
李:从2015年写“静谧与喧嚣”这篇文章到现在,我更为强调的是面对现实——面对多样的现实,进行“理想实践”。人们对理想空间的向往一直都将存在,但理想空间的实现将随现实条件而不断变化。 “桃花源”是中国文化语境下的一种理想空间原型,“瞬时桃花源”就是探讨了当下真实的现实环境中如何营造公共理想空间的可能性,现在我对理想空间营造方向的认识可以叫做“现实桃花源”,这体现了理想空间的某种变迁。“桃花源”作为一种“图式”其实在历史上有一个从非现实向现实不断转化的过程:最开始“桃花源”出现在仙境山水,而不在人间;后来由文人如陶渊明、苏东坡等所崇尚和描绘,开始成为人世的“理想空间”;再后来变得更加生活化、世俗化以及“隐居实地化”,最后发展到大众日常生活空间中的人造“桃花源”,也就是所谓的“城市山林”——园林。园林的早期形态是自然山水为主,王维的“辋川别业”就是营建在天然山林谷地中的自然园居,后来随着城市发展,人口不断聚集增加,人均土地资源不断减少,人们没有条件再生活在自然山水之间,所以“桃花源”这种理想空间就转化为了“城市山林”,也就是在住宅旁边建造具有微缩和抽象的山水画意的园林,形成一种“宅园并置”的状态。那么到了当代,人均土地资源被进一步大大压缩,“城市山林”这种“桃花源”也不可行了。多数人都住在高层建筑或大杂院里面,所以可以看到大家都拼命把阳台扩大,或者在屋顶上私搭乱建做个私人花园什么的,这其实是人性中天然地对理想空间的追求。现今我所努力思考的,就是在当代的现实条件下,建筑师还能怎样为人们营造出“桃花源”式的理想空间。我把“现实桃花源”也叫做“现实理想空间”。
范:就像您在唐山第三空间这个当代高层居住项目中的探索?
李:其实这个项目可看作是“垂直的桃花源”(图5)。在这个城市中心的高层居住综合体中,我们通过变化结构体系,形成错落的楼板,营造出人工地形,以这种地形为基础,对每一单元居住空间进行漫游式的组织(图6),并把这种组织延展到外部,应对原本枯燥的城市景观。因为这种营造,居住者可以日常体验从“喧嚣”到“静谧”的过程,也获得一种“人工化的自然”,生活因而具有了一种诗意,其实这就是“胜景几何”,是对“现实桃花源”的营造。
如果说唐山第三空间是垂直性的,那么最近完成的北京大院胡同28号院改造则是在水平性上探讨一种现实的理想空间,其实从更大意义的角度讲,是北京城市结构从“细胞层级”向“分子层级”加密的可能性。北京实际上一直在加密,从元大都到明清北京,随着人口增加,街巷网格在不断变密,四合院的尺度也在不断缩小。但即使缩小了,每个家庭都仍能拥有一个独立的院子,才能算是自己的理想空间——因为只有在这个院子里,天地人才是完整的,哪怕院子缩小一点都可以,这是中国文化和建筑的传统。但如今大杂院把这个东西破坏掉了,因为这样的状态当然不是人们真正期待的理想空间。另外,我理解北京这样的城市模式中,城市和建筑没有相互的界限,是同构异型的不同尺度和规模的组合,也就是城市有建筑的属性,建筑也有城市的属性,它们的尺度在不断变化,但是原理是一样的,结构是类似的,所以可以说是一种“同构异型体”。由于上述两个方面的原因,再加上解决旧城更新、居民生活等现实需求矛盾的角度,我认为北京城市结构可以再次加密,如果说明清、民国时期北京四合院的尺度是细胞层级的,那么在当代我们有可能把它加密到分子层级。因此我们把“大院胡同”这个项目也叫做“微缩城市”(图7)。它原来是一个占地200平方米的大杂院,我们把它改造成由五套大小不同的合院、一个园庭式立体公共服务空间和把它们串联起来的内部小胡同组成的一个“城市街坊”。同样占地200平方米,但能容纳更多的家庭住户,同时城市结构延伸到院子中,把一个院子变成了一个街区/社区,把原来的大杂院变成了一组合院群(图8)。最后,在这个项目中还探讨了“宅园合一”的可能性——当下的现实条件下,“宅园并置”是不可能的了,那么如果实现了“宅园合一”,就是把生活空间同时也当成精神空间来营造,既解决现实条件下有限土地资源和人口增长的矛盾,又解决更极限条件下人们对理想生活空间的追求,这就是一种“现实桃花源”,操作方法就是“胜景几何”(图9)。“宅园合一”,也使“胜景几何”能够超越那种知识分子逃避现实的小众空间,服务于更多人的日常生活空间(图10)。

图5:唐山第三空间(张广源摄)

图6:唐山第三空间(张广源摄)

图8:“微缩北京”(苏圣亮摄)

图9:“微缩北京”(苏圣亮摄)

图10:“微缩北京”(苏圣亮摄)
这种对理想空间的探讨,虽然是从东方文化和传统出发,但抵达的目标是具有普适性的,可以超越地域、时间和文化的,同时重要的是理想空间营造对多样现实的应对。
范:您提到中国传统城市和建筑有同构异型的关系。这让我想到您在《静谧和喧嚣》一书中也提出了“新模度”的概念,探讨设计中连续的尺度转化。实际上,前面提到的“房”跟“山”两类元素,它们之间的相互转化也可看作是“新模度”的尺度变化。
李:“新模度”的提法目前其实还算是一种假说,是我直觉可能会存在的东西。对于尺度和模数的问题,前人有很多研究,比如柯布西耶的“模度”,又比如《营造法式》中的材、分制度和陈明达、傅熹年等先生对中国古代建筑与城市的模数设计研究等。我认为,既然中国的城市和建筑的概念之间可以没有边界,那一定会有某些共通性的原则在起作用,比如说前面提到同构异型的尺度变化问题,这种变化可以把人的尺度和自然的尺度结合在一起,把设计带入到更丰富、智慧而具体的层次。中国传统中有些说法已经暗示了这种对尺度变化进行的设计控制,比如“千尺为势,百尺为形”——在城市层面和与建筑有较大距离的层面讨论,是“千尺为势”;到与建筑中等距离的层面,就是“百尺为形”;这种尺度变化可以一步步延伸,甚至到家具层面。因为从家具层面到城市层面,都要跟人的行为对接,所以存在这样一种“新模度”系统的可能性。
在“瞬时桃花源”中对这件事也有讨论。这个项目的关键营造元素是施工用脚手架,脚手架可以被视为一个极限化的、跟人体尺度有关的结构和空间单元,它的长宽高跟工人的身体和建造尺度都有关系。我们在大尺度城市场地中用它搭建出不同位置、规模和形状的临时装置物,就产生一系列不同层面的尺度关系。我希望在我们的建筑设计中,能够“研发”出这类东西,它既跟人的绝对尺度相关,又能变化尺度,与从城市到家具的一系列层面空间发生有机的关系。而人对不同尺度空间转换变化的体验,又产生了叙事性。当然“新模度”还与模数化、预制化有关,有利于装配式快速建造。我们前些年的“乐高假山”装置作品是这种尝试的起始(图11),乐高砖块的标准化构件就暗示了尺度变化的可能——你可以把它看作一块山石或者一座假山,也可以看成是一个超级巨型城市的模型,这时乐高就由一个小小积木块转换为一个房间甚至一个大型空间单元。绩溪博物馆庭院中的“片石假山”也是类似的尝试,后来在鸟巢文化中心项目里,我们作了一个比绩溪更大规模的实验。以上这些,都算是对“新模度”的研究和尝试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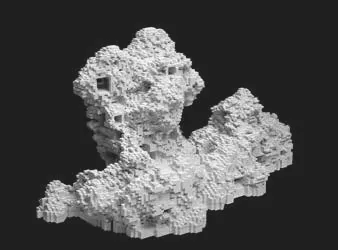
图11:乐高2号
范:在绩溪博物馆这个项目中,我也能感受到一种连续的尺度转化。博物馆位于最大尺度的远山和较小尺度的民居之间,其建筑尺度刚好处在中间状态。建筑主体屋脊的方向呼应了远山走势。而为了保留古树空出的院子,很自然地露出了山形屋顶断面,这是第一次尺度转化。而庭院中类似乐高假山的处理,又一次回应了山形轮廓,并进一步把尺度减小到身体层面。最后,经过二层游廊和观景平台,人们能够俯瞰庭院并眺望远山。这就让人的感受从身体尺度回归到远处的山体尺度。而在这一系列的尺度转化过程中,场地中各类不同的元素被整合在一起,观者也获得了丰富变化的空间体验。
李:设计的时候,我考虑这个房子的屋顶尺度是介于自然山体尺度和小镇民居尺度之间的(图12),它算是一个中介,也是一种人工物和自然物之间的转化。上面的屋顶在庭院中露出断面,就形成了近景山的意象,甚至把屋顶瓦作延伸到墙面,形成一种类似画面透视的错觉,给人以“入画”之感。有了近景的“山”还需要有前景,于是做了这些更小尺度的“片石假山”(图13),是这么个发展过程。“片石假山”里面是半隐藏着楼梯的,人在里面既可以感受到“山石”与身体的互动,又称为其他参观游览者眼中的“画中人”。另外,最初的屋顶形式设计强调的是作为视点和远山之间的中景视看关系,并在整组建筑的东南角设计了一个观景台能够领略这个画面(图14)。在施工过程中,我走在这些坡面屋脊之间察看现场,感觉像是在起伏的山中行走,就想到其实是可以如此体验这个屋顶的,不过当时已经来不及做那么大的设计调整。后来,在深圳的一个公园项目中,我们延续了绩溪博物馆屋顶的形态做法,并且强调了人在起伏屋面之间的体验。这也说明我的很多想法其实来自现场的直觉而非事先的理念性意图;但同时我也会通过项目实践不断反馈,进行深入的思考,然后形成某种有意为之的理念性意图。
范:您曾多次提到大学时期登景山看故宫的经历。如果从精神分析的角度看,其中隐含了您执着的文化模式和建筑原型认知,也预示了“胜景几何”的概念。我觉得您的故事可以拆成两部分。一是站在景山顶端的万春亭里,朝神武门方向看到故宫建筑群的恢宏景象,这就是静谧的空间性胜景;另一方面,您提到了当时和女友爬山的过程。这很像游园的叙事性过程,也可看作是从喧嚣抵达静谧的过程。实际上在您的许多作品中,既有胜景的画面,也常常会有攀登到上层的游廊和观景台。这似乎是对早年那段经历的不断“重现”。
李:通常人们参观故宫是从南面的天安门进去,她是北京人,知道北面景山上有那么一个场景很好,说带我从特别的角度看故宫。那时我从没进过故宫,也没有从天安门循序渐进的经验,我第一次看故宫就是这么看的,所以它突然呈现在眼前,非常深刻的体验和感受。另外就是爬景山的过程:景山上对称的五个亭子,中间是万春亭,东路西路各有两个亭子,我们选择其中一路上去,景山还是有一点高度的,在爬山的过程中,每个亭子都是观景点,在第一个亭子的时候,只能看到一小点黄色的屋顶,半遮半掩;沿着台阶再往上爬,到了第二个亭子,身体也有点累了,又能多看到一些;等登到山顶的万春亭,突然一下子看到了故宫的全貌(图15),不光是那些殿宇的屋顶,还有从层层叠叠屋顶之间的缝隙、庭院中穿插而出的树木,还有隐现远处的现代城市轮廓背景——真是动人的胜景。

图12:绩溪博物馆(李哲摄)

图13:绩溪博物馆(夏至摄)

图14:绩溪博物馆(邱涧冰摄)
今天看来,这就是 “曲折尽致”,是一个抵达胜景的“叙事”过程。可能是一种天意或者是偶然中的必然,我从那时开始体验并感受到,中国传统建筑和城市有这么强大的力量,而且是对于现代的人仍然有这么强大的精神性力量。我想,它能产生如此的力量,背后一定是有着高妙的“设计”或者“意匠”,是一种不随时间而消逝的、有长久价值的“传统”。这就是我对中国传统城市、建筑乃至后来的园林、聚落等产生探究兴趣的开始——研究寻找其背后的原理并试图影响自己的实践。你提到文化模式、原型认知以及对后来设计思想的预示,很有道理。但现在对我来讲更有意义的是,如何将这样的经历体验和思想认知转化成可在实践中运用的空间模式,我在努力寻找一种属于我自己的空间原型,并用这样的空间原型或范式去认知表述和用实践表达。如今我的“大院胡同”项目又回到了北京,回到了当年对城市和建筑的兴趣起点,这并非巧合,当然也会比最初的思考更有空间模式的自觉意识,思想更宽博、更能融会贯通。
范:在空间模式的转化过程中,您的几何操作有什么独特性?
李:实现“宅园合一”——日常生活空间和精神空间的统合为一,跟建筑本体元素的操作紧密关联。具体来讲,我比较感兴趣的是结构、空间、形式、建造以及自然等要素的一体化操作。就是结构既是空间,也制造形式,并与自然交互,形成领略胜景的界面和叙事过程。比如说,你用某种简练的结构做出一个使用的房间,它同时形成了有特点的空间和形式,也可以作为园林中的一个观景亭,它是一体化的;你不能做了一个结构,另外做个东西来形成空间,还得做个动作来制造形式,以及单独的观景亭。这样你的设计就不够精练,带来很多的冗余,“宅园合一”不希望有设计的冗余。建筑师总是想要制造一些通常业主不需要的物质性生活空间之外“精神性”的东西,但如果人家并不想花额外的钱呢?这是个现实问题。所以,我希望自己的设计冗余度是低的,但精神性的“附加值”是高的。我希望做一个动作能达到多个目标。
想要空间、结构、形式、建造、自然的一体化,对我来说通常必须基于一种“几何”的逻辑。只有抽象性的几何,能把所有这些东西联系在一起,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强调结构/空间单元的作用,希望用结构/空间单元的组合来形成整体的建筑,这是我的一个更为具体的操作手法。这跟我对传统的认识和研究有关,中国传统建筑乃至城市就是由一间一间房子组成的,一个“间”其实就是一个结构/空间单元,可以说不同数量、规模的“间”构成了建筑或者城市。如此有很多的现实好处,比如功能的弹性和通用性,以及预制装配建造的可能性等。在绩溪博物馆中,结构/空间单元是混凝土列柱支撑的三角钢桁架屋顶;在唐山第三空间中是垂直方向不断重复的水平错层楼板;在天津大学新校区综合体育馆中是各种连续的直纹曲面混凝土壳体;在“大院胡同”项目中是贯穿于整个院落进深的一条一条混凝土廊式结构。
范:您设计的天津大学新校区综合体育馆项目获得了2018 ArchDaily全球年度建筑大奖,还获得了2016年公民建筑奖的提名奖和WA中国建筑奖技术进步优胜奖。在这个项目中,能感受到其结构既有很强的力量感,也带来了空间层面的诗意感。是否这体现了您追求的结构/空间一体化?
李:天大新校区综合体育馆的设计是2011年开始的。在这个项目里所聚焦的各种直纹曲面壳体结构组合的几何操作,的确是想突出结构、空间、形式、建造一体化的探讨,但其中“胜景几何”的整体思考也是延续其中的。
最初对这个项目场地的印象,是一种断裂和空白之感——一片盐碱地上瞬时建起一片新城和校园,这也是建筑师经常会面对的典型当代中国的建设环境。虽然校园的规划设计要求把天大老校区的砖墙元素使用在所有单体建筑的沿街面上,以唤起与老校园的记忆和关联,但我觉得还是远远不够。我能想象学生的归属感会非常弱,更多可能是一种“空降在荒野”的感觉。所以建筑很重要的目标是让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有归属感,其实也就是要营造一种特殊而专属于此的场所感。所以,这个项目首先需要以强有力的结构表达一种自身的存在之感,它将赋予场所空间性的意义和价值,庇护其中的使用者。

图15:李兴钢草图:景山上看故宫

图16:天津大学新校区综合体育馆(张虔希摄)

图17:天津大学新校区综合体育馆(张虔希摄)

图18:天津大学新校区综合体育馆(张虔希摄)
同时,将各类运动场馆空间依其平面尺寸、净高及使用方式,以线性公共空间串联,犹如多簇运动空间组合而成的密集“聚落”(图16)。空间中结构的不同尺度和形状呼应着人的身体及其运动所产生的不同延伸状态,这样可以把人也看作一种特殊的自然元素,人的身体运动景象就相当于一种特殊的“自然景观”,通过结构与人的身体在尺度和空间界面及氛围的呼应,产生了人造物与“自然物”的互动,呈现出一种别样的“胜景”(图17)。来自场馆空间侧上方的自然光不仅照亮了结构,也映射着运动的身体,人们在空间中感受到人工结构的存在和庇护,同时又强烈地感受到自然的围绕和笼罩,从而形成强烈的空间场域和氛围,并唤起一种使人沉浸其中的诗意情境(图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