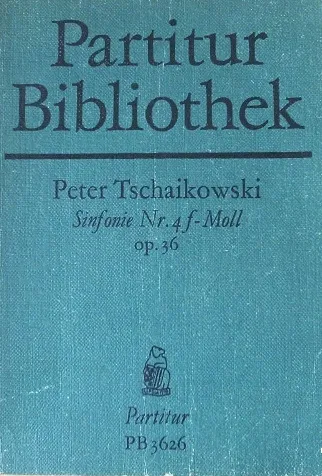柴可夫斯基《f小调第四交响曲“命运”》真实背景揭秘
2018-10-25苏立华
文/苏立华

◎ 柴可夫斯基认为:命运是无法战胜的(彼得·伊里奇·柴可夫斯基,1840.5.7—1893.11.6)
音乐是一种文字语言无法替代的特殊语言。这种语言专门用来记录和传递人内心深处的心声、难以言表的情感和思想,甚至可以表达对生命和人生的理解与诠释。音乐,从形式上看,是时间和声音组合的科学和艺术,从其功能上看,低看它可以是娱乐,高看它可以是诗歌和哲学。从不同角度看它,它就可以成为不同视角中你所希望的任何东西。音乐非常神奇,而其神奇则是通过你如何使用它及如何感受它才能得知。
贝多芬《c小调第五交响曲“命运”》很多人都知道,在爱乐者中已经是听得烂熟的经典;而柴可夫斯基的交响曲,最出名的是《b小调第六交响曲“悲怆”》,他的《f小调第四交响曲》相对没有那么出名,更少人知道作曲家自己给这部交响曲取名“命运”。命运,艺术家笔下永恒的主题,不同的艺术家对命运有不同的理解和不同的诠释。柴可夫斯基心中理解的“命运”和贝多芬理解的“命运”完全不一样。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柴可夫斯基“命运”交响曲中所要诠释和表达的命运是一种什么样的命运。这部交响曲的创作背后有很多鲜为人知的真实故事,今天一起端出来。看完了这些故事,你再去听这部交响曲,也许会听出你内心深处之前没有听到的更多心声。这些心声有多少是和作曲家能共鸣的呢?
十九世纪欧洲民族浪漫主义音乐时期,俄国著名作曲家柴可夫斯基的《f小调第4号交响曲》(作品36)是他第一部摆脱欧洲交响曲创作套路的交响曲。这部交响曲创作于1877-1878年期间,于1878年2月22日在莫斯科举办的俄罗斯爱乐协会演出季音乐会上首演,指挥是莫斯科音乐学院创办人和院长、作曲家、钢琴家和指挥家尼古拉·鲁宾斯坦,柴可夫斯基重要的支持者和好友之一。
灾难性婚姻后遇到了一位给予神助而不允许见面的女神,第四交响曲由此诞生
人们都知道柴可夫斯基是一个同性恋,他的初恋是中学同学谢尔盖·吉列耶夫(Sergey Kireyev),那是一段强烈和纯净的同性恋。但是,他也真正地与女性相爱过,他1868年与保加利亚女高音歌唱家德茜列·阿托(Désirée Artôt)相识,并很快订婚,后来因为德茜列不愿意为了婚姻和家庭放弃事业,也不想在俄国长居而遗憾但友好地分手。1877年柴可夫斯基与他的学生米琉科娃(Antonina Ivanovna Miliukova)经历了两个多月的灾难性婚姻。柴可夫斯基于1877年年底到了意大利去逃避这段婚姻,专心创作。这期间,他同时在创作歌剧《奥涅金》《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和《f小调第四交响曲》。不久,柴可夫斯基经朋友尼古拉·鲁宾斯坦(莫斯科音乐学院创始人之一,钢琴家、作曲家和指挥家)和小提琴家高迪克(Iosif Kotek,柴可夫斯基的好友,亦曾盛传是作曲家的同性恋密友)引荐,认识了俄国铁路大亨富孀梅克夫人(Nadezhda von Meck)。梅克夫人很欣赏柴可夫斯基的音乐,于是她托这两位音乐家朋友把书信交给柴可夫斯基,并让他们转告柴可夫斯基她愿意为他提供经济上的资助,条件是两人不可以见面。尽管如此,柴可夫斯基还是甚为感激,并把这部交响曲题献给梅克夫人,称这部交响曲为“我们的交响曲”(为何叫“我们的交响曲”,请看后面的故事)。创作期间,他写信对梅克夫人说:“我在这部作品中听到你与我在情感和思想上的共鸣”。柴可夫斯基在给朋友的信中也说她要将这部作品题献给梅克夫人,并会在总谱封面上写道:“献给我最好的朋友”。

◎ 贝多芬誓言:“我要掐住命运的咽喉;它永远休想征服我”
俄罗斯爱乐协会倡导赞助人与作曲家在艺术创作上保持平等的交流,赞助人并不是出钱在作曲家面前低头哈腰来表达自己的艺术追求和艺术见解。柴可夫斯基将这部作品题献给梅克夫人正是要表达这种平等的艺术关系。梅克夫人对柴可夫斯基的这份感恩之情也欣喜接受了,并回信要求柴可夫斯基写一个提示性文字介绍这部交响曲。这导致很多作家引用柴可夫斯基为这部交响曲写的解说大作文章,将人们对音乐的关注和感受移到了文字上的解读。英国著名乐评家汉斯·克勒(Hans Keller)在描述第一乐章时说:“这是人类交响音乐文献中最宏伟的一部交响建筑”。柴可夫斯基这个文字解说在很长时间里阻碍了这部作品的流行,音乐家同行很反感用文字来解读音乐。美籍德国乐评家阿尔弗雷德·爱因斯坦等多位著名音乐学家公开批评这部作品。不过,阿尔弗雷德·爱因斯坦这做法也是自黑行为,他对柴可夫斯基的音乐了解甚少,没有听过这部交响曲的演出之前就评价。尽管文字的描述给作品带来一些负面的东西,柴可夫斯基的文字解说也并非是无稽之谈。他说:“第一乐章表现命运”,而音乐也很好地传达了他的这个命题。1878年,柴可夫斯基给梅克夫人的信中说:“第一乐章开始发出的那段音乐(20多小节)是吹响命运主题的号角声,定音鼓上轻轻滚奏出的音乐是整部作品的主要乐思动机,这就是”命运“主题。这是一个阻止人类去获得幸福的厄运。对于这样的命运,人类除了顺从和悲伤,别无选择”。柴可夫斯基解释说第一乐章表现的是“人的一生就是通过不断梦想如何逃避痛苦的现实来憧憬未来的幸福。天堂根本就不存在。生命就是漂浮在大海上的一片树叶,慢慢被海水侵蚀腐烂,最后由凶恶的海浪卷入海底深渊”。对第一乐章表现“命运”主题的立意,柴可夫斯基在给作曲家好友塔涅耶夫的信中再次提到。他对塔涅耶夫说第四交响曲是一部标题性作品,主题思想和贝多芬《c小调第五交响曲》的主题思想是一样的,都是表现“命运”。乐评家汉斯·克勒将贝多芬第五交响曲第一乐章开始处描写命运主题的四个音符乐句与柴可夫斯基第四交响曲第一乐章开始的号角乐段进行了对比。不同的是,贝多芬音乐中的命运是一种人类意志对人类命途多舛的挑战,最后是人的意志战胜命运的统治,而柴可夫斯基的命运是一种召唤,人的意志向它屈服。可在第四交响曲中却出现了罕见的意志战胜命运的声音,第四乐章也如贝多芬第三“命运”交响曲的末乐章一样充满了胜利的欢庆。
欣赏性作品分析
第一乐章
第一乐章,f小调,速度变化多,从行板到快板。音乐由圆号和木管组奏出,随即小号以一个高八度的降A音加入演奏,音乐逐渐展开,进入了一个宏大和慢速的切分音和弦,随即出现两声如闪电雷鸣的短促和弦,每个和弦巨响后是死一般的寂静。然后,木管组奏出了由弦乐声部引入的主旋律。这个主旋律发展迅速,在乐章的后半部,小号再次奏出那个令人难忘的降A音。命运的主题就是那个降A大调的乐句,它不断地出现,成为第一乐章奏鸣曲式结构三个部分的链接部分。这个乐章演出时长20分钟左右,是柴可夫斯基所有交响乐作品中演出时长最长的乐章。
第二乐章
第二乐章是如歌的小行版(降B小调-F大调-降B小调),音乐由双簧管奏出的忧郁旋律开始,高潮处的音乐呼应了笼罩在第一乐章中那凶狠的命运主题旋律。
第三乐章
第三乐章,谐谑曲,这是一个由弦乐声部拨奏的乐章(F大调-A大调三声部),双簧管悠长的高音A音奏出了A大调三声部。随后,铜管乐进入,轻轻地断奏。这个乐章只有弦乐、木管和铜管三个声部演奏,打击乐只有定音鼓。该乐章以弦乐拨奏开始,也以拨奏结束。作曲家没有对这个乐章有具体的说明。命运再不好,也会出现一些乐趣。这个乐章是一个带有忧郁的欢快,如果理解为苦中寻乐,也没有什么不可以。
第四乐章(末乐章)
第四乐章是热情的快板,F大调。柴可夫斯基在这个乐章中引用了一首俄罗斯民歌《田野中的白桦树》作为第二主题的旋律,先以a小调出现,然后是降b小调、d小调,最后回到了第一乐章降A大调那个乐句(用大钹演奏)。尾声充满了欢庆与喜悦。
遵循规则还是跳出规则?理性与感性碰撞孕育出不一样的永恒音符

◎ 柴可夫斯基与梅克夫人
《f小调第四交响曲》是柴可夫斯基试图摆脱欧洲古典音乐创作传统模式(奏鸣曲曲式)的开始。浪漫主义作曲家是用音乐来思考和联想,他们笔下的音乐个性鲜明,表现音乐的技法不拘一格。奏鸣曲式是德国作曲家们搞出来的,它强调作品要讲究结构艺术,来龙去脉必须清楚,前后有呼应,结构得平衡。而浪漫主义作曲家在表现自己的情感和思想时,喜欢以很自由的方式表达内心真实情感与自由的思想。教条性的传统奏鸣曲式结构则会束缚浪漫主义作曲家的自由情感表达和艺术手段的自由使用。柴可夫斯基从创作第四交响曲开始,打破了这种固定格式写作的桎梏,所有表现手段和作曲规则不再如他之前三部交响曲的创作那样循规蹈矩,而是让技术和规则服从自己的情感表达需求。从第四交响曲开始,柴可夫斯基用音乐写自己的情感和思想。他的音乐成了他的一种自传,戏剧性强,音乐的描述从外在描述到心理刻画,栩栩如生,扣人心弦,内外呼应。这种情感的宣泄是直接的,对于聆听者的感染力是很强的,甚至充满了一种情绪暴力。在情感洪流的冲击下,浮出了一曲异常动心的旋律。柴可夫斯基是一位旋律大师,歌唱性是他的音乐特点之一,这种歌唱让人听了会穷其内心所有文字来描述那难以言状的感受,正如托尔斯泰听了柴可夫斯基的音乐发出的那些感叹一样。音乐自由的表达与传统严格的曲式结构规则却产生了对立,自成一体不受曲式结构约束的独立旋律流动打破了西方作曲家约定俗成的奏鸣曲式平衡美。旋律是情感的歌唱,它可以重复,却不能给打散和分解,而奏鸣曲式中的音乐发展则需要音乐在旋律、节奏、和声等元素上的展开,展开了才能发展,而展开就离不开旋律的解体。在创作规则理性与音乐表达感性的冲突中,柴可夫斯基选择了理性服从感性。这就是为什么,作曲家同行听了他创作中期之后的作品,觉得写作上有很多“问题”(专业技术上的规则遵循问题),而普通听众听了之后,则被卷入了他的情感洪流,与他一起仍被冲刷与浸泡。
和俄罗斯“五人集团”(又称“强力集团”)一样,柴可夫斯基将李斯特创立的交响诗体裁与交响曲体裁揉合在一起,用交响诗的体裁表达了音乐中的文学寓意,用交响曲的大布局创造了丰富多彩的乐队交响音色,将文学叙事、诗歌抒情和音乐渲染有机组合在一起,构成了这部音响场面宏大、音色变幻无穷和情感如火山喷发的《f小调第四交响曲》。所以,柴可夫斯基才这样在信中对梅克夫人说:“你问我是否在创作中坚守传统的曲式结构。我的回答:是,也不是。如交响曲这样的音乐是需要使用人们熟悉的传统曲式结构,我从外在结构上还是遵循了传统交响曲写法的,但只是用了交响曲的框架结构,比方说乐章的布局就很传统。而在这个大框架内的细节,即便乐思的发展有规则要遵循,我则认为完全可以灵活处理。比方说,在我们的这部交响曲(柴可夫斯基视第四交响曲为他和梅克夫人共同创作的,所以用“我们的交响曲”)中,第一乐章就有很多明显偏离传统奏鸣曲曲式规则的东西,第二主题,按照规则应该是用关系大调,我用了关系较远的小调。再现部时,第二主题没有再现。末乐章也与传统曲式结构背道而驰”。柴可夫斯基独创的这种混合曲式结构让他可以将一个个独立的对比性乐思段落串在一起,让不同的情绪在一个乐章里汇聚而得以戏剧性地爆发,而不是一个乐章表达一种情绪。这种思维方式也许是受俄罗斯民歌结构的影响。俄罗斯民歌基本都是由几个音和几个节奏型不断演变。这种音乐写作的问题是换汤不换药,只是变个调,而音乐本身没有变化,这是西方古典交响曲写作中忌讳的无聊重复。传统曲式强调音乐按照一种美学规则变化和发展,而柴可夫斯基则是音乐结构不以设计和逻辑来构建,而是用情感自发构成。在柴可夫斯基的音乐中,旋律、调性、节奏和乐队配器色彩共同构成了一个不可分离的音乐表达整体。在第四交响曲第一乐章的铜管乐声部中,他运用了节奏非常鲜明的主题。这个乐章用了一系列不同转位的三和弦(F-降A-B-D-F),再现部则出现在主音下方的一个三和弦。铜管乐在第一乐章中主导了整个音乐结构的发展。为了强调这个乐章的戏剧性,柴可夫斯基在节奏、曲式织体和乐队配器色彩上花了不少心思。这个乐章中的音乐情绪紧张度不是用德国式的主题变化营造出来的,而是用表现那扑面而来的“命运”主题(铜管乐奏出)中强烈的节奏与弦乐和木管组交替奏出的圆舞曲第一主题之间的冲突来表现的。

俄罗斯“五人集团”
第四乐章是对前三个乐章很好总结与呼应。第一乐章中“命运”主题再次出现,最后消失在欢庆的气氛中。这种欢庆与贝多芬《c小调第五交响曲“命运”》和《费德里奥》序曲的欢庆结束,以及柴可夫斯基《1812序曲》的曲终欢庆场面是一样的。柴可夫斯基用这个乐章表现了俄国贵族当时的精神追求:民族爱国主义精神和英雄主义精神。这种精神贯穿于俄罗斯的文化,直到今天都是如此。
首演及最初演出的反应
柴可夫斯基《f小调第四交响曲》的首演反应不是很好。首演时,梅克夫人独自一人耐着寒冷坐在包厢里听,而柴可夫斯基那时正在意大利的弗洛伦萨度假和创作。演出后,梅克夫人第一个给柴可夫斯基写了信。他音乐界的朋友对于这部作品不是太明白(因为不守传统规则的创作),只有塔涅耶夫和鲁宾斯坦等几位较贴心的朋友给他写信轻描淡写地说演出成功了。尼古拉·鲁宾斯坦在电报中也只是说首演乐队演奏很好,对于听众和乐评的反应只字未提。一个月后,柴可夫斯基写信给塔涅耶夫,塔涅耶夫立即给柴可夫斯基回信。信中,塔涅耶夫如往常一样直言不讳,他对柴可夫斯基说,作品的各个声部还是写得很好的,只是整体效果听来逊色了些。塔涅耶夫很喜欢第一乐章,但觉得时间过长了。塔涅耶夫认为第一乐章就是一部交响诗,之后的三个乐章只是为了要让这部作品成为交响曲而粘贴上的。尼古拉·鲁宾斯坦则最喜欢末乐章。柴可夫斯基给塔涅耶夫回信进行了一番辩解,同时也表达了他对塔涅耶夫真诚直言的欣赏。柴可夫斯基似乎感觉到塔涅耶夫回避不谈首演来自听众的冷淡反应。第二年十一月,这部交响曲在圣彼得堡的演出,听众反应就好了很多。
1890年美国的首演,听众反应也很冷淡。一位《纽约邮报》评论员写道:“柴可夫斯基的第四交响曲是纽约这座城市迄今为止上演过的俄罗斯味最足的交响曲,野劲十足!如果柴可夫斯基给这部交响曲取名“西伯利亚的雪橇”,不会有人觉得这个名字取得不妥”。1893年,柴可夫斯基应邀前往英国接受剑桥大学给他颁授荣誉博士,他亲自指挥这部作品在英国首演,获得巨大成功。前来接受荣誉博士受聘的还有法国作曲家圣-桑、马克斯·布鲁赫、阿里戈·博依托、格里格(没有到场)。演出现场座无虚席,每个乐章演出完,听众都报以热烈的掌声。这是自这部作品首演以来最成功的一次演出,柴可夫斯基亲自感受到了真实成功的喜悦。
对这部作品的评价,有极端的赞美,也有极端的批评。1897年一位德国乐评人写道:“柴可夫斯基这部交响曲中那些无聊的音乐让我很烦。铜管乐一阵瞎闹,定音鼓敲个不停。让我听不下去”。
这部交响曲经历了各种赞誉与批评,如今已经是世界各大交响乐团重要的演出保留曲目之一,从十九世纪后期开始就很流行,经常上演,也被后人视为柴可夫斯基所有交响乐作品中的经典之一。据不完全统计,到2018年为止,正式出版的录音就有200多个不同演奏团体或同一个演奏团体的不同录音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