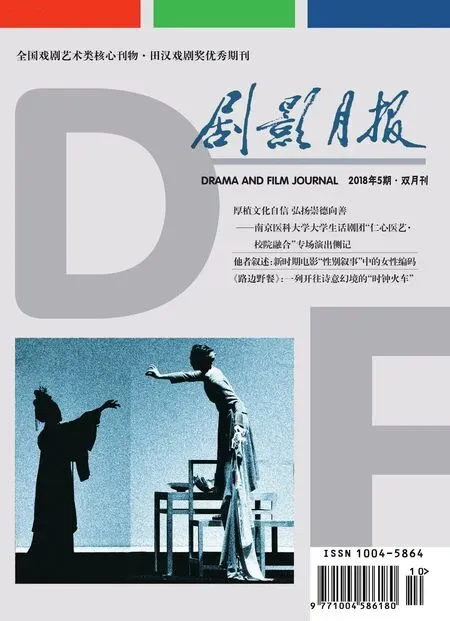皮相还是救赎
——以《布达佩斯大饭店》为例浅析电影的形式意味
2018-10-25
作为受制于欲求的高级个体,人在追求美的无尽道路上,总能在或荆棘或平坦的岔口与众多艺术形式不期而遇。以至“形式”成为司空见惯的必经,而非苛求偏执的目的地。艺术的形式在不同门类间可谓大相径庭,如若将“声、光、色”视为一部影片的构成要素,那这也必是“第七艺术”的形式之基。纵览斑斓浩瀚的电影史中,观者又总能走入形式美布设的罗网,被之俘获。
一、情怀的执拗
马赛尔·马尔丹将电影视作语言,他敌视那些没有丝毫美感的作品,认为“这些影片缺乏的,就是人称为‘灵魂’或‘吸引力’,被我命名为‘存在’的东西。”这里的“存在”,既可理解为人云亦云的艺术性,更可指向切实地表意形式。形式是电影击溃观者心理防线的必要手段,“手段”一词虽带有些许的狡猾,但却是这伟大戏法的关键道具。韦斯·安德森是这个时代的大魔术师,在他的作品中,贯穿着一种昭然若揭的优秀品格,那是对旧时代的迷恋与高度风格化调和的产物——一场难以名状的梦。
《布达佩斯大饭店》是韦斯·安德森于2014年的导演作品,获得第87届奥斯卡最佳艺术指导、服装设计、原创配乐等大奖。影片的叙事结构是将四层时空相叠套,通过无名作家与饭店主人穆斯塔法于席间的一番交谈,呈现出布达佩斯大饭店的前世今生。故事主线游走于前主人古斯塔沃与D夫人遗嘱间的波折,伴随着厄运的袭来,既有主仆间感情的升华也有一个时代消亡的悄然而至。影片以全景视角描摹了欧洲战前文化褪色过程中的最后一抹余晖,纵使有众多迥异人物穿梭忙碌于不同的运动镜头、机位景别之中,但那扑面而来的童话般冲击力,无不在触动着观者的心弦。整部影片像一例深刻而独到的装置艺术。说其深刻,是源于故事本身在嵌套式叙事结构下,流淌着一个令人悲悯心动的时代。“昨日世界不复存在”的矜持呻吟,似乎在当下具有了更微妙的时效性——是不堪回首,还是难以磨灭。
而这里的“独到”正是指向导演倔强的情愫所在。“美要依靠体积与安排。”纵使再光怪陆离的艺术创作,也是对亚里士多德的美学概念笃定的实践。韦斯·安德森甜蜜不轻佻的视听话语与他所钟爱的复古情调浑然天成。形式在这里作为他传情达意的载体,是最具权威的执行官。直截了当的符号堆砌,干练果断的镜头组接。无论是在人物包装还是氛围营造上都层层裹挟着看客们的官能武器。古斯塔沃和门童一丝不苟的工作套装;武装部队于火车上查验证件时,背景配乐响起的军队符号化的鼓点;毫厘不差的对称镜头、温润的高级灰色调。这里韦斯·安德森将形式的功能性发挥到极致水平,并与他心中的感官盛宴同符合契。
二、肉眼的欢愉
芙蓉出水也好,错彩镂金也罢,终究要落脚于形式美之上。电影的形式风格大致由场面调度、摄影、剪辑和声效构成,导演的想象梦境具象于荧幕上,搭以形式之媒涌入观众的眼、耳、神经。观影经验告诉我们,在欣赏过程中如若出现“电影把整个人都吸进去”(即与影片中人物产生同构)的体验,那必定是同时调动了人的全部感官与心智功能。
艺术形式的概念盘踞于电影创作中已有一个多世纪的年头,于实践者、评论者还是观赏者心中都是一个神秘而可靠的存在。从电影诞生之际的记录、杂耍之争到关于本体论的蒙太奇、长镜头之辩,都可归为艺术形式变迁的母题。于上世纪二十年代在欧洲大陆兴起的先锋电影运动,对电影的形式特征进行了全面深入开掘,也是辉煌影史上的里程碑段落。先锋派艺术家大多秉持着不以叙事为目的的理念,追求纯粹视觉的形式美感,目的在于营造出节奏、形状同光影拼接的盛宴。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谢尔曼·杜拉克既是提出“纯电影”概念的理论家,也是最忠实的践行者。她认为完整电影是“形状的电影”和“光的电影”的汇合,旨在为观众呈现一场“视觉交响乐”。如美国美学家布洛克所说毫无二致,“只有抽象形式才是纯粹的形式,真正的审美理解指向这种纯粹形式”。在其后掀起影像巨浪的,是发生在德国的表现主义电影,一战所积存的恐慌以及对现实生活的逃避,导致艺术家们躲入不自然的形式和变形的世界中表达内心的紧张、焦虑。造型风格上使用超现实的布景,人物着装怪异夸张,以完全人工化的高对比照明来突出整体氛围的神秘感。以上这两种远离传统的影像革命,在对人眼进一步刺激的同时也在电影形式上取得了影响深远的进步。
谈回《布达佩斯大饭店》。韦斯·安德森以疾行的步伐行走于世界影坛的先锋之列,其独树一帜的影像风格离不开刻度表般精妙的形式技巧。说他是好莱坞最会用对称构图的导演不足为过,这也成为他作者风格的鲜明标志。布景装置、角色走位,就连光影对比的细微之处都将画面平衡感刻画的淋漓尽致,严谨又有趣。异曲同工之处的,是对黄金分割比例的操控。不仅在于被摄主体的站位、角度,就连人物移动也遵循这一比例节奏,保证对象在画面中的稳定状态。整体情绪的轻重缓急,人物状态的安适肆意,全凭镜头的灵活运动去书写。在保证叙事严密性之余,冷幽默的小插曲也为影片增色不少。为了驾驶雪橇追赶冷血杀手,不惜果断地击碎神像——意在嘲讽宗教的无力,只有自己才是救世主。即使在被逮捕前危机四伏的山巅,古斯塔夫也要为忠仆的牺牲默哀;而逃狱出来的第一件事竟是安然自若地向仆人要“羽之味”香水,诸如此类的“不合时宜”更凸显了这场冒险的荒诞氛围。而沦陷后的黑白色调、方形的画幅比例也增强了全片的古典氛围。总之,不论怎样的故事,韦斯·安德森都能变幻出一个万花筒般流光溢彩的世界。
三、存在的救赎
“在哲学上有一种看法认为,形式是我们据以理解世界的范畴,没有它,客观世界将是无法理解的。”通过形式的意味来理解寓于作品中所投射的世界,这“世界”是作为对象物的客体所在,也即艺术家的思绪所在。存在的个体吸允形式之上所安放的慰藉,同时获得抒解、救赎。电影艺术对这世间的存在所给予的,是在特定时空段落使其沉浸于用影像勾勒出的另一个绚丽世界里。观者在其中与每个迥然不同的异次世界产生认同,受到情绪上或喜或悲的冲击,以此获得释放与自由。
将平凡的现实提纯、赋予意义是通过形式变奏得来的直接效益。如宗白华先生所言,“‘形式’里面也同时深深地启示了精神的意义、生命的境界、心灵的幽韵。”与上述“纯电影”、“表现主义电影”同期发端的法国印象派,便有一种电影对人精神世界的萌芽意识。它承袭了印象派的绘画传统,极力斟酌着每一场景的光影气氛,探求自然物象于人物心理的精神对照。在画面的把控上运用了情绪化的主观视角、移动镜头等摄影技巧,虽不济CG(Computer Graphics,意为数码图形)特效的美轮美奂,却也令人心神向往。当观者踏入这飘渺虚无的光影之地,悠扬的静谧伴着无限的身心安抚扑面袭来。
当我们回顾起久违的影视作品时,那些在心中留存的印记又有多少能切实明晰在脑中、眼前呢?大抵是些碎片的面孔、朦胧的配色,若有些许捧腹的情节,那便是极幸运了。此刻回想起《布达佩斯大饭店》时,就像是韦斯·安德森给这出小闹剧的最外端,套上了一个温柔世界的滤镜。每一抹和煦朝霞,每一帧对称画幅,每一秒节奏韵律,都能在拿捏着观众期许的同时带来意料外的雀跃。那藏匿于浮华间的细腻考究,不仅带来高享受的观影体验,更是他在电影形式驾驭上的登峰造极。
电影形式在这一艺术门类中担当的是艺术家与观众间的摆渡船,是作者情感的直接媒介,作品思想的可靠依托。尽管有些许言论指向《布达佩斯大饭店》有形式大于内容的嫌疑,但这就是韦斯·安德森。所有泾渭分明的规矩都是理所应当;所有条理明晰的章法都是心悦诚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