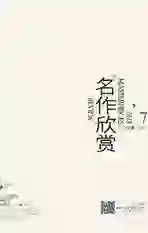照妖镜
2018-10-20郑雅匀
郑雅匀
摘 要:《张曼娟妖物志》里的那些妖物被抽离开原来生存的时空,将虚幻的故事放进现实生活的环境,这些妖物越活越滋润,竟然生出更昌盛繁茂的生命力。本文力图打开妖物世界向人间虚掩的门扉,对照他们的生命和我们的生命,探寻人类热衷于创造神话、衍生传说、再造妖物的原因,透析读者更深的心理层面:我们为什么要“妖”?
关键词:妖物 现实 情爱 救赎
一、妖声四起
2006年9月,著名作家苏童用现代方式重构孟姜女哭长城的传说故事,是为《碧奴》。加入英国坎农格特出版社发起的“重述神话”系列,是图书市场的一次全球性跨国合作,另两位著名作家李锐与叶兆言也加盟其中,分别阐述《后羿》《人间》,可见“妖”之炙手可热,令作家们趋之若鹜。
“中国的小说,和世界各国一样,是从神话和传说开始的。神话是把神‘人化,传说是把人‘神化。这两者之间的界限是很难确切划分的,其共同点都是演说故事。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志怪志人小说。志怪小说大多以鬼怪神异为题材……唐代的小说叫传奇,始于唐初,由六朝志怪发展演变而来,多以历史、爱情、侠义、神怪等故事为题材。传奇,即传写奇事的意思。”古人对鬼怪神异的热情,早前《山海经》已见端倪,《女娲补天》《夸父追日》《精卫填海》等故事家喻户晓。晋人干宝《搜神记》、东晋陶渊明《搜神后记》、宋代李昉《太平广记》、清初纪昀《阅微草堂笔记》、蒲松龄《聊斋志异》都不失为个中翘楚。《干将莫邪》《东海孝妇》《画皮》《胭脂》等为后世的文学艺术再创作奉上了无数蓝本。民间《白蛇传》《宝莲灯》等也大放“妖”彩,至今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现代人也有恋恋于妖物故事的作家,其代表可看香港女作家李碧华,《潘金莲之前世今生》《青蛇》《胭脂扣》《饺子》都是一时之选,妖风四起,“妖”有声色。一“妖”未平,一“妖”又起。台湾女作家张曼娟从中国历代古典笔记小说里汲取了七则妖物故事,写出了一本全新的现代人心目中的《妖物志》。把笔记小说里的那些妖物抽离原来生存的时空,将虚幻的故事放进当下生活的环境,这些妖物越活越滋润,竟然生出更昌盛繁茂的生命力。本文便借由这个缺口,打开妖物世界向人间虚掩的门扉,对照他们的生命和现代人的生命,探寻人类热衷于创造神话、衍生传说、再造妖物的原因,透析读者更深的心理层面:我们为什么要“妖”?
二、妖言惑众
《张曼娟妖物志》由八个妖故事组成,其中,花仙的故事《后来,花都开了》来源于她个人的梦境,所以本文主要讨论七个在古代书籍典藏中有根有据的妖故事。这些故事中,人妖混居,人妖纠结,妖人爱恨,或情断弦绝,或难割难舍,或愿望落空,或身败名裂,无法掩盖结局悲伤的缺口,引发宿命感叹。因为这个世界本没有妖,没有怪,没有仙,没有精,人的世界里只有人。那种种妖物,都是人想象出来的。为什么在清醒地明白了这一切之后,人还是会缠绵于妖物的世界,被妖言惑众、自甘沉溺?
(一)小小的芭蕾舞步·少女猪(妖物前世出自干宝《搜神记》)
失去灵感是作曲家古丰乐的悲哀。哪怕是在睡梦里,失去灵感,也成为永劫不回。想拼命再睡去,希图续上原来那个梦,却发现已经回不去了。梦难续,空惆怅。这个落差就造成了“妖物现形”,往往直抵人命。乐曲可以写得很完美,爱情可以想象得很完美,未来可以计划得很完美,当一切回到残酷的现实时,殘留下来的,只是一个支离破碎的粉红色的梦。有时候,有些人,有些物,救得了他人一时,救不了一世。失去他们,还连带失去了自己。如此一来,像猪一样酣眠,永远沉浸在自己温暖得直哼哼的睡梦里,真是最幸福的事了。妖来了,有何不可?
(二)永恒消失·女螺(陶渊明《搜神后记》)
怀疑顾忌,常常成为人活着不快乐的根源。事出有因,却未必有果。有时候即便那结扣快解开了,又暗自用力,使之成为一个死结。将自己捆绑囚禁的段子淳,遭遇一只从客厅鱼缸的壳里爬出来,企图化解家庭悲剧的苹果螺。人与妖始终未能达成共识。妖物用妖的思维帮助人解决问题,而人用自己的思维判断问题,人不尝试做可能的努力和沟通,只学会去等。等坏的过去,等好的缓步而来,从天而降。这故事里的女螺,颠覆了原来的红螺女,是个有思想、有个性的“妖”。她掌控局面,如果人一再犯错,那么是要让他付出代价的。现代的女螺和传说中的一样决然,而在古老的传说故事里,小伙子因为红螺女,最终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三)雨后·虹精(干宝《搜神记》)
有时候,会有这样一种极致而受人尊重的情感。我爱你,却知道永远无法靠近你。那么我会成全你,无论你心里有谁,无论你去向哪边,无论你是人是鬼。笔者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另类的妖故事。主人公季子惟和他的情敌虹精没有任何交集,妖夺走了可能属于他的一切:女人、孩子和梦想。妖物在这个故事里,不是赠予者、救赎者,相反,是一个私心颇重的吞食者,妖物世界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算计到了人的头上。这在妖故事里,不太多见。人希望人能遇到一个善良的妖,可以带动自己欢笑,而不是一个利用者。但是人有权利去责问妖吗?因为,人有时没有能给予他爱的人最大的安全和保护。人做不到的,妖做到了。或许仍然应该感谢妖,是妖借由他们的魅力和法力,才给了人梦幻般的彩虹天堂。
(四)星星倾巢而出的夏日·羽衣娘(陶渊明《搜神后记》)
这个故事可以这样解释:我带不走你,那我只能带走你的孩子。“钩星”如勾心,当一个人的心被勾走了,那么,他的全部也就被带走了。妖怪羽衣娘,有专门偷别人家的小男孩的癖好,她为什么窃取别人的孩子,她要带他们去哪里,做什么呢?钩星为什么会爱上勉生?“只要染上了我的血,没有一个要不到的。只有你,你是我钩不到的星星。”“愈是要不到的,就愈想要。”追根究底,还是因为心里那份痴缠。她不肯走,并不只是因为那可能会被藏起来的羽衣,或是为了享受人间繁华的生活,而是一颗系在别人身上的心。她们不停地勾着别人的心,自己的心又不知不觉地被人勾走,人与妖,苦苦纠缠,奋不顾身,堕入红尘。
(五)永恒的奔驰·马男(干宝《搜神记》)
奔跑,是人对于生命、爱情、自由、快乐的追逐和向往。因为勇敢奔跑成全了生命里的完美,像风一样,掠过时间之河。看过干宝《搜神记》的妖前生,发现关于马妖的故事和原来的故事差别较小,更符合现代人的阅读习惯。故事中的马男,因为具有马本身的雄性力量、奔腾与飞扬的个性,所以符合一个有担当、勇敢的男性标准。无疑,马男是无可挑剔的男子汉,他比许多真实存在的男人更像一个男人。马男如同一位血性男子,在小说里有过三次奔跑,而且一次比一次强烈,如同战鼓,节奏越来越激昂。他不要停下,而要奔向属于他们两个人的永夜。可惜如花娇艳随风凋零的都市女性,却没有机缘遇到马男一样的妖,她们遇到的都是人形结构完美、情爱严重萎缩的“男种细胞”。
(六)尾巴的诞生(郑常《洽闻记》)
这个故事比较值得回味的地方,是阿逸的身份和态度。阿逸因为海难而对人鱼怀有怨恨和戒心。他的抗拒超出常人,却又同样因为对那条被劈断入海的人鱼的愧疚,最终将她豢养在池中,喂给她红玫瑰花瓣。在他和人鱼的交合中,他找回了他认为一辈子都不会再有的男性的渴望和感觉。这是多么的难以抗拒!如陷入流沙,这个人鱼柔软的鱼尾巴给予他唯一的快慰和拯救。他的尾巴突然长成,无比轻盈,在水中欢快扇动。他自己原来就是一条人鱼,之前不过是用一双残疾的腿冒充人类混进人群,这种假装只给他一个身份的证明:他是残疾人,是不合群、不快乐的人。从人到鱼的蜕变,是他寻找自我的过程。不被社会接受,在社会认定范围内从来没有幸福感的阿逸,必须重新找到自己的身份,才能变得完美,成为一条幸福的人鱼。如果不能获得快乐的人的身份,那就做一条鱼,抛弃假肢,甘愿在深海里变成一个妖。
(七)不太远的地方·狐妖(干宝《搜神记》)
狐妖,通常来说都是女性,最多的狐妖故事来自清朝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全书有八十三篇故事是描写狐狸精的,可谓狐妖大全。小翠、婴宁,娇娜可爱;青凤等狐妖,美丽妖魅,善良聪明,轻易俘获男人的心。狐狸精还进一步演化为人们用来形容女人的专用词汇。“狐狸精”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女性的专属。同时人类还基本认同了这样一种狐妖和人结合的模式:男人可以娶女狐妖,将她们收归到现有体制,但是很少能接受女人跟一个男性狐妖结为夫妻。张曼娟这个狐妖故事,把狐狸精设计成男性,一开始就颠覆了读者可怜的想象。这男性狐妖的名字——阿紫,是女性常用名。更加令人想不到的是:这个男性狐狸精,爱上了一个男生。这一下如同触了电,这才是对于想象力最大的考验。干宝《搜神记》里的狐狸精原本是妇人形的,并非男妖。为什么这里的阿紫别出心裁地成了男妖,而且还因为当年其母养育之恩爱上男子清泉?2005年,著名导演李安的镜头里,两个年轻英俊的牛仔杰克和恩尼斯在断背山上,生出深刻的同性情意。纯粹而隐忍的情感,使得这部电影,在男女异性相爱为主流的社会传统中,并没有因为同性恋情而减损艺术价值。主人公的命运,感动了全球口味挑剔的观众,并一度引发了对于人性情感的深刻思考。所以,在一次次的惊诧之后,读者慢慢变得平静。这个故事是压卷之作,也许作者的意思,就是让读者在经历了各种情欲与悲欢的纠缠后,可以简单而自然地回归本质:释放欲望,回归性灵。如果仅仅是一个象征和符号,那阿紫是什么性别并不特别重要,因为同性爱比异性爱更为艰难。有时它几乎被视为绝路,而能在绝路上相逢相知、生枝开花,本身就是一个大逆转。它不为教条化的规则所束缚,将被异化的人渐渐拉回到本质的人。同性爱,也有深刻而无法道尽之感怀。他们不需要救赎和宽宥,男妖也好,男人也罢,心存如此深厚缠绵的爱,是爱之最空灵和感人的境界,有足够的力量使人低下羞愧的脑袋。
三、照妖镜
(一)妖物世界与异度空间
妖物世界存在于人类的想象可能触及不到的地方。我们凭借理智可以知道它们或许并不存在,但是从感情上看,未必如此。晋干宝《搜神记》自序中说:“群言百家,不可胜览;耳目所受,不可胜载。亦粗取足以演八略之旨,成其微说而已。幸将来好事之士,录其根体,有以游心,寓目,而无尤焉。”这里我们应注意这六个字“有以游心,寓目”,也就是说妖的世界对许多人来说是妄说,但是大家又喜欢听妖言,用来娱乐自己的身心,甚至浮想联翩,逸兴遄飞。我们从感情上接受了这个虚幻的妖世界,甚至热衷于妖故事,在妖物身上寄托了自己在人的世界里所不能妄言的情感。在他们眼里,这里的世界真奇妙,这里的妖物真可爱。《聊斋志异》自序中说:“披萝带荔,三闾氏感而为骚;牛鬼蛇神,长爪郎吟而成癖。自鸣天籁,不择好音,有由然矣。松落落秋萤之火,魑魅争光;逐逐野马之尘,魍魉见笑。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闻则命笔,遂以成编。久之,四方同人又以邮筒相寄,因而物以好聚,所积益夥。”在这里,写妖谈鬼,录其故事,简直是堪比屈原苦吟《离骚》的大事体。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固然可彰显屈子人格;牛鬼蛇神狐狸精,翩翩身影,也不辱蒲生风采。四下同道中人互为交流,把妖物世界发扬光大。旷野苍茫,借宿古庙的书生在深夜盈盈摇曳的烛光中,瞥见娇弱不胜的年轻貌美女郎,挡不住深夜孤枕难眠,甚至不用调情攀谈,便抵死缠绵,不管红尘纷扰,功名利禄。美人无名,前程莫测。及至天色将曙,温香软玉倏忽而起不告而别,转瞬不见了踪影,书生不以为怪,亦不生疑,反而因为回味更期待下一个夜晚的快快到来。小说《画皮》中书生引女鬼回家,哪管他人非议;电影《画皮》里女鬼被重新塑造为千年白狐,温柔如水,为了爱不择手段。而将军王生竟然也有所感:“不是我不爱你。小唯,只因为我有了佩蓉。”反过来便是:如果不是有了佩蓉,即便你真的是妖,我也爱你。此言一出,白狐的眼泪纷纷掉落,晶莹剔透,美艳妖冶的人形终于肯灰飞烟灭。因为爱,他们都选择了牺牲自己,成全爱人。好一出含蓄委婉的人妖恋。人又怎样?妖又怎样?无情者人不如妖,多情者妖可爱于人。贫穷困苦、躬耕南亩的小伙,又累又饿,回家竟然发现灶上有饭有菜,那锅尚冒着热气,自己无父无母无兄无弟,是谁为他做下这顿可口热饭?那是一个红衣服的面目姣好的姑娘,細问之下,原来竟是自己救过的一只田螺,如今前来报恩。这些妖,是真善美的化身。他们幻化人形,总是出现在最寂寞最孤单的人身边,带着他们走向对于人而言不可企及的幸福和光亮。被法海擒拿镇压在雷峰塔下的白蛇,起因也是为报前世恩情。在烟雨迷蒙的西湖,一把纸伞,结下情愫,誓同生死。“小青,你不懂的。”面对那终不能理解的妹妹小青,白娘子这样说。因为尝过了人间情爱,妖流连忘返,即使赔上千年的道行又有何悔?这是异度空间中人和妖物共同的逻辑基础。
(二)现实世界的不完满与缺憾
书中的妖物,每一个都是在主人公——也就是人类,最孤独、最寂寞、最无助、最困顿的时刻现身。生活在物欲横流的都市丛林中,日夜忙碌的疲惫不堪的狩猎者遇见了充满诱惑力的妖物时,他们突然定睛,或者放慢了脚步,如同捕捉萤火虫的孩子,屏住呼吸,轻轻地向那发出微光的物体伸出自己的双手,想拢住火光,拢住心头的一点亮和温暖。
每个人都带有一个天生的生命缺口,对这个真实的人的世界充满迷惘和怀疑,仿佛需要接通另一个世界的电源,人类机器才能强力运转。山东大学教授马瑞芳讲《聊斋》时说:“在仙、妖、人、鬼四境中,只有妖境是没有法律的,是最不虞制裁的,它成了中国人畅遂其欲望的一个理想渠道。”“如果说《聊斋志异》里的狐妖故事是中国人‘个人原我及‘社会原我的显影,那么作为‘个人超我的道德意识及作为‘社会超越的人间法律和礼教,在这里都派不上用场,对它们都少有制裁的力量。”既然如此,人类为什么不放下作为人的虚伪的自我,去那个可以放飞“原我”的世界与妖同游?最瑰丽奔放的人生可能并不在这个人间,而在于那个飘忽不定的妖物世界,人类所有的狂想都是遵循某种情感方式的。自由、平等和公正,在生活之中,也在生活之外。妖的世界教会人一种特别的思维:人们在生活之艰难中,放下一切,尽情地跳到生活之外,也便能得到解脱。梁山伯与祝英台、刘彦昌和三圣母、许仙与白娘子,就像《妖物志》里的古丰乐与金铃子、马男与萱儿、阿紫与清泉,在那个世界里,世界呈现出简洁而温暖的线条,人的情爱欲念有率性而粗陋的答案,所有严酷冷峻的现实问题可以得到顺利解决,一如可以被轻易穿越的瑰丽彩虹。也许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对于这个世界和那个并不存在的世界的最独特的认知,对一颗颗看不见的跳动的纯朴的心的认知,对一种业已久违的情感的认同。许多妖的故事是传奇,但那不是某一个鱼精、田螺或白狐的传奇,是属于民间,属于整个人类关于自己和未知世界的传奇。基于此,才有孙悟空大闹天宫、沉香开山救母等故事,幻化出一个现实世界的擎天大手所无法触及的世界:我行我素、情天恨海、自由自在,顺遂了人内心深处最隐秘而热切的渴望。
(三)人类情感的枯萎、衰竭、冷漠、变异
现代人也已发生异化,面目全非,人心变得千疮百孔,可能人类已经很难知道安抚寂寞、驱除内心鬼怪的办法。为了唤醒已经麻木的肉体和灵魂,人们上下求索,望眼欲穿,朝如青丝暮成雪,所等待的那个人还不来,沉重的疑团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痛苦哭泣,累过之后,感觉自己是一个箱男或箱女,小小的木箱子装下一个扭曲的身体,别别扭扭沉沉睡去,难道只能去妖的世界寻找牢固的“感情创可贴”吗?从某种意义上说,妖物世界是飞翔的黑暗现实,也许说到底依然沉重,但人仍可借此短暂摆脱现实,得到愉快的体验。摆脱,再投身其中,那已经是一个彼岸。也许人在这个世上唯一拥有的永恒实体——人类的身体,便是所有灵魂沟通的入口和出口,只有爱或者做爱,才能重新获得力量,发现生命。人与妖之间,全然不可用什么物质名利、思想学识来进行比对。操控着人与妖的,此时只剩下双方唯一可以给予的情感,来自身体本能的欲望与欢爱。人的本能是简单的,但人类之间却不懂得互相理解,不断在和这个纯真的世界疏远,最终得到毫无价值的东西。他们生生地抛弃了简单纯粹的快乐,让自己的寂寞成倍地放大。我们到不了其他的世界,除了死亡,只能进入另一个虚无。而妖精的现身,仿佛自井口垂下的一条长绳,可以让人攀缘而上。为什么以身体的形式出现?因为身体是我们在这个世界唯一从生到死拥有的东西。用身体去接触和安抚另一个寂寞的身体,解除所有的束缚,释放出人心深处最真实的渴望和欲念,这难道不是爱到最后的极致表现吗?所以《张曼娟妖物志》里的大多数妖物,都曾经用身体与他们选中的人发生了情欲关系。这是一部让男人们心旌摇荡的现代《聊斋》,这是一段段奇妙的体验。如果延伸开来看,人与妖之间发生亲密关系时,所显示出的特质,应该不再是单纯意义上的社会人。这时,人类的动物本能凸显,身体的快感操纵了灵魂,所有的道德观念、社会秩序土崩瓦解,溃不成军。那些妖物在没有被道德秩序所禁锢的思维中,用他们最本原的身体来救赎这个世界的人。正如张曼娟自己所说:“想要炙热地爱人或者被爱,理智是无用的。非得有些妖气。人在做爱时最为妖媚,人在恋爱时法力无边。”在拥抱时,肉体的碰撞是最真实、最可感的。这大概就是被一些社会秩序所异化、所孤立的那些非常寂寞的人找到自己确定位置的唯一方法。这也是新品种妖物们所存在的最真实的作用,即使原来虚幻的故事变成了可能的桥梁。
它们用自己的身体,撕开了那层阻隔人与人之间亲密距离的网,尽管这种种看起来稍显轻率鲁莽的情爱使故事在某种程度上更带有荒诞的特质,但是它们却是还原自我、回归此岸的那座木桥。欲望如海,海水无边;欲望如船,载着人们摆渡光明与幽暗、现在与将来。最初的原初,甚至三生石上,在那里,人类最终回到了人。也许错身未知,也许缄封成秘,也许不愿承认,妖物活在你心里,这些妖精,这些仙怪,人类没有见过,又有谁真正见过呢?隔着深不可测的崖岸,人和妖互相凝望,常常,人类手拿明亮如雪的镜子,看不见他们;而它们,轻而易举地看到了茫然失措的我们,看到了人的透明和苍白,看到了人类内心深处的痴情狂热、自私虚伪、空洞无助、寂寞绝情。妖物掩口摇头嗤嗤而笑,那笑声甜蜜温暖如同洁白的羽毛。它们不是彻底救赎我们的那根绳子,但人类因为没有出口,还是上前抓住了。
此刻人要假设和思考的是:当某天,遇到一个深深爱慕自己的男妖或女妖,在它们那个世界的门口向人招手微笑,背后有鹅黄色温暖而奇异的光芒,四目投注,心动神驰,人们会不会稍作迟疑,将手中照妖鏡反转,一步一步走向那神秘莫测的光之所在?
参考文献:
[1]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2] 马瑞芳.马瑞芳讲聊斋[M].北京:中华书局, 2005.
[3] 马瑞芳.马瑞芳揭秘聊斋志异[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
[4] 蒲松龄.聊斋志异[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