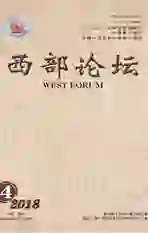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第二次飞跃
2018-10-20
摘 要: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发展,已实现了从人民公社制度到家庭联产承包制的“第一次飞跃”,但仍需要向规模化经营和集体经济方向进行“第二次飞跃”。本文基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考察了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两条路径,提出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是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第一次飞跃的理论依据,这表现为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第一条路径。而生产关系改革引领生产方式演进和生产力水平跃升,则是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第二次飞跃的理论依据,这表现为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第二条路径。在对安徽小岗和贵州塘约进行实地调研的基础上,本文提出: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和经营体制的改革可以明确土地股份合作制的发展方向,着力改变目前农地集体所有权的“空置”状况,恢复和增强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收益功能。在此基础上,分类设计农地制度的三类具体形式,一是引导农业专业合作社发展的大中型农地股份合作社,二是引导种田大户和家庭联合农场发展的中小型农地股份合作社,三是引导“农户+公司”模式发展的农地股份公司。
关键词:农地制度改革;农业生产方式;集体所有权主体;股份合作制
中图分类号:F321.1;F0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131(2018)04-0004-08
一、引言
新中國成立以来,我国农地制度经历了农民土地所有制(1949—1954)、集体土地所有制(1954—1978)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78—)三个历史阶段。1978年,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十八户村民签下土地大包干契约,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在统分结合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农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实现分离,农民获得了长期稳定的土地承包权和经营权,不仅可以直接经营土地,也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实现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然而,随着城市化、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实践中不断暴露出制度缺陷,譬如集体土地所有权不断弱化,土地细碎化导致规模经营受阻,农地流转后经营性质发生改变,等等。这些问题的出现,无疑提出了开展新一轮土地制度改革的迫切需要。
近年来,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不断深化,各地涌现出形式多样的土地流转模式,农地的确权工作也在全国铺开。同时,将承包权和经营权进一步分离并由不同经济主体掌握的“三权分置”方案也在进行试点。但从总体来看,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仍然面临着较多问题,在具体实施方面还存在着一些难点环节。其中,最为突出的困境在于:以进一步分解农地“权利束”为指导思路的农地制度改革,在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加快农村社会建设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发挥的作用并不显著。也就是说,在目前统分结合的农地制度框架中,“分”已经实施到位,但在“统”的层面,很多农村基层集体实际上已经丧失了农地所有权赋予的收益权,缺乏对农地使用权和经营权的制约能力,这使得农业生产的基础设施配套和公共服务严重滞后,并已经成为目前农村土地制度和农村建设方面所面临的最大问题。
2017年7—8月,本文课题组奔赴安徽省蚌埠市凤阳县小岗村、贵州省安顺市塘约村开展了为期三周的实地调研,通过大量的人物走访和田野调查,获取了两地农村土地制度和生产经营活动的第一手资料,为本文的创作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基础。本文将首先从小农生产方式及农村土地制度的内在联系出发,探讨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实现“第二次飞跃”的必要性;接下来,结合实地调研所获得的数据资料,分析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收益功能缺失导致的恶性循环;再结合贵州塘约组建农村土地合作社的经验做法,提出推动我国农业生产方式演进的制度举措。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本文是本课题组系列论文的实践篇。此前,周绍东(2016)探讨了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推动农业生产方式演进的作用机制,提出在新科技革命背景下,小农生产方式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资本主导的农业生产方式演进[1]。周绍东和田斌(2017)运用“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的唯物史观框架,提出资本主导的生产方式将推动农地制度朝着私有化方向演进,要扭转这一趋势,就必须通过加强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主动引领农业生产方式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2]。通过以上这些探讨,改革农村土地制度、加强农村集体所有权收益功能的必要性已经从理论上被揭示出来了。本文的主要工作是根据课题组实地调研获取的一手资料,从实践层面对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和生产方式演进进行案例分析。因此,本文对涉及到的理论问题进行了简化处理,重点探讨具体实践中的做法。
二、农村土地制度演进与农业生产方式改革
1.小农生产方式及其演进
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框架中,农地制度改革与生产方式变革,都与生产力发展紧密联系,因此不应孤立地讨论所谓“最优农地制度”命题。农地产权是农地所有权在法律上的表现形式,而农地所有权又属于生产关系范畴。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引发农业生产方式演变,进而推动农业生产关系调整。因此,一方面,农地制度改革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和生产方式演变所提出的新要求;另一方面,又必须遏制农业生产方式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演变趋势,通过农地制度改革主动引领我国农业朝着社会主义农业生产方式的方向转变。
农业生产方式可以被分为小农生产方式、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方式和社会主义农业生产方式等三种类型。其中,小农生产方式是传统农业的基本生产方式,属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生产技术落后,生产规模小,家庭自给自足,缺乏生产过程的分工和协作,大多使用落后的传统农业生产工具和技术。这些特征都决定了小农生产方式必然向更高层次的农业生产方式演进。
随着新一代科技革命浪潮席卷而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材料技术和能源技术的广泛应用,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力,这为小农生产方式演进提供了契机。第一,农业科技发展为资本监督劳动提供了多样化的技术手段。信息采集、作物数字模拟、农业专家系统、农业遥感、地理信息系统、产品信息追溯等技术不断取得突破,并广泛运用于农业领域。这些技术的应用,使得资本监督劳动的重点,从对劳动者本身的监督转变为对农业生产进行全过程、全方位的信息覆盖。第二,农业科技发展为人工控制农业生产过程提供了可行性。在强大的信息收集、处理、决策的基础上,农业科技发展为人工控制农业生产过程提供了可行性。随着计算机技术、材料科学和生物技术的长足发展,设施和工厂化农业应运而生,出现了计算机全自动控制甚至装备农用机器人的连栋智能温室、植物工厂和太空农业。同时,高效节能型日光温室、钢架大棚、遮阳网、防虫网、田头冷柜等设施农业技术也在加速发展。这些新兴技术的采用,很大程度上解除了农业生产在土地地力、气候条件、病虫危害、农田水利保障等方面所受到的限制。
小农生产方式的演进方向,既有可能是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方式,也有可能是社会主义农业生产方式。在这个演进过程中,农村土地制度的引导作用尤为重要,因此,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方向的选择,其实质上是引领农业生产方式朝着哪个方向升级的问题。
2.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收益功能缺失导致的“恶性循环”
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实现形式,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界定来看,其实质是生产资料所有权获得经济收益的途径和方法。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实现形式,即是指土地所有者如何通过这一所有权获取经济收益。地租是土地所有权的实现形式之一,土地所有者将土地租给其他经济主体耕种或经营,并以此收取地租。目前,在我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收益功能受到严重削弱,并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这个恶性循环的表现是:农业分散经营导致农户议价能力低、农业经营收益微薄,由此村集体无法凭借土地所有权获取相应地租,从而导致土地所有权在实际上被架空。村集体的经济实力被严重削弱,无力开展农业基础设施和公共产品投资,无法为大规模集中经营提供相应的设施配套,农户不得不继續进行分散经营,由此这个循环自我复制、自我增强,不断持续下去,成为我国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巨大障碍。
在我国目前统分结合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农地实际上处于分散化和碎片化状态,农业经营仍然停留在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经营阶段。在信息经济迅速发展的背景下,这种分散经营的格局,使得农业投入产出的效益与农户家庭自身的人口状况和劳动力结构紧密联系起来。对于那些拥有更多青壮年劳动力的家庭而言,可以通过更为现代化的技术手段开展农产品的种植和销售活动,而对于那些以老年人为主体的家庭而言,农业经营的效果往往不佳[3]。这种差距在农业互联网和农业电子商务愈发普及的背景下更为明显,年龄结构老化的农户往往缺乏更好的产品销售渠道,在农产品议价过程中处于劣势地位。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国农产品价格尽管近年来一直在上涨,但总体上处于一个较低的价格区间。相对于农业生产的基础性地位和农业资源的稀缺性而言,农产品价格明显偏低。
农业经营效益的低下,造成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土地集体所有权事实上被架空。严格意义上来说,由于土地本身的稀缺性,耕种任何一块土地都需要向土地所有者缴纳地租(绝对地租)。但是,在农产品价格偏低的大背景下,很多农业经营者根本无力向村集体缴纳地租。由于地租是土地所有权的实现形式,地租的缺失使得土地所有权完全流于形式。另一方面,随着农业税被取消,各种名目的农业收费受到严格管理。地租缺失、税费下滑严重,村集体的财力支持无法得到保证,这也是造成目前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农田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的重要原因之一。
目前,我国农村的村级集体存在着较为明显的“有权无利”现象,尽管掌握着名义上的土地所有权,但这种所有权并没有为村集体带来收益。从1990年到2011年的20年间,我国农村集体的收入在不断萎缩,很多村集体不仅收入没有增加,反而逐步退化成无收入的村集体(见表1)。1990年,无收入的村集体只占10.2%,而到2011年,无收入的村集体翻了5倍,达到52.7%。收入在5万元以下,以及5到10万元的村集体则在不断萎缩,由1990年的65.3%、13.5%分别下降到2011年27%和8.4%。
村集体收入减少的直接后果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和公共产品供给的短缺。近年来,我国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见图1)。除个别年份外,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都要低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以水电设施建设为例,水电建设是农村固定资产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农业生产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2005年以来,我国农村水电设施建设投资增长率就开始落后于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008年后农村水电设施投资甚至呈现负增长的状况(见图2)。可见,目前我国农村水电基础设施建设已经处于严重滞后的境地,亟待改善。由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滞后,大规模的集体经营更加无从谈起,农户不得不选择分散的个体农业经营。由此,这个恶性循环自我复制、自我增强,成为农业和农村发展面临的最大瓶颈。
课题组在安徽小岗村的调研也证实了以上问题。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声春雷,“小岗”一度成为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旗帜和方向。通过分田到户和“大包干”,小岗模式有效地激发了农民生产经营的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在实践基础上,提炼总结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农地制度框架,实现了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第一次飞跃”。但是,完全分田单干造成土地细碎化状况更为严重,而这种分散经营的局面又是难以通过单纯的土地流转来解决的。课题组通过实地调研发现,安徽省小岗村从2011年起开始推行土地流转,到目前为止已有超过三分之二的土地流转给种田大户和农业企业。在这个过程中,土地转出方与转入方自行对接,村委会只作为公证人见证双方的土地流转行为。由于村委会不参与具体的土地流转工作,因此也不具备整合土地产权获取经济收益的能力,在农业生产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农田水利设施基本上是由上级政府拨款兴建和维护的。
从小岗村所隶属的凤阳县来看,其经济发展表现并不十分突出。2010—2014年,凤阳县国民生产总值指数均低于安徽省总体水平,2015年、2016年略高于安徽省总体水平(见图3)。在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方面,2014—2016年,凤阳县农村常住居民可支配收入分别为8 080元、8 823元、9 617元,而安徽省该指标为9 916元、10 821元、11 720元。
三、中国社会主义农业改革和发展的“第二次飞跃”
在社会经济形态演进中,“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的唯物史观框架表现为两种作用方式:第一种方式以生产力跃升为启动端,进而推动生产方式演进和生产关系变革,这也就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第一条路径;第二种方式则是以生产关系革命或调整作为启动端,进而引领生产方式演进和生产力跃升,这也就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第二条路径。中国社会主义农业改革和发展的两次飞跃,分别体现了两条社会经济形态演进路径。
1.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历史进程及理论依据
邓小平同志对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进行过深刻阐述,这其中又特别以兩次飞跃为核心思想。1980年5月31日,针对有人担心实行包产到户会影响集体经济,邓小平在和有关负责同志谈话中指出,“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可以肯定,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集体经济不巩固的也会巩固起来。关键是发展生产力,要在这方面为集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5]1990年3月3日,邓小平同志在同江泽民同志、杨尚昆同志、李鹏同志等谈话时正式提出了我国农村改革和发展的“两个飞跃”思想。他说:“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6]
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第一次飞跃,是顺应生产力发展和商品经济形态演进的要求,将小农生产方式部分地改变为商品化的农业生产方式,并相应地调整农地所有制实现形式,保证农民拥有土地经营权,这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第一种方式。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第二次飞跃,就是要先行调整生产关系,改变农业生产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土地的所有制实现形式,进而引领农业生产方式朝着规模化经营的社会主义农业方向演进,这同时也就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第二种方式。
2.第二次飞跃的实现路径:构建农地集体所有权的明晰主体
中国农业发展的第二次飞跃,并不是要把集体土地所有制改革成为农民土地私有制,而是要明确或构建一个能有效担负起土地保值增值责任,并对土地进行整体规划、合理使用、统筹协调的集体所有权主体。换言之,我国农地制度改革的对象并不是集体所有制本身,而是要改革现有的集体所有制实现形式,改变目前土地集体所有权事实上的“空置”状况。在此基础上,主动引领小农生产方式向规模经营、人地协调、利益共享的社会主义农业生产方式演进。塘约道路表明:任何一种所有制都必须采取一定的实现形式以获取收益,股份合作制是土地集体所有制较为可行的实现形式。设计土地股份合作制,必须与农业生产方式的具体类型相匹配,构建引领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发展的治理结构。
以明确和构建农地集体所有权主体为起点,可以勾勒出深入推动我国农地制度改革的设计思路:将农地所有权通过确权、颁证的形式授予农户,鼓励、引导农户以股份合作的形式建立起相应的集体所有权主体,该主体与农业生产方式的演进方向相一致,并能够有效地引导和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针对不同类型的农业生产方式,农地集体所有权主体可以采取三种具体形式。
第一,引导农业专业合作社发展的大中型农地股份合作社。农地股份合作社的主要作用是引导和培育农业专业合作社,农地股份合作社的构建方式是:在农业专业合作社范围内实施劳动联合和资产联合,吸收合作社社员持有的农地股份,社员大会作为农地股份合作社的最高权力机构。农地的使用权经营权实际上被划分为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微观的农地耕种权利,这当然是赋予给农户本身,第二个层面是宏观上的细碎化土地整理、农田水利设施规划建设等工作,农地股份合作社可以聘请专业的土地管理机构来从事这项工作。此外,农地股份合作社设立监事会等组织,一方面可以从社员内部产生监事,另一方面也可以聘请农村基层行政人员担任监事。
农地股份合作社的特点是与农业专业合作社紧密结合,其股份合作界限由农业专业合作社的规模决定,既可以与自然村、行政村的边界重合,也可以与之不同。合作社社员通过投入的农地股份获取财产收益,同时也拥有农地股份合作社重大决策事项的投票权。需要指出的是,为了与合作社的运作原则保持一致,土地股份合作社也需要实施“一人一票”的决策机制,避免农地合作社被部分土地大户所操纵。在股利分配方面,既要参照农户投入的土地面积大小,同时也要根据合作社利益分配的“惠顾原则”进行综合考虑。
第二,引导种田大户、家庭联合农场发展的中小型农地股份合作社。与第一类农地股份合作社相比,这一类农地股份合作社的特点不仅在于其规模较小,更重要的是,中小型农地股份合作社强调的是资产合作而非劳动合作。在这种模式中,农户以农地所有权作为股份形成合作社,同时将农地使用经营权赋予种田大户,并根据投入股份获取股利。投入股份的农户不再从事相关的农业生产活动,仅凭借其股东身份对农地使用状况进行监督,并在事关土地的重大事项上进行决策。相对而言,中小型农地股份合作社的治理结构比较简单,其核心在于种田大户、家庭联合农场的经营方获得农地的使用经营权,而农地流出方通过建立股份合作社的方式,避免了其农地所有权的“空置”问题。同时,这种农地股份合作社并不要求社员之间进行劳动合作,农地所有权和使用经营权分离得比较彻底,因此,农地流入方在农业生产经营上能够获得较大的主动权和灵活性。
第三,引导“农户+公司”模式发展的农地股份公司。“农户+公司”是在农业产业化背景下形成的新型农业经营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农业产业化企业转入农地使用经营权开展规模化经营,农户既可以选择进入农业产业化企业工作,也可以选择转出土地获取租金报酬。“农户+公司”模式推动了传统农业与现代市场的对接,不仅实现了规模经济效应,而且也有利于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实施农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改变传统农业低加工度、低附加值、低品牌效应的“三低”现状,通过将传统农业与现代工业相结合,走农产品深加工、高附加值、强品牌效应的发展之路,这就迫切要求在农业经营过程中积极引入战略投资者,实现农户规模化种植、工厂规模化生产、品牌规模化营销。
四、塘约道路:推动农业专业合作社向农业土地合作社的升级
破解农业和农村的恶性循环,一个关键性的做法在于恢复和增强农村土地集中所有权的收益功能,提高集体的土地收益,从而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产品供给提供资金保障,为土地集中化规模化经营奠定基础。“塘约道路”的内在精髓,正是通过推动农业专业合作社向农业土地合作社的升级转变而实现的。
贵州安顺塘约村的经历,是农地制度改革倒推农业生产方式演进的典型案例。塘约村位于安顺市平坝区西部的乐平镇境内,距平坝城區12公里,距沪昆高速天龙收费站5公里。塘约村拥有10个自然村寨,11个村民组,921户,3 393人,居住有汉、苗、回等民族,耕地面积4 860亩。2014年以前,塘约还是一个省二级贫困村,全村有1 100多人外出打工,是一个典型的“空巢村”。2014 年6月3日,塘约村遭受百年未遇的特大暴雨灾害,许多房屋、田地被冲毁,道路被冲垮,村民们一下子变得一贫如洗。面对这种局面,是完全放任农地自由流转,发展资本化农业生产方式,还是把农地制度改革和农业生产方式演进结合起来,重新发展农业集体经济,这是摆在塘约人面前的重大道路抉择。
塘约村选择了后者,与其他地区成立农业专业合作社不同的是,塘约选择了建立“农村土地合作社”的办法,进而统筹推动农地制度改革和农业生产方式演进。与农业专业合作社只涉及某一类农产品的生产经营不同,农村土地合作社的核心资产是农业土地,组织架构是“村社一体”,村支“两委”是合作社的运作主体,负责全村土地流转经营、产业培育、市场开拓等。塘约在原有“塘约村农民种植专业合作社”和“土地流转中心”的基础上,协同开展了农业经营模式改革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并将这种农地制度命名为“金土地合作社”[7]。
2015年,全村70%的土地流转入股进入合作社,2016年村民全部入股。通过两年多的努力,塘约村的贫困人口数从2014年的643人,降到2015年的82人,2016年则全部脱贫;2014年,村集体经济不到4万元,2015年增长到81.4万元,2016年更倍增到202.4万元;2014年村人均收入3 786元,2015年翻一番达到7 943元,到2016年时涨到10 030元。2014年、2015年、2016年,塘约村农民外出务工人数逐渐下降,分别为860人、352人、50人。集体经济实力进一步壮大,集体资产逐渐提升,分别为 3.9万元、81.4万元、202.5万元。
把农业生产方式变革同农地制度改革结合起来,利用农地制度改革倒推农业经营模式创新,塘约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功经验。第一,为农业生产的结构性调整提供了土地保障。根据农业生产的具体需要对农地进行整合规划,有效规避了农业专业合作社仅仅在市场销售上统一协调而农业生产仍然分散的劣势。譬如,全村统筹规划羊肚菌种植,目前种植面积达到150亩,每亩产量300—350斤,除去每亩地9 000元的投入,一亩有2万多元的纯利润。再例如,启动了乡村旅游业发展,村中心区域的房屋按照红屋顶、黄墙面、拱形窗户的样式统一外观。
第二,有效拓宽了农民收益渠道。农业专业合作社属于公益性组织,合作社本身不以赢利为目的,主要作用是协调农户生产,增强农户的市场谈判能力。而通过建立农地合作社,农户可以通过土地入股获得股息红利,这就拓宽了农户收入渠道,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此外,塘约在合作社内部组建运输公司、劳务输出公司、妇女创业联合会和建筑公司4个机构,有效把剩余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转移,增加劳动力就业机会。
第三,为农村集体经济提供了重要的资金保障。塘约村不仅对承包地量化确权,而且对农民宅基地、承包的山林、集体土地所有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集体财产权、小水利工程产权都进行了确权。通过确权,纠正了村民建房侵占集体土地、种地侵占集体沟渠、开荒侵占集体荒山的现象。塘约村将集体土地入股农地合作社,并按照合作社、村集体、农民之间3∶3∶4的比例,对集中经营土地进行利润分成。这种做法实现了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收益要求,壮大了集体经济实力,为农业生产的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和农村社会建设提供了重要的资金保障。
五、结论与启示
小岗村的发展历程表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一定历史阶段能够激发农民个体的生产积极性,这要归功于土地使用权分散化所带来的“劳动自由度”的提升。但是,中国农业发展不能仅仅满足于第一次飞跃,而是要进一步明确土地集体所有权的收益主体,增强农村基层组织的经济实力,推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发展规模化经营和合作化农业。塘约道路深刻地揭示出,推动我国农业生产方式变革,必须紧密结合农地制度改革同步进行。农业土地在所有权和使用权层面真正实现公有化,是引导农业生产方式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重要保障。塘约村是在统筹考虑土地制度、经营模式、组织方式等各方面因素的前提下,成功实现了我国农业发展的第二次飞跃,这就要求我们重新审视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缺位和私人资本主导农业生产方式的根本缺陷,从农地股份制合作入手,建立起与农业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差异化的农业生产方式。在这个层面上,塘约道路提供了引导农业专业合作社发展大中型农地股份合作社这一具体经验,不同地区可以根据自身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农业经营模式状况进行具体操作。
从农地制度改革而不是单纯的农业经营模式入手开展改革,这就要求有一个强有力的主体牵头改革。塘约道路不仅仅揭示了农业经济学原理,更重要的是探索了中国农村问题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解决方案。任由市场力量发挥作用,目前的农业生产方式演变趋势必然将农地制度推向私有化方向。因此,这个带头人必然是建立在村、镇的农村基层党支部,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有可能从政治导向高度推动农地制度的公有化方向改革,进而推动农业生产方式朝着大生产、大协同的社会主义方向变革。
参考文献:
[1] 周绍东.“互联网+”推动的农业生产方式变革——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的探究[J].中国农村观察,2016(6):75-85.
[2] 周绍东,田斌.从被动适应到主动引领:农地制度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7(6):22-31.
[3] 乔俊峰.基于需求导向的农村公共服务调查及完善对策[J].经济纵横,2017(8):99-103.
[4] 国鲁来.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演进轨迹与发展评价[J].改革,2013(2):98-107.
[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641.
[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1310-1311.
[7] 周建明.从塘约合作化新实践看毛泽东合作化思想和邓小平第二个飞跃思想的指导意义[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7(1):52-56.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ocialist agriculture has realized the first leap forward from Peoples Commune system to family contracted land system, but still needs the second leap forward from family production to scale production and collective economy. Based on Marxism materialism philosophy,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two paths of social economic pattern evolution, and proposes that production relation fitting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ity is the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first leap forward of Chinas socialist agriculture, which embodies the first path for socialist economic pattern evolution. However, the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second leap forward of Chinas socialist agriculture is to use production relation reform to lead production method evolution and productivity level rise, which embodies the second path of social economic pattern evolution. Based on spot survey on Xiaogang Village of Anhui Province and Tangyue Village of Guizhou Province, this paper advances that the reform of Chinas rural land system and management system can clarify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land share cooperation system by changing the “empty” status of rural land collective ownership and by restoring and enhancing the gain function of collective land ownership. On the basis of that, three kinds of concrete forms of rural land system are separately designed, one is to lead agricultural specific cooperative to develop big and medium-sized rural land share cooperative, the second is to guide big planting farmers and family alliance farmland to develop medium-sized and small rural land share cooperative, and the third is to guide “farmer family + company” mode to develop rural land share company.
Key words: rural land system reform;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method; collective ownership main body; share cooperation ownership
CLC number:F321.1;F042 Document code: A Article ID: 1674-8131(2018)04-0004-08
(編辑:易 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