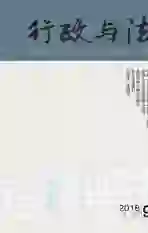法定职责外行政协议的适法性
2018-10-16张祺炜金保阳
张祺炜 金保阳
摘 要:新《行政诉讼法》将行政协议纳入到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使行政协议的理论研究和审判实践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但司法解释将行政协议的范畴限定在“法定职责范围内”,未将行政机关超越法定职权签订的协议纳入行政协议的范围。本文认为,协议的依据不应限于正式法源,应包括公共政策等非正式法源,协议应为实现行政管理目的而签订。因此,有必要通过立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判例的方式,逐步实现法定职责外行政协议的类型化和法定化,从而在实现政府行政管理协商共治的同时,提高相对人对行政行为的合理预期。
关 键 词:法定职责;行政协议;行政管理
中图分类号:D92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207(2018)09-0100-08
收稿日期:2018-04-04
作者简介:张祺炜(1985—),男,四川康定人,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庭員额法官,法学硕士,研究方向为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金保阳(1988—),男,山东嘉祥人,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庭法官助理,法学硕士,研究方向为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
有学者称行政协议为行政合同或行政契约。理论界关于行政协议概念的主流观点存在合同目的论、合同标的论等几种认识。合同目的论的核心在于行政协议为实现行政管理目的,而合同标的论的核心在于行政协议为形成行政法律关系。“行政合同是行政主体与相对一方当事人基于行政管理的需要,依法设立、变更、消灭行政法律关系的协议。”[1]此定义即兼具目的论和标的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适用行政诉讼法解释》)第11条第1款规定,行政机关为实现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在法定职责范围内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协商订立的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属于《行政诉讼法》第12条第1款第11项规定的行政协议。因此,是否将行政协议的范畴界定在“法定职责范围内”,是司法解释与理论观点之间的区别。然而,实践中的行政主体与相对人签署的协议存在协议类型或协议内容无法律依据的情形。所以,此类协议是民事协议还是行政协议,倘若认定为行政协议,该如何看待可能存在的“合法性危机”。鉴于此,有必要对此类协议所涉理论基础及应用实践作进一步探索。
一、法定职责外行政协议的实践与司法解释之间的矛盾
行政机关在法定职责范围内所签订的行政协议主要有两种:一是作为行政行为补充或者替代方式的协议。如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25条第1款规定,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之间,在补偿方式、补偿金额等方面可以订立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又如行政强制执行和解协议,《行政强制法》第42条第1款规定,实施行政强制执行,实施机关可以与当事人达成执行协议,但是不能损害社会公益或者第三人的权益。上述协议的特点在于根据相关规定,行政机关在行使行政管理职责的过程中既可以直接作出处理决定,也可以采取行政协议的形式替代,行政机关具有选择权。二是行政协议本身即系行政机关的一种法定处理方式。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中明确规定了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与土地使用者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相关程序,土地使用者按照合同约定付清土地使用权出让金、依法办理土地登记手续后,即可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此类协议的特点是行政协议与行政处理行为是合一的,行政机关必须通过协议的方式才可实现行政管理目的。上述两种协议的共同特点在于法律对协议的主体、类型、内容、签订程序等均有明确规定,即行政机关签订此类协议系“在法定职责范围内”。在行政管理活动中,即便法律没有赋予行政机关具有与相对人签订行政协议的职权,但存在大量行政机关通过签订协议的方式达到行政管理目标的事项。如基层政府在征地拆迁中签订的搬迁协议,搬迁协议与国有土地上房屋的征收补偿协议之间的区别在于搬迁协议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协议所涉地块一般未经法定程序征收为国有土地,政府也未发布征收补偿决定,协议一方可能是行政机关,也可能是村集体经济组织,甚至可能是拆迁公司。又如息诉罢访协议,即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的韩甲文诉黑龙江省肇源县人民政府行政协议案[2]所涉的协议。韩甲文与肇源县政府签订的协议条款包括韩甲文收到158.4万元补偿款后,对处理“马场地”引发的纠纷过程中,行政机关、公安、法院等机关所作的一切行为之目的为息诉罢访。此外,我国有些地方政府还实施了政府服务外包制度,如《宁波市政府服务外包暂行办法》《大兴安岭地区服务外包试行办法》等。[3]对于上述协议类型,笔者结合《适用行政诉讼法解释》第11条“法定职责范围内”的规定将其定义为“法定职责外行政协议”,主要指行政机关在法律未授权或未对协议类型及内容作出规定的情形下与相对人签订的协议。对于此类协议,如果将其一概视为民事协议,可能有“公法遁入私法”之虞,但如果将其纳入行政协议范畴,又该如何看待此类协议的合法性,均需进一步思考。
二、法定职责外行政协议纳入行政协议范围的可行性与必要性
行政协议的合法性问题,本质上是协议中蕴含的契约自由原则和行政行为所遵循的依法行政原则之间如何平衡的问题,此冲突在法定职责外协议中表现尤为明显。司法解释就行政协议有关“在法定职责范围内”的定义,不仅与行政协议的基本理论相悖,也给行政协议案件的受理与审理带来了一定困惑。但从法治政府的发展方向、最高人民法院案例以及地方政府立法等视角均可发现,法定职责外行政协议已广泛应用于行政管理实践中,并为司法裁判所确认,因此,行政协议的范围不应仅限于法定职责范围之内。
(一)执法之维:行政协议是服务政府实现管理的有效模式
现代法治政府治理国家的模式逐渐从管理模式转变为治理模式,公共治理亦朝多元化、协商化方向发展。行政管理开始强调服务、指导与合作,国家和个人之间不再是对抗关系。社会发展证明,合意理念所蕴涵的优越性、开发性和包容性使人们无法再对非强制性行政行为的魅力无动于衷。[4]国内倡导多元化解矛盾纠纷以及国外替代性纠纷解决方法,均体现了政府管理模式的重要转变。这种在尽可能协商的基础上化解矛盾纠纷的模型,没有理由不应用于行政行为实施过程中,行政协议即为这一模型的主要表现形式。
行政协议的基础是行政自由裁量权。英国学者迈克·希尔等人通过对公共政策执行的长期观察认为,“在某些条件下,增强基层的自行裁量权对于政策执行可能会比对其进行约束更为有效”,“公共政策发展所具有的特征是其前所未有的复杂性程度。在那些政策执行不足的地方,实际上就允许低水平的行动,中央政府乐意授权地方执行者让他们在大部分时间里按自己的方式行事”。[5]行政协议作为具有两造互动、平等协商、自由选择等性质的行政手段,有助于充分实现行政管理目标的积极效果,形成行政机关与相对人的和谐关系。但就目前法律规定的行政协议类型而言,远远不能满足纷繁复杂的行政管理事务之需要,协商自治的运行路径即在于通过法律框架之外实现对社会事务的高效管理,如果苛求行政机关签订协议的法定性,不仅不利于行政协议等柔性执法方式在更多领域的适用,也与协议行为所蕴含的意思自治的内在本质背道而驰。
(二)司法之维:最高人民法院为行政协议的范围和类型提供了裁判样本
传统理论认为,我国不施行判例制度。事实上,我国虽然不存在普通法系国家那种以判例制度为主的法律体系,但判例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确确实实发挥着“先例”的作用。2010年11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明确要求: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各级人民法院审判类似案例时应当参照。2015年6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又发布了前述文件的实施细则,进一步明确了各级人民法院参照指导性案例裁判要点的前提条件是其审理的各类纠纷与指导性案例所涉及的案件事实和适用的法律存在相似之处。2017年8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实施意见(试行)》规定了类案与关联案件检索机制,明确要求法官在办理案件时应对最高人民法院审结或者审理过程中的类案与关联案件进行全面检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发布的司法政策性文件来看,法院审理案件参照的案例已逐步由指导性案例扩大到了最高人民法院审结的其他案例,这说明我国司法判例制度的深度及广度得到进一步拓展。在最高人民法院公开发布的裁判文书中,不乏法定职责外行政协议的案例,这些案例都是司法审查的重要指引。
在前述韩甲文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肯定了息诉罢访协议属可诉的行政协议,其裁判理由是行政机关与上访人签订的息訴罢访协议,实质上是行政机关为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公共利益和实现行政管理职能的需要,根据属地主义原则在其职责权限范围内,与上访人达成的有关政府出钱或者是给予其他好处、上访人息诉罢访等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属于可诉的行政协议范畴。笔者认为,《信访条例》未许可行政机关通过协议的方式处理信访事项。换言之,行政机关并无与相对方签订息诉罢访协议的法定职权,最高人民法院对息诉罢访协议主要从协议目的角度加以识别,从而认为该协议属于行政协议,对“法定职责范围内”作了相对从宽的解释,为司法实践中进一步拓展法定职责外行政协议的范围起到了一定的指引作用。最高人民法院郭修江法官亦认为,《适用行政诉讼法解释》第11条将行政协议事项限定于行政机关“在法定职责范围内”所签协议,似有将越权协议排除在行政协议范围外之嫌,若删除“在法定职责范围内”一句,司法解释对行政协议的定义更为准确。[6]
(三)立法之维:地方政府文件对行政协议的认定较为宽泛
虽然行政协议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始于《行政诉讼法》的修改,但在近年来地方政府的规范性文件中,行政协议已经得到了广泛体现。如《江苏省行政程序规定》第五章对行政合同进行了专门规定,其中,第77条规定了行政合同的概念是指行政机关为了维护公共利益,实现行政管理目的,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经双方意思表示一致达成的协议。该条还规定了可以适用行政合同的若干情形。第78条至第82条规定了行政合同订立的条件、方式、程序等。《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第93条规定,行政合同是指行政机关为了实现行政管理目的,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之间,经双方意思表示一致所达成的协议。其他如汕头、兰州、西安等地区的行政程序规定亦有相类似的表述。总体上观察,各地方政府的规范性文件中规定的行政协议范围较为宽泛,认定行政协议的核心要素在于实现行政管理目的,而不以“法定职责”为充分条件,这与理论界的通说观点基本吻合,反映了长期以来行政协议在政府社会治理过程中的实际运行状况。
从立法技术的角度而言,对于行政行为的概念一般应当在行政实体法或程序法中加以规定,而不是在诉讼法中予以界定,如行政强制、行政处罚等行为均规定在了相应的部门法中。又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对政府信息的概念作了明确界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则对哪些政府信息公开行为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哪些行为应当排除在外作了进一步规定,而不涉及政府信息本身的概念。大陆法系国家,如法国、德国等均将行政协议规定在其公共合同法典、行政程序法中。我国尚未出台行政程序法之前,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解释的形式对行政协议作出界定,确实起到了定纷止争和指导司法裁判的作用,但对于地方政府行政程序规范性文件中关于行政协议的概念范围亦应当给予一定的认可和尊重。
(四)权利之维:法定职责要素导致协议无效不利于法律关系稳定
从诉讼的角度来看,职权依据属于法院对行政行为实体审查的内容,如果把“法定职责内”作为判断是否属于行政协议的标准,则职权依据成为了法院对协议是否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程序审查内容,不仅导致大量此类协议游离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之外,也导致行政协议“超越职权”的可能将不复存在,有悖于行政诉讼基本理论。根据《适用行政诉讼法解释》第11条第1款的权威释义来看,首先,行政机关在法定权限之外签订的协议是无效的。其次,行政协议是否在法定权限内签订,还是需要在诉讼过程中进行判断。[7]也就是说,在司法实践中,法定职责要素一般不作为受案范围的条件,仍属于实体审查的内容。
行政协议与民事协议的区别在于行政协议除可能根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导致无效外,还可能根据《行政诉讼法》“实施主体没有依据”的规定而无效。行政协议作为行政行为的一种,不仅涉及行政机关和相对人之间的二元关系,还涉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等诸多利益,因此,行政行为的安定性在行政协议中亦应得到体现。在行政诉讼中,确认无效判决的适用本就存在很严苛的条件,即必须存在“重大且明显违法”之情形,而一般的没有依据不足以导致行政行为无效。尤其是虽然行政机关没有职权依据,但签订的协议能实现行政管理目的且对相对人有利的情况下,如果动辄以超越职权为由认定协议无效,无论是相对人合法权益还是行政法律关系的稳定性,均存在随时被侵害之隐忧。我国台湾地区“行政程序法”第141条第1项规定,行政契约准用“民法”规定之结果为无效者,无效。翁岳生对该条规定提出了深刻的洞见,“因为如果行政契约准用民法无效规定亦归于无效时,将使得所有违反任何法令之行政契约尽属无效”,“宁可删除第141条第1项之规定,以避免无效(其法效果犹如炸弹,具摧毁效果)之法律效果肆虐已经缔结的所有行政契约,盖只要违反任何法令规定之契约,为强调依法行政要求,而皆以无效后果绳之,恐非利益衡量,保护契约当事人之信赖所应采取之僵化决定。”[8]
三、法定职责外行政协议的制度化路径
作为一项行政行为,行政协议应有自身的特质,否则与民事行为无异,可能导致被滥用的风险而有损公益,因此,针对法定职责外行政协议,应当探索并建立一条既有别于法定职责内行政协议,又有别于民事协议的制度化发展路径。
(一)法定职责外行政协议的主体
行政机关作为协议主体一方自不待言,行政法著述亦多将行政协议的特征归结为行政机关地位恒定。笔者以为,行政机关作为行政协议的一方更应该指涉的是实质意义上的而非形式意义上的所谓形式意义即协议的签约方必为行政机关,而实质意义则指协议的签约方可能是行政机关,也可能非行政机关,但体现行政机关的意志。根据《行政诉讼法》第26条第5款“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所作的行政行为,委托的行政机关是被告”的规定,即可得出这一论断。
以搬迁协议为例,有观点认为,搬迁协议系行政机关与被搬迁人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签订,或者有的签订主体是拆迁公司与被搬迁人,故应准用民事法律规范。而笔者认为,搬迁协议不同于一般民事协议,其虽无实定法依据,但我国土地征收征用、房屋拆迁补偿的公益性、行政性相当明显。从目的上看,该类协议主要涉及土地利用、城市建设等行政管理目标,这些领域必须通过行政手段才能得以推进,充分体现了公权力的作用。拆迁公司在没有行政机关允许或授权的情形下不具有签订搬迁协议的资格,此时,即使行政机关未直接出面签订协议,仍不影响其属于行政协议的认定,当相对人就某协议提起诉讼时,法院应当解开对方当事人的“面纱”,直接以相应的行政机关为被告并承担后果。如季洪忠、季晓波诉江苏省启东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案中,[9]原告以启东市汇龙镇人民政府为被申请人要求撤销《房屋拆除搬迁补偿协议》。启东市政府认为,协议签约方为季晓波与村经济合作社、征收服务公司而非汇龙镇政府,不符合行政复议的受理条件,故驳回原告的复议申请。法院认为,基于汇龙镇政府与征收服务公司签订的委托拆迁合同以及汇龙镇政府发放拆迁补偿款、协调处理原告拆迁事宜等行为,足以认定协议系征收服务公司受汇龙镇政府委托所签,汇龙镇政府是协议的签约方,案涉协议属于行政协议,原告的申请属于行政复议范围,遂撤销启东市政府所作复议决定,责令启东市政府受理原告的复议申请。
(二)法定职责外行政协议的法源
虽然行政机关签订行政协议可以突破法律法规等正式法源的限制,但作为一项行政行为决不可完全依赖意思自治,而应当符合作为公共政策等非正式法源的要求,这既是法定职责外行政协议与民事协议的区别之一,也是行政管理的应然之义。《行政诉讼法》第63条规定了只有规章以上的法律规范才可以作为法院审理行政案件的依据。但行政行为所依据的法源与行政诉讼所适用的法源并非同一概念,行政行为所依据的法源往往不限于规章以上的法律规范。我国作为一个政策大国,在行政管理和司法审查过程中不可能无视政策的作用。最高人民法院江必新副院长亦指出,在行政实践中,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等构成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指引规范,因此不得因为效力层级不高,就否认其对行政机关自身的约束作用。只要是合法有效的规范,且具有实质拘束力,从行政法的角度就不能简单地置之不理。从国外立法看,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只要在位阶上优于行政协议,都可以作为协议合法性判断的依据。机械地限定于法律、行政法规,是形式主义法治观念的产物。[10]
在行政机关签订的大量法定职责外行政协议背后,时常蛰伏着公共政策的影子,如搬迁协议可能涉及一个地区的旧城改造、基础设施建设甚至商业开发,协议条款亦非完全取决于双方合意,往往需要参照政府发布的有关协议搬迁的政策或文件,如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政府发布的《通州区规范房屋搬迁补偿安置指导意见的通知》、崇川区人民政府发布的《关于对钟秀路北侧城闸大桥西南侧地块项目范围内非住宅房屋实施协议搬迁的决议》等。又如息诉罢访协议,行政机关签订该类协议往往不是基于法定的行政执法事项,更多是与化解信访、维护地区稳定等公共政策紧密相关。当然,行政协议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也可能违法或存在瑕疵,如符合《行政诉讼法》第53条规定的条件,法院可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在审理协议类案件时,对依据的规范性文件予以一并审查。
(三)法定职责外行政协议的目的
行政协议与民事协议的主要区别在于行政协议具有公益性,体现了行政机关行政管理职能。实践中,行政机关在无法律依据情况下签订的协议较为多见,但并不意味着都属于行政协议,只有满足行政协议目的要素的协议,方可认定为行政协议。正如有学者所言,简单地把行政契约一概归之于公法契约或私法契约是不妥当的,而应该对契约的内容逐条逐款进行分析,那些只有具备行政权能的行政主体才能实现的条款是公法性质的,而私人也能实现的条款则是私法性质的。[11]有学者认为,公共利益的范畴远比行政管理目标宽泛,如果以公共利益为目的作为标准,恐怕会涵盖所有行政主体作为一方当事人的合同。[12]笔者以为,无论公共利益还是行政管理目标均属不确定概念,之间并无明确的界限。事实上,实现公共利益本身也是行政管理的必然要求,因此,二者均是法定职责外行政协议的识别标准。
不可否认,无论行政管理目的还是公共利益,认定标准均较为抽象,基于立场、观点、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等不同,会出现不同的认识,其识别更多的依赖于司法实践中个案的判断。德国著名的利益法学派代表人物菲利普·黑克指出,法官也要像立法者一样界定利益,并对利益冲突进行判决……法官不仅要适用具体的法律命令,也要保护制定法认为值得保护的利益的整体。[13]如崔恒龙诉江苏省海安县人民政府息诉罢访协议案中,[14]双方约定“同意对崔恒龙给予两套安置房安置,安置房价格按海安县人民政府海政办发[2008]41号、86号文件执行,并依据拆迁评估报告确定的补偿数额相互结算差价。对崔恒龙反映的财产损失及人身伤害,按法院生效的判决执行。补偿安置问题解决后,崔恒龙承诺此后不再信访和上访。”该协议条款有明確的文件依据和生效裁判依据,符合公共利益要求,法院遂判决海安县政府履行协议内容。而有的地方政府在“零上访”的压力下,可能满足上访人一些不正当的经济需求签订协议,而这种经济需求势必由公共财政承担,但显然其不符合公共利益。
(四)法定職责外行政协议的发展进路
虽然行政协议等柔性执法方式是行政管理的发展方向,但任由行政机关创设协议的类型及内容断不可取。因此,应然的发展路径是逐步实现行政协议的法定化。对此,胡宝岭认为,严格意义上的法定化(或称全部法定化)并非仅指制定有关行政合同的法律,而是指由法律明文规定的行政合同的种类、形式及部分内容,法律明文规定之外的合同则不能认定为行政合同。但由于各国行政合同立法均未达到《物权法》《刑法》那样详尽的程度,这种严格意义上的法定化短期内难以贯彻。因此,欧洲国家实行的是部分法定化,即由法律明文规定某几类合同为行政合同,在法律明文规定之外,既不排斥行政机关依照法定标准创设行政合同,也不反对司法机关通过法定标准确认其他类型的行政合同。[15]
笔者认为,实现行政协议法定化包括立法和司法判例两条进路。一方面,需要通过立法的方式,循序渐进地扩大行政协议的类型和范围,先将公益性较强、适用范围较广、频率较高的一些协议纳入;另一方面,囿于法律的稳定性及滞后性,有必要通过法院对不断涌现的法定职责外行政协议纠纷进行司法审查从而实现规则引领。尤其是针对部分新类型、新变化的公共政策或行政改革事项,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裁判的形式予以肯定或否定,实际上起到了“创制”某种新的公共政策或行政管理规则的作用。正如韩甲文案中对于息诉罢访协议这一颇具敏感性同时又大量存在于实践中的协议类型,最高人民法院实际上通过司法裁判的形式“创制”了息诉罢访这一行政协议类型。可以预见的是,随着行政协议纠纷的不断增多,最高人民法院也将会通过案例的形式“创制”更多的协议类型。
总之,行政契约何时使用才具有正当性,的确是一个很重要又很棘手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不解决,实践中对泛行政契约化的指责,甚至对行政契约正当性的质疑也始终挥之不去。[16]过于强调行政协议的职权法定,结果只会是行政机关采用协议方式实施行政管理的空间越来越小,行政协议沦为执行法定职权的方式之一。然而,基于行政机关恪尊依法行政的原则,并提高相对人对行政行为预测的可能性,理应用法律规范对行政协议进行较为细致界定。行政协议和服务政府、多元化解矛盾纠纷的理念是一脉相承的,在我国行政权长期高度发达,重管理、轻服务的治理模式尚有遗存的情形下,更要在行政管理中发挥行政协议的作用,不能因噎废食。因此,适当找准行政协议在职权法定原则与缔约自由原则之间的平衡点,在理论及实践不断探索和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拓展行政协议的适用范围,最大程度实现行政管理的协商共治,是行政协议发展的应然之道。
【参考文献】
[1]王克稳.论行政合同与民事合同的分离[J].行政法学研究,1997,(04):19.
[2]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行申45号行政裁定[Z].
[3]马怀德.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法律问题研究[M].中国法制出版社,2014.111.
[4]姜明安.行政程序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286.
[5](英)迈克·希尔,(荷)彼特·休普.执行公共政策[M].黄健荣等译.商务印书馆,2011.38,56.
[6]郭修江.行政协议案件审理规则——对行政诉讼法及其适用解释关于行政协议案件规定的理解[J].法律适用,2016,(12):45.
[7]江必新,梁凤云.新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M].中国法制出版社,2015.108-111.
[8]翁岳生.行政法[M].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752-754.
[9]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苏06行初72号行政判决[Z].
[10]江必新.行政协议的司法审查[J].人民司法(应用),2016,(34):11.
[11](日)南博方.日本行政法[M].杨建顺,周作彩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65.
[12]周汉华.行政法学的新发展[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106.
[13](德)菲利普·黑克.利益法学[M].傅广宇译.商务印书馆,2016.29.
[14]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苏06行初148号行政判决[Z].
[15]胡宝岭.行政合同争议司法审查研究[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63.
[16]余凌云.行政法案例分析和研究方法[M].中华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235.
(责任编辑:苗政军)
Abtract:The new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Law brings the administrative agreement into the scope of accepting cases in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which makes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trial practice of the administrative agreement rise to a new height.However,the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limits the scope of the administrative agreement within the scope of “statutory responsibilities”,and does not include the agreement signed by the administrative organ beyond the statutory authority into the administrative agreement range.This paper holds that the basis of the agreement should not be limited to formal sources of law,but should include informal sources of law such as public policy.The agreement should be signed for the purpose of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Therefore,it is necessary to gradually realize the typification and legalization of administrative agreements beyond statutory responsibilities through legislation and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precedents,so as to improve the reasonable expectations of the counterparts for administrative acts while realizing the Co-governance of government administration through consultation.
Key words:statutory duties;administrative agreements;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