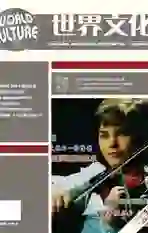“迪南在索尔费利诺”
2018-09-25余凤高
余凤高



1859年6月,第二次意大利独立战争中,奥地利军队与法国—撒丁、皮埃蒙特的联军在意大利伦巴第地区进行的战争打响。6月4日,奥军约13万人在马真塔战役中被击败,向东撤退,奥地利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一世亲临前线指挥。法国—撒皮联军14万人在法王拿破仑三世和撒丁—皮埃蒙特国王维克托·伊曼纽尔二世的共同指挥下穷追奥军。24日,两军不意在斯蒂维耶雷堡的东南,大约4英里处的小城索尔费里诺(Solferino)及其周围地区正面遭遇。从清晨4:30左右开始,到下午3点左右奥军全面撤退,激烈的战斗,使双方都损失惨重:奥军死2386人,伤10807人,并有8638人失联或被俘;联军也有2492人战死,12512人受伤,2922人失联或被俘。瑞士商人亨利·迪南(Henry Dunant,1828—1910)刚好在那里,目击了这场“可怕的肉搏战”。他后来回忆说:
奥地利和法国—撒皮联军相互践踏着,在血淋淋的尸堆上你奔我杀。他们毫不留情地用步枪射击敌人,用马刀劈向敌人的头颅,用刺刀刺入敌人的胸腹。没有饶恕,拒不纳降,这完全是一场屠杀,是残暴的野兽之间为血和愤怒而疯狂的搏斗,甚至连伤者都战斗到最后一息。没有了武器,他们就掐住敌人的喉咙,用牙齿撕咬他们。
……枪炮打在散落遍地的死伤者身上,脑浆在车轮下涌出。四肢断裂,人体被残害得辨认不出原来的模样。泥土混拌着鲜血,尸横遍野。(杨小宏译文)
迪南是偶尔才亲见这个场面的。
三年前,1856年,迪南获许在法国殖民地阿尔及利亚创立一家企业,但是拖了很长时间,在土地和水的授权使用上仍然不明确,殖民当局又不肯好好合作。于是,他决定带着他写的一册奉承拿破仑三世的书《复活神圣罗马帝国查理曼皇帝的拿破仑三世皇帝》,去直接向这位法国皇帝申诉。当时,奥地利占领了大部分意大利领土,拿破仑三世的总部就设在小城索尔费里诺。
得知拿破侖皇帝三世的所在之后,迪南乘一辆小型篷式出租汽车前去追赶,途中就看到这样的惨剧。面对这样的惨状,迪南还能想什么呢?
迪南是日内瓦一名加尔文教徒的大儿子,全家都重视社会服务的意义,父亲曾在监狱和孤儿院工作,积极帮助孤儿和假释犯,母亲也把救济病人和穷人看作自己的本分。迪南在宗教觉醒中成长,可谓“信仰复兴”(Réveil)。他从小就常跟随母亲一起去看望穷人和病人,为他们做善事,从而孕育出一颗笃信教义的慈善之心,对病人、弱者、倒霉的人以及其他底层人物表现出无限的关爱,毫不吝啬地将自己的财产施舍给他们。18岁起独立生活之后,迪南从事的慈善活动有了进一步的扩展:他不但开展宗教救济活动,又积极参加当地以救助他人为宗旨的“日内瓦施舍学社”,后又仿效两年前刚从伦敦开始成立、后来迅速推广到整个英国和其他国家的“基督教青年会”组织,发起成立“基督教青年会联盟”,以发扬基督教徒的高尚品质。由于迪南的首倡和奔波,先是有“日内瓦基督教青年会联盟”在1852年11月正式宣告成立,并在1855年8月发展成为世界性的组织“世界基督教青年会联盟”,总部就设在日内瓦。
马修·纽科姆在2015年第34卷第4期《修辞评论》杂志上发表的论文《从旅行者到规划师:迪南为“索尔费里诺回忆录”的影响做准备》(Matthew Newcome:From Tourist to Planner:Preparing for Affect in Henri Dunants A Memory of Solferno)中写道:
迪南来自日内瓦的一个富有的家庭,是一位热情的加尔文主义者。他慈善仁爱的心地早期就在好几个方面涌现出来了。他与基督教徒和犹太人一起共同参加活动,是日内瓦施舍协会的成员,这个协会意在给生活在贫困和病痛中的人带去物质和精神上的帮助。他不是成功的企业家,他在这个领域的困境让他有这一“机遇”出现在意大利。
此刻,展现在迪南面前的是怎样的一种场景啊!他写道:
战场上布满了人和马的尸体,道路上、壕沟里、峡谷里、灌木丛中和田野上到处散布着尸体,尤其是在索尔费利诺附近更是尸横遍野。
……那些受伤一整天后才被发现的可怜伤员已是面色苍白、精疲力竭。有些重伤员已经神志不清了,好像听不懂人们对他说什么,只用憔悴的双眼看着你。可是身体的极度虚弱并没有使他们对疼痛失去知觉。另外一些人由于精神过度疲劳而显得焦灼不安,一阵阵地抽搐着。还有一些人的伤口开始化脓感染,痛苦得快要发疯了。他们哀求人们杀了他们,以解除痛苦。有的还在地上扭动着身体,他们的脸在与死神的搏斗中变了形。
在这样的时刻,这位一直在做善事的慈善家还会想到为自己的事去见拿破仑三世吗?他首先想到的是立即投身于发起和组织救护伤员的工作,因为在那个时候,为军队的医疗服务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于是,由他参与,一个个看护队被组织起来了,数以千计的伤员被安顿到教堂、学校和民房里,“不分国籍地照顾那些伤员”,慰劳他们,给他们包扎伤口和喂食,一个个城镇都变成临时的医院。但是,除此之外,迪南还想得更多。
迪南以他的远见预测,人类不可能完全避免战争,而在未来的战争中,将会有更可怕的武器被发明出来,因此将会更加残酷。为了防止他在索尔费里诺战役中目睹的这类互相残杀和因为没有医疗护理而悲惨死亡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场景重新出现,他提出一项设想。这是他的宏伟理想:“如果在索尔费利诺战役打响的时候,有一个国际救济会存在……那么他们会做多少有益的事呀!”这理想,具体地说,主要就是:“在和平安定的时期成立一个救护团体,让那些热心、忠实并完全可以胜任的志愿者为战时的伤员们服务”,并制定一部神圣不可侵犯的国际公约,使伤员和救护人员在战争中被视为中立受到法律保护。因为“人性和文明急切呼吁着成立这样的伤兵组织”。为此,迪南把自己在索尔费里诺的亲眼所见和他的这些想法写成一本书,以《索尔费里诺回忆录》(Un Souvenir de Solferino)为题,于1862年自费出版。
迪南的这部回忆录立刻被译成德文、意大利文、瑞典文等多种文字,产生了十分广泛的轰动效应。大作家维克多·雨果说自己深深地受了感动,龚古尔兄弟称赞此书“比荷马的诗优美一千倍”,著名哲学家和历史学家欧内斯特·勒南在给作者的信中称颂说:“您创作了本世纪最伟大的作品。”弗洛伦斯·南丁格尔也给他写信,表示要积极支持他的倡议。还有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耶路撒冷的宗教首领圣约翰长老都保证支持迪南提出建立一个国际性机构的理想,还有萨克森王国的国王和亲身参加索尔费里诺战斗的拿破仑三世,也都许诺愿尽自己的一切可能给予帮助。

迪南的呼吁迅速被转化成为行动。1863年2月9日,五位瑞士公民在日内瓦召开后来被称为“日内瓦公共福利协会”的会议,“对《索尔费里诺回忆录》中提出的建议进行认真考虑”,并任命以居斯塔夫·穆尼埃律师为主席的五人委员会,并决定按照迪南书中的建议,先是以“伤兵救护国际委员会”的名义立即开始工作。一周后,委员会在2月17日的首次会议上宣布自己是一个国际性的常务委员会。随后,他们又在3月17日开会,终于促成10月26日至29日的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会。在这次来自16个国家36名代表参加的日内瓦大会上,决定采用一块白色的臂章作为大会的标志,后又补充加上一个红十字。这次大会的重大成就是确定了伤兵救护国际委员会的职能和工作方式,并通过10项决定,从而构成红十字运动的宪章,开启了国际红十字运动。

迪南是一个商人,一个旅游者,如他自己所常说的,他“不过是一个旅游者”。他只是出于偶然,才意外恰逢索尔费利诺战役,使埋藏在他的心中的慈善之心获得进一步的释放,并最终在1901年,与法国经济学家弗雷德里克·帕西一起,共获第一届诺贝尔和平奖。
不同于迪南的无意之中目睹了这场索尔费里诺战役,另一个人,阿道夫·伊冯则是有心去索尔费里诺战场的。
阿道·伊冯(Adolphe Yvon,1817—1893)是法国画家。他受教于法国学院派画家保罗·德拉罗虚,以创作一系列拿破仑战争题材的绘画而著名。
1855年9月,以俄国为一方,英国、法国、奥斯曼土耳其人为另一方的克里米亚战争结束之后不久,伊冯受法国政府委托,画一幅大型油画,表现法军刚于9月8日袭击塞瓦斯托波尔的俄国防守据点马拉霍夫,使俄军不得不在11日炸毁这一要塞。伊冯于1856年2月19日前往克里米亚,经六个月的前期准备,于1857年完成了《强攻马拉霍夫,1855年9月8日》。此画在巴黎沙龙上展出,并获“荣誉奖”。
沙龙上的获奖,使伊冯出了名,还引起拿破仑三世的注意。于是伊冯又创作了两幅有关马拉霍夫的作品《马拉霍夫的护墙》和《马拉霍夫的“咽喉”》,提交1859年沙龙。《纽约时报》判断《“咽喉”》“无疑是多年来法国画出的最优秀的战争场景”,“注定”会再次获大奖。但是乔纳森·马维尔在《现代意大利复兴运动战争》(Jonathan Marwil:Visiting Modern War in Risorgimento Italy)中说:“但这和(拿破仑三世)皇帝无关,他希望伊冯画他在意大利的战争,让这些作品在未来一代代公众的心目中一直具有意义。伊冯渴望去拥抱这一新角色。”于是,当巴黎庆祝马真塔的胜利时,伊冯便决定去往那里,并最后完成了他的大型油画《索尔费利诺战役》(The Battle of Solferino)。另外还有一幅油画《迪南在索尔费利诺》(Henry Dunant at Solferino)可能也是伊冯的作品。这两幅作品,因再现了索尔费利诺战场上的残酷搏斗场面和迪南在这里与民众一起实施战地救援的令人感动的景象,给受众以强烈的震撼,而成为世界名画,深受人们的赞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