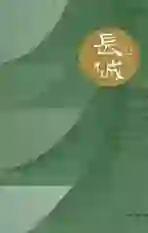那些年,那些作家朋友
2018-09-24
题 记
老作家汤吉夫(1937.9—2017.11)先生,生前多次向我讲述了他在河北的经历,也讲述了他与河北几个作家的深厚情谊。从他神采奕奕的回想和追忆中,我真切地感受到,即便他人生后半久居天津,然而他的心没离开过河北,香河、廊坊是他的精神故乡,永远也离不开也不想离开的故乡。因此,即便是他离开河北近三十年,每当回想起河北的那些作家朋友们,例如贾大山、刘真、陈冲、铁凝等人,他就眉毛上挑、喜笑颜开地讲起各种逸闻轶事。如今汤吉夫先生驾鹤西去,翻检出当初他那些透露着俏皮、幽默又满含深情的文字,实在不忍心一个人欣赏,索性拿出来以飨读者。
和浩然的莫逆之交
浩然姓梁,梁浩然,是一个颇受争议的人,在“文革”期间,是中国文学界的最高权威,写了《金光大道》《艳阳天》,他是天津宝坻人,和我私交很好。当年,学校一放寒假,我就围着火炉,啃着白薯干,看《艳阳天》,一边看一边乐。
浩然的小说不说了,歌颂合作化,肯定已经过时了,但他人很好,很厚道,也没架子。1982年,浩然为一个出版社编选农村题材的小说,发现我的小说虽不是农村题材,但是沾边,就在病中亲自写信给我,向我约稿。他的字很漂亮,很帅气。后来我的小说选收进了两篇,他还给我写了个评论。当时他给我写信约见面,告诉我他正在干什么,他怎么看我。后来他借管道局搞文学讲座的机会,来廊坊看我,他讲课,我作陪。
浩然与我见面以后,给我的印象相当好,称兄道弟,很热情、直爽、真诚,很低调,而且不吹牛,字写得也很漂亮。他对待我就像提携小兄弟似的,我们之间可以说是莫逆之交。
记得我当时想买一套《鲁迅全集》,买不到,就写信托他,他很认真,给我写了回信,告诉我:“《鲁迅全集》只印行三万套,早已分配完毕,目前也不准备再版。”这就是那时候的特点,买书还限量。
浩然这个人还有个好处,粉碎“四人帮”之后,他坚持写作,不是风派,不随风倒。我挺喜欢这个人。
当时浩然的工作单位在北京,但是住在河北省三河县,做了三河文联主席,后来还兼任了廊坊文联主席,他走了以后,就是我兼廊坊文联主席了。浩然做文联主席当时是挂虚名的,我也只是挂虚名,没有具体业务工作。我俩一样,都是摆设。
当时我经常与浩然见面、聊天。他有时候也发点关于个人际遇方面的小牢骚,他跟我说:“王蒙当中央委员了,做文化部部长了,我却到三河县来当个文联主席。”
诙谐智慧的贾大山
跟我接触的河北老作家、新作家很多。我和贾大山很熟,经常开会在一块,他比我小,小个四五岁,年龄和蒋子龙差不多。这个作家呢,短篇写得非常好。他的小说《取经》(载《河北文艺》1977年第4期,《人民文学》1977年第11期转载,并获得全国首届优秀短篇小说奖),获得全国奖,一下子成了名作家了。
河北开笔会一般都是请北京的作家去,像汪曾祺、林斤澜、从维熙、刘绍棠等。那时候河北作家中比较活跃的是贾大山,他会以很庄重的样子开玩笑,所以汪曾祺、林斤澜等对贾大山的印象都非常好。回想一下,大山的口才是很好的,字正腔圆,他的性格亦庄亦谐,看起来很庄重,实际上很诙谐。
贾大山有个习惯,就是说话的时候好拍人腿。有一次航鹰去河北,吃饭时贾大山跟航鹰挨着,他们凑着一块说话,大山边说话手就不自觉地拍人家的腿。你想啊,吃完饭手上都是油,就全抹人家腿上了。航鹰说:“吃完饭以后,大山你负责给我洗裤子,手上的油全擦在我腿上了。”
拍大腿,是农村作家的一个习惯——并没有恶意,也不是轻浮,是亲近的表现。
大山是一个很传统的作家,很固执地认为文学就是为农民写作。他年轻的时候写小说,主要是学赵树理。赵树理的小说是语体的,能说能听,最重要的是能听,他注重语言的表达要像口语似的。贾大山学得很像,他的小说也是可以念给别人听。他认为他的文字一定要让人看(听)得懂,尤其是让农民看(听)得懂,就是这个观念。到了后来,他迷上了孙犁。贾大山学孙犁学得也非常像,他后来的小说有很浓厚的孙犁的味道。
孙犁的小说有什么特点呢?其中一个就是不直接写政治,他侧重描写人性。有三个词:人性、人情、人道主义,这是文学的灵魂。孙犁的小说人性、人情很浓,人道主义也很浓,贾大山的小说像孙犁就在于,他不直接写政治,写人性、人情和人物。
在河北省作家群里,不崇拜孙犁的几乎没有,孙犁在河北的影响极大,包括我在内。孙犁不是一个一般的作家,是有引导性的作家,他生活在天津,但他的心、他的思想、他的爱好、他的美学,都来自于他原来的家乡——河北。
大山是一个真正的作家,不想当官,不是以小说为敲门砖,他不是这种人,他的小说也有为政治服务的影子,但是不露痕迹,这是一种艺术。铁凝说过这样的话:“河北短篇小说作家中,我最佩服的就是贾大山。”贾大山的短篇小说写得很精粹,干净利落,不铺张,篇幅很短,句子也很短,我也很喜欢。我的一个研究生,毕业论文做的《贾大山论》。因为写贾大山的论文很少,他可能是第一个系统寫贾大山的。
我和贾大山是好哥们,我俩很亲切,很默契,也很投脾气。他去世之前给我打电话,他不知道我的电话号码,先找到铁凝,然后找到蒋子龙,蒋子龙给他一个,是我先前的,后来找到我现在的电话,费了很大周折,终于打给我了。他说:“吉夫同志,咱们俩说会儿话吧,我刚做了手术,现在养病中。”他还说:“我们见个面吧。”我当时没在意,也没再给他打电话,以为不久就要召开全国作协第五次会议,到时见面可以畅快地说。后来在会上碰到河北作家,才知道大山得了癌症,已经扩散了。于是急忙在京西宾馆打电话,结果没有打通。我想,大山不会那么快就走,找个机会去正定看他,可是他很快就没了,我很后悔,一直到现在。后来我写了一篇文章(《想起大山》,载《河北日报》1997年9月8日),表达我的怀念。
大山是农民作家中的天才,文字模仿能力很强,在中国作家协会在北京办的那个学习班里他是班长。班级里有两个班长,一个是蒋子龙,一个是贾大山,蒋子龙是工人,贾大山是农民,他俩当班长。
那时候有个作家叫叶文玲,是浙江人,在河南生活。这个人也有很多故事,她当时化妆别人都看不惯,大伙就议论。有一次,叶文玲从外面进来,大伙哄堂大笑。
叶文玲说:“你们都在说我吧,肯定是都在说我呢。”大山说:“没错。”她说:“你们说我什么呢?”大山说:“你出去,一会告诉你。”
然后她出去,一会就回来了。贾大山说:“刚才我们说你,小叶,文章写得好,身上也很香,女孩子嘛,从来就是喜欢穿衣打扮,一万年以后也是这样,你们信不信?反正我信。”
这句话是贾大山模仿毛泽东的语气来评价叶文玲,完全是毛泽东的口气,像极了。模仿《毛主席语录》,是大山的一个特长。他能模仿的语录,据说有五十多条。这是一个极端聪明的作家,这样的话编了好多,不用打草稿。
贾大山很会开玩笑。一次,我和贾大山两个人,去给河北青年作家讲课,去的是晋县周家庄,河北作家赵新也去了。大山挺“嘎”的,大山的“嘎”表现在什么地方呢?我举个例子。我们去的地方是一个村子,招待我们最好的饭就是面条。我们去了以后,第一天早晨是面条,中午是面条,晚上也是面条,第二天、第三天也还是这样。时间一长,大家就有点受不住了。贾大山就说:“赵新,你去找‘老坚决反映一下,不能一天给我们三顿面条吃。”
“老坚决”叫张庆田,是河北省文联副主席、《河北文学》的主编,负责管我们伙食事儿的。赵新就去找“老坚决”反映说:“‘老坚决,你不能这样招待作家啊,一天三顿面条,上顿面条,下顿还是面条,这个太不好了吧,大山都有意见了,汤吉夫也有意见了。”
刚反映完,大山就去了,说:“‘老坚决,赵新同志变了,刚吃几顿面条就受不了了,赵新同志这个人意识不好,觉悟不高。”
他做的扣儿,然后去“出卖”人家,他这样“嘎”,结果赵新被“老坚决”批了一顿,把我们笑得呀!
我在河北作家中是另类,不写农民,不写工人,而写知识分子,在河北我可能是第一个以知识分子为题材的。贾大山跟大家说:“汤老师是学者,他的话你们得好好学好好听。”
他这话好像是捧我,但我还没怎么讲呢,所以也可以说是损我呢。之后,我讲一段,他就重复一下“汤老师说得对啊”。大山就这样,挺调皮,挺机智。
北京的作家汪曾祺、林斤澜到正定遇见贾大山就夸:“说话一字一句,句句经典,另外是字正腔圆,过目不忘。”
贾大山确实是说话很慢,说话还字正腔圆的。写小说是想来想去,然后想好了就一字一句地写下来,写完念给他媳妇听,然后就完事了,真的有点像赵树理的那种写作方法。
大山晚年欣赏孙犁,所以他的小说后来写得像孙犁。河北作家受孙犁影响最重,其次是赵树理,赵新是学赵树理的。
贾大山当时在全国很有名,八十年代与贾平凹是齐名的。中国“二贾”——贾平凹、贾大山,在日本有研究所,大概叫“二贾”研究所,挺了不起的。
我当时被反对的人批判,就是批《今夜他是个普通人》那篇。但从来没有人批贾大山。那时他是省政协委员,我也是,我们经常在一块开会,创作会、批“自由化”等我们都在一块。
批“自由化”的时候,我们经常谈到意识流,他非常反感意识流,他常对我说:“汤老师你说,咱中国的农民,你一个字一个字念给他听,他还听不懂呢,云山雾罩的怎么听得懂?”
王蒙曾说起过一段插曲,他在北京给作家班讲课,讲意识流,讲完以后,问贾大山:“大山,我讲得怎么样?”贾大山来了句什么呢?“好哎,好!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天上一拳,地下一脚,讲得好哎。”王蒙一听就是假的,贾大山给他耍聪明,王蒙知道他心里不满。这话此前大山就跟我说过,那是1981年,就是去晋县周家庄讲课那次,我俩住在一个屋里,天天晚上不睡觉,彻夜长谈。大山一支接一支地抽他的“荷花”烟,有时他还爬进我的蚊帐里。那时对意识流抵制的河北作家,贾大山是带头的,他的基本创作理念就是这个。
一个淳朴的好人。
敢叫板的刘真
我和丁玲没有多少交流,只是在偶尔开会见面时打个招呼。在会上,丁玲穿着猩红的外套,她的丈夫陈明在旁边陪着她。她那时候虽然已经是个老太太了,饱经苦难,但依然很华贵,很有气场。
说起丁玲来,得说一下河北的一个女作家,丁玲的学生刘真,代表作是小说集《长长的流水》。她是和茹志鹃同时代的,我认为,那时南方是茹志鹃,北方就是刘真。
刘真是个很重要的作家,不是一个一般的作家。1959年,批刘真是一场政治运动,河北省文联搞的。她的《英雄的乐章》{1}挨批斗,省委组织部的人和她谈话,她一句话都不听。最后人家说:“我跟你谈了两个小时,你都在想什么?”她说:“我什么都没想,我在数你脸上的黑雀斑,一共二百个,不信你自己数数。”
刘真的性格很刚烈,谁压都压不服,《人民日报》发表批评她作品的文章{2},说不真实,歪曲现实,她就和《人民日报》叫板说:“我比你们真实,瞧瞧你们1958年的文章都真实吗?到底亩产多少斤?”这就是刘真干的事。因为她是“小八路”出身,九歲参加革命,所以有些摆老资格。
后来刘真嫁给了文化部的一个处长,移民去了澳大利亚。有一次回国,来天津看我和金梅。她跟我们说起,入海关的时候,海关百般刁难她。她说:“我是中国人,我是刘真。你们这是干什么?”海关的人说:“你像个藏族老太太。”
她真的像藏族老太太,又脏又黑,到了澳大利亚也是这样。她跟我说,澳大利亚政府以反法西斯老干部的名义发放退休金,给的钱还不少,就是因为自己当年是共产党的“小八路”。
刘真的皮肤很黑,长相很土,爱抽烟。用现在的眼光看,没有一点可爱的地方。刘真是河北省文联副主席,她作报告就是说大白话,不会用官腔官调。有一回她主持河北创作会,在讲话中说:“同志们,咱们的会开得好啊。汤吉夫当校长了,有什么好处呢?你看,他坐着小汽车就来了。”大会上那么多人,她作报告就是这样。会议都有录音,我每次听到以后就会哈哈大笑,她是很纯真的一个人。我就想,那个年代的作家,出了一个这样的人,没有文化,敢想敢干敢说,难得呀。
“文革”期间,刘真挨斗。开批斗会时,保定自行车厂的一个青年工人每天骑自行车带着她去开会,然后接她回家,那个人比她小很多,一来二去就产生感情了,她就嫁给这个青年工人了,生了几个孩子,我见过其中的一个,叫“小土豆”,长得像她,黑不溜秋的。
有一次,我和河北的另一个作家赵新,躺在宾馆的床上聊天。刘真去串门,我和赵新就都起来了。她却说:“都躺下,都躺下,我也躺着,咱们三个躺着聊天。”还有一次开会的时候,她去我宾馆房间聊天,我坐着,她躺着。开始我不习惯,但慢慢也就习惯了。她的脑子里没有男女。
有一次在北京开会,刘真和铁凝住一个屋,有个刊物找铁凝约稿,那个刊物主编来拜访铁凝,但没有人找她,她很失落,就跑到我那里去说:“老汤,现在没有人理我了。”我说:“你认了吧,退回三十年,也有人找你。”
刘真天生是个作家,是个感性的人,她跟我说过,她十来岁的时候,妈妈被国民党抓走了,她自己在家带着弟弟妹妹。那天晚上,油灯一亮,屋里的墙显得阴森森的。后来警察来了说小屋太黑,她就把一瓶酒倒在杯子里,打开洋火点着,一下子就亮起来了。灰色的光,让墙壁显得更灰了。
我觉得这就是作家的特点,普通的孩子不会有这种感觉,她说她觉得墙壁都是灰的,我感觉她从小就有艺术细胞和艺术想象。
刘真对我也很好,听说我要走,很不舍,写信给我说:“自从听说你要离开河北,我就很不高兴。又听说你去山东并不那么顺利,不知真假。总之,不愿河北失去你。”
河北作家都很怀念她,这个人是个好人,没有害人之心,坦坦荡荡。
时髦的陈冲
陈冲不是女演员,是男的,很多人误会,他开始写小说之后收到不少男青年的求爱信,以为他是女的陈冲。他跟我说:“很多读者给我来信,但都是男的、小伙子,向我求爱的,他们不知道我是个老头。”陈冲和我同岁,2017年6月去世了,他也是我的好朋友。我挺伤感的,一个好朋友、好战友,走了。
陈冲的经历很复杂、很曲折,什么都干过,卫生员、文艺宣传队吹拉弹唱,嗓子是公鸭嗓但是特别好听。他没有学历,没上过什么学,1955年就发表过作品。二十多岁当“右派”,“极右”那类。他当时是工会干事,在保定列电基地。
我们成名几乎是同时的,1980年。我、铁凝、陈冲,三个人的出现,在河北是很重要的事。河北作家历来从农民中选拔,他们接地气、有生活,河北喜欢培养这样的作家,用外地作家的话说:“河北作家土得掉渣。”八十年代初期忽然出现一个我,不是本土的,不是农民,是大学生;出了一个陈冲,写工业;出了一个铁凝,写知青,写人性,所以那时河北文坛有一个说法叫“汤铁陈”。“汤铁陈”的意义不在于这三个人怎么样,不是说地位,而是说这几个人改变了河北文学的传统,成为八十年代河北文坛的一个现象。
陈冲和我说,河北作家没有理论、没有思想。他认为,文学要发展没有思想是不行的,所以他到处讲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并且自学理论。他是有理论素养的小说家,挺喜欢理论。在河北有人请做报告,我俩常一起去,我主讲,他帮忙配合我。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在这个背景下储备了相当好的理论基础,自学成才。他对于社会看得很透,毛笔字写得也不错。他给我写信都是毛笔字,而且都是竖写的,开头第一句:“吉夫兄,见字如晤。”我们那时交流很多,经常写信,讨论文学创作,一写就很长,我记得我给他写的信有十几页。
陈冲人精瘦精瘦的,两腮凹陷,天津话就是“啄腮”。陈冲也很时尚,河北作家里边,最早穿西装的就是陈冲。在西陵参观的时候,看清朝皇帝的画像,陈冲啄腮很像道光皇帝,贾大山就说陈冲是道光皇帝,也一直管他叫“道光皇帝”。
陈冲确实很时髦的,八十年代中期他去北京回来把头发烫了,一弯一弯的,穿着西装,很标新立异的。后来他一直是中国小说学会小说排行榜的评委。冯骥才说:“我们的评委会由教授、专家、评论家和一批有理论兴趣的作家组成,比如韩石山、汤吉夫、陈冲。”陈冲就属于有理论兴趣的作家。
陈冲的思路是逆向思维,你要这么说他偏要那么说,老百姓话说就是“杠头”,总是标新立异,和别人不一样,所以当年当“右派”很正常,总反着说能不当“右派”吗?不听话。他死在脑血管病上,脑出血。刘绍棠也是脑血管有病,浩然也是,韩石山也是,十年前我中风一次也是脑血管的病,但是没死,说明作家这个行业用脑太多了。
今天说陈冲,是对他去世的一种纪念吧。
铁凝对我的真诚挽留
1979年,在石家庄开会,各出版社、刊物的编辑也要到会上采访,会上有一个编辑是天津的,他问我:“你知道铁凝吗?”我说:“我不知道。”他说:“就是跟你一组的那个小姑娘。”
我那时对河北创作情况不是很了解,铁凝那时还没写出《哦,香雪》。散会的时候,她和另一个作家一起回保定。我们都要从石家庄火车站一起上火车,她背着一个大包。我给铁凝说:“你的包太沉,我替你背吧。”于是我就一直帮她背到火车站。
我当时是四十多岁,铁凝二十多岁,她比我整整小二十岁。我对她的印象就是一个小姑娘。我刚认识铁凝的时候,她是一个业余作者,河北的作家都很喜欢她,特别是老作家们,极力培养她。
我进入创作在年龄上实际已经很晚了,“文革”后从“牛棚”里出来就已经三十八岁了,我四十多岁才开始创作的,写到《大学记事》,差不多就算“收秋儿”了。
刚开始创作的时候,跟铁凝交往不是很多,最先是1979年那次创作会。那次会后不久,我就写信给铁凝,向她要作品做研究,也约请她到廊坊师专做交流,前后有两三个来回。铁凝回信很谦虚,在第一封回信中,她这样写道:“我在各方面都很不成熟,文章写得幼稚、浅薄。但您看后如能给我提出意见,指出问题,我是非常高兴的。”“关于和同学们见面事,我考虑还是不要向我们单位发请柬为好。因自己在文学创作上尚是一名小学生,还是踏踏实实地在生活中多学习、实践。将来有机会去廊坊,一定去看望老師和同学们。”
后来我们接触稍多一些,也有过一些书信往来,谈创作,谈作品,也相互约稿。1983年的时候,我记得我给她写信谈起过《哦,香雪》写得好,可能会获奖的事,她给我回信说:“对于《香雪》获奖,我不抱太大希望,我只是非常感谢您对我真挚的鼓励。但愿您的祝福能保佑我今年能多写点东西——八三年我还一个字没写呢。最近常常为怎么写而苦恼,要做到不重复别人,又不重复自己是那样艰难。我常感到自己底气不足。真的。”
我注意到,铁凝在开会的时候很少说话,静静的。她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思想,只是闷头写作,别人爱说什么说什么,批评她也不在乎。铁凝在1986年做了河北省文联的副主席,我在河北省作协做副主席,因为是兼职的,所以我们之间也没有什么特别密切的沟通。
我和铁凝的交流主要是我要离开河北那阵,尤其是后来我要走的消息传开了,她听说我要走,就想挽留我,为此她写了好几封信,大概有四五封。
她在1987年8月的一封信里写道:“这几天我来石家庄,参加省委召开的一个会。会上遇李文珊书记(时任河北省委副书记)、陈玉杰同志(时任河北省委常委、组织部长),李书记说想办法让你留下并作安排,陈部长也是真心实意为你说了许多话,并且也在竭力想办法安排得理想些。这令我感到欣慰,并且也是我所盼望。”“我想许多同志和我一样,是不希望你离开的。人生原本就是‘不如意事常八九,在什么地方均有什么地方的麻烦。当年你恨一个地方时也许说明你爱它。日子并不总随人意的,一些领导和同行能理解你,希望你能留下来,和同行们在一起做点事情,这毕竟是件好事。”
9月的信里提到她给李文珊书记写了信,在石家庄当面谈及我的事,她告诉我“这不会是一般的敷衍”(1987年9月26日信),让我耐心等一等。
在11月的一封信里,她又写道:“陈部长说会后会跟你约时间谈一次。不知是否已谈完,结果又如何。我也不知我还能做些什么。”
两封信都写得很诚恳,也很令我感动,但是很遗憾,最后我还是选择去了天津。不过,我很怀念那段在河北的日子,尤其是离开河北后,也怀念与河北作家们的友谊,包括铁凝在内。铁凝留在我记忆里的永远都是一个小女孩的样子。
注释:
{1}《英雄的乐章》,写于1959年,文章本来是应《人民文学》之约而写的,写完拿给河北文联的人看,想做修改,结果文联的领导认为是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潮,可以当作靶子批判,于是发表在文学半月刊《蜜蜂》第24期,同期配发“本刊评论员”的批判文章《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坚决反对修正主义思潮》,其中写道:“《英雄的乐章》以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观点看待革命战争和爱情问题,这是当前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在文艺界的反映。”文章特别强调,要以此为例,“坚决把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文艺思潮打击下去”。1959年12月8日至年底的全国文化工作会议上,周扬将这篇文章和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一起批判,说:“在社会主义国家提倡抽象的人道主义,锋芒是反社会主义;用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口号宣传阶级合作、和平主义、改良主义,反对革命斗争、革命战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宣传个人主义,反对集体主义。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披上社会主义外衣,危险性就大了。对其进行斗争仍然是当前一个重要任务。”《文艺报》在1960年第1期,发表了王子野写的《评刘真的‘英雄的乐章》,进一步批判。1963年夏天,周扬到天津为刘真平了反。刘真在回忆周扬的文章《他的名字叫没法说……》中,写周扬对河北省文联的负责人说:“人家还没有发表的作品,你们就拿出去批判,这是不道德嘛!”并鼓励刘真说:“党需要你在政治上和艺术上都尽快成熟起来,你是有才华的。”“文革”中,《英雄的乐章》被打成江青讨伐的“黑八论”之一的所谓“反‘火药味论”的一个黑标本,又一次遭到批判。刘真被批斗、侮辱、游街、关入“牛棚”、强制劳动改造……1980年,刘真的文章得到彻底平反。这一年,《河北文艺》在第1期上重新发表了《英雄的乐章》。
{2}远千里:《谈作家的世界观问题》,《人民日报》1960年1月13日。文中写道:“1959年出版的第二十四期‘蜜蜂上附发的两篇小说,就是与时代精神不合、歪曲现实的作品。刘真同志的‘英雄的乐章,是以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观点,来看待革命战争和爱情问题,把壮烈的革命战争,写得那样暗淡。作者把个人幸福和革命事业对立起来。作者所歌颂的人物有着资产阶级的頹废没落的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