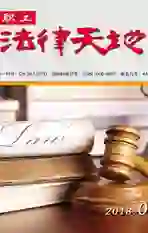“三权分置”下推进农村承包地法律制度改革的思考
2018-09-20黄民
摘 要:我国承包地法律制度在改革开放之初建立。但随着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农村人口逐渐涌入城市,农村里的承包地被大量荒废着。国家对此探索分离农地的承包主体和经营主体,在承包地上新设一种经营权进行流转,提出“三权分置”的改革。“三权分置”即将农地的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进行分离。“三权分置改革”有助于推动农业发展。
然而,我国现有承包地制度在立法和实践上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主要是:农地经营权流转的方式规定得不明确;关于承包地的法律规范不完整;农村集体成员资格权的取得混乱;承包地的确权登记不一致。本文认为,在“三权分置”下推进改革要将承包期限延长的政策落到实处,要探讨经营权作为一种独立物权的法理逻辑,要多样化地去实现“三权分置”的内容,更要善于借鉴和吸收国外的经验和教训。
关键词:三权分置;承包地;制度改革
一、我国承包地制度的由来
我国农村承包地制度来源于上个世纪80年代初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俗称“包产到户”)。我国1993年《宪法》修订案中规定:“农村中的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和生产、供销、信用、消费等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是社会主义劳动群主集体所有制经济”。2002年制定的《土地承包法》更是将土地承包制度以一门单独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在我国目前的法律规范中,无论是《农村土地承包法》,还是《物权法》《草原法》《渔业法》《森林法》等法律,都是把农地承包权规定为农民的基本权利,这种权利虽然派生于集体所有权,但这是一种相对独立的承包权。
二、“三权分置”改革的概述
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初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将农地所有权和承包权相分离的“两权分置”,那么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将农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相分离,那就是“三权分置”了。笔者认为,这是我国新时代农地改革的一个伟大创举。“三权分置”是指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其中的经营权可以自由流转。以前农村的农用地一般是所有权与承包权分离,而现在又新增了经营权,赋予了经营权以法律地位,目的就是要放活经营权。而放活经营权的目的就是提供土地利用率,促进农业发展。“三权分置”最早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始部署,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上提出:“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其后,《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等意见相继提出:“稳定承包权,放活经营权,允许以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向金融机构抵押融资”等。目前,农村土地的“三权分置”已经成为学术界的研究热点。
三、现有承包地制度存在的问题
任何改革都是要针对问题着手,承包地法律制度的改革也是如此。本文认为,目前我国的承包地法律制度存在立法与实践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立法问题
我国关于承包地制度的法律规范主要有:《宪法》《物权法》《土地承包法》等,以及国务院及其部门、全国各地的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等。目前,我国关于承包地的法律规范还不是非常完善,部分法律规范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问题如下:
第一,农地经营权流转的方式规定得不明确。笔者查阅我国所有关于承包地的法律规范,发现现行法律规范没有对农地经营权流转的方式作出过规定,但是我国法律允许了以家庭为单位的土地承包经营流转模式,这就使得在农地经营权流转的实践过程中,经常出现互换、转包等混乱的形式,极容易造成土地纠纷,也极容易被不法者利用法律上的漏洞来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这会大大影响到农村的发展。
第二,关于承包地的法律规范不完整。目前,我国关于承包地的法律规范主要有:《农业法》《土地管理法》《農村土地承包法》。但是,这些法律规范针对承包地“三权分置”的内容非常少,尤其是土地经营权如果要进行抵押是很缺乏法律的依据的。《农村土地承包法》第32条规定,家庭承包的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只可流转,没有抵押的权能。《物权法》规定,以公开协商、拍卖、招标等方式取得的土地承包权可以抵押,而耕地这种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仍不得抵押。《担保法》也规定,如果土地使用权由集体所有,是不得抵押。虽然国家“三权分置”改革准备赋予农民对承包地经营权的抵押、担保的权能,但还处于早期的探索环节,很多法律规范没有修改到位,所以承包地经营权的抵押在法律还几乎是空白,在实践中会陷入“无法可依”的尴尬境地。
(二)实践问题
在承包地实行“三权分置”改革的实践过程中,我们会产生一些问题和不足。
第一,农村集体成员资格权的取得混乱。在实行“三权分置”改革过程中,我们需要对承包地的承包权、经营权予以确权登记。而承包地的承包权必须是由本村集体的成员才能享有,但是经营权可以流转给村集体组织以外的成员。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对当事人是否具有村集体成员资格进行确认。现实中,由于有的农户迁入迁出次数频繁、有的农户转入城镇户口却仍然享受着村集体的福利,是否具备村集体成员资格可能会很模糊。所以这方面的模糊,会给后续工作带来混乱。
第二,承包地的确权登记不一致。在进行“三权分置”改革的过程中,我们要推行农地经营权的流转。那么,在农地经营权流转的时候,我们就有必要确定土地的面积和承包权的归属权。由于,现在第二轮承包地的面积,基本上按照第一轮承包期限到期时的人口数目为依据进行分配的,到现在已过20年的时间了,人口数目变化很大,那么土地的调整就十分复杂。有的地方按照现有人口数进行了重新调整,但有的地方认为“承包地在30年期限内不变”而未对土地进行调整。所以在重新确权登记的过程中,全国各地往往处理不一致,完全没有统一标准。
四、承包地法律制度改革的建议
(一)将土地承包期延长落到实处
中共十九大之后,我国再次延长了土地承包期30年。我国土地承包期限共经历过3个阶段,延长过2次。第一轮土地承包期限为15年(从1983年至1997年),第一轮土地承包期到期后,延长了30年,所以第二轮土地承包期是30年(从1997年至2027年)。在中共十九大之后,国家又将第二轮土地承包期再延长30年(从2027年至2057年)。笔者对这种延期的做法表示赞扬。因为土地承包期限延长,有利于提前稳定农民的承包经营预期,给广大农民吃了一颗定心丸。
孙宪忠教授认为:“长久不变在法理上是行得通的”。虽然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从集体所有权中派生出来的,但土地并不一定就因此迟早必须要回到集体手中。我赞同孙宪忠教授的这种观点。我和孙宪忠教授都认为,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最初是从农民入社这一历史事件中得来的,所以实际上并不是农户的地权来源于集体,恰恰相反,是集体的地权来源于农户。正是因为如此,“土地承包权长久不变、期满后自动续期”这在法理上是讲得通的。有的地方官员主张对“土地承包期”进行不断地调整,迟早要将承包所有权收归集体,这种主张会严重损害农民的利益。本文认为,我们对此应有清楚的认识,坚决纠正错误的观点,严格将土地承包期延长的政策落实到位。
(二)在法理上探讨承包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合理性
2008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切实加强农业基础建设进一步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若干意见》指出,要认真开展延包后续完善工作,确保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到户。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说明,中央将土地承包经营权视为一种单独的基本权利。但这仅仅是将“土地承包经营权”视为一种单独的基本权利,并没有更细致地将“土地承包权”和“经营权”都分开视为一种单独的基本权利。因此,本文认为,要实现“三权分置”,就必须要在法理上探讨承包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合理性。
本文认为,应在法理上将经营权单独视为一种物权。如果将其视为债权,可能会影响到抵押和流转。将“土地承包权”和“经营权”分开,原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将丧失,这也符合“一物一权”的物权原则。将“土地承包权”和“经营权”分开,并将“经营权”视为一种单独的物权,这有利于推动经营权的抵押,保障土地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推动土地适度规模化经营。
(三)探讨实现“三权分置”的多种形式
本文认为,“三权分置”的实现,关键在于经营权流转的实现。因此,本文认为,“三权分置”的实现形式不仅仅只有一种,可以是多样化的。“三权分置”的实现形式有以下几种:
第一,租赁承包型,是最主要的实现形式。它是指由农地经营者直接与农户签订土地租赁协议,进行农业规模化经营。这种直接协商签订租赁协议的形式,需要由经营者去直接面对所有的农户,谈判成本较高,具有较强的自发性和不确定性。或者还可以由农户将承包土地委托给村集体组织,由村集体组织统一对外签订租赁协议。这种形式则谈判成本稍低,比前者有更大的保障性。
第二,股份合作型。它是指以土地承包权来折价入股农村或农民的专业合作社,实行土地统一经营、集中流转、保底分红的经营方式。
第三,土地量化型。它是指把每一户村民的承包土地直接量化为村集体组织的股权,直接把土地资源进行股份化。这种形式不但可以通过“不确地但确权”的方式化解广大农村土地确权登记中的困难,也可以突破土地经营权流转中所经常面临土地承包期限了2028年的困境(不过现在土地承包期已经自动延长30年了)。
(四)吸取日本的教训实现“三权分置”
在任何一项法律制度的设计上,我们都要善于吸收国外的有益经验或吸取国外的失败教训。在日本,农村土地采用私有制。日本政府曾经为了鼓励土地流转,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日本政府也采用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的流转制度,并且在资金政策方面对使用权流转者予以奖励。尽管如此,日本的土地使用权流转仍然出了问题。由于农户拥有一小块土地的所有权,所以在这样小规模、分散化的土地上难以实现集中连片的流转。所以,土地经营者很难寻找到集中连片的大块土地。所以,日本很多农村的农业生产仍然无法采用大机器来进行。本文将这种情形称之为“土地流转上的日本陷阱”。
笔者认为,我们的土地使用权流转制度改革也要避免出现“日本陷阱”。部分学者认为,为促进承包地经营权流转,应该把农户承包权做大做实。笔者对此种观点,不予赞同。本文认为,承包权可以适当强化,但过度强化承包权,反而会将农村集体所有权架空,导致土地的流转都是小块化、分散化,最终会僵化土地经营权。我认为,农村经营权流转可以采用这种方式:发挥集体的资源配置功能,实现土地的集中连片流转。村集体组织可以将农民是否愿意流转的意愿统统汇总起来,村集体组织统一将愿意流转的农户家的土地集中连片地流转出去,并给予那些土地经营者以集中连片的土地。农村集体组织可以每隔5年或10年时间重新调整一次,重新汇总农户的流转意愿。
五、后记
“三权分置”是我国承包地物权体系的一次重新调整。本文认为,要落實好承包地期限延长的政策,在法理上重新构建起“三权分置”下的承包地物权体系,探讨经营权作为一种独立的物权在法理上的逻辑。我们也要在立法上去明确更多的“三权分置”实现形式,令实践“有法可依”,为改革提供些许指导。当然,我们也要尽量避免过分强调承包权而忽视农村集体所有权这个物权体系中最根本的所在。充分发挥农村集体所有制的优势,放活经营权流转的形式,一定能够最大限度激发农业生产力,推动新时代农业发展。
参考文献:
[1]黄季焜.中国的农地制度、农地流转和农地投资[M].上海:格致出版社,2012年版第10页.
[2]赵阳.新形势下完善农村土地承包政策若干问题的认识[J].载于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2年第2期.
[3]孙宪忠.推进我国农村土地权利制度改革若干问题的思考[J].比较法研究,2018年第1期.
[4]陈思.改革破局——建立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J].党史博采(纪实),2018年第2期.
作者简介:黄民(1992~ ),男,汉族,浙江杭州人,法律硕士研二在读,研究方向:民商法、物权法、土地法。